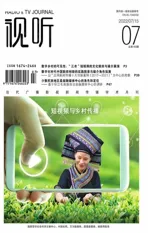美颜自拍对用户个人形象自我认知的影响
2022-02-18邱文中
邱文中 晏 皓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智能手机拍摄硬件的更新迭代,用户个人自拍行为的操作门槛极大降低,手机自拍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之一。这也为美颜相机类App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坚实的受众基础,伴随而来的还有众多的个人问题及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人内传播的范畴,结合一致性理论、曝光效应等心理学理论,进一步探析美颜相机的使用对用户个人形象自我认知的深层次影响。
一、“镜头自我”的形成
自拍(selfie),即拍摄自己的人像照片。早在1984年,自拍一词便已出现,当时其英文学名为Self-timer,意指一种单纯的定时拍照功能。时至今日,自拍早已成为风靡全球的网络社交风尚。对于自拍的概念界定,从广义上来讲,是指借助相机、摄影机等拍摄器材对个体形象进行的影像记录,而拍摄行为的执行主体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人;狭义的自拍则是指人们通过智能手机的拍摄功能对自己进行的拍照,被拍摄者与拍摄行为执行者均只是自己,而且人们通常会对自拍照加以修饰后上传至社交媒体进行分享。自拍者在自拍、美颜与传播的过程中享受着身体主宰权的“最大化”,体验着社交资源的“最大值”,通过将自身的“自然存在”孤立出来,构成自己膜拜的对象①。
数字化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胶片摄影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与智能成像技术的大众化应用,手机美颜自拍技术应运而生,并受到无数年轻人的追捧。美图公司发布的《2021年美图用户价值报告》显示,美图月活跃用户总数达2.46亿人次,平均每月产出影像70.2亿帧②。
智能手机产业发展迅猛,原本属于相机、摄影机等影像设备的拍摄功能已经“嫁接”到了智能手机上,智能手机在软件和硬件层面的不断更新迭代极大地降低了以往横亘在大众面前的技术门槛。如今市场上的智能手机就广泛采用超高清像素、光学图像防抖、AI增强等新兴智能科技,以提高操作效果。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类美颜相机App的出现。不同于PS等专业图像处理软件,美颜相机没有烦琐的程序,其自带的一键美白、一键瘦脸等“傻瓜式”功能使得自拍、修图成为一种人人都可操作的行为。技术赋能下的“美颜自由”使得自拍开始成为一种全民狂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个人的话语、文字、思想完全可以由自己来决定,但自身的形象却始终由肖像画师、摄影师和专业后期制作人员所掌握。人类社会在迎来自拍时代之前,个人对自我形象的呈现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直到科技发展冲破技术壁垒,人们对自我形象的掌控权才终于回归到自己手中。我们在自拍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镜面再现,而是在现实形象的基础上进行着迎合内心渴求和主流大众审美等综合因素的重新构建。
二、“精致自我”的证明
一致性理论认为,在对外部客体的认知行为上,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会使得二者努力趋于一致。一旦自我对客体的认知无法达成一致或无法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人们便会出现不适,进而试图去减少它。而减少失谐的一个机制就是:避免不一致的信息或有选择性地寻求支持信息。当人们通过美颜相机拍摄的照片来观察自我形象时,所看到的是经过软件算法修饰、加工、美化过后的“精致自我”。这也使得自拍者在面对真实的自我时,对个人形象的认知态度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自拍者本身在进行美颜自拍的这一过程中,其实也有将现实自我与镜头中的“精致自我”进行相似度的比较,如调整不同的拍摄角度、拍摄姿势等使得照片中的人物更为趋近现实环境中的自己。这种比较也是出于对自我认知的一种调整。
在这一认知调整的过程中,用户对美颜相机的使用极易造成自身“巴纳姆效应”的产生。所谓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指人很容易相信一个较为模糊笼统的人格特点描述,并认为它特别符合自己且准确地映照了自己的人格特点。在心理学上,“巴纳姆效应”产生的原因被认为是“主观验证”的作用,主观验证与个人信念的需要相关,换言之就是“我要相信”。如果对某一件事持强烈的偏执态度,我们总是可以为之找到一个恰当的逻辑,让它与自己的预先设想相符合。一个是由美颜相机镜头塑造的“精致”形象,一个是现实中原本的自我形象,在对二者进行认知辨识的过程中,自拍者往往更倾向于前者,而美颜相机在其中就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即提供“证据”。
三、“完美自我”的确认
当人们观看“自己图像”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变成“客体”进行审阅,然后得出对“自我”的一种判断,进而“主体性”被建构起来③。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拍行为,随着其使用频率和使用深度的累积,会产生一种心理学上所描述的“曝光效应”,因为在对事物的比较中,人们会对频繁出现在面前的事物有着更高的好感度。尽管人们已经无数次看过镜头中的自己,但是在利用美颜软件自拍时,不同的角度、光线、滤镜特效等依然会使人们发现更多的“陌生我”。为了追求那个“完美自我”,人们不断地重复自拍,直到挑出自己觉得最好看的那张照片来增强自信。这种虚妄的自我欣赏和陶醉,也进一步激发了用户对美颜自拍的热情。
同时,个人自我呈现的欲望使得自拍者将自己的自拍照上传到社交平台,并且渴望着收获社交平台上来自他人的赞美和积极正面的评价,达到自身虚荣心与自恋情结的满足。在点赞、评论、回复等沟通交流过程中,自拍者完成了对于自我身体图像和自我身份的想象、塑造与建构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利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⑤依据镜中我理论,个体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会知晓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期望,并会依照他人的期望来塑造自我形象,树立个人的自我期望,进而影响其行为⑥。社交网络的发展使美颜成为绝大多数自拍照的最终归宿。由此可见,自拍者的拍摄不只是对自我的审视,相反,他们对于自我的认同和评判,极度依赖于“他人的目光”。来自外界的态度、评价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颜自拍用户在“完美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认知界限。
四、个人及社会问题的显现
(一)自拍成瘾
自拍成瘾指的是为了能够拥有一张完美无瑕且能充分展现自我形象魅力的照片,而在自拍和后期修图上花费大量时间的行为。自拍成瘾已经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上瘾者”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希望能够通过自拍来获得一种满足感。一旦其拍出来的照片无法达到自己主观的满意程度,便会产生失落、焦躁等负面情绪,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自杀行为的产生。
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和印度Thiagarajar商学院的研究者通过一项对400名实验对象的调查研究证实自拍成瘾的存在。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者们将自拍成瘾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Borderline(疑似),一天至少有三次自拍行为,但不会发布至社交网络;第二个层次是Acute(急性),一天至少有三次自拍行为,并且会将每张自拍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络;第三个层次是Chronic(慢性),无法抑制自拍的冲动,一天将自拍照片上传至社交网络六次及以上。
研究学者还认为,典型的自拍“上瘾者”通常都对自身缺乏信心,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想要融入周围的社会集体中。他们将自尊心的缺失和亲密关系的空白寄托于自拍行为,以此寻求内心情感的代偿。多芬品牌针对女性受众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在接受调研的女孩中,有80%的女孩从13岁起便开始使用美颜滤镜进行自拍,52%的女孩认为美颜自拍已经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接近一半以上的女孩会在每次自拍后花费10~30分钟的时间对照片进行修饰。种种行为都暗含着其自拍成瘾的可能。
(二)体象焦虑刮起的“整容风”
体象(Body Image)最早是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师Paul Schilder提出的,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在自己头脑中形成的样子,即我们的身体尺寸、形状和外形的内化。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总会抱着特定的看法,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此,体象包含着人对自己身体的美感和吸引力的看法。
移动智能时代,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人们在媒介接触习惯上越来越倾向于图片、短视频等仅需浅层次思考的“热媒介”,这也为大众身体美学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了技术和受众群体的支持。大众媒介精心挑选出“俊男靓女”,再根据每个用户的喜好加以算法推荐,逐渐使得这些审美化的图像成了大众的身体偶像和标准。在各种影视剧作品和时尚杂志封面,男性角色大多身材挺拔、面容英俊,而女性多是身材纤细、肤白貌美的形象。此外,近年来,在各类选秀活动中出现了男性偏柔化和女性阳刚化的中性打扮,一部分年轻人逐渐将其视为新的身体外在审美标准。人们对自身体象的焦虑也大部分来源于这些所谓的身体标准,于是,为了建立完美的自身形象,诸如化妆、穿搭、医疗整容等各种身体“改造”技术应运而生。
美颜滤镜不仅让用户用完美无瑕的形象来衡量自己,而且用一个虚假的自己来衡量用户的真实自我。不少自拍者难以从美颜相机的世界中抽离,在面对现实自我的时候会不适应,甚至难以接受,进而产生对自己外在形象的否认,觉得自己的身体有违大众审美,无法让自身满意,导致体象焦虑。于是,自拍者期望以美颜滤镜中的自己为标准,通过医疗整容的手段对自己的容貌进行重塑,更有甚者会甘愿为此尝试各种高风险手术。有新闻报道,一女子通过所谓的“小腿肌肉阻断术”切除小腿肌肉神经以达到瘦腿的目的,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余生将无法久站,并与剧烈运动无缘。
美国面部整形与重建外科学会的新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内容会对年轻人的心理及身体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今“千禧一代”进行“整容手术”的主要动力之一便是社交媒体的自拍。随着手机美图App行业的发展,在已有市场规模之上,一些企业也开始通过积极布局美妆、美肤与医美等产业链,帮助用户的“颜值改造”从虚拟走向现实。
(三)数字“造颜”下的个性缺失
对美丽面容偏好的心理机制几乎是人类在漫长进化史中形成的本能,而美颜自拍技术的入场与互联网缔造的赛博空间的形成,既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渠道、手段去追求美好形象的呈现,又因为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导致对存在于真实世界的每个个体的评价机制变得愈加复杂与矛盾。虚拟的数字世界正在以不可见的速度侵入真实的物质世界,人们在享受着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被动接受着“智能算法”施于我们的审美甚至思想。
美图等修图软件依托人脸识别的技术算法,构建出高鼻大眼、清秀俊朗的容颜体系,形成了对用户自身创造性的禁锢。随之而来的是,自拍逐渐趋于“统一审美”。个体逐步被技术异化,丧失了批判性与审美,沦为技术的附庸。总体而言,自拍行为是社会建构下的一种有限的自我个性的呈现,一边要迎合主流审美取向,另一边又要遵循旧有的规则框架,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标准化的数字颜值。在技术干涉和群体影响的情况下,美颜自拍者的个性消失,盲目追求审美一致。这些现象可能会加剧社会审美的趋同化、表面化,不利于审美朝着追求内涵的方向发展。于个人而言,忽视了自我所需的内涵与修养,由美颜相机制造出来的理想自我只能是一具空壳,一个仅供人欣赏的花瓶。
(四)网络社交的认同危机
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交往中,得益于技术发展所形成的多元化、多平台、多形式传播环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晒自拍照、上传短视频等方式在社交平台自由展示自身形象。同时,随着各类美图软件的出现,自拍者使用磨皮美白、亮眼瘦脸等对图像人物进行美化的操作,甚至对图像的原貌进行全方位“改造”,生产出与现实完全不符的虚拟形象。
社交媒体上的虚拟理想自我在美颜相机的加持下被放大并加以“证实”,满足了个人虚荣、炫耀的心理。在互联网时代各种媒体推波助澜下所形成的外貌至上主义,也使得一个个的“虚假自我”在社交网络空间“野蛮生长”。在社交媒体上,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自我呈现及其表演性被加倍放大,无上限的过度美化与修饰令虚拟世界的虚假性暴露无遗,社交网络上的“精修”形象逐渐令人心生反感。由美颜自拍技术所构建的“想象身体”终究只是个人真实自我的部分数字延伸,一旦脱离美颜滤镜的光环,真实所见的形象偏差必将遭致他人的非议。虚假的自我呈现对人际交往之间的关系终会产生一种疏离⑦。加之社交网络宽泛的言论表达自由与信息碎片化加工传递,他人对“虚假自我”的负面评价可能会导致自拍者陷入更深的认同性危机⑧,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信任资本的枯竭。
五、结语
自拍是人们通过外物来进行自我表达的渴望,对理想自我的憧憬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着自身做出有益的改变,如科学合理地减肥、有规律地安排作息等。但是过度的沉迷乃至“异化”会使个人在自拍行为中因认知偏差无法修正而产生极端行为。此外,我们还应当警惕由商业资本助推的种种美颜软件在无形之中对审美意识的有意形塑,避免被诱导而落入仪式化的技术陷阱。以上种种,均要求人们在自拍文化盛行的当下,持以辩证的眼光和冷静的思考。
注释:
①刘汉波.自拍,一种互联网时期的青少年亚文化——从自我凝视、数字造颜到脸谱共同体[J].中国青年研究,2017(11):12-17.
②2021年美图公司用户价值报告发布:月均产出影像数超70亿[EB/OL].证券日报,2022-01-1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756750860638309&wfr=spider&for=pc.
③祁林.从画像到自拍——技术背景下自我形象的建构与认同[J].文艺争鸣,2015(12):116-122.
④余富强,胡鹏辉.“我拍故我在”:景观社会中的自拍文化[J].新闻界,2018(03):61-67.
⑤[美]乔纳森·布朗.自我[M].陈浩莺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34-41.
⑥张振华.美颜相机下的内驱动心理探究[J].大众文艺,2017(01):171.
⑦杜凯雯.探析美颜相机对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影响[J].新闻研究导刊,2018(21):91.
⑧饶武元,陈林.基于扎根理论的大学生符号消费式“网络自拍”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22(01):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