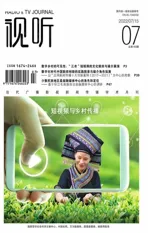新型电影生态下新主流电影的范式创新:从“硬性宣教”到“软性询唤”
2022-02-18周子琪
周子琪
新主流电影是主旋律电影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自我革新和嬗变的一种新型电影形态。近几年,《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我和我的祖国》(2019)、《八佰》(2020)、《长津湖》(2021)等“现象级”新主流电影掀起全民观影热潮,不断刷新国产电影票房纪录。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浓厚氛围下,全年上映的新主流电影多达16部,电影总票房高达94.4亿元。据M大数据、1905电影网、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联合发布的《2021中国电影年度调查报告》,“新主流电影”一词被评为2021年中国电影产业六大关键词之一。
在“文化强国”的时代语境和中国电影“总体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背景之下,新主流电影正在以崭新的面貌从市场边缘迈向舞台中央,成为当下影坛和学术界不可忽视的一种电影现象。值此全新电影格局逐步成型的重要历史节点,聚焦新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的创作实践,厘清新主流电影从“娱乐至死”到“寓教于乐”、从“硬性宣教”到“软性询唤”的发展开拓之路,并深入探析新时代背景下新主流电影的范式创新,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创新发展,持续打造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①的高质量影片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娱乐至死”到“寓教于乐”:新主流电影的生态话语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无法脱离社会、时代、历史环境而独立存在,电影艺术也不例外。要探究新主流电影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开拓路径和范式创新依据,应先理解其背后的政治、产业、文化逻辑,以及支撑其诞生发展的良性电影生态话语。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好莱坞”商业电影等国外大片的冲击,中国的电影创作开始朝着“好莱坞”化和“高概念”化进军。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拉开中国商业大片的时代帷幕,奠定了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里程碑。随后,以《无极》(2003)、《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夜宴》(2006)为代表的商业电影相继问世,助推了“娱乐至死”的电影生态的形成。在追求娱乐狂欢的“感官时代”和“视觉文化时代”,不断涌现的商业电影为中国迈入电影生产大国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以市场和娱乐为价值导向的电影创作生态也呈现出弊端:娱乐生态下的多数电影生产为了迎合大众表层感官刺激,忽视了电影作为艺术的文化使命和美学品格,国产大片逐渐丧失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大地”以及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精神建构,陷入了“叫座不叫好”的商业怪圈。在娱乐狂欢之作风靡的电影文化生态背景下,整个影视市场缺少精品力作,缺乏文化担当和历史使命,“任何附带价值与意义的深度叙事模式和观影经验被置之脑后,甚至成为戏谑对象,短暂性娱乐和快感成为他们的追求。”②
针对以上沉疴积弊,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推动中国电影创作大繁荣”座谈会上提出,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电影创作,处理好主旋律和大众化、商业化的关系”③,切实解决好“喜闻乐见”和“寓教于乐”的问题。随后,在国家文艺政策的极力推动和倡导之下,“娱乐至死”的电影文化生态开始逐步让位于“寓教于乐”或者说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生态话语。
“寓教于乐”电影生态话语的提出旨在保证电影娱乐性的同时,深化电影的政治教化功能。它的建构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市场的商业化运作,以及主流文化所渲染的纪念氛围等政治、商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近年来爆火的新主流电影正是“寓教于乐”电影生态的生动实践。
一方面,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以来,大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意识不断提升,服膺于视觉快感的满足和纯粹观赏的“媚俗”电影,以及“流量明星+大IP”的娱乐模式逐步失灵。与此同时,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主流媒介和宣扬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功能日益凸显。新主流电影的频频“爆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之间的融合。在电影审查制度日益严苛的创作环境下,新主流电影通过植入主流意识形态理念,借用主流文化的资源提升自身价值,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内的艺术形式。而主流文化则借新主流电影的大众文化市场“盘活”政治性极强的意识形态话语,从而将新主流电影成功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生产中,使之成为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编码的产品,以及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新主流电影的爆火不仅深刻契合了我国主流观众日益多元化的审美旨趣,而且深刻契合了当下爱国主义激情高涨的时代语境,以及民众对大国英雄和大国崛起的精神需求。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提出,要在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重要纪念节点上推出一批“主流大片”和“精品力作”。为响应国家号召,顺应时代需求,《南京!南京!》(2009)、《建国大业》(2009)等一大批国庆献礼大片在影坛亮相。这些影片的大获成功对中国电影的“历史转向”和“重新定位”具有方向性意义。在“新主流电影”概念被提出20年之后,伴随着电影生产体制、商业市场的成熟,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浓厚的纪念氛围的营造下,新主流电影实现了与国家宏大主题的融合,占据影坛中心地位。
从我国电影生态的转变透视新主流电影建构,不难看到,“寓教于乐”的电影生态为新主流电影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借助国家文艺方针政策和主流文化机遇,中国新主流电影一开始就着眼于自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载体和文化消费品的双重定位,并朝着“缝合”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大众娱乐与艺术追求的方向阔步前行。
二、从“硬性宣教”到“软性询唤”:新主流电影的范式创新
在全新的电影生态话语之下,新主流电影为了摆脱传统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的双重桎梏,将主流意识形态表述、艺术化追求以及商业化运作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开始着眼于电影生产范式的创新发展。
新主流电影的范式创新可以说是一场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是从“硬性宣教”到“软性询唤”的转变。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电影运动”中,一大批学者就已经对电影的“软”和“硬”展开了精彩论战。1933年,黄嘉谟发表文章《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将左翼影评提倡的具有左倾意识的电影称为“硬性影片”,认为这些影片“使软片上充满着干燥而生硬的说教的使命”④。他主张“软性电影论”,即抛弃一切政治说教,“让电影艺术用其艺术技巧自由发展以达到娱乐观众之功能。”⑤这场“软硬电影”之争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场政治立场与商业属性的美学交锋。如今,站在中国电影文化转型的重要当口,重新审视这场“软硬电影”之争,不难发现,“新主流电影”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界提出的“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的重谈和超越。
如前所述,新主流电影是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继承和发展,它旨在打破传统主旋律电影中政治主导一切的硬性、浓厚的说教模式,为主旋律电影注入商业话语和“美的观照态度”,从而以“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方式,将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调和”进商业化和艺术化的表述中,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软性询唤”。由此,新主流电影便获得在商业效应和社会效应上的平衡和共赢。在意识形态表达策略从传统“硬性宣教”向“软性询唤”转换的过程中,复合式的审美取向、多元化的共情策略、集萃式的制作模式成为新主流电影的显著特征。
(一)双重肌理:复合式审美取向
为了调和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冲突,实现电影艺术在政治性、商业性和艺术性上的“三性统一”,新主流电影在坚守主旋律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打造商业和艺术的双重肌理:对外迎合商业消费逻辑,打造视觉文化下的“惊艳美学”;对内坚守艺术文化品格,打造具有审美功能的“召唤结构”,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获得商业与艺术的复合式审美体验。
1.视觉奇观:艺术坚守下的商业表达
新主流电影坚持着眼艺术坚守下的商业表达,打造新主流电影的“惊艳美学”或者打造周宪在《视觉文化的转向》中提出的“视觉奇观”,即利用镜头转换、声音渲染等手段营造极具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众所周知,电影是一种被“凝视”的艺术,其“观看之道”呈现出大众性和公共性特征。作为一种在公共空间呈现的艺术,电影更加需要得到大众的接受和认可。一旦脱离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旨趣,电影作为文化消费品的价值就难以实现。在崇尚“感官快感”和“标新立异”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中,新主流电影要想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获得票房上的成功,就不得不利用日趋成熟的技术手段和喜闻乐见的娱乐元素,用一种“陌生化”“奇特化”的手法满足大众对感官刺激和奇异性的审美追求。为此,突破观众原有的审美期待,制造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所说的某种“震惊”效果,让“麻木”的观众短暂地惊醒,并获得强烈的心理刺激成为新主流电影的常用手段。因此,在影片中呈现各种能够为观众带来“震惊”体验的奇观影像,也就成为当下新主流电影的显著特征。
近几年,中国的文化工业极度繁盛,电影工业体系日趋成熟,3D、4K、60FPS、AR和VR技术等先进放映技术的运用也愈加成熟,这些都为视听奇观的打造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比如,《流浪地球》运用2003个特效镜头,为观众呈现了逼真的冰封城市、急剧恶化的自然环境、铁甲洪流般的运载车、极具工业感和未来感的行星发动机、精密的空间站等恢弘壮丽又细腻真实的特效。尤其是北京冰封国贸这类镜头,以极度逼真细腻的刻画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从而为观众带去前所未有的审美刺激和沉浸式体验。2021年爆火的《长津湖》则通过高清逼真的画面、宏大悦目的场面、大气磅礴的音效以及数字特效的渲染,为观众呈现呼啸而过的炮弹、震耳欲聋的轰鸣、四处散落的残肢以及严酷的战争环境,以逼真的视听观感渲染了战争的悲壮与惨烈,为观众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在沉浸式快感欲望的满足中,观众的无意识自我审查机制得到放松,而电影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观念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接受。
2.审美召唤:商业肌理下的艺术品格
视觉奇观的呈现满足了观众对“直观感知”的快感消费需求,“审美召唤”则聚焦影片在商业肌理下的艺术品格,创新了消费语境下的艺术表达。“审美召唤”概念来源于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提出的“召唤结构”(Appellstruktur)概念。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一文中,伊瑟尔指出,文学文本结构中存在着许多“空白”和“不确定性”,各级语义单位之间存在的“空缺”成为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桥梁,使读者不再是纯粹的文本接受者,而是一个文本参与者和建构者,可以通过想象填补文本的空白,实现对“第二文本”的书写。新主流电影正是利用与大众互动生成的“第二文本”,让观众体验到更高层次的参与感和审美快感,同时在观众的主动参与中释放新主流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完成给观众的审美刺激和意识形态言说。
近年来,在新的电影生态下,受到观众喜爱的新主流电影都潜在地具有某种“审美召唤结构”。它召唤着观众主动参与电影文本审美欣赏和审美建构,以此解决快感消费所带来的思想深度欠缺、社会效应式微、艺术品格低下等影视困境,实现影片社会效应、商业效应和美学效应的多重联动。例如,《战狼2》之所以能够撬动亿级观众群体,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史上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观众期待视野的迎合与超越,焕发出强大的审美召唤力量。《战狼2》上映之际,正值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期间。在主流媒体的渲染下,观众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作为战争(军事)片的《战狼2》在题材上就对观众产生了一种隐性的召唤力。而当观众怀着自己的“前理解”和“期待视野”走进电影院后,影片一开场就以一段长达3分钟的水下打斗长镜头为观众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让观众迅速带着疑问进入影片所营造的真实幻觉中。随后,电影利用非线性的叙事技巧、充满悬念的情节节奏,以及本土化的物品意象不断刺激着观众,吸引观众主动参与情节建构,将个人的人生经验、爱国情怀与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形成链接,最后在撤侨的高潮情节中完成“第二文本”的书写,实现观众自身对“强国梦”和民族自豪感的隐喻表达和想象性满足。
(二)集体共鸣:多元化共情策略
情感表达是电影艺术在商业肌理下的诗性特质,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得以输出的重要手段。近几年,新主流电影不仅聚焦观众期待视野和审美诉求,让新主流大片在审美经验方面实现了从“单一”向“复合”的转变,还积极探索主流电影在价值表述和情感表达上的策略转变,促使新主流电影实现了从传统“煽情”模式到“共情”(empathy)机制的转向。
“共情”是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术语,又称“移情”或“神入”。所谓“共情”,也叫“共感理解”,即“一个把客体人性化的过程,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别的东西内部的过程”⑥。“煽情”与“共情”的区别在于,“煽情”是从外向内的强行灌输,而“共情”则是从内向外的主动体认。在自主意识和个人意志空前觉醒的后现代社会,普罗大众对“强行煽情”日渐反感,传统电影中浅薄和单一的“煽情”和“媚俗”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行中国意识形态输出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要求。为了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对观众的软性“询唤”,新主流电影在创作中经常采用普泛化和同情式的共情策略,让观众与角色产生身份上的模糊和置换,从而发自内心地认同和接受影片所传达的主流价值观。
1.普泛化的共情策略
所谓普泛化的共情策略,即把握当下观众普遍的“情感结构”,在宏观表达上寻求观众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关于“情感结构”,按照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的说法,“情感结构”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基础,是一代人共同拥有的对生活的情感和经验。在《电影导言》中,威廉斯进一步指出,“这种共同的情感或经验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它是理解艺术的基础。艺术家和普通受众共同具有这种情感结构,它是他们之间进行沟通和理解的桥梁。艺术家和普通受众拥有的这种情感结构越多,他越能够产生共鸣。”⑦
回顾近几年的新主流电影,不管是刻画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们的《革命者》《1921》等历史片,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战争片,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等意外灾难、抗疫灾难片,还是《夺冠》《我不是药神》等影片,都在不断寻求当下观众共通的审美情感和普世化的共同体美学。这些影片通过对大众熟悉的历史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的想象性书写,最大可能地唤醒观众对重大历史和重大事件的“文化记忆”,旨在利用普罗大众普遍拥有的“文化记忆”和“情感结构”,让观众与电影所要传达的意识形态观念达成默契和共鸣,从而因势利导地强化观众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
2.个人化的同情策略
如果说普泛化的情感结构为观众不自觉地进入影片所要传达的话语体系打开了大门,那么个人化同情策略的使用则为观众走进这扇大门开辟了路径。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孔繁森》《焦裕禄》等传统主旋律电影对“高”“大”“全”的人物刻画和大写“历史”的宏观表达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大众的审美需求。当前的新主流电影逐渐从对大写的“历史”的关注转向对小写的“人”的刻画。在情感表述和价值传达上,新主流电影积极寻求与普通观众的对话,致力于用平民化的视角表现宏大的主题,并借助私语化的故事讲述方式和“小我”式的情感表达实现个人情感与国家、民族情感的缝合,让观众在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式理解中被影片所传达的意识形态“询唤”为主体。
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系列电影颠覆了传统主旋律影片宏大的家国情怀表述方式,利用微观叙事和拼图结构,塑造了“负责升国旗的升旗手”“为原子弹研发事业而放弃爱情的科学家”“把奥运会开幕式门票让给汶川孩子的出租车司机”“为中国航天事业而默默奉献的母亲”等真实可感的“小人物”形象,讲述了各个领域的“小人物”将自己的琐碎生活融入民族国家伟大历史进程的故事,拼接出一幅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接续奋斗的历史画卷。这类新主流电影将国家意识和主流文化“包裹”在小人物的生命体验中,不仅能够让观众在真实可感的环境和日常琐碎的生活中与主人公同悲同喜,还能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发挥同情式理解的作用,“完成个体与国家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国族想象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⑧,从而实现影片对观众的软性“询唤”,达到新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构建效果。
(三)联合执导:集萃式制作模式
电影虽然被誉为世界“第七大艺术”,但电影制作不仅仅是“艺术”问题,更是“产业”问题。电影艺术生产体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多重协作的、程序化的、流水线式的生产体制。2004年1月1日,国家广电总局颁布实施第21号令,电影首次被明确定义为一种产业。此后,中国电影朝着“工业化”和“产业化”方向阔步前进。近几年,中国电影工业化模式日趋成熟,而“集萃式”制作模式也已经成为当前新主流电影的全新探索。
所谓“集萃式”制作模式,即集中调动荟萃优秀人才和创作力量,以最短的时间和最高的效率完成特定影视剧创作任务,打造符合新时代特质的电影产业形态。这种制作和叙事模式博采众长,聚集了各方优秀力量,融合了不同导演和编剧的风格特征,因此呈现出一种“集锦式”的美感。从某种程度上说,“集萃式”制作模式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的“导演中心制”的颠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界的“导演中心制”成就了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创造了中国艺术电影的辉煌。但是,“导演中心制”过分强调导演私人的、感性的、情绪化的表达,不仅难以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的审美需求,而且无法满足新主流电影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双重诉求。因此,2000年,评论家马宁在《2000年:新主流电影真正的起点》中就提出,“新主流电影希望在独立制作和制片厂体制中找到一种务实的合作方法。”⑨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化发展、商业化诉求和观众审美等多重因素的博弈之下,中国新主流电影开始朝着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转向,一种由多位导演联合拍摄一部电影的“拼盘式”“集锦式”影视制作模式逐渐流行起来。以近年爆火的新主流电影为例,《我和我的祖国》中的7部短片分别由陈凯歌、徐峥、宁浩、文牧野等7位导演联合拍摄,同系列的《我和我的家乡》由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和彭大魔、邓超和俞白眉组成的5组导演联合拍摄。这类“拼盘”电影不仅融合了长短剧的优势,还深刻契合了当下年轻一代主流观众在“短视频”冲击下的多元化审美需求,因此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除了“拼盘式”的联合执导,还有《金刚川》《长津湖》等“集锦式”联合执导影片。《金刚川》由管虎牵头,郭帆、路阳两位导演协助。在3位导演的分工合作下,仅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整部电影的拍摄制作,并且影片呈现的特效技术和电影质感都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可,总票房突破了10亿元。而2021年爆火的《长津湖》更是实践了一种多导演与监制、制片人合作的新机制。影片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黄建新担任总监制。他们相互配合,在角色表演、特效场面、电影节奏方面各自发挥所长,最终呈现了一部政治性、艺术性和商业性兼具的新主流电影大片。不同于“我和我的”系列“拼盘式”的故事结构,《长津湖》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黄建新合作构建的一个完整故事。“陈凯歌式的人文关怀、徐克式的天马行空、林超贤式的紧张激烈、黄建新式的老成持重,互相磨合、彼此制约、取长补短,融为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整有机体。”⑩
作为一种全新的尝试,“联合执导”的集萃式制作模式近两年才被广泛运用于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中。虽然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模式实现了资源整合利用的最大化,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需求,也是中国电影朝着“体系化”和“工业化”开拓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集萃式制作模式对科幻、戏剧、武侠、动作等多种类型元素的吸纳和引入,模糊了传统的影视分类界限,不仅契合并尊重了“新观众”群体多元化的审美需求,也更加凸显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特征,使新主流电影具有了更博大的文化胸襟,赢得了更加广泛的观众群体。
三、结语
伴随着国家文艺方针政策调整、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巩固以及市场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新主流电影聚焦多维度审美体验,融通多元化表达策略,整合多样化资源平台,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达策略和创作范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新时期的新主流电影不仅契合了当下主流观众的审美逻辑和接受心理,还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表述,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重要抓手。纵观新型电影生态话语下新主流电影的范式创新,可以预见,新主流电影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将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方向。未来,它将扛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旗,带领中国电影持续打造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⑪的高质量影片,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注释:
①⑪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
②段运冬.中产阶级的审美想象与中国主流电影的文化生态[J].当代电影,2007(06):136-138.
③赵实.坚持正确导向推动全面创新更加自觉主动地促进电影创作大繁荣——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推动中国电影创作大繁荣座谈会”上的讲话[J].当代电影,2008(01):4-9.
④⑤刘昊.“软硬电影”之争的文化阐释[J].电影文学,2018(18):24-26.
⑥闫欢.建党百年主旋律电影特点亮点传播效果分析[J].新闻论坛,2021(05):26-28.
⑦李丽.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123-128.
⑧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消费[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04):4-13.
⑨马宁.2000年:新主流电影真正的起点[J].当代电影,2000(01):16-18.
⑩陈旭光.《长津湖》:“新主流”电影的新台阶[J].群言,2022(01):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