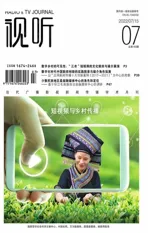乡村振兴背景下短视频中农民的乡村叙事与自我认同
——以抖音“张同学”为例
2022-02-18严文耀
严文耀
抖音博主“张同学”真名张凯,来自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建一镇松树村,是抖音上的剧情短视频创作者。“张同学”于2021年10月4日在抖音平台发布了第一条原创短视频作品,该视频获赞25.5万,评论量超2.8万,所带话题为“我的乡村生活”。此后,“张同学”持续在抖音平台更新带有“我的乡村生活”“乡村味道”“农村生活”等话题的短视频。截至2022年3月,仅仅半年时间,“张同学”的抖音粉丝数已达到1916.9万,多个视频点赞量超百万,单个视频最大点赞量超200万。“张同学”是抖音最火的账号之一,也是农民在短视频平台参与创作的典范。
一、农民参与短视频建构日常的实践内因
(一)媒介使用的日常化
现代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给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革命性影响,新媒介形式的出现也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展现超越时空限制。与“三农”题材相关的新闻在主流媒体的报道语境中数量较少,而且面临阅读量和收视率尴尬、地位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①。短视频作为新兴媒介实践形式,成为我国许多农民进行表演和交流的“新舞台”,成为嵌入农民群体日常生活的媒介。相比于微博、贴吧等社交媒体软件,移动短视频平台界面设置简单,功能选项清晰,在软件的主页即可实现视频拍摄、内容观看,便于农民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二)技术赋权下的传播主体性
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提出,文化表征方式对意义生产过程非常重要,文化意义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而且能影响人们行为,并产生实际后果②。在技术赋权下,农民取得话语自主权,并具有传播主体性。一方面,传播话语权不再由传统媒体垄断。由于抖音、快手等新信息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资源开始被配置给普通人。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于是资源分配关系得以重新构建,社会结构有所调整③。在内容与形式上,农村自媒体拍摄短视频以具有乡土气息的劳作生活、娱乐休闲等场景为主,较为真实地反映当下的乡村生活现状。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和短视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农民通过发挥新媒体的优势,成为信息生产的主体。“张同学”即是在移动短视频平台诞生的农民自主传播的典型案例,他不迎合传统意义上对乡村的建构,而是“朴实而不做作”“让乡村生活走到观众面前”。这是传播主体性的体现,也是乡村振兴能够实现的必由之路。
二、农民短视频乡村生活演绎的叙事逻辑
(一)叙事内容的来源:日常生活
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提到:“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④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技术赋权大众,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再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乡村短视频也逐渐成为一种媒介景观。从其定义出发,乡村短视频是由农民、乡村居民作为拍摄者和拍摄对象,视频时长3~8分钟,以乡村生活为主题,包括田园风格、日常劳作、风俗习惯、特色美食等内容的创作视频⑤。区别于宏大的叙事,乡村短视频的叙事内容贴近短小叙事。因此,日常生活成为乡村短视频的叙事内容来源。
“张同学”的短视频拍摄取材于他自身的日常生活,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东北乡村的生活起居场景。李子柒的视频创作更多表现出乡村生活的美与诗意,以此唤起人们对美好乡村生活的憧憬。与她不同的是,“张同学”短视频中的画面较为“粗犷”。他使用手机原相机拍摄,没有夸张的滤镜,也没有刻意拍摄优美的景色,而是展现出平凡的生活片段。正是这样的日常生活,成为“张同学”持续创作的灵感来源,也使得视频更具真实性。视频的真实性不仅体现在对乡村事物的无滤镜呈现上,还包含了叙事者真实的情感与认知。“张同学”打水洗漱、超市赊账、喂鸡喂狗的日常也传达了他朴实的情感与勤劳的品格。观众在观看“张同学”视频时,被这样的真实性打动,进而联想到自身的生活经历,产生共情,从而更加认可“张同学”。
(二)叙事内容的重组:乡村符号与文本语言
乡村符号是对乡村自然环境、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符号化表达,也是对乡村经过长期积累所形成的一般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真实记录⑥。符号的选择在乡村短视频中尤为重要,特定的符号可能会影响观众对乡村的印象。通过短视频平台,乡村日常生产生活中凝练出的符号语言突破时空限制,突破城乡的阻隔,汇入互联网,实现了乡村符号的流动传播。此外,乡村符号具有意义化指向,在短视频平台上形成了独特而又具体的乡村图景。总体而言,“张同学”视频中呈现的乡村符号兼具人物符号、情景符号、声音符号。
“张同学”为自己打造了“东北单身汉”的人设。他通过展现行为举止、生活习惯等元素,使自身形象更加立体化,如随意丢放物品、大力开关门窗、简单炒菜解决饮食、袜子穿到破洞、抽屉里有各种各样的小零食,等等。与某些网红、明星营造出的“完美人设”不同,“张同学”的人设与其呈现出的生活环境、行为举止完美融合。
情景符号主要体现在居住的特定环境与常见物件中。“张同学”的视频几乎都拍摄到了相同的场景和物件,独具乡土特色,包括东北土炕、碎花窗帘、较为简陋的平房、不平整的土路、储藏食物的地窖等。这些物品和场景都是20世纪90年代东北乡村地区所常见的,已经成为“张同学”短视频中独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
乡村的声音符号更多表现为自然声音与方言。“张同学”发布的视频除前三条全部使用视频原声外,其余视频都配有背景音乐,但背景音乐并未喧宾夺主,而是起到增强节奏感的作用。同时,保留视频原声中的自然音响,如吱呀作响的门窗、捣玉米的声音、大力剁菜的声音等,用以辅助视觉符号,带给观众更为真实、立体的呈现效果。
此外,在乡村短视频中,创作者往往会使用当地的方言叙事,通过真实的表达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张同学”是辽宁营口人,他的视频原声带有浓厚的东北口音。找老板娘“嘎肉”,一声声“二涛”和“大叔”,展示出了原生态的东北乡村地域文化。这种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也对大众有天然的贴近性。同时,视频中方言的使用能够唤起在外务工的农民群体或已经迁居城市的人们的情感共鸣,拉近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三)叙事视角的着力点:乡村内部视角
叙事视角即叙事者或故事中的人物从什么角度来讲述故事⑦。乡村短视频一般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创作者以“我”的身份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分享“我”的体验与感受,具有乡村内部视角。这样的叙事视角一方面降低了短视频拍摄的技术难度,创作者只需一部手机加上后期简单的剪辑即可创作一则短视频;另一方面拉近了创作者与观众的距离,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增强视频内容的真实性与沉浸性。
“张同学”作为叙事主体,他的大部分镜头源于手持拍摄,并以第一视角呈现。作为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松树村的一员,他具有内部人的身份,他的叙事是自我陈述。“基于第一视角,自我陈述能够直观呈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也毫无疑问排除了转述者理解偏误的情况。”⑧观众在观看“张同学”的视频时也能体会到参与感,产生情感共鸣,这也实现了乡村文化在短视频平台的有效传播。
三、短视频视域下农民关于自我认同的建构逻辑
根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农民在社交媒体中的身体表演是一种“虚拟在场”,他们一方面记录生活,另一方面也带有建立社交关系、在互动环境中构建自我形象的目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对自我认同的定义中强调个体反思的重要意义⑨,个体在互联网构建的新秩序中不断调适,在反思中寻求自我意义。
(一)真实自我的再现
安东尼·吉登斯强调:“个人的身份认同,也表现为将自己特定的叙事方式持续下去。这种叙事方式需要吸收个体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并将其分类归纳至有关自我的‘故事’中。”⑩这也表明,自我叙事与自我认同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短视频为农民群体提供了连续性的记录形式,农民在虚拟空间中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传递情感,以此展现自我。
在“张同学”的视频中,当庄稼丰收时,观众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张同学”的喜悦之情;当他与二涛拿着轮胎一起滑雪时,观众也能清晰感受到他们纯粹、朴实的快乐;当他和霞妹一起吃饭却被二涛打扰时,他的神情也能让观众感受到他的调侃和自嘲。同时,“张同学”视频的主题都与他的日常生活和人情往来息息相关,是不脱离真实生活的再建构、再表达。日常生活经验是农民确认自我的中心,他们的自我叙事是真实自我的再现。
(二)短视频的角色演绎
虽然农民短视频呈现的内容是基于真实生活的,但其中也存在自我润饰和精心安排的成分。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理想自我”指的是“我想成为的自我,它是自我认同的核心,为自我认同叙事的展开提供表达渠道”。“张同学”的短视频制作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他通过人物设定、背景音乐、剪辑手法来赋能他的角色演绎。“张同学”拍摄视频的这间房子实际上是他爷爷的老房子,他在视频中的人设是东北单身青年,但他实际上已经结婚了。“张同学”的人物设定是刻意而为的,但他的经历呈现又具有真实性。总体而言,这样的自我修饰可以增强表现力与吸引力,带来更多正向效益。
在背景音乐选择上,“张同学”使用最多的一首歌是德文歌曲《Aloha Heja He》。这首节奏明快、曲调欢快的歌曲因“张同学”的频繁使用而出圈,两者无形中产生关联。人们一听到这首歌,就会联想到乡村短视频创作者“张同学”。当“张同学”的视频没有使用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时,人们还会发表“换音乐有点不习惯”的评论。“张同学”的短视频不仅有专属的声音符号(背景音乐),其中的剪辑手法也极具个性化特征。“张同学”的短视频镜头安排紧凑,一条视频往往包含上百个镜头,每个镜头时长平均不到2.3秒⑪,镜头的呈现与背景音乐形成卡点,让整个视频更具节奏感、生动性。
(三)社会互动后的角色强化
安东尼·吉登斯在自我认同概念里强调了个体反思意义。对农民个体而言,其反思性自我意识会影响自我认同的形成,但自我认同的形成并不局限于封闭环境。经历社会的互动,与他人交流或对话也是构建自我认同不可或缺的过程。根据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自我理论⑫,创作者通过与观众的互动交流,把观众的评价、反馈作为自我调整的依据。换言之,自我的概念在社会互动中得以实现。例如,“张同学”对希望改回原来背景音乐的评论进行回应,回复“好嘞”。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张同学”获取评价与反馈,并积极反思与调整,将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结,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自我认同。
四、乡村短视频发展反思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数字异化”的风险是农民群体需要警惕的,这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力量⑬。短视频平台虽然运用大数据给农民群体带来信息,但是其中蕴含着隐性规训。一是在高频率接触短视频的过程中,农民接受来自主流话语、资本和精英文化的权力规训,同质化、模式化的农村自媒体形象不断产生。二是短视频利用大数据向农民精准推送内容,农民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容易形成“信息茧房”,从而扩大自己与精英群体的信息鸿沟。三是短视频平台为了扩大市场,往往利用原创内容补贴、流量变现、网红光环来吸引农民群体注册账号,贡献大量的视频。但是,大量的农民创作者无法持续产出优质内容,也就很难获得流量支持与经济效益,因而“只能成为迎合资本商业话语的‘网络劳工’”⑭。
我国社会正处于重要转型期,随着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提高,城乡关系也在调整与演进。在此过程中,乡土文化难免会受到冲击,乡土文化的话语权有可能逐渐走向消解。本文以抖音热门乡村博主“张同学”为例,从农民参与移动短视频建构日常的实践内因出发,探究媒介如何嵌入日常生活及农民传播主体性的体现,进而梳理出短视频中乡村生活演绎的叙事逻辑与农民自我认同的建构逻辑。在看到农民通过短视频平台实践助力乡村文化焕发生机的同时,也要注意潜在的危机。自上而下的“数字异化”和自下而上的“自我异化”都受到消费社会的影响。对此,政府、平台、农民应共同发力,展现出真实乡村的厚重议题,不落入同质化和低俗化的窠臼。农民作为传播主体,其短视频叙事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一步,但仍存在不足与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群体真正的话语崛起仍道阻且长。
注释:
①张爱凤.“底层发声”与新媒体的 “农民叙事”——以“今日头条”三农短视频为考察对象[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49-57.
②[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3.
③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8(11):114-134+204-205.
④[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
⑤赵红勋,李孟帆.日常生活的影像再造:乡村短视频的叙事逻辑研究[J].新闻论坛,2021(05):45-47.
⑥赵金海.乡土符号在美丽乡村景观载体中的应用[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49-53.
⑦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
⑧张纯刚.数字时代的乡村叙事与媒介传播——基于“张同学”现象的分析[J].农村工作通讯,2022(03):33-35.
⑨⑩[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8-59.
⑪张梦曦.从创新扩散视角看“张同学”乡村生活短视频的走红[J].新媒体研究,2022(01):85-88.
⑫[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刘海龙,于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8-99+104.
⑬刘楠,周小普.自我、异化与行动者网络: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的文化主体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07):105-111.
⑭胡疆锋.意识形态媒体商品——亚文化的收编方式[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01):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