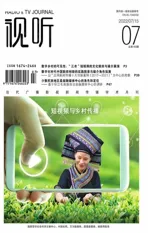新主流电影的叙事嬗变与策略创新
2022-02-18杨雨璇
杨雨璇
新主流电影是基于意识形态,通过整合多方位视角、融通多元化修辞手段、创造多点化连接式景观的方式来满足受众心理需求的一种新的电影形态①。这类电影的镜头在时间上结合历史与当代,在价值上交融家国情怀与个人梦想。新主流电影借电影的教育功能,于潜移默化中向观众传递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在媒介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的同时,我国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之一的“电影艺术”愈发彰显出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独特魅力。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主流电影创作模式的创新驱动,新主流电影在叙事层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与突破,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既展现出中国百年影史积淀的文化底蕴,又充分结合了20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理念与大众媒介范式。同时,当代受众的媒介素养和审美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他们更期待在银幕中看到符合时代气息、具有人文关怀的新主流电影。众多导演也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实践,陆续推出了《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战狼》系列和《长津湖》系列等新主流电影。这些影片将商业片的表现手法与主流价值观的传递相结合,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聚焦平民视角,呈现影片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影片艺术性与大众性的并行。
一、见微知著:叙事主体的转向
过去的主旋律电影多集中于对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刻画,力图为观众完美呈现红色英雄人物或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历史事件,如早期的历史题材和英雄人物影片《开国大典》(1989)、《七七事变》(1995)、《孔繁森》(1995)等。这些影片都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或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径直向观众灌输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及当时的革命思想。然而,直白的宣教和道德神化的英雄模范人物解构了作为文艺作品应有的艺术魅力②。尽管主旋律电影在当时的确能起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影片所引发的共鸣通常是基于观众对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高度认可的前提下才得以产生。实际上,由于观众与影片所刻画的历史背景仍存在一定的时代隔阂,他们所产生的代入感极其有限,这也使主旋律电影丢失了电影艺术本身应具有的艺术性与观赏性。此类影片在市场“遇冷”后,电影创作者开始意识到传统主旋律电影唤起观众情感共鸣的有限,以及影片艺术性缺位所造成的电影观赏性的下降。于是,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试图通过对小人物的刻画来传递宏大历史事件或历史场景中普通个体所蕴含的真挚情感,以减少观众的抵触情绪。
新主流电影在叙事主体选择上的转变,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2019年国庆节期间上映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一方面,该片首次通过大银幕用人民大众的平凡故事重现特定年代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该片不再执着于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而是注重还原故事主角的普通人特质,成功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影片每个单元的叙事文本多改编自真人真事,共同传递了电影的主题——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将电影聚焦体系分为视觉聚焦、听觉聚焦和认识聚焦。听觉聚焦又分为零视觉聚焦、原生内视觉聚焦(单个镜头本身体现视点)和次生内视觉聚焦(镜头之间的衔接构成视点)③。次生内视觉聚焦构成的人物视点能引领观众主动代入人物视角中,增强观众对影片人物的情感认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观众借由“胆小”工程师林治远的视角见证伟大新中国的成立;透过“两弹一星”科研人员高远的“失联”,知晓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背后的艰辛;借由小男孩陈冬冬与青梅竹马的女孩“错过”,再次感受中国女排举世瞩目的夺冠瞬间;透过升旗手朱涛的苦练场景,再现香港回归当晚激动人心的时刻。《前夜》篇导演管虎在采访中表示,他有意识地将镜头聚焦在伟人身后,想看看那些平时不被注意的普通人做了什么。这也体现出导演在叙事对象选择上的“有意为之”。
“不完美”的人物形象更能体现出接地气的普通人特质。《长津湖》的伍万里、《中国医生》的张竞宇和金志刚以及《烈火英雄》中的江立伟和马卫国等人物形象的选择与塑造有意消解主角光环,呈现出草根化、立体化的趋势。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也会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角色的专业身份设定也会出现失误或犯错,如《战狼》中的军人冷锋为了保护烈士家属而伤人,最后被开除军籍。《红海行动》中的观察员李懂因无法战胜对子弹的恐惧而失误,导致狙击手罗星脊柱重伤。此类冲突和失误往往会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逐渐和解,人物形象也在此过程中成长、升华,体现出其中微妙的意识形态诉求。
二、由线到点:叙事模式的转变
麦克卢汉提出,我们塑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也塑造了我们。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的碎片化、即刻化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面对海量碎片化信息,人们的阅读习惯也逐渐碎片化,思维方式逐渐断裂化。近年来,短视频的蓬勃发展也正说明受众影像阅读习惯的转变和视听感觉机制的重构。而在电影领域,受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主要反映在观众渐渐不再满足于以往传统又单一的线性叙事模式,而是开始追求内容的丰富性与跳跃性。察觉到受众观影习惯和需求的微妙变化后,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模式随之进行了新的尝试。
碎片化叙事最早来自达达派的拼贴作品和达利的意象元素组合的抽象画。其切碎、插入的策略在文本叙事中得到实践和普及,它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模式,可以让观众随作者的随意“拼接”而进入不同的叙事模式和剧情设置④。新主流电影的叙事模式变得更为碎片化,这首先体现在影片的单元式集锦呈现上。如冯小刚在1997年导演的内地第一部喜剧电影《甲方乙方》就已经采用了单元式的叙事模式,主要讲述了“好梦一日游”公司承诺帮助不同的人过上理想生活的故事。2018年,国内出现了典型的非线性叙事电影《无问西东》。而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乡》以及2021年的《我和我的父辈》,都采用了多位导演合作、分段叙事的模式。尽管影片是由多位导演执导的单元故事组成,但电影的中心思想始终作为核心线索贯穿全片,给观众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观影体验。与此同时,在空间场景的自由转换中,观众也可以窥见新主流电影叙事的多点并行。如今,人们借助技术随时切换不同的信息页面以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多任务处理的行为模式正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而在新主流电影的创作过程中,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不同空间场景的自由切换和平行蒙太奇的后期剪辑中。导演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有意弱化叙事时间的概念,突出空间场景的整体呈现。比如,《战狼2》中,冷锋为拯救人质,在商店、沙滩、仓库、荒野、实验室等多个空间场景中不断穿梭,多个运动镜头的组接给予观众更为惊险刺激、游戏式的现代观影体验。《烈火英雄》的油罐区救火任务则是通过火场现场救援、远程供水队、总控指挥室等场景频繁的平行蒙太奇剪辑来最大限度地还原火场救援的危急局势。
三、由简入繁:奇观场景的塑造
大卫·波德维尔在《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中谈到:“为了欣赏电影的艺术可能性,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这部影片的故事组织,亦即为了创造特定效果而串联各部分的方式。在布景、摄影画面、声音与剪辑上的这些决定,深深地将我们的心情带进了故事当中。”⑤作为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电影是十分典型的视觉艺术,主要借由视听语言完成叙事。无论是前期的策划、布景和拍摄,还是后期的剪辑、特效和包装,每个环节对于镜头画面的塑造都十分关键。奇观镜头多指通过精心制作为观众呈现的较为罕见、震撼人心的时空场景。过去主旋律电影的制作受限于技术水平,如今在技术的赋能下,这类奇观镜头有了更多机会和形式呈现于银幕,在刺激观众感官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影片的临场感。如电影《中国机长》为增强视听效果,采用后期特效完成了航班“四川8633”在云层、闪电、雪峰中穿梭的奇观画面,以及驾驶舱玻璃破裂后机舱内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配以逼真的同期声和音效,成功重现了当时飞机上胆战心惊的危急状况。
同时,于2021年上映的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导演将实景拍摄与后期特效巧妙结合,为观众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战争。主创团队对战斗场面的刻画始终追求表现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动用超过7万人次群众演员,进行了超百公里的战役战术设计,视觉效果极具科技感与震慑感。此外,主创团队多采用实景和真枪实弹进行拍摄,最大程度上收录现场爆破的同期声。后期特效还原出难以重现的历史场景,实景拍摄则赋予了画面更强的临场感。《长津湖》中,第一次空袭、捣毁信号塔以及全歼指挥部这三场戏在战斗场景的制作上呈现出剪辑节奏紧凑、画面感染力极强的效果。其中,从空袭到捣毁信号塔这一段剧情还采用了一镜到底的形式,再结合多个近景的运动镜头,让观众仿佛置身在激烈的战场中,获得沉浸式体验。不同景别的战斗镜头经过紧凑的蒙太奇剪辑,最终成功渲染了当年战场上摄人心魂的震撼感和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正是主创团队对无数奇观战斗场景的真实、细腻刻画,让观众能在观影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永不退缩的革命精神。
四、新主流电影叙事方式的未来走向
(一)叙事文本更具包容性
互联网打破了时空壁垒,社会新思潮不断涌现,多元观点在此碰撞交流。当下,全球文化生态正呈现出比以往更为开放、包容的发展态势,多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更是空前激烈。尽管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文化自信也在增强,但面对西方影视作品对我国形象的屡次误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正变得愈发紧急。为降低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效应,重构国家形象,艺术创作者必须拥有国际视野,以更为开放包容的眼光,增强叙事文本的可读性和多元性。
新主流电影对于构建国家形象、输出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容忽视。“新主流电影与主旋律电影相比,拥有着更多的自信和从容,它能够包容更多元的文化,在影片之中化解多元文化的对立性。”⑥正如我们已能在《战狼2》中看到美国援非医生、非洲华裔商人等新型角色之间的互动,在跨国联合制片的《红海行动》中看到蛟龙突击队代表国家利益在海外战场上与多国势力之间的博弈。未来,新主流电影将不仅注重国内反响,而且会通过创作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文化包容性、多元性的叙事文本,实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柔性传播,在电影场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牢牢把握住主导权。
(二)叙事风格呈现刚柔并济之趋势
对新主流电影而言,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价值的有效对接,始终是其重要的使命所在⑦。主旋律电影宏大的叙事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观众对其产生径直宣教的刻板印象,而新主流电影为引起新时代观众的共鸣,开始采用人性化的叙事策略,其叙事风格随之呈现出“刚”“柔”共行的趋势。“刚”指的是新主流电影中政治的“硬”诉求,如传递主流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等。正如麦奎尔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的媒介规范与传播制度相较于发达国家,应和国家政策保持同一轨道,推动国家发展和传播本国文化。新主流电影有着一定的政治特殊性,需将传播本国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置于首位。而“柔”指影片中的人文关怀,如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平凡故事与情感表达。尽管目前电影创作者已经意识到影片要注重对小人物的叙事,以唤起观众的共情,但如何自然地将叙事对象与国家意识形态融合,充分发挥普通故事的张力来传递时代精神与时代价值,仍需在新主流电影叙事文本的打磨与实践中不断探索。
新主流电影用“情”讲故事,也试图用“情”唤醒观众心底的爱国情怀,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叙事风格从“刚”与“柔”并行走向融合并济的可行路径。正如《我和我的祖国》透过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个体故事传达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刚柔并济”的叙事风格,一方面抛弃了过去纯粹说教的宣传逻辑,使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都更为立体和饱满,充分彰显人性之光与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赋予家国叙事以时代特点,创造了中国特有的电影语法与美学气质。最终,新主流电影在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成就的过程中弘扬主旋律,增强民族凝聚力与精神力量。未来,新主流电影将力图呈现出“刚柔并济”的叙事风格,进一步挖掘平凡人生中的不平凡,经由一个个鲜活的平民视角传达宏大的时代主题与主流意识形态。
五、结语
时至今日,新主流电影受到广泛关注,已多次引领观影热潮,其不仅承载着对内唤起民族认同感的职能,而且肩负着对外建构国家形象的使命。虽然它是诞生于新时代的电影类型,但是没有为迎合受众新的观影习惯而丢失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主流价值观,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和创新,推进了中国电影和社会文化的共同发展。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在叙事策略的创新上成绩斐然,获得了市场与观众的好评和认可。《红海行动》《长津湖》的制作更是彰显出可与好莱坞大片相抗衡的潜力。但新主流电影在创新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过度商业化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输出效果有限,奇观场景喧宾夺主导致影片思想深度弱化等。电影质量始终是检验电影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加之新时代观众的审美和对电影艺术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如何在故事内容的叙事上平衡好商业化与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同时保持影片的高质量,还需要电影工作者持续努力和探索。
注释:
①张婵.从社会心理修辞学的视角分析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以《战狼2》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9(20):3-4+8.
②刘帆.从《集结号》到《战狼》: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传递与观众欲望的隐秘缝合[J].电影艺术,2016(04):42-46.
③刘云舟.电影叙事学研究[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99.
④林婧婧.类型演进、形象重塑和影像叙事——中国新主流电影变迁(2007至2019)[J].戏剧之家,2020(19):105-108.
⑤[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电影艺术(插图第8版):形式与风格[M].曾伟祯,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6.
⑥杨子昊.融媒体时代下的新主流电影[J].艺术大观,2021(07):84-87.
⑦张燕,姚安颉.新世纪20年新主流电影发展景观[J].文艺论坛,2020(03):1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