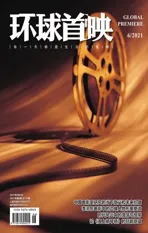从《老无所依》看当代美国独立电影视阈下的新黑色电影
2021-08-05孙菁北京电影学院
孙菁 北京电影学院
篇幅所限,本文所做的依然是单向度的以《老无所依》影片为例,先粗略描述黑色电影美学脉络、后梳理科恩兄弟的作者观念和美学构成,辅以稍许的其他影片的引证和互文,最终以此回馈到对影片的拆解上。
一、黑色电影的美学脉络
对于科恩兄弟的继承性美学的脉络梳理,显然要从黑色电影的生成开始。
黑色电影,是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电影生产中一种现象的经验总结,而总体上的描述是基于其影像风格和叙事模式,低调、高反差的布光,光影、不平衡构图对人的塑造,以及对于某些暗示性意象和实景的选取偏好[1]。黑色电影作为一种风格而不是一种类型,究其原因在于类型电影的程式/空间的封闭性对黑色电影来说并不适用,它可以完美地融合于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去,成为一种基底。
70年代起,新黑色电影的产生离不开新好莱坞电影出现后对旧有古典主义语法及叙事规则的再生成,这对黑色电影美学表现方式的影响在内部体现为作者本人的主观心理的绝对异化(梦的体现——再造现实)、在外部表现为更具写实性的介入性代入[2],这种写实感并不意味着等同于现实主义,而是一种黑暗的官能真实。对于这两种路径的轻重平衡,前者倾向更明显的体现在大卫林奇的《橡皮头》(1977)——极端情境的产生——畸形儿与现代工业的压抑(某种程度上会让人联想到《红色沙漠》)、《象人》(1980)——极端人物的产生——象人来作为表达的,后者可在1974波兰斯基导演的《唐人街》中看出,用叙事将现实的黑暗性笼罩在影片上空,即便这是一个非美国体制内的作者,但从出品公司和同时期潜在的影响仍然可以得出这种倾向。
至于今日非常显著的当代美国独立电影,其甫一出现,对美学形式上的反主流就天然的贴合黑色电影对于美国电影作为超级市场——类型固化[3]的边界破坏。
二、科恩兄弟的美学构成
纵观科恩兄弟的电影,自1984年自编自导《血迷宫》起,西部片、犯罪片可以说是其痴迷的电影类型,故事通常是一个犯罪故事,糅合西部地域性元素的表征,以悬疑、惊悚展开,间或夹杂些许喜剧元素,这种展开带有着作者自身观念指导下天然的幽默性解构。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些表征之外,其作品内里是对于黑色电影的心灵幽暗意识的绝对继承,外化为明显的、可识别的美学风格,也即影片的基调。这种继承和发展,有别于古典主义的语法使用,如《血迷宫》(1984)中开场摄影机运动镜头的主观破除、画外音内容的选取和叙述者的偏离,提示着作者介入的本身,这种对观众的间离实际上也是互动的,被看作是“新古典主义”式的语法使用[4]。
当代美国独立电影模式下的新黑色电影的主要作者,除却大卫林奇的自编自导在美学延伸方面体现出极重的作者性,其他几位的商业属性和对应的受众群体效应更为明显,他们各自的延伸性美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语法的观念和使用上。从九十年代整体来看,昆汀塔伦蒂诺对于暴力的延伸明显吸收了东方美学(中国香港电影)以及日本动漫色彩——参见《低俗小说》《杀死比尔1、2》(后两部片子某种程度采用了黑色电影的方法,但似乎脱离了其幽暗内核和心灵深渊),大卫芬奇更多基于MTV、实验性视觉美学[5]以及对美国电影作为超级市场的商品性解构[6]——参见《搏击俱乐部》。
而科恩兄弟成长期的源泉,则来自美国当代侦探、犯罪等小说的文学滋养[7]、好莱坞大制片厂时代末期的B级片以及对作者导演极其重要的地缘文化[8]。在《血迷宫》之后的创作中,科恩兄弟每一次都是在以极限式的方法挖掘空间场景,他们的作者性不止体现在导演层面(这一点明显有别于不写剧本的大卫芬奇),还在于从自制剧本伊始到非常详实的分镜图[9]体现出的他们对影片从头到尾的严格把控。对比《后窗》中主观镜头回望和受众一体的单一技巧性使用,而在《巴顿芬克》(1991)中,整个电影是巴顿芬克的经历现实还是其创作内容的想象无疑将“看与被看”——电影作为媒介使用的景框[10]观念再一次扩大化。
三、《老无所依》的美学观念
(一)定位
《老无所依》(2007)的定位实际上有着某种革新的古典主义色彩,其野心在于构建一个科恩兄弟式的黑色电影的现代性范式。这一点,从影片在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中得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这两个奖项足以看出。不过,排在这种范式前的,一定是作者性,这也是美国独立电影这些年发展下的明显表征。影片在技法上的精准范式体现在对光影、声音的精简使用上,使其成为非常清晰的感官性叙事内容。
不论是低照度高反差下,黑暗中宾馆客房门缝高光的阴影骤现(图1——Chigurh来追杀Moss),还是画外音对脚步声的音量的精准调整来并置画外人物动作,以达到与画内的对立戏剧效果,以及整体上使用声音以静写动[11]来孤立凸显单个场景段落高潮时的戏剧效果。类比于古典主义时期的梦幻代入[12],影片的现代性体现在将早期黑色电影中较跳跃的光影合理化[13]缝合到叙事空间中,这种写实性的处理又是建构在角色机制本身上的主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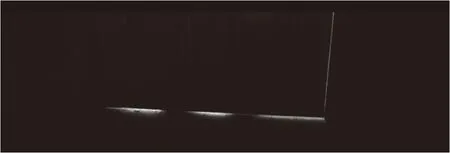
图 1
(二)语汇
1.开场
第一个镜头(见图2)以及后续的系列空镜,准确指向了作品的黑色基调。
看不见的山峦被黑暗主导,地平线微光的破晓抑或黄昏,伴随画外对往昔的追溯——怀旧,叙事情境的进入直接导向一种幽闭意识,对往昔不再的喟叹、对今时的无奈以及衰弱感。通过对西部旷野的剪影式的、大面积阴影下的大远景展现,以及老警察诉说信仰缺失后的后现代犯罪症状,受众对情境的感官已经与文本达成了贴合,即这是一部什么样风格的电影。
定调之外,这里突破性的构成可能在于,叙述者脱离了一般范本的主要角色,而这与《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角色对男主角安迪的互文不同,老警察仅从属于叙事脉络的勾连——以案件开始和Moss死亡结束两段出现为主。究其表述内容,他的存在本身趋于一种作者化巧妙介入,即与观众直接对话,这是明显区别于过往的黑色电影的,这种开场段落的表述,实际上和《镜子》开场段落发声的作者表述异曲同工,只不过,时间流转后前者更具好莱坞式的技巧性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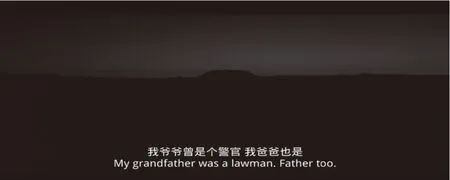
图 2
2.发现Moss死亡的段落
唯一一段极具晃动感的手持摄影段落,是表现老警察进入Moss死亡的现场空间,与全片整体的较稳定的影像风格(以固定机位,微推/拉、摇镜头为主)形成明显的对照,主观化凸显老警察内心震动背后一直叠加的无奈——维护Moss的存活意味着某种旧日般的希望。而这种进入是在青天白日下展开的,阴影的使用巧妙地构建在了符合人物身份的牛仔帽对阳光遮挡上。随着他进入走廊,与身后过曝的外部空间形成对照。
这里对Moss死亡前场面的跳跃性遮蔽,是对既有范式的一种期待性心理的摧毁,通过这种摧毁性的语汇完成作者——观众对于生命不确定性的绝望观念的传递。实际上这也与之前夜里两次繁复的逃避和争斗形成孤立对照。对白日的使用同时也是导演对黑色电影美学的再次解构,举重若轻,光天化日下更见内心对现实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是作者观念的投射。
声音上也对场景空间做了巧妙挖掘。伊始的不断的飞机声、远处交杂的人声、婴儿哭声完整构建了情境,同时克制老警察的话语以进入内心。
3.老警察见叔父的段落
室内空间破败的空间设置,在构图上有了非常多的背景如屋内窗框的切割感,这在通篇的空间使用上比比皆是。而这里体现的结构观念是,在案件结束下,老警察和叔叔提出上帝未曾到来的主题性表达,这是对叙事旅程临近结束的一个提前总结,与开场描述犯罪少年的信仰缺失形成互文。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代入上帝来作出对自我的失望性评价,没有什么比让一个怀有希望的人失望更让人绝望的了。观众同他一起目睹,得出结论。
(三)重构
早期黑色电影中看不见的手被直接魔幻化,显化为影片中黑暗的实体Chigurh。将原著更缥缈的人物写实化,实际上涉及到作者的电影观念,通过不断地构建叙事情境再不断的在情节中用结构语汇打破范式带来的情境代入感(几次情节的奇异转向),传达生命无法掌控的不确定性。因此,Chigurh在片尾遭遇莫名的车祸是作者嘲讽式的标识性电影观念,纵使电影里那只无所不能的手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电影力图复刻八十年代的美国德州,不可避免地带着今人的作者观,时间重构接轨的弥合下还是作者对于当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其通篇的美学构建上展示出现实的消极,但在结尾以老警察已故父亲的等待仍然完成对观众的心理提拉,这就是所谓的电影幻觉吧。
四、结语
当下,新黑色电影的统称是否还准确,新古典主义的复苏是否意味着一种美学的变化延伸,显然以这篇文章作为小范围的组织和思考远远不能论证清楚,但是从《醉乡民谣》(2013)、《消失的爱人》(2014)来看,对比70年代时的新黑色电影,显然随着当代美国独立电影在奥斯卡体现出的声势浩大[14],某种非常当代性的、后现代式的内容已经产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