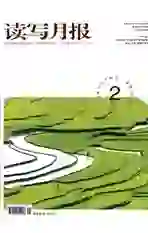多重对话寄寓的哲性表达
2021-06-11余树财
余树财
《囚绿记》作为一篇经典散文,被收录到了不同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对于这篇文章主题的解读,历来存在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爱国说”“心灵说”“反省说”“颂扬说”四种。
“爱国说”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3?教师教学用书》为代表:“(《囚绿记》)含蓄地揭示了华北地区人民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命运,象征着作者和广大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1]
“心灵说”以张斗和老师为代表,他在《<囚绿记>主题解读突围》一文中言:“《囚绿记》是作者在一个特殊时段理智与情感交锋的心灵独语,是作者‘心灵起伏的痕迹,既无关宏大的政治主题,更谈不上崇高的民族气节,只是他对人性某方面的揭示和反思,或者说是他迷茫心灵的自我救赎,象征一切美好事物的‘常春藤,仅仅是他想表达思想情感的一个寄托物。具体地讲,就是文章描述了‘我和‘常春藤之间的交往和纠葛,揭示了爱和占有的关系:爱一旦变为占有,必然会给对方造成伤害;真正爱对方,就要尊重对方,给对方以自由的空间。”[2]
“反省说”(或者叫“忏悔说”)和“颂扬说”,以南开大学徐江教授为代表,认为:“《囚绿记》是自我暴露式的批判,是反思,甚至还有一点点忏悔。……作为一种自我精神的救赎,‘我以记的形式写下这一段经历,以‘我的‘丑行与‘绿藤的‘美德对立来讴歌了生命的尊严,特别是对‘绿藤坚守自身生存的本性表达了敬仰。”[3]
持“心灵说”“反省说”“颂扬说”者往往批判“爱国说”,认为“爱国说”是一种生硬的“知人论世”解读实践,是“对文本进行思想意识层面的图解”“泛政治化地附会”,是一种标签式的解读。在笔者看来,这些解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有一定道理,同时也都有偏差。本文不揣浅陋,从对话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囚绿记》主题,以求教于方家。
西方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具有潜在的对话性,它从多种层次和角度持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4]。《囚绿记》通过记叙作者与“常春藤绿”之间的一段交往经历,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对话,在多重对话中,构建起文本的丰富意蕴。
一、与“绿”对话,寄寓生命哲思
《囚绿记》是一篇回忆性散文,文本以“恋绿”——“囚绿”——“释绿”——“怀绿”为主线,叙述了“选择房间”“凭窗对语”“异爱囚绿”“南归释绿”“归后怀绿”五件事,其中“选择房间”“凭窗对语”和“异爱囚绿”都蕴含着作者与“绿”的对话。
我们先来看“选择房间”。“选择房间”虽未直接展开与“绿”的对话,但这件事是作者与“绿”对话的铺垫,是为引出“凭窗对语”而作的交代。房间非常小,“高广不过一丈”,地面潮湿,非常简陋——“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而且夏天非常炎热,可作者为何在“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还要选择这间房间?主要是因为“这房间靠南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圆窗”“圆窗外面长着常春藤。当太阳照过它繁密的枝叶,透到我房里来的时候,便有一片绿影”,作者“便是欢喜这片绿影才选定这房间的”。这些描写都是在交代囚“绿”的原因,衬托了作者对“绿”的喜爱。
“凭窗对语”直接展开了作者与“绿”的对话。只是这里所说的对话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物语言对白,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对话性既包括外在言语行为又包括内在心理意识。因此,文本中的人物对话除了直接引语,也包括自语、眼神、肢体动作、心理活动等同样需要或预设外界给予一定应答的‘潜对话形式”[5]。也就是说,文学文本中的对话既包括人物语言对白,也包括内心独白(自语)和心理活动等。“凭窗对语”便是作者对“绿”的一段内心独白:
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我懷念着绿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欢喜看水白,我欢喜看草绿。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我怀念着绿色,如同涸辙的鱼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当我在这小房中安顿下来,我移徙小台子到圆窗下,让我面朝墙壁和小窗。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但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我望着这小圆洞,绿叶和我对语。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
在作者看来,绿色是宝贵的,因为它象征生命,带给人希望、慰安、快乐,所以“我急不暇择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绿也视同至宝”。同时,绿色也代表自然,作者热爱自然,自然与作者也心有灵犀——“我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语言一样”。这段与“绿”的对话,表面上看是表现了作者对“绿”的喜爱,但何尝不是对生命的哲思与感悟?所以,读这段文字,读者在感受到作者内心激情的同时,也会受到启示——热爱并尊重自然与生命,这就是哲思带给人的心灵的震颤与触动。
与“绿”的对话在“异爱囚绿”部分也有展开。在作者囚禁了常春藤之后,“绿的枝条悬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旧伸长,依旧攀缘,依旧舒放,并且比在外边长得更快”。常春藤以顽强的生命力感动着作者,作者不由发出感叹:“我好像发现了一种‘生的欢喜,超过了任何喜悦。”这一处与“绿”的对话表达的是作者对常春藤坚守生命尊严的颂扬,也蕴含着作者对生命的深沉感悟。
二、与心灵对话,寄寓爱的哲思
张斗和老师说:“《囚绿记》是作者在一个特殊时段理智与情感交锋的心灵独语。”[6]这个评价是比较合乎文本实际的。但真正体现对话性的心灵独语(对话)还是集中在“异爱囚绿”的叙事中。
“异爱囚绿”是文本最富张力之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异爱囚绿”本身蕴含着矛盾和悖论:作者既然那么爱“绿”,就应该给“绿”以自由,为何又要将“绿”囚禁起来?因为作者对“绿”的爱发生了变异,偏离了“爱”本身:
忽然有一种自私的念头触动了我。我从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两枝浆液丰富的柔条牵进我的屋子里来,叫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我拿绿色来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绿色来比喻葱茏的爱和幸福,我要借绿色来比喻猗郁的年华。我囚住这绿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鸟,要它为我作无声的歌唱。
作者因为喜爱“绿”而产生了“自私的念头”,将“绿”囚禁起来,将“爱”异化成了“占有”(“牵进我的屋子里来,叫它伸长到我的书案上,让绿色和我更接近,更亲密”)和“功利”(“装饰我这简陋的房间,装饰我过于抑郁的心情”),故称之为“异爱”。而“占有”和“功利”的后果是——“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得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为此,作者感到自责和内疚,展开了一段自我心灵对话:
我渐渐不能原谅我自己的过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锁到暗黑的室内;我渐渐为这病损的枝叶可怜,虽则我恼怒它的固执,无亲热,我仍旧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长了。
尽管作者感到自责和内疚,但并未停止囚绿行为,反而心中生长出了“魔念”——继续囚绿,直到南归才释放它。作者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想表现什么?难道只是想忏悔反省自己的自私,告诉读者人性是自私的?显然不是。“异爱囚绿”的心灵对话其实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对自己喜爱的事物往往想占有它,愈是喜爱,愈是想占有,喜爱度越高,占有欲越强。这是不是也在揭示爱与占有的辩证关系,启迪人们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异爱囚绿”的心灵对话其实寄寓着作者对爱的哲思,它启示人们思考爱的真谛: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要给予被爱的对象以自由。
三、与时代对话,寄寓社会哲思
一些解读者反对甚至批判“知人論世”地读解《囚绿记》,认为这样会“政治化地附会”文本。我们当然不赞成随意“政治化地图解”文本,但任何文本的产生与创作都有其历史语境,对文本的读解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历史语境的,否则可能会造成解读上“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偏狭,因为文本本质上是一种对话。巴赫金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观点,认为对话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他认为:“人的个性只能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只能处于阶级之中。他是历史现实和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因为无论一个人每一举动,无论一种具体思想的形成(想法、艺术形象,甚至是梦幻内容)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条件来阐释和理解。”[7]
《囚绿记》写于抗战时期,记录了作者特定时期“心灵起伏的痕迹”,要深入理解文本,我们当然不能脱离时代语境。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卢沟桥事件,作者可能还要多囚禁常春藤一段时间。提前“释绿”这个行为(事件)是因为日本全面侵华,囚绿和释绿的矛盾得以凸显——作者不能再按原计划尽情地囚绿。只有提前释绿,矛盾才能解决。要理解这个矛盾的解决,我们还是要把提前释绿这个行为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来理解。换句话说,我们要还原文本的历史语境。
《囚绿记》写于1938年,作者回忆了1937年夏天与常春藤交往的一段经历。1937年是日寇大举侵华的一年,那一年的夏天,北平的局势已经很紧张,所以作者才“打算七月尾回南去”,打算在离开的时候恢复常春藤的自由。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形势发展比作者预计的严峻,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作者只能提前释绿赶往南方避难。作者为何要释绿?作者可不可以不释绿?释绿之后,常春藤就一定能获得自由吗?在日寇的铁蹄下,常春藤也不一定能逃过战争的劫难,可作者为什么还是要释绿呢?除了爱绿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因为在囚绿的过程中,作者被“绿”“永不屈服于黑暗”的顽强感动了。在作者看来,民族救亡图存正需要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所以作者在临行时“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为什么用“珍重”这个词,如果只是表达对“绿”的愧疚、忏悔,完全可以说“忏愧地开释”或“忏悔地开释”。“珍重”有珍惜、爱惜、重视、尊重之意,除了表达对“绿”坚守生命尊严的颂扬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警醒人们要重视、尊重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唯有发扬这种精神,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取得抗战的胜利。即此时,在作者心中,“绿”不只是一个生命,它还象征着当时的中国,象征着整个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样的寄寓,作者才会有接下来与“绿”的对话:
我把瘦黄的枝叶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
作者只是在向“绿”祝福吗?显然不是!作者在向国家、民族祝福,祝福中国、中华民族早日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囚绿记》亦是在与时代对话,寄寓了作者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思索。这是一种深沉的社会哲思,亦是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一份责任担当。
总之,《囚绿记》是一篇寄寓哲思的叙事散文,文本在与“绿”、心灵、时代的多重对话中,寄寓了对生命、人生、社会的哲理性思考。基于这样一个理解,笔者认为,对《囚绿记》主题的解读,不能只见一隅而忽略了文本的更广阔的天地。这也启示我们,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要敞开胸怀,开阔视野,变换视角,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文本更靓丽的“风景”。
注释: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2(必修)?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2][6]张斗和:《〈囚绿记〉主题解读突围》,《语文教学通讯·初中》,2014年第9期,第57页,第57页。
[3]徐江、刘承英、戚笑微:《“知人论世”:语文教学的哲学错位——〈囚绿记〉是颂扬民族性格还是认识生命尊严》,《人民教育》,2009年第10期,第41页。
[4]邵子华:《论文学文本的对话性》,《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55页。
[5]张开焱:《开放人格——巴赫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7][前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5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成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