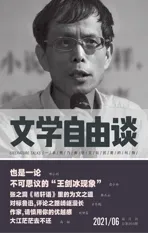做“学术常青树”的乐趣
2021-03-08古远清
□古远清
在2021年5月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的“古远清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会议上,我写了两句话:“渺渺如烟,八十不算华诞;苍苍如天,一生所幸平安。”
既然“八十不算华诞”,也就是不敢倚老卖老,那就赶快做出实绩,这样才能不辜负“平安”二字。
晚年我除继续深耕“台湾文学”这一领域,连续在台北万卷楼图书出版公司推出《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微型台湾文学史》《台湾文艺书刊史》《台湾文学出版史》《台湾文学论争史》等十本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为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一是出版《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二是编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三是编选《“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论文选》。前两种均得到有关部门的资助而面世,后一种就只好自己掏腰包了。自费倒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出版后对岸的书很难寄过去,这对书中入选的作者不好交代。即使海关放行了,这种分上、下两册精装的书,没有“秘书”的我如何提得动到快递站去?就是提得动,不少作者的外文地址(如美国、加拿大、韩国等)书写起来也非易事。有道是“船到滩头自有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出了再说吧。
当下学界,凡是退休的人,极少有做科研的,就是做科研也是报课题,这样才有经费的保障。可我不走这条路,相信学术不能命题作文,而是从兴趣出发。所以我凭兴趣近乎疯狂地写书、出书,以致被人讥为“不会享受生活”。岂可与夏虫语冰?做“学术的常青树”,才是我人生最大的乐趣。到对岸出版竖排的繁体字书,出后读之更是觉得这是“妙处难与君说”的享受。
室外有人跳舞,有人打麻将,有人旅游,而我却以原始的爬格子方式打发时间。人各有志,不必强求一致也。
到了耄耋之年,我庆幸自己仍有一种为新学科添砖加瓦的冲动,庆幸自己追求生命的价值是如此痴迷和乐此不疲。探索新知,永不休止。著书立说,年年出新,不亦快哉!
我在外出讲学时,有的学校出海报说我是博士、博导。其实我连学士都不是,“文革”前在武汉大学读了五年,只拿到毕业证书。我从来没有带过研究生,更没有“古门子弟”。可庆幸的是,无论是海峡对岸还是此岸,我都有些“粉丝”,有的还是“铁粉”呢。没有人民币或台币“打赏”,疫情下又没有机会出去讲学,由此还得忍受寂寞、枯燥、单调,和在有些人看来“不赚反亏”的苦痛。
我这辈子由于不在名牌大学任教,还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和不屑,但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在有生之年交出漂亮的成绩单,要紧的是心态平和,不埋怨当下学术环境不好,不埋怨台港文学研究的论著发表和出版的艰难。选择这样的研究课题,是我的宿命,无怨无悔。我用自己热爱台港文学研究、钟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去形塑自己,完善自己。所幸的是,万卷楼图书出版公司独具慧眼,愿意将我那一本本小书做成精装的大书,以簇新的面貌呈现给彼岸的读者。正因为有“万卷楼”做坚强的后盾,我才会不管别人对我的评价,哪怕对岸有人贬损我说:“《台湾当代新诗史》送到废品收购站,还不到一公斤。”对这种恶评,我不回应,不计较,不逃避,更不敢偷懒,不敢懈怠,唯以不服输的坚守姿态,为世界华文文学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加油、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