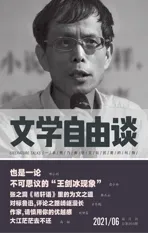诗是诗,歌是歌
2021-03-08□李仪
□李 仪
丁鲁先生的《百年新诗,问题何在?》(《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5期)一文,当时读了并不以为然,只是觉得有些偏颇;但及至细思,才觉得有些问题确实容易造成混乱,应予澄清。下面择要谈两点看法。
1、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丁鲁先生是借说别人的文章来谈自己对新诗的看法,但题旨所在,文中就难免对中国新诗颇多微词。他首先说概念,认为“百年来,中国诗歌论争不断,评价尖锐对立,所提名词、观点越多,越是搅成一团乱麻,一个大毛病就是概念不清,逻辑混乱”。作为读者,我读到的只是丁先生在解释“现代白话就是现代汉语”上的纠缠。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费口舌,不管是否出自丁先生对新诗合法性的怀疑,肯定是在为后文做铺垫。
果然,丁先生紧接着提出理论问题,他说:“中国现代诗歌界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作品,而在于基本理论的缺失;其关键,在于没有摆正内容和形式的位置,长期轻视形式问题。”为此,丁先生要“厘清‘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确实,目前鲜见成体系的诗学研究,但要说摆正内容和形式的位置,怎么摆正,怎么厘清,这才是个问题。
我是这样看的:内容和形式始终是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一个重要关系问题,但也是撕扯不清的问题,实践中又都是“关乎一心”的事。事实上,古人对内容和形式相当重视,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这主要是讲文章要合规矩。至宋代以后,对内容有了要求,强调的是文道并重,文道统一,文道和谐,意思是内容和形式要尽可能的统一。这一说法在那个时代基本维持了下来。新文化运动中,更多的是对“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发起冲击,并未就内容与形式做更深的探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创作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内容与形式才成为起起伏伏争论不休的一对问题。据我浅陋认知,在这方面似乎只有童庆炳教授能够独出机杼,不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划分轩轾,倚轻倚重,而是试图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矛盾中解决这一问题,提出“题材与形式相互征服”的论述。
那么丁先生说要厘清这一对关系问题,是怎么厘清的呢?他采取一边倒的态度,强调的是形式。
丁先生特意先“着重”做了一个说明:“形式是确定事物的基本条件之一,并不只是等同于艺术性。拿人做比方,两腿直立的形式可以解放双手,发展头脑,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并非只是长得漂亮不漂亮的问题。”这个比方打得有点不伦不类。两腿直立是进化,怎么能说是形式?当然,丁先生本意是说形式的必要性,这是对的。我的意思是,就文体来说,形式关乎审美,站在审美的角度,形式即艺术。
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丁先生先是指责“百年来中国诗歌界对语言学的研究非常薄弱”,然后说:“中国古代诗人大都是语言学的行家里手。如何押韵,就是一种语音学研究。”接着又说:“想要解决中国诗歌的基本理论问题,不用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真是可惜,这里强调的竟然是押韵。板子高高举起,打的却不是地方。
我在想,可能丁先生不了解中国新诗界在前行路上对语言的研究和拓展,而是出于个人喜好才指责新诗写作实践中对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忽视;但丁先生既然也认为形式的重要,那么形式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最基本的常识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的形式,是指表现作品内容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部表现形态的总和,包括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而这一切岂能单单用语音来概括?当然更不是丁先生所说的“诗歌形式不过是节奏、韵脚之类的具体问题”。再说了,谈形式必然要和内容连在一起,二者是一种互为依附的关系,单独谈哪个都不会产生意义。
我以为,丁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能秉持了“诗是韵文”的传统说法,但他针对新诗来谈语音、押韵问题,可能是对他一再强调“现代汉语”新诗的认识太过隔膜的原因,这样来谈中国新诗未免有点隔靴搔痒。
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特别是随着胡适《白话诗八首》的发表,具有命名性质的中国新诗诞生,从此,区别于旧体诗的一种新的诗体样式,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生长。新诗的出现有其客观因素,除了古典诗歌的趋于僵化,最主要的是文言退后,日常口语(也就是那时说的白话)走到前台,这是社会的进步。相比古代汉语,以口语为基础的现代汉语发生很大变化,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音词的大量出现,这样就使以语言为介质的诗体形态发生变化。
新诗的变化,当然包括空间物理形态的改变——也就是丁先生说的分行,同时,由于多音词的出现和语言结构趋繁,造成句子的长短不一,还有就是由于语言介质的差异,新诗在平仄和用韵上受到限制,尽管强化了语言的顿挫和节奏感,仍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古典诗歌那种“天然”的音乐美感。但是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诗在对诗性的挖掘,对诗意的追求中,形成了以句为核心,注重句子之间关系和意象呈现的叙事性特征,重新建构了诗的形式和趣味。
在这种情况下,丁先生还要强调“我们不能只会用《文心雕龙》那种文学的写作范式,还要会用科学(即语言学、语音学)的写作范式”,这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姑且不论押韵对新诗重要与否,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体的行为,特别是在面对如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生体验时,诗人更需要采取多样的语言策略与表现手法来反映社会和人生,而不能作茧自缚,固守在一个狭小的天地。
为了说明押韵问题,丁先生在文中还多次提到白话格律诗,认为韵是一种格律因素,五四以来有韵的新诗包括朦胧诗,“都应视作‘半格律诗’”,而不能算作“自由诗”,为“白话格律诗的空间就显得更加狭窄了”鸣不平。事实上,如果从结构方式、诗性感觉、意象使用、修辞方法等方面来看,现在我们称为新诗或者现代诗的这类诗,和白话格律诗显然不同,不能因为有的用韵就把它们当作格律诗。很显然,丁先生的这种说法并不妥当。至于丁先生说的新诗“强调‘意象’而忽视‘意境’,导致作品的碎片化;强调‘形而上’而蔑视‘形而下’”等等说法,我认为也存有偏见,或者说这只是丁先生个人的认识。比如意象是走向意境的桥梁,这是人们对意象生成和意境创设的一个共同认识,不知丁先生对此作何理解。
文随代变,这是规律。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和人们的审美风尚转变等等原因,都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心理结构的改变,使文本发生变化。这是文随代变的内在机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2、“诗”就是“诗”,“歌”就是“歌”
丁先生说,“我这里重点谈谈‘诗’和‘歌’的关系”。他说:“如今,歌词正插着音乐的翅膀高高飞翔,形成了时下最广泛的诗歌运动,新诗界却似乎视而不见。一些人只谈‘诗’,不谈‘歌’,似乎连中文的‘诗歌’这个词也想废弃。在他们看来,歌词就不是‘诗’,歌词作者就不是诗人。按这种意见,古典诗歌中,起码宋词、元曲就不能算诗,因为那些都是歌词,而且是先有曲谱后填词的。”读了这段,真让人感到云山雾罩,不明所以。
首先,“歌词正插着音乐的翅膀高高飞翔,形成了时下最广泛的诗歌运动”,按这种看法,诗和歌就是一回事,这就引出了后面丁先生的诘难:“新诗界却似乎视而不见。”丁先生列出了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怒吼吧,黄河!》、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乔羽的《思念》、晓光的《那就是我》等歌曲,质问:“这些难道不是诗?难道不是好诗?它们的作者难道不是诗人?”
说真的,诗入曲当然是歌,好诗入曲也不影响它还是好诗。但是入曲的难道都是诗么?人所共知的是,已故作曲家李劫夫当初谱的曲不论何时来看,很多就不是诗。还有歌词作者就是歌词作者,如果歌词作者也写诗,当然也是诗人,写出好诗当然还是好诗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丁先生不会不知道,在清末民初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和文化改良运动中,人为推动“诗”和“歌”结合的那段历史,它除了充当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留下的只有叹息。艺术上的拉郎配只会伤害艺术本身,如果不是这样,新文学和新音乐可能发展的姿态更好。其次,“一些人只谈‘诗’,不谈‘歌’,似乎连中文的‘诗歌’这个词也想废弃”——废弃不废弃不是谁能说了算的,完全看个人使用习惯。据我所知,一些人包括我在内,确实注意“诗歌”一词的使用,一般非必要就直接说“诗”,很少说“诗歌”。因为“诗”就是“诗”,“歌”就是“歌”。当然我不反对别人使用“诗歌”一词,因为人家使用的概念含义很明确,指的就是“诗”。
我认为,如果要对艺术样式进行判断,就离不开溯源,比如诗的产生,比如歌的产生,都要溯源;如果没有佐证,可以提出假说,但这就要看哪种说法合理的成分多。鲁迅先生是“杭育杭育”派,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诗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这当然是一种假说,因为没有实物佐证,只能猜想。而我认为语言是人类的心灵之音,对文体的追溯,要观照语言的初始。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会看到,人类从混沌中走出,面对万物,还有自我内心感应的冲动,这是心灵与万物的碰撞,破空而来,绝尘而去。这时候人类的思维状态才是诗产生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心绪飞驰为诗。
当然,心绪飞驰作为诗的一种原初状态,是诗性产生的源头,但在保持诗性的同时,其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诗的音乐性,就是最初的诗与音乐的汇合找到的一种最好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意义主要在于易传播。在这方面,民歌和庙堂祭祀的颂词扮演了重要角色。就这样,诗长了“脚”,让诗得以前行。诗的最初一只“脚”是音乐,诗的另一只“脚”就是文字出现之后产生的文本。
我这样说当然也是强调音乐性对诗所具有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把“诗”和“歌”完全等同起来的理由,因为还有大量不入乐的“徒诗”存在,而“徒诗”更体现了诗性的特征。所以在古代,普遍是把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后人就是据此把“诗”和“歌”统称为诗歌,这仅仅是一种习惯上的称呼,并不严谨。丁先生在文中发出的诘难实在有点想当然,特别是把歌词借音乐传播当作时下最广泛的诗歌运动,让人不可思议。
就丁文说了这么多,我愈发觉得,新诗百年,关于新诗之“新”质的甄别仍然没有解决。比如新诗何以被称为“新”诗,它区别于“旧”诗的地方到底有哪些,新诗如何超越旧诗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等等。这些问题自新诗诞生之日起就面临“旧诗人”的质疑和“新诗人”的困惑。新诗的这种身份确认之旅至今还在路上,新诗文体认同的建构工程仍然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