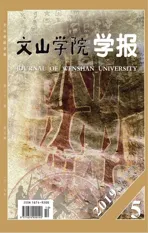道德代偿:孔子政治思想的构建逻辑
——兼论儒家何以不能成为现代政治治理的权威
2019-12-27张国伟
张国伟
(文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通常,所谓的“代偿”是“指某些器官因疾病受损后,机体调动未受损部分和有关的器官、组合或细胞来替代或补偿其代谢和功能,使体内建立新的平衡过程。”[1]春秋末期,争霸和战争严重破坏社会机体,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原有法度名存实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从礼仪的规则出发去探寻社会秩序的本原,得出“仁”是社会秩序和规范的终极价值和心理皈依,“仁”外化为“克己复礼”进行社会改造,即通过社会成员的自我约束和自觉认同且遵守等级秩序,实现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建。为使“克己”和“复礼”得到具体的实践,便以“仁”为中心构建道德纲目,使“克己”所指向的理想人格和“复礼”所指向的政治理想有理论和经验的指导。
一、仁:人性改造扩散为社会改造的终极价值和心理本原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纵观整篇《论语》,看不到孔子关于政治制度改造的直接主张,而是通过论述人性改造和塑造完美人格的方式,投射、扩散社会秩序和规范重建的路径,进而达到“和”即天下大治的目的。
(一)仁的思想总归:爱人
仁具有广阔的内涵,主要有:一是敬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2]172,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人而不论身份贵贱;二是慎言,“仁者,其言也讱”,即说话要慎重考虑,做到说出来的话对事对人都有利;三是爱人,即做一个满怀慈悲之心和爱意的人。郭沫若先生指出,“仁的含义是克己为人的一种利他行为,‘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它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3]虽然对性格各异的弟子,“仁”的偏重存在差异,但其思想总归是“爱人”,比如,樊迟问怎样去行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196,他要求弟子坚持以礼的准则约束自我,做到“慎独”,敢于承担责任和尽职尽责、勤勉奉献,真心实意为人为国尽己。可见,恭、敬、忠的指向都不是实现自我私利,而是通过自我约束,尽可能承担责任和作出奉献,具有极为明显的利他奉献精神。又如,子张问如何做到仁,他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256。所谓“恭宽信敏惠”归结起来都是“爱人”外化出来的五种不同的美德。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爱人”如何扩展为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礼”呢?按照葛兆光教授的说法,“爱人”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社会基础,“当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有了这种观念,而且已经把这种超出‘个人’而成为‘社会’的东西看成是普遍合理的‘通则’,用这种以己推人的情感外延来建立伦理的基石。”[4]孔子通过“推己及人”的推导方式架起“仁”和“礼”沟通的桥梁,他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72就是这个意思。
(二)仁和礼的序位排列:仁是礼的本原,仁先礼后
关于仁和礼孰先孰后的问题,虽然孔子对心中的制度蓝本“周礼”几近崇拜,“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32,“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2]171即便如此,“仁”和“礼”的逻辑顺序仍然是“仁”先“礼”后。“人而不仁,如礼何?”,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具备仁的品质和观念,自然也无法做到正确对待社会规范和遵循社会秩序,如此看来“仁”是作为“礼”的指导原则而存在的,对“礼”具有导向作用。在与子夏的对话中,孔子进一步把“仁”和“礼”之间的内涵与外在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他用“绘事后素”来纠正子夏“以素为绚”的“仁”与“礼”关系的理解。认为素色画纸是绘画的前提和基础,先有画纸,而后才能绘画,“仁”和“礼”的关系也正如白色画纸和绘画,只有先具备“仁”的品质,“礼”才有正确发挥的空间。那么“仁”从何而来呢,即人们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秩序的本原是什么?孔子追溯到血缘亲情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8以血缘亲情为中心层层外推形成社会规范和秩序的价值本原和依据,通过这样的排序,为孔子建立以“仁”核心的社会规范和秩序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于是他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论断,赋予“仁”在微观层面上充当个体性的人格理想和在宏观层面上充当所有社会成员的终极价值原则的双重角色。由此,在“性相近”论断的前提下,“仁”作为人性改造进而扩展为社会普遍伦理规则的活动就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仁扩散为社会改造的实践路径:克己复礼
“克己”和“复礼”分别指向孔子的两个政治理想目标,即理想人格—“仁者”和理想制度—“周礼”。“克己”是“复礼”的必要前提,“复礼”又是“克己”的目标指向,“克己复礼”是“仁”对社会成员道德外化的要求,也是孔子实现制度改造的途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2]171。孔子把当时礼崩乐坏的缘由归咎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为此,就需要“克己”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171,克制自己的言行以符合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要求,为重建、恢复和实现“周礼”做微观层面的准备。于是,作为“仁”存在的形式的“礼”,不仅成为“克己”的个体性目标,也成为普遍性泛化于所有社会成员行为的社会性标准,“礼”就从个体自我约束和修养的规范转化为公共性的行为标准。相应地,也就要求“克己”必须从私人行为社会化为集体或整体行为。为了使“克己”从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扩散为大众行为,孔子认为“克己”之士当以仁为己任,以实现“天下归仁”为天职,通过以“仁”作为教化内容使“克己”从私人行为裂变为社会集体行为,并使“仁”上升内化为社会成员的精神以支配行为进而形成自觉理念。当个体的“克己”行为和作为“克己”规范的“礼”都投射和扩散为社会性的行为和公共性的规范时,以“礼”作为核心的“周礼”这个理想的政治运行范本就会得到复活重现,并取代动荡之局。
二、以礼代法:秩序安排由外在硬性约束转向内心归服
相对于法的硬性约束,孔子更注重“礼”对社会秩序安排的作用,他认为以“礼”感化人民,可以使人辨明是非,进而从内心深处归服。通过论证“周礼”的完美,为礼消融法找到历史的依据;赋予“礼”经国家和序民人的双重功效,把“礼”变成具有公共约束力的规范;提倡教化,使“礼”的行为评价特性内化而成为自觉理念。
(一)沿承周礼:礼消融法的历史依据
孔子生活的年代,“周礼”的没落已经到了“事君尽礼,人以为馋也”[2]34的地步,社会充满“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2]38的现象,这些都与孔子“为国以礼”的要求形成极大反差。孔子认为要匡救时弊,应当从恢复和遵行周礼开始。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行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2]8,孔子论述古代先王(主要是周)治国原则的可贵之处就是坚持了“礼”在治国方面的绝对地位,“礼”成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一切行事规范,是实现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不二法门。“礼”被孔子抬升成为了治国的制度保障之后,“法”在与“礼”的关系中就处于从属的地位了,礼本位主义找到了历史依据之后,把法消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依据自己周游列国的见闻,孔子进一步论证“礼”对维系社会秩序的主导地位,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13,换言之,法也可以引导和统治人民,但只是外逼的硬性被动力量,人们不犯罪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有耻辱心而是因为有外在威慑力量的约束。相对于法的外在约束,“礼”是通过感化而使人民自觉形成犯罪的羞耻心来避免犯罪,是人们从内心对规范和秩序的自觉认同及遵循。这样,他从民心归向的形式论证“礼”消融“法”的合理性,为以后礼制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礼的双重功效:经国家和序民人
“礼”被孔子赋予“序民人”和“经国家”的双重功效,“礼”一方面成为个体社会成员的行事规范和标准,另一方面又通过裂变式的扩散社会化为社会性的公共规范。对于个体社会成员而言,“礼”是个人立足于社会和安身立命的准则,即“立于礼”,它通过“孝”和“诚”体现出来。孟懿子向孔子请教“孝”,孔子给的答案是“无违周礼”,后来又对樊迟讲具体做法,“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14。他要求把守孝和行礼有机结合起来,使孝在礼的范围内展开,又使礼通过孝表现出来;林放向孔子请教“礼之本”,答曰:“大问哉!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2]26,他要求守孝要以真诚情感贯注,礼才能有效地渗透到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成为行事规范和标准。对越“礼”行为,孔子坚决反对,这一点从他对季氏旅于泰山、八佾舞于庭和鲁君禘祭的愤怒以及对“管仲器小”的批评中可以得到体现。对于“经国家”而言,孔子认为“礼”不能被束之高阁,而应该运用到实际中,让它发挥作用,“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2]46。他认为“礼”应该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制度性保障,所谓的恭、慎、勇、直等美德都需要“礼”作为约束力才不会无过无不及,强调“礼”是上至为政者下至老百姓的个人修养都应该遵行的准则和公共规范。“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2]205,有了“礼”的约束,才能真正实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34的理想状态。
(三)礼取代法的方式:礼社会化为公共道德规范
礼从国家层面的规范转变为社会层面的普遍性行为准则,关键在于获得民众普遍的自觉认同,孔子在做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断后,礼社会化为道德观念就成为题中之义了。在整部《论语》中,“仁”“礼”“德”构成其思想的三大支柱,以“仁”为核心,辐射衍伸出“德”的条目,“德”再由“礼”外化成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形式,之后又经过“礼”作为制度的公共性将“德”的观念泛化,最后形成“德治”。这样,“德”泛化的过程也就是“礼”社会化为公共道德规范的过程,当“德”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礼”也就社会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理念,礼取法过程就完成了,礼也从国家规范转化为民众的道德规范。为实现此目标,孔子有两种重要的实践方法:一是办学,“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的惯例,也打破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二是君子自觉的道德表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关键是“君子”统治集团在民众中起着表率的作用,那么道德理念在民众之中的感化就会像风吹草一样,弥散到各个角落。当民众都受到了感化,“礼”也就成为行为的自觉理念,实现“有耻且格”。
三、为政以德:“礼”合法性存在的价值辩护和承载主体
孔子崇拜“周礼”,推崇周公“明德慎罚”和“敬德保民”的施政理念,并把商亡周兴的原因归结为失德保德。在这种逻辑之下,可以说德治论是孔子延续“周礼”政治主张下的必然产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以德育为抓手,以德导民,培养君子,为“礼”的合法性存在进行价值辩护和寻找承载主体。
(一)据于德:为政以德的理论准备阶段
在孔子的教育方针中,德育的方针和内容居于中心地位,智育、美育、体育都是为了“据于德”。曰:“行有余力,则学以文”[2]4,主张以德为本,以学为末。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88,“志于道”即以行道作为理想和志向,“据于德” 即以道德为根基,“依于仁” 即以“仁”作为思想言行的准则,“游于艺”即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些内容都反映了孔子的教育方针是以德育作为中心内容,智育、美育、体育都以实现德育为根本目标的。从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来看,孔子是支持和希望其弟子去参与政治、治理国家的,但在他看来,掌握六艺固然可以为“经世致用”提供了准备条件,然而门槛准入却更须达到“德”的修养要求。从他与孟武伯的对话中对子路、冉求、公西赤的评价足以证明“德”在经世中的核心地位,子禽和子贡的对话也可以证明孔子重视“德”在参与政事和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2]6孔子认为,了解一个国家的政事原委得失需靠高深素养去观察、分析和判断,而不是依靠打听而得,此意味着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和流露,也是了解国家政事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在古代的中国,“经世致用”的途径和知识分子的追求就是“致仕”,正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即做官以后,仍要进行学习增进道德修养,使自身德才兼备,以备在仕途上建功立业,那么就有余力做官,使“德”通过“政”来显现和转换为治国的实践。正如朱熹所评的那样:“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验其学者遗广。”[5]
(二)以德导民:“礼”获取社会支持的主渠道
孔子德治论的最有力依据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12这为后世的道德治国理念定下了基调。之所以提出“为政以德”,离不开孔子对“周礼”的推崇,他认为“周礼”是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理想政治的重要保障。在追查维系“周礼”运转的力量来源的时候,认为周实行“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施政理念是其兴盛的主要原因。现在,学术界也普遍认为孔子“为政以德”的德治论源于周公的“明德慎罚”的治国原则。“德”成为“礼”重要理论支撑,并为“礼”的合法合理进行事实和价值的辩护。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就任而已。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2]214首先指出人才的难得,进而指出周代兴德而得人才,赞叹周德对人才的巨大吸引作用,而人之所以尽其才于社会,最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的政治制度的预期与其心理预期趋同,从而信任和支持。如此,孔子修民之德的国民精神建设的治国原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修民之德的办法就是以德导民。具体做法是正身、节用爱民、清廉、取信于民,通过道德的教化,使君臣、君民之间形成以“德”观念为纽带的相互认同和信任,“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成员对当局或典则的道德效力有一种坚定的内在信任,那么,即使当局的输出或失败行动对成员造成了不断的打击,支持仍有可能继续存在”[6]。
(三)君子:“礼”合法性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孔子赋予君子承担“为政以德”的重任,通过君子的品质和使命来践行和维护“礼”的合法性,作为理想道德人格的承担者,君子的主要品质是达到消除名利的自在境界。孔子认为进德修业是持续一生的过程,他按不同的年龄阶段提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2]256,256要求言行符合身心健康的要求和合乎社会礼仪规范。又因政治统治的需要,使“礼”成为公共性,提出具有明显阶级统治色彩的等级敬畏要求,“君子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256,又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2]257,其意就是君子成德需要从多个角度看问题,才会把握全面;听取各方意见,通过比较才能反映真实情况;提高自我修养,才能做到心善面和从容自然;讲信用,实事求是认真办事;多学习请教,解惑释疑;抑制情绪冲动,行动符合道义。不难发现,以上所述是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相符的,也就是说君子的言行要符合礼的要求。君子的使命是:第一,为民作表率,引导民众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2]105,孔子主张为政者亲体力行,从亲亲之义出发践行以礼治国,为民众起着领路导航的作用,引导民众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优化社会风尚。第二,积极营造“礼”治的社会环境。“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2]124孔子坚信,君子所在之处,必定会以大道(周礼)去影响民众,使人们从不知礼变为知礼。第三,为民谋福,使民安居乐业。“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得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2]206
四、儒家何以不能成为现代政治治理的权威
可以说“儒学热”至今方兴未艾,兴起的标志事件是“七五”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再次于1992年成为“八五”的重点课题。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也传入中国的思想界,以关注微观个体日常生活世界为切入点进而改造宏观世界的儒家被看成是解决现代性进程面临困境的良方,比如强调“天人合一”解决现代性宏大叙事与微观琐碎之间的断裂问题。在此命题下,有人提出“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21世纪儒学必将在全世界复兴”、儒学“是我们走向21世纪的重要的精神依据之一”、儒学“是现代化文明的医师”这样的论断。儒家参与并主导现代政治治理过程的呼声也很快就出现了,其中极具代表的就是《政治新儒学》提出的王道政治构想,其主张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来重建制度,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
问题的关键在于,儒家是否有主导现代政治治理过程的资格?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来回答。第一,政治治理的内核把握发生了变化,由被动接受天的感应变为积极主动把握执政规律。“仁—礼—德”三位一体的思想构建逻辑对应的实践逻辑是天道、王道、王权三者合一,而天道、王道、王权则构成王道政治的基本构架。对于现代政治治理而言,所谓的道已经从过去由天赋予的神秘感变成自觉的对执政规律的积极把握和运用,王权也由人民权利所代替。第二,政治治理的原则发生了变化,由德治主导变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自孔子提出德政思想之后,孟子进一步发挥将之移植到施政原则上,明确提出“仁政”学说,开启了政治伦理化的理论先河,后经董仲舒把政治和伦理互动过程实质化,德治成为古代政治治理的主导。现代政治治理除了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之外,还坚持法作为规范和秩序的底线,形成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道路。第三,政治治理的权力运用发生了变化,由依靠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变为自上而下的监察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由随意性变为制度和程序的约束。对权力的运用,儒家强调的是自律自爱,但却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造成了“内圣外王”的理论要求和“苛政猛于虎”的现实权力滥用之间的脱节。在现代政治治理过程中,权力是在法律、制度、纪律的范围内运用和试行的,“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要强化公开,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7]
“儒学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自信的一种实践,但无论如何需要本着批判反思的态度进行审视。儒家学说的闪光点自不必多说,然而儒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绝对的权威,更应该思考的是它如何参与到现代政治治理的过程中来,“儒学已经不可能再回到“经”的位置,政治、社会、文化已全面变化,将来中国会成为一个更加现代的国家,儒学更重要的问题是怎样作为一种经典思想资源参与这一进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