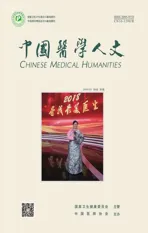医生,机长让我问您,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
2019-07-03甄理达
文/甄理达
2018年5月,甄理达医生和太太去华盛顿参加儿子和儿媳的医学院毕业典礼,令人激动。没想到在返家途中的飞机上,亲身经历了另一场激动!这是甄医生第二次在旅途中救人。万米高空,命悬一线,来听甄医生讲讲这个真实的故事。
突发状况
2018年5月20日,我和太太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尔的摩返回洛杉矶,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黑人乘客。
起飞后不久,我不经意地看了那个乘客一眼,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怪,脸部僵硬,嘴半张着。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的双眼开始向上翻白,头垂了下来,身子倒向一边。
医生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个乘客出事了!
我立刻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反应;伸手触摸颈动脉,没有脉搏!在他坐着的情况下,我立刻给他胸前做了几个狠狠的按压。但是,他仍然没有反应。

我立刻大声呼叫空姐,在她们的帮助下费劲地解开病人的安全带,连拉带扯地把他放在窄小的过道上。飞机上空间狭小,只能容纳一个人躺下,我就只好骑在他身上做心肺复苏(CPR)。
当时我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抢救成功,肋骨骨折的代价是相对较小的;万一抢救不成,骨折与否也没有任何意义。
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好人保护法”,不管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被家属起诉(Good Samaritan Laws,《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
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当时就集中精力抢救病人。
空姐们也非常有秩序,按照程序搬来氧气筒、面罩和急救箱。一些乘客也都站起来帮忙。飞机的震动从地板直接传到病人的头颅,使得测量脉搏变得很艰难。我每次测量都不是很确定病人是否有脉搏。但因为病人腕部的脉搏是触摸不到的,所以我就继续做了心肺复苏。
做了几组心肺复苏后,病人有反应了,他的手开始移动;慢慢地,他可以说话了。我紧紧地握着病人的手,一边安慰他,一边询问他的情况。
他的妻子说,病人今年64岁,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长。平时很健康,只是胆固醇高,目前正在服药治疗。根据这个情况,我立刻跟其他乘客要了3片81毫克的阿斯匹林,让病人咀嚼之后咽下。
时间似乎走得很慢,但病人的情况在逐渐恢复。在病人没有了胸痛和气短的症状之后,空姐和一些乘客帮助我把他扶到座椅上躺下。
看到病人此时情况比较稳定,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才感觉到背上凉凉的,想必背心已经湿透了。
压力山大
这时,空姐的一句话,让我又马上紧张起来。
“医生,机长让我问你,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
对于病人来说,送到急诊室接受进一步救治,自然是最好的。
空姐问我:“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 她强调说:“你是医生,如果你觉得病人有生命危险,你就可以命令这个飞机立刻降落。”
我?命令飞机紧急迫降?
此时此刻,在这万米高空,我从一个普通乘客,一下子变成这么重要的决策人物,肩上瞬间觉得沉甸甸的,“压力山大”。
此时飞机正在接近芝加哥,我们可以在那里降落,直接把病人送到邻近医院。我知道对于全体乘客来说,紧急迫降就意味着要耽误行程,所有转机都会受到影响;飞机也许要在空中丢弃一部分航空燃油,这对航空公司来讲也是很大的损失。可如果不降落,万一这个病人之后有生命危险怎么办?看了看飞机上满满的乘客,又看了看脸色苍白的病人:一边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不便和经济上的损失,另一边则是病人的安危,甚至可能是一条人命。
我左右为难。
按照医生的思维,病人应该马上接受下一步救治,因为我根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病人意识不清、没有脉搏。权衡之后,我决定实话实说。我跟空姐说,我所知道的病人信息有限,不能确诊是什么疾病。按照医生的常规思路,他是应该马上送到医院救治的。但是,这个病人现在的情况还算平稳,血压与脉搏都在正常范围,所以无法确认是否应该立即降落。
空姐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机长。机长开始跟地面的指挥塔电话联络,请示情况。
继续飞行
过了一会,空姐让我到飞机的前面,用无线电跟地面的空中紧急医疗中心里的医生对话。我跟对方汇报了情况后,对方作出如下指示:
“建立静脉通道,为病人提供食物与饮料,每半小时测一次脉搏和血压,继续飞行!”
空中的无线电对话,声音嘈杂。我听完之后,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建议,确保我准确理解了对方的意图。
谢天谢地,不必做这个重大决定了!擦擦额头的汗珠,我如释重负。
此时,病人已经恢复坐位。我从飞机上的紧急救护包里找出了静脉输液针头与输液管。
新问题
然而,新的问题来了:我不会插输液管啊!
虽然多年前临床实习时做过,但是我对插入输液管的操作非常不熟悉。平时工作中都是护士们做,他们做得又快又好,根本不需要我插手。
更糟的是,这个病人说他的静脉超级难找。我无比尴尬地跟空姐说明了情况。她说不要紧,立刻从前排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我给护士当助手,她很快就麻利地完成了静脉插管。
有了静脉通道,有了生理盐水,但飞机上没有挂瓶子的地方。这个就是小问题了。一个空姐跑到头等舱,找来了一个衣架。我用衣架的挂钩勾住了盐水袋,然后把衣架塞入行李架内,一个简易飞行救护室就成了。看着透明的液体一滴滴进入病人体内,再一次,我如释重负。

平安降落

一共5个小时的飞行,大概有4个多小时都在忙着救治这个病人。
终于到了洛杉矶机场,机长广播说让病人和Dr.Zhen先下飞机,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机舱打开了,救护人员鱼贯而入,把病人带下了飞机。所有的旅客都待在座位上,没有一个站起来急着下飞机。我们从机舱内走过的时候,乘客们都在鼓掌,仿佛是在欢送一个英雄。
我也莫名地跟着一起感动了:5个小时的飞行,那些能帮忙的旅客都过来帮忙,帮不上忙的旅客都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过来看热闹,甚至在我们讨论是否需要中途紧急迫降时都没有任何的异议。仿佛在说:你们决定吧!
如果没有这么多善良的乘客帮忙,没有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空姐们的协助,没有护士的帮助,我很难想象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会有什么作用。
我想,正是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诚把我们凝聚到一块。一个叫Debra的空姐说她家在凤凰城,她老公是个牛仔,非常会做美国西部菜,请我有空到她家做客,仿佛大家是相识许久的老朋友。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病人的太太打电话过来说,病人已经出院,并且预约好了心脏科医生。
感谢各位热情洋溢的留言,很暖心!我相信,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也一定都会伸手援助。人性的救助超出了国界、种族、语言、性别、年龄与职业的界限!
后记


(来源:“同语轩”微信公众号 图片:林小慧)
点 评
我非常热心地向同道们推荐甄理达医生的短文。不仅因为甄医生是我大学同窗好友,更重要的是我被他还保留着当初直率、坦诚、执着个性的故事所感动。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就前往美国深造,经过多年的努力,他考取了美国的执业医师。他每次回国,我们常会有一些学术和行业的交流,了解到他在美国取得的成绩。这次他在美国航班上救人之举,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也为他获得的英雄般的礼遇感到骄傲。便把他的故事发到多个朋友圈,获得一致的赞誉和好评。欣喜之后,不由地产生一种思虑,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国内,出现在我或国内同行身边,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行们都会表现出一种职业的责任感,救死扶伤的本能冲动,我们都会做得很好。但是在飞机上,在很多公共场合,社会机构和公众对此举的认同感和宽容度又会怎样?机长会不会也征求我们的意见,是继续飞,还是停下来?同机的乘客会不会认同你的意见,下机时会不会像对待英雄般,鼓掌向你道别?我们太需要这种社会环境,也需要一部保护见义勇为、保护肯于救人于危难的“好人法”。作为医生我们拥有在任何情况下救死扶伤的责任和义务,也应该带动全社会树立救人于生死之际的风尚,这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通过国外同行的一个小故事,应唤起我们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沈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