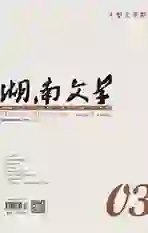龙头铺的源远流长
2019-04-21倪锐
倪锐
龙头铺取名意义深远,相传过去此地一直干旱,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南海龙王之子同情民间疾苦,于是降雨救灾,从此数千年来这里雨水充沛,老百姓丰衣足食。为纪念南海龙王之子,老百姓将此地命名为“龙头”。
早在明清时期,当地有一条古官道,从醴陵经湘潭至长沙共有十八铺,龙头为其中一铺,“龙头铺”由此得名。
问问龙头铺的老人,原来,源远流长的龙头铺,曾有幽深清新的麻石街、雄伟高大的教堂、远近闻名的唱戏亭以及庄严肃穆的杨家祠堂,古色古香,回忆绵长。
麻石街和麻塘
明清时期,龙头铺就有一段用麻石铺成的小街,長两百米。麻石成条状,面有一条条线状的凹痕,按横向放置,铺在了龙头铺老街的古巷中。这是一条盐、茶、米的商贩马车必经之道,还有邮差快马。两边茶楼亭榭,中间麻石绵长,热闹时车水马龙,安静时古巷幽深。
现年七十八岁的龙头铺唐升高爷爷,回忆起麻石街,全是童年的快乐,他说,他就是在麻石街长大的。麻石街不仅是一条驿道,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集市。每到赶集的日子,龙头铺周边的农户和远近的客商,都会把商品摆到麻石街,前后绵延几百米,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打闹的孩子,寻觅的买主,吆喝的卖主,固定的摊贩,移动的商家,鸡飞狗跳,鱼跃猪嚎,整个麻石街热闹非凡。但后来抓五风不准搞小自由,派民兵值守,收缴物品,龙头铺成了重点打击对象,躲了段时间后,集市迁移到了林学院。
小时候一到逢一逢六的日子,就听姑姑婶婶她们喊“到龙头铺赶场去咯”(龙头铺人叫赶集为赶场)实则是去赶林学院的场,只因这个场的起源地是龙头铺,而成了口头禅。
麻石街,是龙头铺一个古老的存在,也是老龙头铺人的集体回忆。
因麻石有了麻石街,因麻石还有一口麻塘和一个麻塘巷子。麻塘就位于麻石街的入口处,塘水清澈见底,塘边垂柳依依,过往麻石街的行人商贩,累了渴了,都去麻塘掬一捧麻塘水,清凉解渴,也可以洗一把满是汗水的脸,或给有几分疲惫的马匹饮饱喝足,继续赶路。麻塘水也是附近农田的灌溉水源,塘下有一个塘眼,用一个塞子塞住,农田需要水时,农民就可以抽出塞子,把水引入农田。所以,麻塘水是活的。
那个叫麻塘巷子的地方,不知何故,离麻塘较远,在现如今的龙头铺交警队对面。问了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巷子和麻塘有什么渊源。
教堂和唱戏亭
麻石街处有一所大教堂,可同时容纳五六百人。教堂顶端一大两小细细的尖顶直冲云霄,塔尖立着十字架。相对于周边矮小的平房,教堂就那么高大雄伟有气势地立在那里。教堂有一座钟,每到集会时,就会敲响,响声浑厚悠远,方圆一公里都能听到。教堂的窗户很大,挂着更大的暗红色窗帘,内有一排排长条靠背椅,正上方是讲台。
到了五十年代,教堂在龙头铺就很低调了,在里面开过几次大会以后,就弃之不用了。不久,里面被洗劫一空,只剩一个偌大的空架子,除了一批批孩童在此玩耍,早不见任何教会的人员出入。六十年代末,教堂被新建的民居取代,消失得无影无踪。
教堂旁边有个亭子,闲时,过往客商可在亭子处歇脚喝茶,忙时,从正月初五开始开锣唱大戏,一直延续到正月二十,远近看戏的人山人海。
亭子不算大,就一个两百平米左右的舞台面积,四个立柱,一个雕梁画栋的亭顶。左右立柱上有联曰“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台下是一大片的宽阔草地供看戏的人或坐或站。
每年初五,龙头铺方圆几十里的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涌来,或抱小孩,或扶老人,或背长凳,或扛靠背椅,走路的,骑车的,甚至还有推轮椅的,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戏班子的人马早在初四就已安营扎寨,服装道具舞台一应俱全。初五大清早,演员们就把那些红的绿的粉的油彩往脸上描画。先是一阵正宗的紧锣密鼓,接着“当”的一声锣响,大戏便开场了。
都说“唱戏的癫子,看戏的肥子”,这话一点不假,台上唱戏的一旦开腔,嬉笑怒骂泪流满面。台下的一众看客,黑压压一片,前面的坐,后面的站,从爬在树上的男孩到骑在肩头的女娃,再至坐轮椅的老人,无一不被台上的一举一动牵着目光走。搞笑时捧腹大笑,悲戚时抽抽搭搭,气起来恨不得上台揍坏人一顿。
一场戏结束,就是厕所最俏的时间,也是小商贩们生意最好的时间。卖气球的,卖冰糖葫芦的,卖糖果瓜子的,一停戏就吆喝。也有好奇的,喜欢跑到后台去瞧瞧。刀枪棍棒十八般武器,长溜的大胡子,五颜六色的凤冠霞帔,以及吹拉弹敲的各式乐器,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
龙头铺麻石街的唱戏亭,正月连唱十五天,半个月的锣鼓喧天,半个月的人头攒动,半个月的车水马龙,半个月的周边茶楼饭庄生意火爆。直至正月二十,戏班子卸妆上车,人们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杨家祠堂和槠树
杨家祠堂在麻塘对面,由一座四合小院组成,据说,这里原来住着杨姓人家,一九五八年土地改革,就分给了唐姓和余姓两大户。在麻石街、麻塘、教堂和唱戏亭全部都无影无踪的今天,杨家祠堂摇摇欲坠、千疮百孔地残存着。
最初的杨家祠堂,坐北朝南,四面相拥,青砖灰瓦红梁,有两堂屋两厢房两侧房,正中间是一口天井。原以为天井就是水井,经了解,天井的作用是汇聚祠堂四面的屋檐水,然后经下水道,一齐流向下方的龙母河。
今天的杨家祠堂一半是后来重建的民居,真正遗留下的只有三间。中间一间全然没了屋顶,大门也没有了,主人在屋里放了一些废旧轮胎等杂物,杂草从屋外长到了屋内,后山的树枝早已将头从露天屋顶探了进来。左边进去有两间,外面的一间外墙歪歪斜斜还剩一半,几根檩条凌乱地搭在墙上,瓦片檩条上几片,墙头上几片,地上屋里各几片。屋里几台废弃的摩托车,墙壁用屋顶掉落的另几根檩条支撑,随时有垮塌的危险。
我不敢久留,但被墙上的一块青石板吸引住了。这是一块长约一米,宽约半米的长方形青石板,上面清晰地记载着光绪七年辛巳岁三月重建杨家祠堂时的捐钱捐物明细。只是不知何故,右下角有一块正方形的凹处。由此追溯,今天的杨家祠堂,建于光绪七年三月。
右边一间进去的小门已被主人封住,只能从中间的里面进去,因为实在太危险,还是没敢贸然闯进。这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墙面上的一个圆形大洞,这个洞不是因为年久失修,而是人为造成的。龙头铺人有一个土单方,当夏秋干燥季节或吃了上火的东西,火毒太重时,就用一种叫尘壁土的泥土来泡水喝,清热下火特别有效。而尘壁土就取自年代久远的老土房子的墙壁。杨家祠堂修建年代早,又是正宗的土壁,所以,龙头铺远远近近的人,火毒重了,都会来杨家祠堂讨一坨尘壁土。三伏天吃伏鸡伏狗时,来讨“尘壁土”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久而久之,墙壁就被大家挖了一个大洞。
杨家祠堂的后山有一棵槠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粗壮的主干一个人都抱不了,将近三米才一分为二变两个枝干,接着往上一个劲地分枝长叶,最后形成一把巨大的绿色大伞。槠树在灾荒年代曾立下过汗马功劳。槠树结槠粒子,槠粒子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吃,还可以做槠豆腐。五十年代,槠树下是孩子们的乐园;七十年代,槠树已不受青睐,因为这棵槠树结出来的槠粒子有苦味;九十年代,附近的村民已不许孩子们独自上山玩了。
看到我在拍槠树照片,八十多岁的唐四娭毑特意走过来告诉我,“株洲,又名槠洲,就是因为这棵一百多岁的槠树,这是株洲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棵树了。”
据记载,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一代大儒朱熹在诗中写道:“泥行复几程,今夕宿槠洲。”这是“槠洲”名字最早的文字记载。株洲因长满槠树的湘江小岛而得名。槠洲亦写作株洲,南宋后期,株洲逐渐流传开来。
虽然无从考证“株洲”的得名来自这棵一百多岁的槠树,但龙头铺杨家祠堂后山的槠树,正顽强而孤独地茂盛着。
街 头
过去的麻石街,现在叫龙头铺老街,这条承载了几代人的梦想的古老街道,繁华的是过去,今日已在陆续拆除,不久即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
严格地说,龙头铺老街应从做豆腐的那家算起,一直延伸到太平桥的桥头,总长不过三百米。现在还残存的有面貌全非的街头、内涵不变的古井、偃旗息鼓的粮店、改商变民的沙金狗肉店、仅剩招牌的酱厂,以及野草摇曳已成废墟的剪子张理发店和几家采用现代技术做传统手艺的小店。
龙头铺老街的豆腐,起先是由一个外地人租了老街头户人家的柴房做生意。因外地人勤劳肯干,买的豆子黄得均匀颗颗饱满,煮豆子全用的山上砍来的柴火,真材实料,他们家的豆腐炸出来硬是比别家的外更酥里更嫩,所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只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一夜之间回了老家。那家主人常年耳濡目染,自然也学会了做豆腐,于是自己开炉也干起了豆腐营生。可能关键的独门绝技没学到位,那家男主人推着一土车木柴,女主人在前头甩着一头长发,拉着“纤绳”走了不到两年的光景,老街豆腐店黯然收场。
一方唱罢一方登场,后又一“吊酒”(当地人叫“酿酒”为“吊酒”,原因是真正的土法酿酒还真是一滴一滴像吊水一样慢慢吊出来)的租了那间柴房,并迅速崛起,方圆几十里的都来龙头铺老街“打酒”(当地人叫“买酒”为“打酒”)。这个吊酒的师傅也是个实在人,买来上好的早稻谷,浸泡、煮熟、摊凉、用柴火蒸,每道工序一丝不苟,直到一滴一滴地“吊”出香飘四溢的酒来。打酒都是自带瓶子或酒壶,老板拿一个细长细长的木把小筒伸进酒缸,把酒打上来,瓶或壶上放一个漏斗,酒顺漏斗而下,钱按瓶算,不论斤称。老板大方,每瓶都会打得满满的,少一点他都会把小筒伸进酒缸,再舀一点补上。凡来打酒的喝酒人士,无论男女,都可以免费品尝一小盏白酒,经常有好酒之人红着脸从那咂巴着嘴出来。龙头铺周边人家如要办婚丧喜宴需大量谷酒时,都是备好谷子和柴火,把吊酒师傅请到家里来吊酒,钱按桌算,就是蒸一桌酒多少钱。也许物极必反,也许久盛必衰,后来,不知为何,那家主人又接过了吊酒的行当,不过热火朝天不多久,又偃旗息鼓了。原因大概是时代变了,商场超市琳琅满目包装奢华的酒类,让人们逐渐淡忘了那悠长小巷远远飘来的酒香。
现在,里面只偶尔传出几段花鼓戏的曲调,那是主人在家吊嗓子呢。
古 井
再往里走一点就是老邮电局了,说老邮电局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四十岁以上的倒还是清晰地记得当年老街那栋点缀着绿色的房子。门口两边立着两个绿色的大邮筒,经常会停着两三辆绿色自行车,自行车上还会有标志性的绿色邮袋挂着,里面装着书报和信件。老邮电局的红火光景延续了一个时代,信来信往的日子,在邮电局上班可牛气了,穿着绿制服在老街上走一趟,那感觉硬是腰板子挺得直些。再說,在这个乡下人聚居的地方,邮局里的可都是人人羡慕的吃皇粮的主啊。
不知道老邮电局的人多,但不知道龙头铺老街古井的少。老邮电局原来是个四合院,院子正中间就是古井,这口井到底多少年岁,已无从考证。因老邮电局背靠大山,古井常年清澈,三年干旱,远远近近的井都干涸了,唯有老邮电局的古井依然保持水平线,乡邻们都来古井取水,也不见那水平线下降。那时的取水很简单,一桶一绳,抓着绳,把桶往古井一扔,一摆,即桶满,再往上一提,就取好水了。
邮电局搬走后,没半点冷场,就搬进了一个更具文化气息的“教育办”。教育办统管全乡十几所村小学和一所中学。人事任命、工资发放、培训学习,大事小情,全部由教育办主任说了算。主任在当年的龙头铺那叫一个“一呼百应”,人人见了点头哈腰。平时的教育办人来人往,节假日更是门庭若市。我在乡小学任代课教师时,去教育办开会,也会去古井旁瞧瞧。那时的古井已配上了摇泵,古井的水摇上来,夏天对着脚冲,清凉舒爽,冬天洗下手,水是温的,更多的人喜欢摇一泵水上来,双手虔诚地捧住,然后畅饮,两个字——清甜。
后来,教育办撤了,中小学全部由教育局直接管理,那里的房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卖给了一个当地人,因了那口福井,那家倒也人丁兴旺,其乐融融。
特意去找了下古井,在全民用自来水的时代,那家人仍将古井保留完好,一日三餐饮用和生活用水,全部来自古井,不过新配上了电泵抽水。
粮 店
老邮电局过去就是粮店了,占地七八亩的粮店,呈现一片荒凉。看我到处拍照,守门人倒是十分热心地帮我打开了大门。零星的几张门上写着“买米请拨XXXXXX”,还有写了几十年的一个大大的“糠”字。以前开票收钱的那个门口,头顶都空了,瓦也没了,只有墙壁上的一块烂黑板,在向人昭示,这里曾经是记录买米的地方。还有那个厚重的铁门上方挂了个“原料库”的牌子,显示这里曾经放过原料。几乎每张门的上方都有一个“严禁烟火”的小牌牌,凑近门缝,里面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
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秋收后,父亲总会用麻袋把谷子装好,一袋一袋地用土车运到粮店,十几里路,来回好几趟,山路又高又陡,还要母亲拿根绳子在前面使劲扯,这叫“送粮”。粮食送到后经过检查,有扁谷不要,没晒干不要,再过秤,还要自己背到粮仓码好,才算结束。每到送粮季,各家各户从四乡八邻推着独轮土车而来,排队等候过秤,那车队足足排满整个龙头铺老街,而且彻夜不眠不息。因为我家人多田多,送的粮也要多,有一次,父母回家运第二趟粮食去了,要我在粮店守着粮食,我硬是眼睛一眯伴着满鼻的谷香就睡着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才被周围那“吱呀吱呀”的土车声吵醒,一看,还是那么多的土车排在那里等候。
粮站兴旺了很多年,即使后来私人老板承包了,也发了大财。就连在粮站开票的那个女孩,据说当年因了那份人人称羡的好工作而眼光高,拒绝了很多的追求者。
我在粮站里里外外足足走了半小时,居然没找到一粒粮食的痕迹,倒是被两个不速之客吓了一跳,一个是来此地找粮食的老鼠,一个是追老鼠的狗。其实,粮站也早已是名存实亡了。
沙金狗肉店
老邮电局的斜对面,是“沙金狗肉店”。我走过去时,他们一家五口正在乐呵呵地吃饭。说起当年沙金狗肉店的名号,株洲四五十岁上下的,恐怕无人不晓。沙金狗肉店的老板就叫沙金,那是龙头铺的一把勺,做出来的狗肉,颜色鲜艳,辣得劲道,香沁心脾,吃了还想吃。别的老板辛辛苦苦赚几年,沙金三天就赚回来了。
沙金平时打打小牌,唱唱小曲,店里由伙计打理。他自己出手,仅做三伏。每到盛夏三伏天,他家七大姑八大姨全部上阵帮忙,大蒜籽、辣椒、桂皮、八角,全部用货车运。九十年代开小车来吃沙金狗肉的排队从龙头铺老街排到新街,吃客还没起身,旁边就好多排队等座位的,天气炎热,那时又没空调,狗肉又燥,经常出现因抢座位而打架的。远近的大小老板更是巴结着沙金,希望到了三伏帮他们留个座位。龙头铺街上的人家是不用去争抢座位的,到了三伏,大家一早就拿着钱排好队,轮番从沙金家一脸盆一脸盆地往家端狗肉。
后来,分路口的一个老板,出巨资买下沙金的招牌,重金聘请沙金去分路口掌勺狗肉,分路口的“沙金狗肉”又红火了很多年。
沙金回到龙头铺,仍有人不断请他出山。有一次有幸尝到沙金的手艺,那色,那香,那味,还真是名不虚传。
沙金老了,掌勺不动了,儿子有更好的发展,不愿继承他这辛苦活,所以,现在龙头铺老街的沙金狗肉店,也就仅剩招牌了。
酱 厂
沙金狗肉店的旁边拆了一大片,只留下残砖断瓦。再往里走,赫然立着一栋大土屋,高高的,有点突兀。这就是当年的酱厂。酱厂出产酱油,也腌制榨菜。在豆腐和肉要凭票购买的年代,打酱油也要排队,有时还要找关系走后门。大大的酱油缸摆满了酱厂,每个酱油缸的上面都有一坨用布包的东西重重地压在缸口上。打酱油开始也像打酒一样,从酱缸中吊上来,只是总感觉酱油的味道远不如酒来得香。
小时候有件事一直没弄明白,就是老师经常说班上一个成绩差的女生“望哒酱油舔哒恰得”。回家问母亲,母亲骂道:“酱油舔哒恰得不咯!”平时在家不敢真试酱油味,害怕没煮熟的酱油有毒。那次趁去龙头铺老街酱厂打酱油之机,麻起胆子偷偷地舔了一点瓶口溢出来的酱油,有丝丝的豆豉味,也有一点咸,没觉得酱油舔哒恰不得啊。
榨菜起先是大坨大坨的,咸得很,后来又添加了切成片和丝的,再后来添置了机器,也有了塑料袋包装的。上学时,榨菜带饭,我起码带了六年,很多年后看见榨菜我还浑身发毛。
酱厂两张斑驳的大门上方,依稀还可以辨认出“株洲市龙头铺供销社酱厂”和“门市部”几个字,还有一张门上挂了一块锈浊斑斑的铁牌,上书“龙头铺供销社生资门市部”,这几个都是龙头铺老街留存最久远的字迹了。
时至今日,龙头铺酱厂,人烟早已全无。
剪子張
酱厂右边又是一大片拆迁的痕迹,在这堆废墟上,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剪子张”的家。剪子张就姓张,长得眉清目秀,一肚子墨水,加之手艺了得,远远近近的好多姑娘都对他中意。剪子张挑了本村的一个,高大漂亮,又聪慧能干,生得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里里外外操持得整整洁洁。剪子张得名于手头的一把剃头剪刀,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都慕名而来。以前,总看见村里的“术爹”背着一个剃头挑子走村串巷地招揽生意,剪子张就不用,都是人家找上门来。从没有招牌到门上自己用手写了三个字“剃头铺”,再到请人写的三个字“理发店”,他的门前就没冷落过。小时候,母亲也会趁赶集的日子带我一起去剪子张的店里剪头发。每次去剪头发都要等好久,“剪子张”剪发倒是利索,只是一屋子排队等候的人太多。只见剪子张一把剪刀上下翻飞,头发顷刻间飞絮样落满地,稍微修剪一下,就一把刷子边刷边吹,一掀披在身上的披斗,即可起身,再把剃刀在那黑漆漆的剃刀布上“嚓嚓”两下,就“下一个”。剪子张剪发利落,口才也不一般,为了打发等候的客人那无聊的时光,他还会经常边剪头发边给大家讲笑话,往往在一屋子人哄堂大笑之际,一个整洁精神的寸头又在他的手下诞生。他那几十年总不见老的老婆则在屋里屋外端茶倒水,洗头发,配合得天衣无缝。
剪子张享晚辈的福,早几年就搬去了城里,拆迁后就没来过龙头铺了。面对那几根长长的在残砖断瓦间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颇有荒草萋萋的苍凉。
小 店
龙头铺老街本来有几家小的老店,古老得可以申遗了,一个是弹棉花的店,以前是拿个弓箭一样的东西在那弹,然后拿个磨盘在上面反复压,最后拿线一条条地牵。棉花是实实在在的土棉花,龙头铺人娶媳妇嫁女都要来老街弹几床棉花被,那种手工弹出来的棉被经久耐用,柔软暖和。也有自己买棉花,请弹棉花的师傅上门来弹的,主要是自己买的好棉花,如果放在店里,担心弹棉花的老板偷梁换柱。只是现在都变成用机器弹棉花了,而且丝棉的、羽绒的、毛线的,甚至蚕丝的,不一而足。
还有一家修鞋兼配钥匙的店。修鞋最开始是一块垫布,一个钻子,一套针线。鞋子垫在膝盖的垫布上,钻子钻个孔,针一钻,线一扯。如果是套鞋(雨鞋),就一瓶胶水,先把烂了一个洞的地方用陶锉磨薄,再找出一块颜色相近的车胎皮,剪好,磨平,最后用胶水一粘即可。现在,鞋子烂了也就丢了,顶多钉个鞋跟什么的。修鞋店也顺应时代潮流,缝个面,钉个底,都有机械化,擦鞋也不要擦鞋布了,直接拿液体鞋油一抹,又油又亮。
配钥匙是一个细致活,要把原钥匙的纹路用锉刀锉得一模一样,锉呀、打呀、磨呀,对着灯光照了又照,拿着原钥匙比了又比,少不了一个时辰,拿回家还不一定打得门开。现在好了,放在电动机上“哧溜”一声就配好了,保准不要返工。
只可惜这几家现在都是在老旧的房子里进行着现代化的操作。
供销合作社
决定去找找龙头铺的记忆。绕过一排门面,经过龙头铺社区居委会,一栋摇摇欲坠的红砖房呈现眼前。
这栋房子应该是龙头铺最早的红砖房了,在龙头铺汽车站的马路对面,当周边还是池塘、农田和远远近近的几栋土砖房时,这栋红砖房就建在了当年的公社现在的镇政府对面。
一路走过,门上,墙壁上,满目都是“危房,请勿靠近”的暗红大字。门前凌乱停放的民工摩托车、河沙、卵石,还有水缸和竹跳板,说明旁边在建房子。这栋昔日风光无限的房子在寒风中岌岌可危,大门正上方“龙头铺供销合作社”八个大字已斑驳得只剩下“合作社”了。左右两边的对联辨认半天也只找出个“八”字,大概是“八方来客”吧。在一堆把窗子都淹没了的砖头上方,原本的一个铁架子倒在墙头,边上飘着红色烂绸布的上方,断断续续可以认出“发展经济,保证供销”八个大字。透过连一块碎玻璃都没有的四开大窗户往里瞧,除了墙壁就是垃圾,记忆中,这里曾是儿时最向往的地方,也是龙头铺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唯一商场。
还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到镇上看望爷爷奶奶,来爷爷家,必去的就是龙头铺供销社。供销社里的商品可多了,几十个家门口的小商店都抵不过。正中间那一排是卖吃的,瓜子、花生、葵花子、小花片、猫屎筒……更可喜的是柜台里一年四季都有红苹果、黄梨子、紫葡萄和粉桃子。多少次我扒在柜台边望着那鲜艳欲滴的水果不肯走,若干年后才知道,那些水果都是塑料的。
右边过去是卖文具和生活用品的,文具里的气球最为吸引人,供销社里的营业员,会把小气球做成苹果或葡萄的样子挂在那里,当然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好看而不是吸引顾客。他们不用招揽,生意自然来。七八十年代明显的优越感,让供销社里上班的城里人有一种傲气,他们是看不起我们这些满腿肚子泥巴的乡下人的。
儿时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唯独气球是个例外,最为奢侈,要拿钱买。母亲一般只每人买一个。我们姐弟几个一个比一个胆子大,气球都吹得鼓鼓的了,还要在气球屁股处捏一捏,如果是软的,就再鼓几口气,直到按上去硬硬的才罢休。如果力度没把握得好,一口气吹炸了气球,那心情,不是用失落可以形容的。气球炸了我们可舍不得丢掉,可以把炸掉的洞洞扎起来,继续吹。如果气球玩烂了,哪怕只剩点破碎的气球皮,我们也可以放到嘴里唆泡泡,泡泡唆了一个又一个,然后拧到一起,还可以玩。
扯远了。供销社左手边进去是卖建材的,螺丝、钉子、铁丝、插座、电线等。再往后就是单车缝纫机等大件物品。当年的龙头铺人嫁女三大件,单车、缝纫机、手表,十之八九出自这大气的供销社。
再往里是扯布和床上用品的柜台,我家的被套、床单和枕巾等都曾在这里买过。扯布的柜台生意较好,一捆捆五颜六色的布料,棉的、麻的、绸的,还有那风靡一时的的确良。附近乡邻都会来这里扯布回家请裁缝做衣服。售货员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一量一剪一撕即成交。龙头铺人叫撕为扯,叫买布也就为扯布了。
供销合作社的后面,两扇锈铁大门,一个杂草高出屋顶的院子,地面腐叶叠了一层又一层。瓦片早已不知去向,但还是可以看到屋顶一根根大木头搭成的檩条,墙头比蜘蛛网还密的电线。一棵大树直接从屋里长到了屋顶,枝叶直伸墙外和天空。
收购门市部
供销社旁边的红砖房稍新一些,但年代仅次于供销社,暂还没打上“危房”的烙印。“收购门市部”五个大字清晰可见,门上方的左边四开大窗的玻璃,以及右边小空中窗的玻璃均已破碎,依稀可辨门的颜色是朱红。收购门市部也是当年吃公粮的肥差部门。
十岁左右的夏天,我为收购门市部作出过很大的贡献。那时这里收购破铜烂铁废纸啤酒瓶包括牙膏皮子烂鞋底等,还收购“桃油”,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桃胶。一到夏天放暑假,忙完双抢,我就和邻居女孩茂芝一起,挎着一个小编织篮,去周边走村串巷捡桃油。说“捡”,其实是从桃树上把黏在树干上的桃油掰下来。我们一个山坡一个山坡地寻找,只要见到桃树,就飞奔过去。有的桃树桃油很少,而且又干又黑,捡起来手掰得生疼。有的桃树桃油很多,一朵朵一簇簇像花儿一样开放在粗大的桃树干上。我们两人经常抢桃油,但從不吵架,每天相约一起去捡,一起回家。桃油再生能力强,这次捡了,过几天去又可以捡到,尤其是下过雨之后长得较多。天气热,桃树上又有毛毛,还要不停地寻找,其实捡桃油是个辛苦活。
记得有一次,我们捡桃油到了一个无人的荒山,那里居然出现了一棵桃树,稀奇的是,桃树上居然挂了一树毛桃。摘下一个在衣服上蹭两下,咬一口,酸甜酸甜,都脱核了。提着满满一篮子毛桃回家,那成了我和茂芝最开心的一次捡桃油之行。
桃油捡回家晒干后,妈妈就会趁赶集的日子帮我挑到这个收购门市部来,论斤收购,价格很低,但只要能赚到钱,于我已是十分幸福的事了。
收购门市部是一排民房,正在我东张西望时,左边一个大红铁门里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的老板模样的人,看来,这里还在经营中。
糖粒子厂
供销社红火了N年以后,仿佛一夜之间就散了。有聪明的职工看准商机,承包了供销社的批发部,也就是龙头铺的黄金码头,以前的老汽车站,现在的卫民综合批发部。因批发部早已装修,后面又建了豪华别墅,人家的发财史暂且不提。沿卫民综合批发部右边有一条画了白色标线的水泥路往上走,一边是大树从裂缝中长出的围墙,另一边是晒着民工裤衩的平房。
糖粒子厂就在这一栋。一间熬糖制糖,分门别类,牛轧的、水果的、牛奶的、酥心的,一间机器压糖,压出来的形状又分方圆长短或球形。另一大间为包装车间,包装为纯手工,一大群老的小的,全部是女的,围坐在一个大长桌子的周围包糖。糖纸又分为纸的或塑料的,花花绿绿一包包。
姐姐十四岁就在糖粒子厂包糖,眼疾手快是她的特色,吃苦耐劳是她的本性。据姐姐说,糖粒子厂是没有椅子的,所有包装工人都要从家里带椅子去上班。每天早上七点,姐姐准时在爷爷家背一把椅子出门,晚上六点,又准时从糖粒子厂背椅子回爷爷家。其中十一个小时,除了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起一下身,就是轮番跑到压糖车间去用一个大撮箕铲糖倒在中间的大桌子上的时间起身了。所有人员都在埋头苦干,因为铲糖会耽误包糖时间,所以铲糖实行严格的轮流制,大家铲糖都是当糖快包完又没包完时,快速地跑去铲糖倒在桌上,这样不仅自己节约时间,也没耽误其他人的包糖衔接。包一斤糖两毛五,姐姐年龄虽小,但从小就练就了一双快手,包起糖来丝毫不比那些周围的阿姨奶奶们慢。记得姐姐回家那天,好远就欢天喜地地喊妈妈,还给我们带回了好好吃的糖,交了八十块钱给妈妈,说这是她这段时间的所有工资。我好生羡慕,姐姐在糖粒子厂上班,那不是每天都可以尽情地吃糖吗?姐姐偷偷告诉我们,上班的时间是不许吃糖的,而且出厂时也是不可以带糖的,发现一次扣一块钱。这次回家,总共给我们带了十粒糖,还是她分几次从糖粒子厂偷偷带出来的,她自己舍不得吃,全留着给我们了。
炒货房
再往上走,左边一排平房,六个空窗户,两张烂木门,门前树比屋高,草比人高。门上有一小块长方形的木牌,走近才可以看清楚是“厕所”二字,另一张门上的“危房”字样很显眼。
这里原来是炒货房,只是闲置久了就做了厕所。八九十年代,花生瓜子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进生货,堆进货房后,一批批再运进炒货房炒熟。咸味的就放盐,甜味的就放糖,原味的就用沙子炒,当然还有放八角茴香炒出来是五香味的。这炒,得有专业的师傅,一要有力气,二要有技术,一口大锅一把大铲,要端得起,放得下。盐放多了会咸,放少了没味,炒久了会糊,不到火候又没熟。别看炒货房的师傅每天烟熏火燎的,整个龙头铺各大小商店的炒货都在他一翻一炒的掌握之中。
记得五香葵花子刚出来的时候,我那个馋啊,总是央求妈妈给我五分或一毛钱去学校附近的小商店购买。那时的小商店可方便了,你给他一毛钱,老板都不用秤称,直接用他那专用的竹筒,对着装葵花子的大铁桶一舀,满满一竹筒葵花子往你口袋一倒,连袋子都省了。以前衣服口袋大,可别小瞧那个竹筒,一毛钱的五香葵花子,足以装满你的大口袋。遇上关系好的同学,我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把分享,关系一般的,就会装没看见。
有段时间,与我同班的红英每天都有五香葵花子吃,同学们都围着她转,胆子小的巴结她说“我跟你玩好不”,胆子大的會对她伸出手说“搞点来试哈味咯”,红英被大家像女皇一样簇拥着,好骄傲好骄傲的样子。直到一个午后,红英妈妈跑到学校来把她狠狠地揍了一顿。原来,红英家并不富裕,甚至比一般的家庭更贫困,那一阵子,红英妈妈赖以到集市上换肥皂洗衣粉的鸡蛋越来越少,一查,原来是红英偷了换五香葵花子吃了。可怜的红英为了五香葵花子,一顿板子炒肉吃得那叫一个惨。
副食品加工厂
炒货房的另一边是副食品加工厂,蛋糕、桃酥、饼干,不仅花样繁多,而且味道纯美。附近的居民都拿自家的鸡蛋来副食品厂换油盐钱,那可是当今城市居民托人才能买到的正宗土鸡蛋啊。副食品厂最大的特点就是香,蛋香、奶香、淀粉香、芝麻香,香飘万里,惹得四里八乡的都闻香流涎。
一车车面粉白糖,一袋袋芝麻食盐,一筐筐鸡蛋,源源不断地运往副食品厂,经制粉、蒸炼、成型、干燥、烘烤……一盆盆的副食品运往包装车间,一袋袋的成品运往供销社仓库,直至销售。那时的一袋是一大袋,轻则十斤二十斤,重则五十上百斤,堆满仓库。零售时,有专门的防潮大铁桶装着,售货员有专门的食品包装纸袋。糊纸袋也是一门技术活,先把一张纸对折黏合,然后取一端往上折一小截,打开,左右各往中间折一小角,将对边线对折黏合,一个纸袋即糊好了。姑姑开店子时,我曾帮她糊过纸袋,我一次糊一个,姑姑可以一次糊一叠,仅最后一道程序要分开来做。也有专门糊纸袋赚钱的,糊纸袋比包糖粒子的工价还低,再说需求量也没那么大,所以糊纸袋一般是农妇们忙完农活后,晚间就着煤油灯,糊点零用钱。一般的小店糊纸袋的材料是报纸,也有用其他纸质的,只有供销社才偶尔能弄到牛皮纸,经久耐用又美观。
我喜欢吃副食品厂的饼干,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也喜欢吃副食品厂的蛋糕,不管是甜的还是咸的,更喜欢吃副食品厂的桃酥,不管是撒了白芝麻还是撒了黑芝麻的,还有那百吃不厌的老式法饼,简直回味无穷。其实,在那个年代,我只有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尝到点副食品美美的味道。
外婆拿出来的副食品永远有股霉味。有亲戚来外婆家,会提一包或两包副食品,有时候是雪枣,有时候是猫屎筒,还有时候是小花片。外婆舍不得吃,总留着自己走亲戚时就可作礼品再送出去。外婆的床底下有个专门的陶瓷缸存放副食品,缸里放了很多石灰,是防潮的。我们趁外婆不在屋里时,就偷偷地爬到床底,一手掀开缸盖,一手往里掏,掏到里面有纸袋,就轻轻抽出来,打开纸袋,拿点放衣服口袋里,然后再把纸袋包好放进缸中,留待下次再来偷。每次不是嘴角边的残屑被外婆发现了,就是地上散落的石灰被外婆看到,反正,我们的案件就从来没有不被外婆破获的。外婆后来就把那个陶瓷缸藏到了一个我们怎么也找不到的地方。这下好了,我们偶尔可以吃到外婆的霉蛋糕了。因为存放过久,等外婆打开陶瓷缸时,里面的蛋糕十之八九有点霉了。我们并不介意霉蛋糕,而且吃了霉蛋糕也从来没闹过肚子,真是贫穷的年代铁打的身躯。
仓库和办公室
如果说合作供销社是龙头铺最早的红砖房,那这一栋二层危楼就是龙头铺最早的楼房了。因为那满目的“危楼”字样,让我不敢靠近,只能远观。一楼外面烂门烂窗烂瓦加烂叶,这里曾装着整个龙头铺的炒货、副食,包括生活日常用品,总之是物品的重要集散地。
二楼是办公室,办公室可是领导坐的地方。从前的龙头铺除了这里也就乡政府、派出所、卫生院和学校有办公室。这二楼的办公室,沿走廊,右边三个砖柱,左边墙上两块黑板,黑板曾是当年考勤和进出货的记载处。考勤和进出货由会计和出纳记载,一般会计和出纳除了会记账会打算盘还会一手好粉笔字。在没有计算机和电脑的年代,每个会计出纳的办公室,都会有一个大算盘,平日里记账算账全凭一个大算盘噼里啪啦。黑板就像一个单位的脸,来单位办事找领导的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办公室外的黑板,粉笔字当然要好。当然,领导也都有一手好字,有些领导不仅有一手好钢笔字、好粉笔字,甚至还有一手好毛笔字。走在龙头铺的大街上,如果遇到一位一支钢笔插在衬衣的上口袋,一串钥匙挂在裤腰带上叮当作响的,那不是乡政府的干部就是老师,还有这里的办公室走出去的文化人。因为在众多的卷起裤腿,趿双拖板,荷把锄头的农民中间,文化人实在是太显眼了。
办公室的周主任就是这样的打扮。周主任有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桌上立一本台历,一个笔筒和一叠材料纸。材料纸是那种十六开大小,每行由一粗一细的两条红色平行线组成。平时写个报告计划或总结什么的,都用材料纸。遇上关系好的亲戚朋友要写信,材料纸也是可以送三五张的。爷爷给湖北的叔爷爷写信时,就凭周主任的关系,拿到了一整叠材料纸。
做工的时间一般都不去办公室,只有发工资的日子,才可以去一下会计室,签字领钱恭恭敬敬。
人去楼空寂然一片的小楼院里,两棵梧桐,深冬已无半吊枯叶,枝丫半耷半拉在二层小楼的屋顶、屋脊……
罐头厂和服装厂
曾经,在仓库的围墙下,龙头铺公社的围墙里,还有一个罐头厂和一个服装厂。
罐头瓶统一是玻璃的,圆圆鼓鼓,矮矮的,没有太多花样,只有瓶外贴的标签不同。有梨子罐头、荔枝罐头、桔子罐头、糖水葡萄等。其中,又以桔子罐头最多,荔枝罐头最贵。
水果罐头的季节性很强,罐头厂指派专门的技术人员下乡指导把关,把原材料采购回来,再组织职工生产。经常是一车车的红橘运回来后,在罐头厂的前面摆满一大坪,堆积如山的红橘成了红色的海洋,蔚为壮观。
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罐头成了人们羡慕的美食,看望亲属、探视病人、馈赠朋友,带上几瓶罐头是既体面又实惠的礼物。
罐头厂的旁边是服装厂,罐头厂衰落的年代,恰逢服装厂的兴盛。
一排排脚踏缝纫机,一捆捆布料,哧哧哧的踩机子声音。服装厂清一色的妹陀,那时不叫美女的,都叫妹陀,师傅徒弟全是二十左右的妹陀。附近扯布做衣服的,都来龙头铺服装厂,只见那些服装厂的师傅,一把尺子在你身上一量,衣长、肩宽、胸围、腰围、裤头、臀围、裤長,一边量一边记,记好后过几天就可以来拿新衣服了。做衣服时,一块布料,一片画粉,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一量一画一剪,就可以拿到缝纫机上去“踩”了。还记得我在龙头铺一所小学代课时,教育办为参加区教师节的活动排练节目,我们就曾去这个服装厂做演出服装。那是一件黄底亮花的短袖衬衫和一条高腰蓝色长裤,演出后,我还穿了很多年,大家都说好看。如果是成批的,比如厂里的工作服、学校的校服,就会有一个专门的裁剪师,把布料统一裁剪好,其余的员工就领裁好的布料直接做衣服。长得漂亮,又学了一门当时吃香的手艺,服装厂的妹陀们,总是引得龙头铺周边的年轻满哥三五成群地往那凑,也因此结成了不少的好姻缘。
罐头厂和服装厂早已找不到一丝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宽阔的室外停车场。
龙头铺供销合作社、收购门市部、糖粒子厂、炒货房、副食品厂以及仓库和办公室,还有那早已踪影全无的罐头厂和服装厂,方圆不过几百米,可见当年的龙头铺这个片区,其繁华程度不亚于如今的株洲芦淞服装市场。只是今天,这里满目疮痍,除了危房还是危房。
龙头铺是有历史的。
责任编辑:吴 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