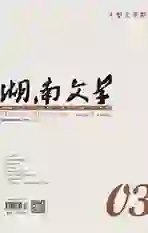忌日
2019-04-21朱彩辉
朱彩辉
凌晨三点,莹莹又发烧了,睡在吴姐身边,不时嘤嘤地哼一声。吴姐爬起来,灯也没开,就着窗外朦胧的月光揉着眼睛摸到客厅。尽管睡眠浅,但闭上眼睛就做梦,梦里净是摸黑走路,睁不开眼睛。这几年健忘得厉害,吴姐在玄关处站了好一会儿,就是想不起退烧贴放在哪里了。
老王坐在沙发上看世界杯足球赛。客厅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盛满了烟蒂。又不懂球,还能熬到半夜。吴姐嘀咕着走到窗子边打开纱窗。
退烧贴放哪儿了?吴姐返过身来问。
老王也不答话,走到电视机条柜边,扯开抽屉,拿出一个白塑料袋。里面几乎全是少儿药品:宝宝一贴灵、少儿止咳糖浆、开塞露、阿莫西林颗粒、……莹莹不像鹏飞小时候,鹏飞小时候几乎不生病,偶尔发一回烧,背到卫生病,打支退烧针,就又活蹦乱跳四处疯玩去了。
吴姐拿着退烧贴进了睡房,老王跟在后面。吴姐用手背在莹莹的额头上试了试体温。莹莹三天两天生病,吴姐觉得自己现在可当半个儿科医生。吴姐撕开退烧贴的外包装,拉伸了一下,轻轻地贴在莹莹的额头上。老王站在床边呆呆地看着莹莹。莹莹哼了一声,把手举起来放在耳朵边又睡着了。莹莹睡觉的样子跟鹏飞小时候一模一样。老王在心里念叨。
“你也去睡吧。你的血压这些日子又升高了,医生讲要注意休息,你又忘记了。明天还有许多事。”吴姐坐到床上,用踏花被盖住自己。自莹莹出生后,两口子分床睡。老王睡鹏飞的房间。
应该是今天,不是明天。老王心里嘀咕,不过,他懒得讲出来。“嗯”了一声,走出睡房。
吴姐臉对着窗子躺下来。一轮满月清清亮亮地挂在窗户的右上角,吴姐呆呆地看着月亮,没了半点睡意。儿子鹏飞走了整整三年了。三年前的今天,鹏飞像往常一样,睡到上午十点才起床,然后在洗漱间待弄他的一头黄发。鹏飞长得跟吴姐一样,眉眼清秀,身材单薄高挑。吴姐一直搞不懂,长相乖乖的孩子,性格却那么叛逆不羁,总是让她闹心。吴姐把他养到二十一岁,也担惊受怕了二十一年,直到三年前的今天,那个傍晚,他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人抬回来。
回想起儿子短暂的一生,吴姐注视着窗外清幽的月亮,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现在,吴姐心里再也不扯心扯肺地痛了,心越来越平静,有时候,她甚至感觉儿子没有死,而是安静地住在公墓里,不再在外面惹是生非,不再让她生气。
鹏飞死时,亲朋好友给她两口子出谋划策,说鹏飞是为茶馆追赌债,应该让茶馆多少赔些钱。可茶馆是鹏飞女朋友家开的。吴姐原来准备让他们“十一”结婚,鹏飞没那命,没等到做新郎,先成了新鬼。鹏飞死时,他的未婚妻已怀孕。鹏飞的女朋友说会替老王家把孩子生下来。吴姐想,这比赔多少钱都值。鹏飞死后没多久,未婚妻有流产的征兆,吴姐抹干眼泪,到菜市场买鸡买鱼,天天抱一缸汤,坐公交车去服侍未过门的媳妇。莹莹出生后,没吃过她妈妈的一口奶水,莹莹一咬她的奶头,她就大声尖叫,吴姐没有办法,只有让莹莹喝牛奶。满月后,莹莹妈妈回娘家住,她偶尔过来看看莹莹,或者,吴姐和老王抱了莹莹去看莹莹妈妈。
儿子死后,吴姐和老王的单位都做了顺水人情,让两口子内退,且拿全额工资。也幸亏不要上班,三年来,莹莹把吴姐和老王的日子填得满满的,让他们甚至连悲伤的时间都没有。吴姐有时候想,是不是冥冥之中,儿子感觉自己让父母操尽了心,亏欠得太多,抽身而去,但又不忍心让父母在绝望地度过余生,于是转世投胎做了他们的孙女。不过,虽然有了孙女,但家里并不热闹,更没有欢愉的气氛,像被什么压抑着,黏贴得紧紧的,摔也摔不脱。鹏飞在世时,家里时常鸡飞狗跳,不是老王咆哮就是鹏飞发飙,但那些愤怒和伤心都是畅快淋漓的。
莹莹睡得安稳了一些,吴姐给莹莹掖了掖被子,转过身去,闭上眼睛。
老王躺在床上,全无睡意,烙烧饼般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就是睡不着。老王患失眠症三年了。但他却从不承认自己患了失眠症,认为这很正常,睡得着才是不正常。鹏飞刚去世时,他的心整日像被大岩石压着,喘不过气来,还尖锐地痛,脑子里空荡荡的,整个人像被抽掉了气,只剩一副空皮囊,每日呆坐,呆坐,呆坐,行尸走肉一般。不知什么开始,他晚上睡不着就起来到小区游荡,从东头到西头。有一天半夜,小区有女人外出,以为撞见了鬼,吓得尖叫,惊醒了整个小区居民。后来,他老婆生病住院,未过门的媳妇在医院保胎,老王不得不强打精神恍恍惚惚来往于家、医院之间,也就是那时候,老王学会了买菜。之前,菜市场门朝东门朝西老王都不晓得。那都是老婆吴姐的事。自从鹏鹏出生后,老王的人生万事大吉,安稳的工作,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工作之余,他喜欢打点小牌,无论输赢,他都趾高气扬的。依他自己的话说是输牌不输精神。每天晚餐必喝点小酒,也不拘菜好菜差,酸豆角、红烧肉,二两就够。当然,他最喜欢的是陪儿子踢足球。学校、教场坪,甚至小区坪场。他不懂足球,坐在球场外远远地看鹏鹏如小豹子一样跑来跑去,儿子初中进了校足球队,他为此感到骄傲,要不是他老婆死活不肯,他甚至打算送孩子去外地专门学踢球。后来鹏鹏混社会,给他带来不少烦恼,但他对生活仍像小孩子吹气球,从没有气馁过。现在气球突然爆了,他成了“无后”的人,虽然他从没指望过鹏飞给他养老送终,但人在老王的寄托就在。即便后来,有了孙女,他再也不能使自己回到从前,他的心也自此没有轻快过。他的头一天到晚耷拉着,眼睑下垂,从不与人对视,也从不仰起头来看前方。老王常常想,老天爷收走了他的儿子,又送给他一个孙女,把他推到绝境,却又不置他于死地,而是不容分说一直在推着他往前走,他就如老天爷的一个木偶一般,容不得他选择。所有人都能看出来,老王也不再是原来的老王,他不再打牌,也不再串门子,烟却抽得越来越厉害了。
吴姐醒来的时候,老王已买菜回来。老家伙未必一夜未睡?吴姐心里一边嘀咕一边穿衣洗漱,然后拐进厨房做早餐。老王靠在沙发上守着莹莹。莹莹平时就有些畏惧老王,这时看老王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心里更是怯怯的,用布娃娃不停在沙发背上敲打。
祖孙三人一起吃早餐。莹莹还是有些发烧,吴姐也没给她蒸鸡蛋,喂了她小半碗白米粥,馒头一口都没肯吃。
老王捡拾去上坟的东西。纸钱、线香、白烛。鱼干、贡梨、荔枝,这些都是鹏飞生前爱吃的东西。前几天,老王还悄悄买了两包芙蓉王烟。平时,老王自己只抽五块钱一包的白沙烟。
先去医院给莹莹看看吧,吴姐也不看老王,像是在跟莹莹说话。
老王弯腰的时候停顿了一下,也不答话,把蜡烛放进篮子,走到窗户边,看了看天,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阵雨,也不晓得这雨什么时候来。吴姐看老王埋头捡拾东西,晓得他是想先去儿子墓地。老王大半辈子都是这副德性,他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还死不认错。鹏飞死后,老王越发像风干的苦瓜,一副苦相。吴姐跟他吵了大半辈子,儿子走后,她突然不想跟他吵了,他想怎样就怎样,更不跟他争长短对错。老王将芙蓉王香烟也放到了竹篮里。莹莹像只小猫一样,静静地偎依在吴姐的怀里,小脸蛋红扑扑的。
老王提了篮子下了楼。小区坪场里一群小孩子在踢球,花坛入口是他们的球门,一个红衣男孩带着球死命地往球门边奔,后面几个孩子你推我搡,大呼小叫着猛追,一个个泥猴一样。老王的心像被蜂子螫了一下。鹏飞以前也爱把花坛入口当球门,每天在足球场踢了不够,还时常在小区里玩到天黑才上楼。
吴姐背着莹莹,边打电话边下楼。
电话是莹莹妈妈打来的,说她直接去鹏飞的墓地。虽然未过门,但在吴姐和老王的心里,莹莹妈妈是他们名正言顺的儿媳妇。
吴姐和老王一前一后向小区外面走。不时有人和他们打招呼,莹莹额头上贴着的退烧贴,像女人的卫生护垫,招惹着每一个人的眼睛。
“怎么啦,小宝宝。”C单元的李姐迎面而来,边说边去抚摸莹莹的小手。
“有些发烧呢。”吴姐停下来和李姐说话。
“三婆孙出去啊?”A单元的老赵也正要出门,他是老王的同乡,还是同事。老王不喜欢和小区里的任何熟人聊天,儿子的死让他觉得羞耻,他感觉每个跟他搭讪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儿子死于非命的事情,仿佛这已成了他老王的标识,他受不了别人怜悯的目光和语气。
“嗯。”老王埋头往前走。
“也是到刘局长家吃酒去?”
“他家有什么事?”老王停下来问。
“他今天娶媳妇呢。”
刘局长的儿子跟鹏飞同年同月同日生,曾都住在单位宿舍里,小学六年,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吃个饭也不分開,不是你端了碗到我家,就是我端了碗到你家。
“你给我带个人情吧,我有事。”说完,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红钞票给老赵。
吴姐在小区门口拦了一辆的士。天半阴半阳,看不出它是想落雨还是想出太阳。车里收音机在唱《桃花朵朵开》: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等着你回来
看那桃花开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等着你回来
把那花儿采
莹莹的宝宝音乐盒里有这首歌,她来来回回地哼着: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老王坐在副驾驶上,目光茫然地盯着前方,风从窗缝中吹来,吹得他瞌睡都来了,但他不想睡,哪怕是眯一会儿。他努力地打起精神,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过二三年,公路两边新修了许多民房。因为地基窄,从山坡打水泥桩,像老式的吊脚楼,不过现在都是红砖屋,三四层,六七层不等,碉堡一样。门前的坪场虽不大,但家家的坪场前或栽了桂树枇杷,或围一个小小花坛,凤仙花月季花紫罗兰,此呼彼应地开着红的花,白的花,灰扑扑的,没了花的看相。倒是远处的山和天,都青郁郁的,有乡村的景象。老王想起老家乡下的房子,以前还计划着退休后回家养老,儿子走后,一年回去一二趟,房前屋后长满了草,一屋霉味,没了人气。那房子迟早会腐朽。不过,人都没了那房子万古不朽又有什么意义呢,倒是这万古青山,人终要归依的场所。现在城里人越来越多,墓地也变得金贵了。原本买墓地应该是子孙的事,但鹏飞不在了,虽然有莹莹,但她一个女娃娃,年纪又小,指定靠不住。鹏飞墓地旁边倒还有块空地,应该把它先买下来。老王胡乱地想着心事,不知不觉的士已载着祖孙仨到了公墓。
莹莹妈妈已先到鹏飞的墓地,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孩儿,二十多岁,左手臂上纹有一只展翅的老鹰,鼻子特别大,一头金黄色的头发竖立着,像一头金毛狮子。莹莹妈妈看到吴姐他们走过来,隔了老远大声喊宝宝,宝宝。吴姐喘着粗气,停下脚步抬头看迎面走过来的莹莹妈妈和金毛小伙子。这小伙子的鼻子跟莹莹长得一样,水牛鼻,老王心里愤愤道,上次听老婆讲莹莹妈妈找男朋友了,看样子就是他。老王觉得这种打扮的人都不是好东西,这莹莹妈妈也是不懂事,带这样的人到鹏飞坟上来。金毛小伙子伸手想帮老王提篮子,老王冷着脸说不要,又生怕他抢篮子似的,把篮子从左手换到右手,踉跄着从金毛小伙子身边走过去。金毛小伙子尴尬地收回手,转身走到莹莹妈妈身边。
莹莹妈妈拍着手来抱莹莹,吴姐嘴里不住地念,是你妈妈,叫妈妈,叫妈妈呀。莹莹张着小嘴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妈妈,就是喊不出来。不过,她终于伸出双臂。
“宝宝怎么啦,不认识妈妈了?”
“她昨晚有点发烧。”吴姐解释。
莹莹妈妈用自己的额头去抵莹莹的额头。
“好象还有些烧呢,早上没有去过医院?”
“她早上看起来还好呢。”吴姐支吾道。
莹莹妈妈嘟了嘟嘴,抱着莹莹走到鹏飞坟前。
老王将贡果摆放在鹏飞的墓碑前。几个人蹲在坟前将纸钱一张一张撕开。老王取出打火机点燃纸钱,大家也七手八脚将纸钱扔到火堆上。吴姐点了三根线香,将莹莹揽过来,捉住她的双手边作揖边念念有词道,你女儿莹莹好乖好懂事,你要保佑她健健康康啊。
老王将香烟盒里的香烟一根一根抽出来,点燃一根,用力吸一口,然后横放在墓碑上。莹莹妈妈看他慢腾腾地点烟吸烟放烟,急不过,拿过一包,取了一把,放在火堆上点,不想却燃起了明火,莹莹一把将香烟丢进火堆里。
老王抬头挖了莹莹妈妈一眼。
莹莹妈妈不置可否地嘟了一下嘴,复又抱起莹莹走到坟堆后面去看开得正盛的女贞子。两只交尾的墨绿色蜻蛉在莹莹面前飞过去。莹莹指着蜻蛉叫“飞,飞……”
“宝宝要豆娘啊,叔叔给你抓,好不好?”金毛小伙子暧昧地看了一眼莹莹妈妈,蹑手蹑脚去抓停在女贞树上的蜻蛉,还未走到树边,蜻蛉双双飞走了。金毛小伙子在女贞树下采了一把开蓝色花的婆婆纳。
莹莹高兴地接过来,返身对坟边的吴姐叫道“婆婆,花花,花花。”
老王和吴姐正在扯坟上的草。被扯过的地方,光秃秃的,露出黄黄的泥土。
草还没扯完,下起雨来了,劈劈啪啪,砸在光秃秃的坟上,砸在老王的头上,清冷冷的。老王用爱抚的目光看了一眼墓碑,也不跟大家打招呼,转身下山。不知什么时候,莹莹已到了金毛小伙子的背上,莹莹被小伙子金色的头发吸引了,怯怯地伸手去扯,扯得小伙子痒痒的,呀呀叫起来,莹莹妈妈哈哈大笑,小莹莹也兴奋得手舞足蹈。
三婆孙一回到家,莹莹呕吐不止。
三婆孙又急忙捡拾东西去医院。医生说要化验。
老王在化验室外面的长椅上等结果。走廊上的人真多,大家或坐或站,互不说话。一个护士伸出脑袋,大叫:张莹莹,张莹莹的结果出来了。老王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走过去接过化验单。
有什么问题吗?老王接过单子问化验员。
去问医生。化验员没好气地回答。
急性肠胃炎,还高烧。怎么这时候才送孩子来?年轻的女医生扫了一眼化化验单。
上午去墓地了。吴姐怯嚅道。
死人比活人还重要?女医生边说边埋下头去开药方。老王被女医生的话憋得满脸通红,魔怔了一般,盯着女医生好一会儿都没有回过神来,脖子上两根筷子粗的青筋像要暴出来。女医生开好处方,往旁边一推,头也不抬地说了声,“下一个。”老王青着脸拿了处方去一楼交钱取药。
莹莹的病床靠窗户,吴姐把莹莹放在床上。莹莹晓得自己又要打针了,带着哭腔道:“婆,我不打针,我不打针。”吴姐也不理莹莹,把床单抹了抹,又将被子叠好放在床头,老王从口袋里摸出烟来,抬头看到邻床穿蓝花衣的老妇人双眼鼓鼓的地看着他。
你不是王……蓝花衣老妇人张口结舌道。
是呢……老王也认出了蓝花衣老妇人。老王一个老同事的姐姐,好多年前,老王在她家打过一次牌。
几年不見,你老了好多哎。
是呢……
这是你孙女?
是呢……
她还蛮像……
是,是……
好,好……
蓝花衣老妇人闭了嘴,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莹莹。这县城,屁股大一块地方,鹏飞的事,她肯定听说过,否则她不会有那副表情。邻床小男孩的床边除去蓝花衣妇人,还有一位武武敦敦的小伙子,年纪跟鹏飞差不多。老妇人转过背在玩手机的小伙子耳边唧唧咕咕了一阵,小伙子抬起头来看了老王祖孙仨。老王耷下眼睑将香烟放回口袋,在床头坐下来,一股莫名的悲愤从心头蹿出来,感觉自己的老脸没地方搁放。蓝花衣老妇人送过来几个香蕉,说是给小孩子吃。老王一手挡了回去,说,不要了,她拉肚子,吃不得。蓝花衣老妇人尴尬地举着香蕉,进不是,退不是。老王不理老妇人,茫然四顾。少儿输液室虽然只有六张床位,但每张床位至少都有二个人陪床,多半是年轻的父母再加一个老人,有一张床竟然有四个老人和一个年轻女人陪床。邻床小男孩不停地嚷嚷,爸爸,怎么还没打完,我想回去,我想回去。小伙子对小男孩说,快了快了,爸爸给你变个魔术。小伙子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硬币说道,你看好了哦,硬币在左手,现在到了右边,眼睛不能眨哦。说着,双手往小男孩面前一伸。小男孩看着他爸爸空空的双手,哇哇大叫道,爸爸你好厉害哎。小男孩的叫声引来齐涮涮的目光。老王怔怔地看着这一对父子。这几年,每当看到与鹏飞年龄相当的男子,老王便习惯性地联想到儿子。他再是羁叛,但本性不坏,成了家有了儿女总应该收敛一些。老王记得鹏飞小时候常常嚷着要他妈给他生个妹妹,莹莹那么乖,他要是在世,该有多喜欢啊。
三婆孙走出医院大门已是四点半,这时莹莹妈打来电话,说是想请祖孙三人吃晚饭,地点“老城旧事”。这三年,吴姐一家很少在外用餐,不晓得“老城旧事”餐馆在哪里,莹莹妈妈在电话里解释了半天,吴姐挂了电话,嘟噜了一句,教场坪入口不就在家惠超市旁边嘛。老王心里哆嗦了一下,两眼无光地看了吴姐好一阵。吴姐没心没肺地在前面带路。莹莹一听说妈妈请吃饭,即刻高兴得从爷爷怀中滑下来就往前冲,吴姐一步奔上去拖住莹莹的手。三婆孙便穿过好吃街,横过辰州中街来到“老城旧事”餐馆。莹莹妈妈已先到了,坐在临窗的桌子边,上午一起去公墓的金毛小伙子坐在她身边。老王蹙了一下眉。莹莹看到妈妈,挣脱奶奶的手,向妈妈奔去。餐厅里人来人往,莹莹妈妈老远站起身来张开双臂迎接莹莹。看到老王走到桌子边,金毛站起来给老王递烟,老王极不情愿地接过来。莹莹妈妈一边指着金毛一边说,上午忘记介绍了,这是我男朋友,小曾。吴姐对金毛笑了笑,算是打招呼,老王垂下眼睑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老王的座位正对着窗户。窗外是教场坪。这个地方老王太熟悉了。几年前,县里曾计划建一个体育场,却因为两栋老房子不肯拆迁,建了一个跑道后便没了下文,现在跑道也稀稀拉拉长了许多草,若不是有一条用水泥板铺成的下水道隔开来,已看不见跑道了,但老王闭着眼都能想起跑道和草坪的样子。不过,老王想不起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陪鹏飞在这里踢过球。鹏飞死后,听警察讲,鹏飞就是在教场坪被人砍得血肉模糊。但具体在什么位置老王没问过。这三年来,老王一次也没有来过教场坪。鹏飞的死禁锢了他的生活圈子,他的活动范围除去家、菜市场、医院,以及一年一两次不得不回的乡下,对了,还有鹏飞的坟地。除此之外,老王想不起自己还去过哪里。鹏飞死后的半年里,老王有几次倒是想来教场坪,看看他儿子倒在什么地方。老一辈人说人死在哪里,魂就落在哪里。可是,那半年,亲戚们把他看得紧紧的,厕所蹲久一点都会有人敲门。老王怔怔地看着窗外的景至,那么陌生那么熟悉,恍若隔世。
服务员过来推销啤酒,说是买三送一,总消费满二百另送二十元消费捐。金毛说,我们来四瓶?
我不喝啤酒。老王板着脸道。
白酒也有,小瓶的有二锅头、郎酒、元陵大曲。服务员接过话来道。
来一瓶二鍋头。老王闷声道。
那就来一瓶啤酒,一瓶二锅头吧。莹莹妈妈抬头对服务员说。
菜很快上齐了。莹莹中午都没吃东西,肯定饿了,先喝碗汤。吴姐边说边拿起碗盛汤。
大家仿佛都感觉到饿了,也不待谁招呼谁,各自拿起筷子夹菜吃。酒水很快也送上来。老王自顾倒了一满杯二锅头。金毛倒了一杯啤酒,站起来想要给老王敬酒,老王举着酒杯道,酒不在一个档次,各喝各的吧。说着将杯中的酒喝了一大半。酒有些辣口,老王咂了一下嘴。金毛尴尬地瞄了一眼莹莹妈妈,莹莹妈妈装作没看见,低头给莹莹喂饭。大家埋头吃饭,只有吴姐不时感叹,汤好喝,或是肉丝炒得嫩。盘子里的菜很快见了底,莹莹妈妈叫服务员过来加两个菜,吴姐说菜够了,老王抬起头来看了吴姐一眼。莹莹妈妈点了一盘红烧粉肠,一盘藕断丝连。莹莹天真问妈妈什么叫藕断丝连。就是丝瓜和藕一起炒。莹莹妈妈边说边端起自己的碗吃饭。老王总是在端杯的空隙里偷偷地瞄一眼金毛小伙子。
莹莹下半年也该上幼儿院的了,你们晓得的,幼儿园跟我住的地方只隔一垛墙,莹莹读书方便。莹莹妈妈突然说。
吴姐一听,抬起头来,鼓着双眼,满嘴的食物将两个腮帮子塞得鼓鼓的,一脸惊诧。
老王耷下眼睑,一言不语,仰头一口把酒闷了,又将杯子倒满。
我们下学期也准备送莹莹进幼儿院。学校都选好了,叫什么囝囡幼儿园。吴姐放下筷子道。
是不是福利院隔壁那个,好远呢。莹莹妈妈不急不慢道。
不算远,再讲,反正我和他爷爷有的是时间。吴姐边喝汤边说。
我是替孩子着想。莹莹妈妈嘀咕道,心里却想你们是有的是时间,可孩子要天天遭罪。
我们给莹莹选的是好学校呢。
我晓得。但莹莹迟早要跟我住。莹莹妈妈轻轻说。
莹莹跟我们住得好好的。吴姐不高兴了。
你还怕我们对莹莹不好吗?吴姐补了一句。
我不是那个意思。莹莹妈妈辩解道。
莹莹迟早要跟我住的。莹莹妈妈补了一句。
再讲,我们下个月准备结婚。莹莹妈妈看了看金毛道。
啊……吴姐张开的嘴半天没有合拢。
从法律上讲,莹莹的抚养权是我的……莹莹妈妈嘟噜道。
你话不能这么讲。当初……吴姐打断莹莹妈妈的话。
好,好得很。老王突然大吼一声。这就是……今天……你请我们……吃饭的意思?
老王仰头又把一杯酒倒进了肚里。像有一支利箭直射老王的心脏。老王又仰头一口把酒喝了,重重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四周的人都转过头来看老王。老王头昏脑涨,脸红彤彤的,不晓得是喝酒的原因还是太过于激动了,大厅里有那么一刻安静极了。老王感觉到了四周的目光,用力地甩了甩头。莹莹听到爷爷的吼声,饭也不肯吃了,偎在妈妈怀里,怯怯地拨弄着妈妈颈上的项链。
大家都不言语。空气沉闷得像吹胀的气球。老王手中的筷子什么时候如一把“X”搁在桌子上,才端上桌的两盘菜几乎还没动筷子。老王怔怔地坐着,两只手下意识地在裤子口袋摸索,但半天也没摸出点什么来。突然,老王站起来,口里念念有词。窗外的教场坪像是飞到了他的跟前,齐膝深的茅草在秋风里摇曳,一群少年在跑道上踢足球,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带球跑在最前面,他那身姿,那消瘦的脸庞,那奔跑的样子……
鹏飞在踢球,我看看去。说着,老王转身转身离开餐桌,向大厅外走去。吴姐一下子怔住了。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