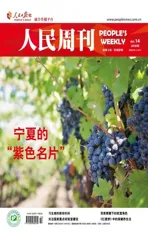我们的村庄
2018-11-19李树茂
李树茂
我的老家在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中卫市的一处村庄,老人们都说村里人的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移民戌边过来的。
村子离北沙窝有三四里地。而村里的农田,就紧挨在沙丘边上。
村里有户肖姓人家,是从河西民勤逃荒过来落脚的父子俩。他们的老家被连年的风沙吞没了。那做父亲的有些文化,常讲一些沙漠灾害的事情,沙漠在他嘴里竟有些怪异,像是危害人间的魑魅魍魉。
村里的长辈们也是谈沙色变,说某个夜晚雨暴风狂、生灵战栗,田野那头的漫天黄沙会暴虐如鞑靼的马群一样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一夜间踏碾掉满地的庄稼,湮没热闹的村庄。
乡下的少年人却不信这些,小小的脑瓜里不知装了多少奇思怪想。他们顺着山墙下的木梯爬到房顶,登高远望,对着茫茫沙漠入魔似的傻想。地平线的那头,沙丘连绵起伏,层层叠叠,一直伸向天际。遇到夕阳西下,灿烂的云朵火一样燃放,一时间流光溢彩、霞光万丈,那天边的大沙海在光的映衬、色的笼罩下,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竟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
到底是风的故乡?魔的巢穴?还是美丽的天堂?
于是,到了能给生产队放驴的年龄,在一个明丽的早晨,小伙伴们三五一伙,驱赶着驴群,向着北沙窝出发了。
大牲畜嗒嗒的蹄声,吵醒沉寂的大地。庄外的田野,稻菽遍地,瓜果飘香,早起的鸟儿快乐翱翔。远处的黑山之巅,烽火台巍峨耸立,那边墙顺山势而下,蜿蜒蛇行远方,尽显沧桑但不失雄伟的身躯把沙漠和绿洲分开两旁。
驴群一路向北,穿过丰收在望的原野,淌过水流清澈的挡浸沟,翻过边墙,再顺着沙枣林带和沙漠的坡脚,一路往西,就到了龙宫湖边。
这是放牧的绝佳之处。龙宫湖像一块巨大的宝石,镶嵌在沙海之中。湖的周边,芦苇荡荡,沙柳依依,林下的草地各色小花竞相开放。驴子自然是欢喜这自由自在的空间,撒着欢子觅食鲜嫩的草茎。
比驴子更欢快是小伙伴们,他们丢下驴群,大声吼喊着进入沙漠腹地,爬沙丘,滑沙坡,拣骆驼粪蛋蛋,在沙山脚下的湿地边采沙葱,攀到高大的沙枣树上摘沙枣。最刺激的是溜进城里单位农场,撕开沙枣刺毛篱笆去偷食,胡萝卜的甘甜、白萝卜的辛辣、青豆烧熟后的醇香,让他们填饱的肚皮回味悠长,也让村里的少年人对沙漠充满了无限的好感。
小伙伴们顽皮活动的重点,还是爬上黑山嘴子烽火台登高远望。苍穹之下,远山如黛,金沙流韵,平原被南部的香山和北部的沙漠紧紧围在中间。平原腹地,碧野铺翠,烟水葱茏,黄河像一条白色的飘带,自西往东从绿洲穿过。氤氲之中,县城居中而立,田野沟渠纵横,村庄散落其间。少年们没有机会远行,北沙窝是他们走得最远的地方。但站在黑山嘴子制高点上,站在久经岁月风霜洗刷而不倒的长城烽火台上,面对着眼前的苍茫大地,小伙伴们的心远了,胸怀似乎也广了。
那时的农村孩子没有机会去见什么大世面,但他们的脑瓜一样灵光。他们生长在并不富裕的农家,有些孩子父辈还是文盲,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有憧憬、有梦想,孩童时代的他们尽情享受着幸福快乐的时光!他们的内心或许还有无知,但无知者无畏,父辈们恐惧沙漠,他们却把沙漠当成了挥洒天性、放飞快乐的天堂!
长辈们虽然谈沙色变,但我的记忆中,他们征服沙漠的信心从来不曾动摇,进入沙漠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
深静脉血栓的预防分为药物预防和非药物预防。药物预防,包括肝素、低分子肝素、华法令等药物使用,根据不同患者选择合适药物应用。研究显示,依诺肝素应用使腹部大手术围手术期血栓发生率更低[18] ,他汀类药物可以有效预防血栓发生[19] 。但药物使用存在出血风险,有出血风险和出血倾向患者则不能使用,尤其是部分危重病患者使用抗凝药物存在禁忌症。非药物预防,包括早期活动[20] 、增加被动运动、压力梯度长袜、气压泵应用[21] 等,为避免出血风险发生或存在药物应用禁忌症,可选择使用非药物预防方法,联合使用多种非药物预防方法,亦可达到很好预防效果。
生产队长李海是个有权威的人,平时摆个面孔不苟言笑,村里人家都很怕他。公社、大队但凡有到北沙窝植树造林的任务,只要他站出来振臂一呼,大家都会踊跃前往,不会有半点迟疑。
长辈们把防风固沙当成了生命的自觉。每年春季,人们套着驴车,背着背篼,拿着铁锹,云集北沙窝,战天斗地,植树造林,会战十天半月。几十年下来,竟在沙漠边缘,栽出一道宽幅林带。这条林带像一道绿色屏障,死死挡住了流沙的南侵。
由防风固沙,人们养成了种树爱树的习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长满钻天杨、左公柳、小叶杨、金钱榆、香叶椿;路旁沟畔渠边,成排成行的白杨树组成了密集的农田林网。这些高大的绿化树严阵以待,像一个个全副武装的卫兵,阻挡着风沙对庄稼的袭扰,忠诚地守护着垦耕者的家园。
有的年份也有风沙侵袭农田情况发生。沙窝边的田地被沙压了,来年翻春,生产队组织上百号人车拉肩扛,硬是把流沙清了出去,把小麦种了下去。
碱“吃”庄稼也是一种自然灾害。虽然大集体后组织群众大搞田文化运动,挖了许多的排水沟,但沙漠边农田里的浸水还是很大的,农田受浸水浸泡,往往会在来年泛起一层薄薄的碱花,这层碱花会把刚萌发的庄稼幼苗“吃”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想尽了办法,当时最直接管用的方法,就是拉来黄沙给泛碱的地压上一层,这样,碱就被压了下去,麦苗也就茁壮生长起来。
人们常年依沙漠而居,到沙漠深处去寻求生产生活所需资源也是一项劳动。那些年,庄稼增产主要靠农家肥。人们将人畜粪便做成农家肥,沤杂草生产高温墩肥,烧土炕产生土肥。为了增加土地的有机质,后来人们又有了新的发明,就是烧土窑破碎后制作农家肥。每年秋后,生产队会把社员们分成两组,一组在收完水稻的农田里挖土坯建土窑,另外一组赶着驴车进驻北沙窝,去打烧窑用的沙蒿草,顺手收割一些冰草和芨芨草。冰草用来搓草葽子(捆庄稼用的草绳),芨芨草用来编背篼和制作粮场上用的大扫帚。当然这些活动都是避开当地蒙古群众的,蒙古人对他们放牧区域的一草一木都护得厉害,发现汉人过去打草,他们会骑着马过来制止,因为这些都是他们马群、羊群赖以生存的食粮。
长辈们为了能持续出入沙漠,特别注意和蒙古人搞好关系。每年秋冬时节,会有蒙古人的马群来访,在打完粮食的粮场和田野里觅食,人们从来不会驱赶,更不会做出伤害的举动来。有些人还和蒙古人有生意上的交往。生产队有一个称为三太爷的大长辈,老当益壮,黑胖敦实,和蒙古人是朋友。每当有叮叮当当的驼铃从远处传了过来时,小伙伴们就会知道,这又是三太爷的蒙古朋友来了。驼队满载着食盐、布匹、白糖、风干羊肉和日用百货,牵驼人会在三太爷家吃饭加水休息后离去。
村子西北沙窝有一处叫小湖岗子的地方,建有高大的烽火台,边墙打这里经过。烽火台两侧,是一处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买卖城,先人们在这里与蒙古人相互交易,汉人用大米、白面换取蒙古人的马匹、牛羊、皮毛。当然一些商人生意范围会更宽些,他们还会有糖茶、布匹、肉食、咸盐和针头线脑、日用百货的交易。双方互市通商,几百年间没有发生过相互械斗流血的事情。村里的人们继承了这种传统,与沙漠里的蒙古人和睦相处。
历史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常年遭受沙漠那边族群的袭扰,长城是他们最可利用的屏障。连年的战祸让双方都尝尽了苦头。和则两利,战则两伤。几十代人的血,最终让先人们聪明起来,学会了用和平的方式与异族打交道。后辈儿孙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相安无事、繁衍生息,得益于先人们的智慧。处沙漠之滨,有一套御沙、治沙的办法,不受沙漠之害;与外族比邻,和外族和睦相处,着实让人感慨!
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像这样的村庄有几十个。
明朝至今六百多年,这些村庄的人们扎根沙漠边缘,在抵御异族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中一路走到现在,祖祖辈辈没有得到过泽被后世的功名,没有实现过大富大贵,只是默默地把热血和生命都奉献给了这块贫瘠的土地。
但历史应该记住这些村庄,记住从大槐树下移民到这些村庄的屯垦者,记住他们的血泪和汗水。这些村庄里的祖先们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太深的苦难,脚下这块陌生而荒凉的土地曾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绝望和辛酸,但他们却依然操着混杂着多地口音的方言,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用他们粗糙的大手,让西北沙漠边缘这块处在中华版图几何中心的土地从此走进了塞上江南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