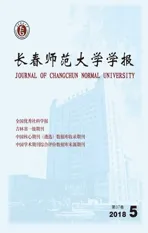第三代顽主的终极关怀
——试论《看上去很美》中儿童视角和人称转换的叙事效果
2018-03-28吴建隆
吴建隆
(宁德师范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0)
“顽主”来自北京方言,最早解释为流氓头目。然而当“顽主”成为一种文学形象,出现在文革结束后乃至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中(尤以都梁和王朔的小说为多),“顽主”所承担的意义和内涵就发生了变化。王朔自小经历文革,目睹哥哥姐姐闹红卫兵,长大后成为了第三代顽主。他这一代顽主似乎是最悲哀的,因为“无事可做”,重温英雄梦的时代已经过去。王朔选择借助语言文字对时代进行调侃,实现对这一代顽主的关怀。
在小说的自序中,作者写道:“这小说写得是复兴路29号院的一帮孩子,时间是六一年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主要地点是幼儿园、翠微小学和那个院的操场、食堂、宿舍楼之间和楼上的一个家。主要人物有父母、阿姨、老师、一群小朋友和解放军官兵若干。没坏人。有一个幼儿园阿姨有一点可笑,仅此而已。”[1]8时间、地点、人物被作者概括得极其清晰简单,但就是如此简单的线索引发出儿童世界里光怪陆离的被想象和自我无限膨胀的记忆事件。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他是在追忆往事。作者在揭开那段回忆的同时更是表露出对那个看似美丽年代的暗讽意味,在对自己有刺痛感的童年进行追溯的同时表达出对自由精神的不懈追寻。
一、审美童年与现实童年的碰撞
小说中最明显的叙事手段就是儿童视角和第一人称同第三人称的频繁转换。但不管是以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的关注点始终放在主人公方枪枪的身上,用“我”来直接表现自己的内心活动,以“他”来全知地刻画方枪枪的行为和心理,都表现了对方枪枪的童年经历和精神世界的极大关注。方枪枪体内两个孩子的出现是在三岁以后他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更为独立的思想意识,在此之前他是由人摆布,一块糖就可以收买的,然而在之后,体内的另一个孩子陪他见证了更多思想情感的变动和独立的意识行为。在小说里,一个是理想主义的方枪枪,一个是现实意义上的方枪枪。正如同一个是“溢美”性质的童年借由“我”来回忆和追溯,一个又是现实童年里的方枪枪。无论美好与忧伤,各种现实事件同时存在着。“我”和方枪枪的区别就在于方枪枪是那个在现实生活里从来不缺席的孩子,而“我”只是他生活中的过客和记录者。也就是说,作者回忆里的那个“我”并不是全貌的方枪枪。现实主义者要承受更多的事情,不如理想主义者那样自动规避一些不愿经历和想起的事情。若像小说中方枪枪所渴望的那样——人生如果像演电影那样,一晃眼就在字幕上打着几天以后的字样——就不用经历现实中艰难的过程了。
然而现实不可规避,第三代顽主的童年即便在多年以后也是不能够溢美的。“看上去很美”,童年的世界是多么精彩曼妙美丽啊——有一丝不苟的阿姨和老师,有一同吃饭睡觉讲卫生的小朋友们,有帅气的军装,有各自占山为王的大院……这些看似是孩子们的回忆和有趣的事件,却反映出那个年代浓厚的政治背景和较为极端的社会风气。作者借孩子的世界观隐隐透露出那个并不美的时代背景对其精神世界的影响。保育院解决了孩子的看管问题,但这种永远不拉窗帘的没有隐私的公共宿舍对幼小孩子心灵的抑制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对孩子的性启蒙教育也是没有的,在大人眼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对于孩子来讲那却是极为重要的。
儿童的世界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他们不能脱离大人的视线,只能在保育院、翠微小学、29号大院等地方活跃。他们不会考虑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不足以理解政治事件和明辨大是大非。复杂的是他们那些始终活跃着的不成熟的思想和身体为他们带来无限的乐趣和忧伤。他们的那方看似狭小的世界并不完全是纯粹的,他们也有敏感的情绪和复杂的想法。小孩子可以把严厉的阿姨想象成吃人的妖怪和特务,可以想象自己勇敢地作战。这看似是对英雄的崇拜,实则是他们反叛心理的体现。对孩子内心世界的刻画和关注正是作者追寻精神自由的深刻体现。
二、“反本质”对价值的消解
反本质主义的对象是本质主义。“我们赞成的是反本质主义求解问题的方式和超越精神,即不能把事物和问题看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并且要有不断进取精神,超越现成之论,走创新之路。”[2]王朔在小说创作中,正是借用这种反本质主义来消解正统的价值观念。
在小说中,王朔借由儿童的视角尽情想象和颠覆一些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和事件,间接透露出作者深刻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作者及其童年伙伴从小就不常在父母身边,对父母的感情比较淡薄。他们反叛放肆,对事物的评判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对当时正统的思想观念更是采取反抗手段,以此来完成精神上的自卫。他们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想方设法用各种新奇的方式来打倒压制他们的人。比如方枪枪脱口而出对唐阿姨说“操你妈”,并造谣说李阿姨是妖怪和特务。在李阿姨揪出说她是妖怪的孩子时,他尽管有一时的恐惧,但紧接着又说她是特务。这当然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电影里的特务和坏人总是一副丑恶嘴脸,孩子在脑海中很容易形成长相凶恶丑陋的人都不是好人的浅层认识。
在小说中,方枪枪的父辈们严谨遵从党的指示和要求,有着激情澎湃的革命精神,对革命的热情和对党的忠诚使得他们有着明确的为党奋斗终身的使命感。然而生活在集体管制之下的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如同监狱一般的地方,什么都要整齐划一,听从阿姨和院长的安排。在个性养成的关键时期,方枪枪这样想要受到更多关注的孩子就会本能地做出一些违背好孩子条例的事情。作者借用儿童的视角,描述了一些荒诞而离奇的想象,实则有深刻的讽刺和戏谑意味。比如在小说中,方枪枪认为孔融让梨并不是因为孔融多么懂事,而是觉得较小的孩子不敢和大孩子争抢,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再比如他对红领巾的理解,胡老师问红领巾为什么是红的,孩子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染坊工人染红的。在胡老师讲解红领巾的纪念意义时,作者写道:“我们跟着胡老师懂了什么叫象征。那意思就是接着点边儿就拉到一堆儿,把可能发生的事说成就这么干的。”[1]200可见对于红领巾的纪念意义,幼小的孩子并没有多大的感觉,只是觉得硬生生把两个有点小关系的事物简单地扯到一起,下了死定义而已。对于固有的传统和正统的价值观念,王朔在小说中通过儿童视角进行概念创新和重新理解,对这些事件的本质意义给予消解和颠覆,从而实现预定的叙事效果。
三、对当下和过去的双重讽刺
作者以一个儿童的戏谑口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远去的童年时代作了双重讽刺。儿童的关注点大多是自己的小世界,是向内转的,他们对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的敏感度不高,思想也远不够成熟。作者通过孩子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对政治运动和社会风气进行了趣味性揭露和意味深长的讽刺。
比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学院组织学生去警卫室礼堂听会。这个会是宣扬文化大革命的,方枪枪在那个年龄哪里懂得何谓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他只是这样想:“文化大革命——好哇,听上去像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大汇演。文化——那不就是歌舞表演嘛;大——就是全体、都来;革命——就是新、头一遭,老的、旧的不要。这下文工团该忙了。”[1]219这一政治事件在一个儿童的眼里不过就是单纯的文艺汇演,他们远不会想到这一事件对广大知识分子和国家造成的严重伤害。“好哇”更是借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的口吻,不动声色地讽刺了那场运动。小说中方枪枪对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私人体会是:“这些虚张声势的大型歌舞加深了我对浮夸事物的爱好。以大为美,浓艳为美,一切皆达致赶尽杀绝为美。一种火锅式的口味,贪它热乎、东西多、色儿重、味儿杂、一道靓汤里什么都煮了。”[1]248革命样板戏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方枪枪将革命样板戏形象地比作火锅,是以儿童的想象力为准的。作者通过方枪枪的视角间接表现出自己对革命样板戏的浮夸、混杂以及过多粉饰等特质的轻蔑和讽刺。谈到红卫兵运动的时候,方枪枪认为红卫兵们和大人“都是著名的喜剧演员,寓教于乐,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欢乐。”[1]244在方枪枪这样的儿童眼里,大字报及满街游行等“闹革命”的行为就像闹剧和演戏一样,他们并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却也懂得这片“大好形势”里的荒诞性。这正好讽刺了那个年代里的不合理事件和行为——颠倒是非,随意践踏生命,曲解毛主席语录。
对童年的追忆难道仅仅是为了反映那个年代的不合理和儿童成长的心路历程吗?儿童对体制的无视和不屑以及对管制的反抗始终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孩子们大多在父母的期望和压制下成长,大人在物质日益膨胀的快节奏生活里渐渐被框定和迷失自我。作者在小说中不仅揭露出第三代顽主的童年心理成长过程,隐约表现出对人们内心被压制和受管制的忧思,并且借助回忆对现实社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那时全球还没有温室效应这一说,北京的冬天很冷,雪纷飞,我们经常踩着没膝的雪去上学。”[1]211这句话有一语双关的意思:既是对当年刮起的“穷风”的讽刺,也是在说当下的温室效应已经成为一个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描写文革期间上街游行的场面时,作者这样写道:“喜欢那种动辄倾巢出动全体上街没白没黑的旧风俗……我的身体这样好,一贯不锻炼也不生病,和小时候经年累月跟大伙一起猛逛大街有关系,不留神健了身。老是觉得今天的社会没有过去热闹,中华民族好多优良传统都没继承下来。我觉得咱们应该规定全国大中城市每年拿出一天……就叫‘全国见面日’吧。”[1]231这既是对上街游行“旧习俗”作出的讽刺,同时也揭示出当下社会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优良传统的过多摒弃,以及城市居民楼里社会各阶层人们关系的淡薄。
《看上去很美》这部小说借用儿童视角和人称转换的叙事手法,使得小说的内容反映得更深刻,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那个时代儿童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刻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制度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参考文献]
[1]王朔.看上去很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J].文艺争鸣·理论,2009(7):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