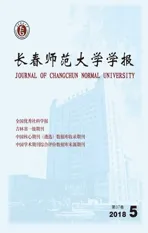洋泾浜协和语与横滨语
2018-03-28宫雪
宫 雪
(大连海洋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3)
一、中国的洋泾浜语概述
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沟通交流的工具。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凡是社会生活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潮,新物质,新观念,新工具,动作,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1]211也就是说,社会环境的改变或多或少要在语言方面体现出来。而语言的嬗变大抵始于异文化的接触或碰撞,其结果基本有三个层次:词汇借用、语言混合、双语现象的产生。洋泾浜语便是语言变异的典型产物。
洋泾浜是清代上海县城北面一条小河的名称。鸦片战争以后,这条小河成为华界与外国租借之间的分界线,人们习惯上将法租界以南到小东门一带称为洋泾浜。关于洋泾浜语的由来,有学者认为,“17世纪后渐流行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特因上海外滩洋泾洪河流域而得名。它是中国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于通商口岸常见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当地人和外来殖民者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彼此妥协而形成的一种临时性交际工具。”[2]101目前,洋泾浜语已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和研究的语言学专门用语,其名称是“Pidgin Language”的音译或俗译,即“皮钦语”或“皮琴语”。该词作为混合语言的代名词,尤指“使用不同语言的若干集团在互相接触、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混合语或称接触语。”[3]85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中国出现过几种洋泾浜语,如洋泾浜英语、俄式洋泾浜语、洋泾浜协和语等。其中,洋泾浜英语出现最早,在中国沿海地区留存了近两个世纪。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在中国与英国、葡萄牙等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洋泾浜英语不同,俄式洋泾浜语虽然也是语言接触过程中的产物,但其本质是殖民主义扩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变异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与掠夺的主要对象之一,沙皇俄国在我国东三省修建中东铁路,强占旅大,久而久之在中东铁路沿线流行起一种“怪话”,即俄式洋泾浜。据杨春宇等人考证,俄式洋泾浜语主要可以分为“音译词”“音译兼意译词”“仿译词”“音译加注词”四种,并且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2]103。俄式洋泾浜语早已随着沙俄殖民势力的消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种语言作为出现在中国的洋泾浜语,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日据时期,中国还流行过一种不中不日的怪胎语言,即协和语。协和语是一种汉语与日语混合的语言表述方式,具有“词汇简化、语言相互混合、语音和语法发生改变”等特点,基本符合洋泾浜语“语言系统简化、缺乏语法的复杂性、词汇经过改造、被赋予新的内容”等特征,因此可以说,协和语是一种日语与汉语混合的“中日洋泾浜语”[4]1。该种语言适用范围广、流传久、影响深,一方面区别于洋泾浜英语、俄式洋泾浜等中欧混合语,是亚洲文化圈语言文字接触和碰撞的体现,接受性、迷惑性更强,语言特点也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该种语言根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能反映出日本在侵华时期进行语言殖民的实态。
综上所述,中国的洋泾浜语起源于不同语言集团的频繁接触、交往甚至是冲突。这些语言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尤其是洋泾浜协和语这种日汉淆杂的语言怪胎,不但是殖民统治的特殊产物,更有理由成为洋泾浜语研究中的一个经典案例。
二、协和语的历史钩沉
在世界近代史上,帝国主义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两种侵略:一种是“武治式”的军事入侵,另一种是“文治式”的文化殖民。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哪一种形态,皆体现为殖民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对被殖民者进行“管控”,从而连带性地促使语言发生演变甚至是异变。协和语便是日本对华文化殖民的一个典型产物。
据笔者考证,协和语在中国的土地上流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该种语言不仅流行于伪满地区,战时侵华日军和日本人所到之处均有协和语的声影,甚至在战时就有日本文化人关注过该种语言并撰文进行专门探讨。如日本文化人中谷鹿二在1925年发表了34回连载,据其所言,“不仅在市内随处可见,除大连之外,只要有日本人居住,无论中国的任何地方,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都‘猛烈’地使用这种不自然的语言。”[5]可见当时此种语言在中国东北大地上流行和蔓延的样态。中谷将此种语言命名为“中日合办语”,顾名思义,即汉语和日语混杂的一种语言。
除此之外,战时还有很多日本人关注过此种语言。有人按照语言特点予以命名,如“日汉混淆变态语”;有人从用途角度对该种语言命名,如“购物中国语”。这种怪胎语言便是协和语。由前文可知,该种特殊语言的流布大抵经历了“大兵中国语”“沿线官话”“中日混合语”三个时期,而它的演变也大致经历了由简单的词汇借用到词汇、语法、语序均发生变化的复杂历程。
关于协和语名称的由来,一种说法是该词中的“协和”二字源于日语词汇“協和”。“協和”的汉语意义为“和谐”,因此协和语本身即有“协和”之意。另一种说法认为,该词源自“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友好相处的‘日满之协和’”[6]107之意。而通常的看法是:该词是因“体现伪满洲国建国精神的‘五族协和’”的口号而得名。
战后中国学者最早论述协和语的文字是发表于1948年的《生活报》上的两篇文章,文章提到:“‘协和语’之所以在伪满流行,是中国人为了迁就日本人能够听懂中国话,而学习日本话的文法、词汇的一种不伦不类、不中不西的语言”;“协和话是日寇十四年统治的产物,是日语和中文语法杂交的变种。”由此可见,战后初期中国方面对协和语的认识:“一是,该种语言与日本侵华有关;二是,此种语言的结构特点是日语和汉语的混杂。”大抵描绘出了该种语言产生的根本原因与语言特点。
那以后至今的70年间,中国方面对协和语的界定与研究基本沿着上述两个脉络进行。而从19世纪80年代起至今,将协和语纳入洋泾浜语范畴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也为数不少,基本观点为:该种语言是日本殖民侵略下,尤其是与奴化教育有关的文化殖民下的一种语言变异,是汉语和日语的词汇甚至语法互相掺杂的洋泾浜语。游汝杰教授认为,“洋泾浜协和语是日军侵占东北期间(1905-1945)在东北产生的一种汉语和日语杂交的语言,其特点是不少词汇和语法结构,尤其是词序用日语(宾语前置于动词)。”[7]225
虽然战后日本方面的研究中出现过“协和语”的字样,但立场和意识形态与中国研究者是迥然不同的,有些学者甚至是刻意回避的。一桥大学的语言学者安田敏朗在其专著《帝国日本的语言编制》一书中提到:协和语只是一种词汇层面的混搭。而据日本学者樱井隆考证,“协和语是中国人之间使用的名称,后被引进日语之中。”[8]13也有日本学者从洋泾浜语的视角研究过协和语。例如,日本学者内田庆市在证明Pidgin时列举“ニーデ、トーフト、イーヤンデ、ショーショー、カタイカタイ、メーユー?”“你的这个我的进上(おまえこれを私にくれ)”等例子,并且认为“这类的语言属于洋泾浜汉语(当时在满洲和军队之间的一定范围内使用的汉语),可以归入‘Pidgin’一类。”内田的举例即为协和语的经典语句,也就是说,内田认为协和语就是一种洋泾浜语。
从洋泾浜语的视角对协和语进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协和语研究的视野。从协和语的定义和特点来看,它确实是一种洋泾浜语。该种语言的使用者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构成特点是日、汉两种语言相互淆杂。从这个角度来讲,协和语与诞生于百年之前的横滨语也有一定关联。
三、协和语与横滨语的渊源
本文探讨的横滨语是指横滨港开埠以来产生的一种横滨方言,而不是指生活在横滨的日本人讲的横滨日语。1859年横滨港开港以后,横滨的国际性贸易活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横滨语也随之发展起来。“‘横浜ことば(横滨语)’是一种英语、马来语、日语等随意结合的产物”,曾担任过英国驻日外交官的萨道义称其为“一种商业用的私生子语言”。
当时中国人以及中国语的活跃是无法忽视的一个存在。据统计,横滨开港以后,来到该地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数量所占比重极大。到1893年时,欧美人数总和才将近中国人总数的一半[9]51。这些中国人中,以买办(欧美人与当地日本人交易过程中的一种媒介)居多,长期活跃在横滨的各种贸易活动当中。日本三井物产第一代社长益田孝曾说:“最初,由中国人担任外国商馆和日本推销商的中介,内外厂商常被他们分隔开来”;“基本上,日本生产者甚至是经理人,都无法见到与之交易的外国人。外国公司中的重要人物当属那些具有隐藏实力的买办。”由此可见,买办担当了当时横滨贸易中的主要角色。与在横滨的外国人沟通时,(中国人)买办使用的自然是洋泾浜英语。“与日本人在贸易中进行接触的不是欧美人,而是中国人。共通的语言是洋泾浜英语。这种洋泾浜英语,不是在横滨产生的,而是中国人在上海等地使用过的洋泾浜语。”[9]52因此可以说,当时中国人使用的洋泾浜英语成为了横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将汉语带到横滨,也带入了横滨语当中。这一点可从《横滨方言演习》一书中得到证实,该书的末章记载过“NANKINIZED-NIPPON”一词,“NANKINIZED”是“南京”或“中国南部的人”,“NIPPON”指日本,合起来就是“中国南部的人讲的日语”。该书还收录了中国人讲的日语,而且证实了当时的横滨中国人使用的日语也是横滨语的一部分,即“横滨语”中确实有中国语的存在。除此之外,《横滨语》一书中记载了从江户时代到横滨开港再到战前·战后产生的新词等共计449个,不但将“中国语·语源词汇”单独列出,还进行了详细讲解。
横滨语中存在大量的中国语成分,日本学者龟井秀雄对此也证实道:“‘洋泾浜日语’、‘横滨方言’和‘私生儿(私生子、杂种、赝品、滥造品)’混合语中的大部分都产生于日本人与中国人交涉的场面。”[10]193由此可见,横滨语和协和语都是一种由语言接触产生的洋泾浜语,而在横滨语中亦能找到中国语和日语淆杂的混合语的影子,这为协和语的追根溯源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首先,从语言构成来看,协和语与横滨语都属于洋泾浜语。洋泾浜协和语的特点是日语与汉语淆杂,如:“他的我的に説話沒有的帰る帰る有”。而横滨语中也有日语和汉语相互借用汉语词汇或者借助中国语进行表达的情况,如:横滨语中的“chi chi amah”的语源是“乳·母(乳·阿妈),以此来表达中国语的“奶妈”之意。从这点来看,协和语与横滨语是亚洲文化圈语言文字的混杂,两者既有日语也包含汉语,是一种中日语混杂的洋泾浜。
其次,从词汇方面来看,协和语和横滨语有重叠的词汇。例如“進上”这个词,意思是“给”,据中谷鹿二的调查[4]4可知,“進上”是战时协和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如:“他的銭給沒有三ビン進上(他没给我钱还打了我)”。而横滨语中也有“進上”这个词语,据《横滨市史》记载,这是中国买办在贸易中对日本人经常说的一个词,即“献上佣金”[11]236-239之意,据日本学者ロング的考证,“進上”等词是横滨洋泾浜日语(横滨方言)的典型词汇。”[11]236-239
最后,从句式方面来看,“横滨语”也叫“アリマス·アリマセン”语,即在结句时,完全使用“アリマス·アリマセン”代替动词进行结句。例如:“アナタ ゴハクリヨ アルナラバ 私 ハイシャク デキル アルか”。同样,协和语中也有很多以“ある”结句的句子。例如:“おくさんやさいゐりませんか、やさいにたあたあある、かふよろしい”、“カンカンよろしいあるか”。这是为了方便交流而进行的语言简化。从二者相同的结尾方式看,协和语和横滨语都能划入中日洋泾浜语的范畴,彼此之间有着极深的渊源。
从“使用者和适用对象都包含日本人与中国人”“语种都是日语与汉语”“具有共同的词汇”“拥有相同的句式”几方面来看,协和语和横滨语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协和语和横滨语都是伴随语言接触产生的语言现象,但协和语的语态特征更加突出,殖民文化色彩也更加浓厚。从洋泾浜语的视角对协和语进行再认识,不但可以为协和语研究开拓视角,也提供了进一步追根溯源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1.
[2]杨春宇,邵大艳.华夷变态:东北俄式洋泾浜语的历史钩沉——东北亚语言接触与都市语言建设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01-103.
[3]薄红昕.从言语接触看语言混合新现象——以台湾多语言现象及“伪满洲国”言语接触为例[J].林区教学,2012(5):85.
[4]桜井隆.日中ピジン―「協和語」への序章[C].浦安:明海大学外国語学部論集,2012(24):1-4.
[5]中谷鹿二.正しき支那語[N].満洲日日新聞(第6009号),1925-02-11.
[6]于湘泳,张守祥.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6):107.
[7]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25.
[8]桜井隆.満州ピジン中国語と協和語[J].浦安:明海日本語(17),2012:13.
[9]桜井隆.ピジン研究における英語とアカデミズムの呪縛—誤解された横浜ピジン[J].明海大学大学院応用言語学研究,2012(14):51-52.
[10]吉見俊哉.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文化政治[M].東京:平凡社,2004:193.
[11]真田信治,庄司博史.事典日本の多言語社会[M].東京:岩波書店,2005:236-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