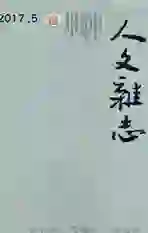中国传统“家”的法哲学表达与演变
2017-06-19彭卫民��
彭卫民��
内容提要 与西方法理秩序中的“无家性”相反,传统中国人以缜密的家内秩序观与完备的家国儒学体系构建起其对“家”的认知图景:作为法哲学基本范式的礼法关系,呈现出“泛家性”的特征,这一特征成为支撑中国传统社会“家者国之则”秩序体系的前提。“家”作为规范性秩序的源发地,不仅是成就身位的场所,更是维系国法的前提。中国传统国家与乡土共同体之间互动关系的演变表明,“礼法”是家内法哲学的根基,家内秩序是政治世界构造的同质性延伸,“家本位”通过“移孝于忠、礼法共存”的介质来规范“家-国”关系中的基本要素。由“家”的法哲学秩序所传递的“先家”“重家”观念,既是理解中国传统礼法关系的切入点,更是重建当代基层伦理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 家 家内秩序 礼法 法哲学
〔中图分类号〕B21;B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38-11
“家”,既是中国人整体观念里概念伸缩性最强的一个象征符号,①也是中国人人格的主要形塑场所。中国人在行动中所表达的法理属性,与生俱来就被贴上“家”的标签。②人被“抛入”与“抛离”他所在的世界,都要借助家的仪则(冠、婚、丧、祭)。③作为一个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④“家”既是权威与秩序的滥觞,又无往而不在各种规则约束之下,其本身就是“秩序”“永恒”“伦理”的代名词。中国文化与政治,几乎全部是在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模式与培育路径研究”(13BKS098);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A级项目“社会管理创新研究”(2012ZDB14);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PY30);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传统‘家的法哲学表达与演变”
① 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亦可见数千年之遗传,植根深厚,而为国民乡导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参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卷39《节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第96册,文海出版社,1996年,第398页。
② 人类学者许烺光(Francis L. K. Hsu)指出,“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实是父子关系的投射。由于中国社会的背景所孕育,中国人的性格因素首先是服从权威和长上(父子关系的扩大)。”美国汉学家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在总结中国人性格中的13种类型时强调,第一类就是“服从权威——父母或长上”,第二类是“服从家庭礼法”。Francis L. K. Hsu,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IL: Dorsey Press, 2008; Wright Arthur F. and D. C. Twitchett,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中译本见许倬云:《中国传统的性格与道德规范》,美国各大学中国语文联合演习所,1968年。
③ “中国古代有冠笄之礼,男二十而冠,女十八而冠,始为成人。但仍是一自然人,必有教,乃成一文化人。中国人重孝弟之道,主要则在未成年前。及婚娶成夫妇,又为父母,乃有齐家之道。家为己之生命之扩大,实亦己之生命之完成。己与家和合成为一体。”参见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三联书店,2002年,第148页。
④ 从“父母子”三角结构来看,家庭的结合是以生物性为基础的。一方面,生物性的家庭必须呈现开放的姿态,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另一方面,这种生物性的双系结合,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否则就无法构成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没有家庭就没有社会,反之,如果先没有社会,也就没有家庭。”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8页;[法]克洛德·施特勞斯:《家庭史: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序,袁树仁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7页。
“家”这一“伦理本位”的观念上建筑起来的。钱穆:《中国文化导论》,三联书店,1988年,第43页;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73页。更进一步说,传统的儒学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一门研究关于“家”在法哲学上的表达与演变的学问,中国传统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都是基于“父子关系”(孝)这一主轴而展开的,可以说“孝”就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价值,是整个儒学道德世界的“社会化”的前提,更是中国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得以维系、沟通的核心。“孝的本质在国家、有司、封建主、父母、老师以及一切有官职的人那里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各自的表述不同而已,而孝的来源,自然是来自于家庭。”归根结底,“孝”在法理上正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体。参见[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3~454页;李亦园:《文化与行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64页;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8页。 而中国的政治组织究其本质更是一种“家长政治”(patriarchy)或家族主义的政治。可参见[日]西山荣久:《中国的姓氏和家族制度》,方兴出版部,1944年,第20页;[日]桑原骘藏:《桑原骘藏全集》卷3《中国的孝道》,岩波书店,1968年,第16页;[日]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卷5《中国论》,筑摩书房,1972年,第316页。
一、“家”在中西法哲学上的各自表达
法哲学与历史哲学的紧密相联,在家庭领域中被抽象为家庭法哲学。家庭法哲学问题往往包含两个面向,即家庭契约的起源与家庭哲学的元问题。Attilio Taddei, Storia Legislazione E Filosofia del Diritto Di Famiglia, Roma: Nabu Press, 2010, p.283.“家庭法哲学适用于普遍的规范原则或标准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影响或关涉作为家庭成员的人。”Laurence D. Houlgate, Family and State: the Philosophy of Family Law, Maryland: Rowman & 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8, P.XⅡ.家庭法哲学在构造逻辑上包含着“结构性”(structural)、“功能性”(functional)与交互性(transaction)三类基本概念。Koerner A. F. and Fitzpatrick M.A.,“Communication in Intact Families,” in A. L. Vangelisti, Eds., Handbook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2004, pp.177~195.
首先,“结构性”强调的是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道德与经济义务。作为一个最基层的单元,家是相互影响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或群体。Burgess E.W., The Family as a Unity of Interacting Personalities, USA: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Organizing Family Social Work, 1926, p.7. 其内包括两个或多个彼此结婚之不同性别的成人,并且包括已婚双亲之亲生的或收养的一个或多个孩子。Murdock G.P,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p.1; George Peter Murdock,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Schmitz C.A., “Social Structure by George Peter Murdock,”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no.2, 1957, pp.309~312; Stephens W.N., The Family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3, p.4.可见,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特定的婚姻形态起着纽带的作用。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正是家族及其在世代意义上的持续,才打破了“自然状态”中人际之间的先天鸿沟,转而从个人的集合(collection of individual)转向家族的聚集(aggregation of families)。[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6页。 其次,“功能性”突出的是家的社会责任与心理功能,为塑造家庭成员的社会角色提供情感与物质的支撑。比如,金耀基说,“中国的家,乃不止居同一个屋顶下的成员而言,它还可横的扩及到家族、宗族而至氏族;纵的上通祖先,下及子孙,故中国的家是一个延展的、多面的、巨型的家(extended,multiple,great family),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都是由家的‘育化(enculturation)与‘社化(socialization)作用加以传递给个人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5页。家族组织往往在自然家族(natural family)、经济家族(economic family)、宗教家族(religious family)以及氏族家族(sib family)四种形态中游弋。Kulp Daniel Harrison,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NYC: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5, pp.112~145.即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单元,它再现了最基础的社会功能。Winch R.F., The Modern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3.再次,“交互性”强调家庭成员通过“爱、敬、忍、恕、严”等情感意识来表达对家庭亲情的认同与延续。中国的家,其实质是建基于伦常关系上的,以父子的互相认同(father-son-identification)作为主轴延展开去的小团体。Hsu F.L.K.,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NY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9, Chapter IX; Hsu Francis L.K.,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91, no.4, 1971.中译本见[美]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王芃、徐隆德译,南天书局,2001年,第51页。家的核心精神就是关怀、沟通、承诺等情感的联结。Levin I., “What Phenomenonis Family? ,”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vol.28, no.3~4, 1999, pp.93~104; Bogenschneider K., Family Policy Matters: How Policymaking Affects Families and What Professionals Can Do, Mahwah, NJ: Lawrence Erl baum, 2002, p.4.通过三种概念的分析,不难提炼出“家”在哲学上的表达:家既是个人理想与价值的反映,又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家既是一个实质的空间,又是一种虚拟的拥有权;家既是外在世界的避风港,又是提供永恒与连续性的场所。Despres C., “The Meaning of Home: Literature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Archi 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vol.8, no.2, 1991, pp.96~115. 家的观念实质上是个人情感的表達与期待。Van der Veen F. and Novak A., “The Family Concept of the Disturbed Child: A Replication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44, no.5, 1974, pp.763~772 .endprint
在前现代的西方法哲学中,“家”这一生存单位,缺位于“个体”“社群”与“国家”之列。在西方伦理中,《荷马史诗》以对家的偏见(如乱伦、通奸、弑父杀母等)为西方人的家庭观蒙上难以祛除的阴影。柏拉图(Plato)认为,家庭这一私人感情的场所妨碍了公共精神,只有消灭家庭才能最终弥合由私人情感引发的各种争端,实现永久和平和团结。因此,他认为儿童应由国家养育,“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457页。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首先在“中观伦理”原则(middle-range ethical principles)上给予了家以适当的伦理-政治地位,“人不仅是政治的动物,也是家的动物”(Eudeminan Ethics,1242a24)。与亚里士多德“家在城邦中相对独立而存在,家庭的‘友爱并非成员之间的‘契约”的观点截然相反,自然法哲学家都相继出来证成“契约”这一家的法权基础。霍布斯(Thomas Hobbes)否定家庭有自然的支配权,认为一切具有统治意味的行为都是人为的结果,人生而平等自由,一切具有权威意味的行动都必有人为的因素。在霍布斯看来,传统的自然秩序,演变成通过订立契约而维系对父权(paternal domination)的“同意”。[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尽管霍布斯承认在人类共同体出现之前存在着自然状态,但是他又强调,世界上一直存在着家庭,而既然家庭是小王国,就排除了自然状态。Hobbes Thomas,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omas Hobbes, Noel Malcolm, eds.,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p.329~332. 洛克(John Locke)则将家庭的权力话语剥离为“父权”(paternal)与“亲权”(parental),反对父母因生育而对子女拥有“自然的”支配权,至于父母对子女应享的权利,并非基于“伦常”而是“义务”,这是因为在自然状态中,“自我保存”先于“保存自己的子女”,家庭契约的维系,依据的是理性与财产权。[英]洛克:《政府论》(上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而孟德斯鸠(Montesquieu)则进一步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细亚国家的家庭秩序原理,是通过恐吓与“极端的隶属性”建构起来的,为了使之尊奉在世的父祖以及死后的父祖,中国的立法者规定了无数近乎苛刻的典礼与仪式。[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67页。这种论断与康德所界定的家庭是“采取物的方式的人身法权”如出一辙。[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为了解开被遮蔽的家的伦理,解救家在道德层面的抽象性和善的主观性,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重新为“家”安置了一个并列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外的制度设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张企泰、范扬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国家观时特别强调,法和道德的东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宣称无需证成地存在,“家”是伦理的真正起源,法哲学第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家庭”。据此,他将中国的国家观归结为“父家长制的家族国家观”。[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2006年,第145页。从西方近代伦理话语中不难发现,“家”是以“无家性”(homelessness)的面貌呈现的,家哲学在西方人眼中就是一个“盲点”。[美]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商务印书馆,2010年。“家”的解构是为了凸显现代社会“个体”的存在,从而巩固个体本位的基础地位。
“家”是西方人哲学视野中的一个盲点,而与之相反,在中国人的法哲学观念中,“家”总是作为一个法理的稳定性、源发性——“家者,国之则”的概念加以体现。孔子在评价晋国铸造刑鼎而弃唐叔虞所创制《唐诰》的做法时,把家推到一个先在于国的位置。孔子说,“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这两句话实际上传递了先秦儒家“家国礼法”观念中两个代表性观点:第一,若先治其家,则国无所不治;第二,若先谨守家礼,则国法无所施于其民。所以孔子在《论语·颜渊》篇中对“仁、智”的构想,实际上既可以行之于国,也可以行之于家,“仁、智一章,不惟治天下国家如此。而今学者若在一家一乡而处置得合义时,如此。”[宋]朱熹:《朱子语类》卷42《论语二十四·颜渊篇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5页。在孔子稍后的时代,“身位、家、国、天下”被孟子明确为是“本正则立、本倾则踣”的关系。在孟子看来,“事君必如其亲,忧国必如其家,爱民必如其子。”[宋]朱熹:《论孟精义》卷1上《学而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页。这一观点,正是先秦时期“修、齐、治、平”思想以及“道之以德、政”与“齐之以礼、刑”思想的一种延伸。
二程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家的法哲学的先在性。程子提出“家者,国之则也”的学说,认为家庭的秩序不仅先在于国法,而且是国法施行的前提,“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与先秦儒家的主张略有不同的是,程子不再仅仅把家庭秩序理解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是扩大为一种自然的秩序,这种秩序有时候表现为教化风俗的德礼,有时候表现为具备“防闲”功能的“法度”:“治家者,治乎众人也。苟不闲之以法度,则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伤恩义,害伦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闲之于始,则无是矣。”[宋]程灏、[宋]程颐:《周易程氏传》卷3《家人》,中华书局,1981年,第885页。这种秩序被程子称为“仁义”,它包含了一切可以称之为规则或者法度的东西。在阐释《学而》篇有子的论述时,程子更进一步指出,“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謂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宋]程灏、[宋]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6《论语解·学而》,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3页。这种主张,将“仁”作为德礼与法刑的上位概念,“仁义”是四端之首,是天理之性,人若知仁义,就能以天理统携规则,以秩序致良知;“孝弟”是“仁义”的表达手法,“孝弟”之所发,既可以说是恪守家庭法度,又可以说是推致天理良知。
朱熹继承程子“家者,国之则”的思想,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进一步发挥程颐的“仁”说,把德礼的修养作为由家及国的先决品德。朱熹认为,家庭组织及其规则具有先在性,“士人在家有甚大事?只是着衣吃饭,理会眼前事而已,其他天下事,圣贤都说十分尽了。今无他法,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自家只就他说话上寄搭些工夫,便都是我底。”[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20《朱子十七·训门人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2886页。冠、昏、丧、祭之礼施于家是家政,施于国是国政,施于天下是天下之政,“天子诸侯之礼,与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学之语”。[宋]朱熹:《朱子文集》卷60《答潘子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23页。家政体现的是父子、兄弟、夫妇在家礼中各自的角色处理,“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为政”。[宋]朱熹:《朱子文集》卷62《答李敬子余国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23页。所谓先在,即天下之名分以国之名分为先,国之名分以家之名分为先,因此说是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
中国的儒家学说认为,“家”是同时承载着天理与人伦的场所。国法之本在家政,国家主义的建构应当遵循两条路径:一条是明确家是宇宙秩序的发源地,国法是家礼所衍生的一种规则;另一条是治国者必须首先懂得治理其家,然后才有资格治理其国。中西方关于家的自然秩序的论证,最早是一致的,其路径则截然相反,但在现代性开始之后,几乎又是殊途同归,即家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东西方,都呈现出萎缩的姿态。
二、传统家国关系中“礼法”哲学的演变
“礼法”是中国古典自然法体系的核心要素与经典表达,是中国“法哲学”的独有发明。“礼法”可以分为“无体”之礼法与“有体”之礼法,言其理,止于尊大其教;言其象,足以轨范于人。“礼法”起于“大一太极”,这个理玄之又玄,故谓“无体”之礼法,而“有体”之礼法在于心以统性统情,重在人定法的践履,人定法即礼的外部表达。“无体之礼,冥然天地之自然,而圣人制礼,所以立无体之用也。夫礼自外作,本在于内,虽有不易之道,而外必尽可陈之法,是以法之在度数也。”[宋]林之奇:《周礼讲义》序,[清]朱彝尊编:《经义考》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1997年,第398页。不管是法家、儒家还是墨家,都认为礼法之本义是天道人情的反映,“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管子·心术》)“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先王之书所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墨子·非命上》)中国传统法哲学是承担礼义强制性功能的结果,而其归于道,是先王所指定的道德律。
中国法哲学中的“示民常”,是礼义适用于刑罚政教的根本旨归。所谓“有德礼,而刑政在其中。”[宋]朱熹:《朱子语类》卷23《道之以政章》,中华书局,1986年,第549页。一则以道德仁义教化于将然之前,一则以法度律令禁于已然之后。礼有法的自然属性,也有法的实体属性,故“礼之规矩森严,度数详明,存诸心则易慢不入,足以杜人之非心逸志也。”[清]黄以周:《经训比义》,第2册卷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8a页。只是两者所表现的形式略有不同,只有“无体”之礼而无实体之法,只有实体之法而无“无体之礼”,礼之德与法之实必须相得益彰,“法制者,道德之显尔。道德者,法制之隐尔。天地之心,生生不穷者也,必有春夏秋冬之节,风雨霜露之变,然后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结于民心,而无法制者为无用。无用者亡。有法制系于民身,而无道德者为无体。无体者灭。”[宋]胡宏:《胡宏集》卷1《修身》,中华书局,1987年,第10页。大约“法”之器即为“刑”,法之“道”即为“礼”,“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于是乎制礼”。[明]黄裳:《周礼讲义》序,《经义考》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1997年,第396页。在礼法未分之前,二者合而为一,既是治教手段,又兼有政刑功能,故因天地之大美,达而为治教,因四时之明法,达而为体政刑事。究法之义,其质本于礼而其义与礼同,“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其致一也。”(《礼记·礼运》)可见礼义是创制人定法的根源,“道判为万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说之大法。礼者,法之大分,道实寓焉。圣人循道之序以制礼,制而用之则存乎法,推而行之则存乎人。”[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序,《经义考》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1997年,第393页。而法哲学为礼义的附属,“夫法本既定,而理则素定,人固可欺,而心难自欺,矧可生可杀。虽君之职,而或命或讨,乃天所为。是必功之等也,付以司勋之掌;法之平也,归于廷尉之持。虽云二柄之我出,必使众心之共知。”[清]阮元辑:《声律关键》卷5《刑赏与天下画一》,民国宛委别藏钞本,第1a页。所以说,礼法本无二分,最初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概念加以呈现的。
礼法的结合是先王治理家国的根本手段。这一点在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以致家国太平之迹的典故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举凡天地日月、山川城域、礼乐刑政、夷狄鸟兽,在《周礼》之书上都分门别类,各得其宜,所以上自朝廷,下及閨门,相率约于礼义准绳之中,而文度蔼然。作为家国治理的“致太平之书”,《周礼》同时也是礼法结合的典范,礼典也即法典,礼义也即刑兵。周代制刑之原意,在于德礼之大经,“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尚书·吕刑》)故法禁明著,若悖于德礼,则是暴行而非威仪,“或为轘裂鼎镬,炮烙菹醢,剥面夷族,以威天下,若是类者,非礼之刑也。”[宋]李觏:《李觏集》卷2《礼论第五》,汉京出版社,2004年,第13页。礼教的主要精神是人伦道德,人伦道德又是法理精神的价值所在,“凡制五刑,必即天伦,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礼记·王制》)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儒法尚未二分之前,“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人定法的精神被先设于礼义之中,法哲学是礼义的一部分。儒家主张“国法先观于家”。如《诗经·思齐》盛赞周文王治理国家之前,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孔颖达疏引毛亨传曰:“文王能敬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又能施礼法于寡少之适妻,内正人伦,以为化本。复行此化,至于兄弟亲族之内,言族亲亦化之。又以为法,迎治于天下之家国,亦令其先正人伦,乃和亲族。其化自内及外,遍被天下,是文王圣也。”[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16之3《思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4页下。此处的“家”,即天下之众家。正因为文王治国,先自齐家始,所以,孔子意欲在《礼记》中构造出“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家国一体”政治图景。
在礼法模式的支配下,先秦时期的“家”并非指同居共财的家庭或亲属,而是指拥有封地与封爵的封建贵族,兼具战斗、行政、祭祀和财产等多项功能的共同体,近亲血缘团体的家庭荫附于其下。所以先秦时期的“家礼”实际上也就是“国礼”,其卿大夫氏室的家、族属关系可以借由《周礼》中的公卿士大夫之礼加以调整。比如“都宗人”与“家宗人”就是掌管采邑中家族礼仪与礼器的职官。大约在春秋时期,代表诸侯政权的“国”与代表卿大夫政权的“家”开始形成二元分立,但二者实际上都具有“公”的意味,这与后世庶族的家庭性质是不一样的。春秋战国以来,西周原有的国、野界限渐渐地消弭,士庶开始合流,相当多的士转为农民,在家庭构成上,父母和若干已婚兄弟共居的联合家庭渐渐多了起来。按照法國学者图德(Todd)对家族形态的理解,家族制度的应有状态,受地域的政治意识形态制约。家族关系处在亲子与兄弟关系的十字坐标体系中。从亲子关系来看,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两种价值模式;从兄弟关系来看,存在着“平等主义”与“非平等主义”两种价值模式。在这四种价值模式的主导下,家庭关系在累世同居的共同体家庭(反馈模式)与独立建制的直系家庭(接力棒模式)之间不断地演进与变迁。转引自麻国庆:《儒学与社会主义》(发言稿),《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秦火之后,汉初所传礼书的内容以及宿儒对礼经的理解基本都局限在“士礼”层面,而朝廷的礼典与宗庙的祭祀仪制却付之阙如,“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缪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汉]班固:《汉书》卷22《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5页。从经学的层面来看,尽管儒家不得不承认家国礼制间存在差异,残存的士庶礼制无从推及于国,但同时也间接说明法家学说中以家庭作为配角来维护国家绝对权力的观点也已经失效。士礼中关于冠、昏、丧、祭的叙述只通行于士庶家庭。随着儒法整合,德刑并用,儒生对于国家礼典在重建过程中的呈现方式以及编纂体例始终未达成共识,因此具有国家法典效力的礼典迟迟不能建立。为了改变这种家-国关系“脱嵌”的现状,继续周代国家“制礼作乐”中“亲亲、尊尊、贤贤”的民彝思想,儒者们试图在士礼与王礼之间寻求可以类推的逻辑,其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便是汉章帝四年在白虎观经学会议上,皇帝与儒生一起以国家的力量将“三纲六纪”中的家庭伦理部分(如父子、夫妇、诸父、兄弟等伦理关系)上升为天理国法,确立了“君臣法天,父子法地,夫妇法人”[汉]班固:《白虎通疏证》卷8;[清]陈立疏证:《三纲六纪》,中华书局,1994年,第375页。 的纲纪名教制度,以形成“闺门之内,俨若朝典”[清]赵执信:《礼俗权衡》,齐鲁书社,1993年,第583页。 的稳定的国家礼典的原则。
西汉后期,农民家庭规模变得更为细小,农民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基本上不见“联合家庭”。具有“公礼”性质的“家礼”礼典开始上行,转化为统治教化天下的国家礼典,而随着儒学士族的兴起,规范外在行为的“家训”便成为了士族自我延续地位的重要家庭法。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台湾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3页。士族兴起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即不专用先代高官厚禄为其表征,而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侯。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页。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士族各家制定家礼(家仪)且行之成文的例子极多,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家族法典重在修身遵礼,强调保全自身而非成就国家,它们反映着特定家族内部所遵循的规约,亦即一家之律法,即所谓“自为节度,相承行之”(《颜氏家训·风操》)。国家建立在士庶家族群之上,而士族之家却渐渐掌握自己的律法,这种律法强调要突破法哲学意义上的男尊女卑、良贱差别。孝道思想在此一时期被普遍推行,从而逐步形成了重“孝”轻“忠”的社会风气,这实际上说明了“魏晋风度”突破了先秦礼法的规范模式。六朝士族通过日常礼仪,努力维持家族之间的秩序,也努力维护家门的安定,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的隋唐时期仍在盛行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士族宗族”,这些大家族、大宗族之间的门阀观念表现在不同宗族之间的高低、贵贱与高门士族内部的尊卑上下之分,禁止嫡庶之间互相通婚,严格地规定谱牒的纂修等方面。可参见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8~257页;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79页;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尽管如此,受到先秦士观念的影响,家训中依旧蕴含着某种“公”的特质。这里的“公”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即门阀贵族把门第当作获得社会地位出发点的同时,在原有封闭的家庭之外,还有对国家开放的所谓公的一面;另一方面,维持整个家族生存意义上的“公务”相对于兄弟之间偏重于自己小家庭的“私情”而言。所以,家的概念在魏晋时期既具私家的一面,也具有公共性的一面。公与私在对立的过程中,公必须真正超越了私才能成立。一个家族不仅仅是私房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能够超越自我封闭,进而向着更大空间发展的家族集团。[日]谷川道雄:《六朝士族与家礼——以日常礼仪为中心》,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6页。与此同时,这种公的性质使得士子们意欲将礼治的秩序、责任与精神传播开来,公布于天下。中古时期所形成的家族礼法(如孝行、仁恕、义断等),虽然具有维护门第的“私”的性质,但是在功能与意义上,士族礼法十分重视礼教秩序,为士大夫群体所认同,这实际上也让家礼具有了公法的涵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治家实践,既是对先秦儒家所主张的“正家而天下定”(《易·家人》)义理法律观的一种重新解释,又是对法家“尽力而守法分,尊主而不敢顾其家”(《管子·明法解》)思想的一种彻底否定,所以,崇尚家庭的自由生活态度也致使魏晋时期的士人通过制定各自的家法来取代追随古代圣贤所制定的单一性标准。
“礼法合流”的局面在唐宋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制度与文本的协调推进体现在家族制度的“礼法合一”“教化为先”“惩恶本欲人惧”等思想上,这也间接导致“大家族主义”的衰落及“宗法主义”的兴起,这与西方中世纪的“联合大家庭”向“主干家庭”的转变颇有几分类似,即史学界所谓的“渐进核心化”论。P.Laslett, eds.,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NY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随着唐末五代十国的动荡,唐代门阀制度瓦解,士族地主受到战争的影响,为了确保累世屡显,门阀永固,开始将目光集中于家规家训的各自表达,因此“家法”在唐代士大夫群体中颇为流行,其目的主要是为宗族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服务,至于完全为调节家内人际秩序家族礼法,则不多见。大致来说,唐代是一个从家风为主到成熟型家法族規过渡的时期。王善军:《宋代宗族与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维持”家道的观念在唐代士大夫群体中颇为流行,其目的主要是为宗族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服务。其最主要的手段,还是重在强调透过家族成员关系的理解来确保家礼价值的传递。
唐宋之际,士、庶人将维持家的长盛不衰与闺门礼法紧密结合在一起,礼法与家学的传承是士庶之家内在文化的特征。比如宋人胡寅(1098-1156年)就说,“汉、唐而后,士大夫家能维持累世而不败者,非以清白传遗,则亦制其财用,著其礼法,使处长者不敢私,为卑者不敢擅。凡祭祀、燕享、婚丧、交际,各有品节,出分出赘之习不入乎其门,而相养相生之恩浃洽于其族也。”[宋]胡寅:《斐然集》卷21《成都施氏义田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439页。礼法对家的维系,实际上是对国家主义构造的另一种方法论的反思,而宋人对“家国天下”的理解,即认为“国法之本在家政”。一方面,国法是家政的拟制,“家国天下”的生成顺序是“孝然后友,友然后政”,[宋]朱熹:《朱子语类》卷24《论语六·为政篇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594页。即国家的治理以家庭秩序作为蓝本;另一方面,家政又是一切规则的发源地,中国古代“经礼三百”囊括了一切国家与社会的礼制秩序,但在宋人看来都不过“只是冠、昏、丧、祭之类”,[宋]朱熹:《朱子语类》卷87《礼四·小戴礼》,中华书局,1986年,第2243页。四礼中所蕴含的人伦关系与法则,是推行王政必须首先参考的基本底线,从家庭秩序的缩影中,可以管窥国家生活的行动逻辑。唐宋之际,从国家《刑法志》表彰基层家庭中的孝义行动来看,家国关系的儒法学说界限已经不再如两汉魏晋时期那么色彩鲜明,“圣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国,国而之天下也,建一善而百行从,其失则以法行之。故曰,‘孝者天下之本,法其末也。”[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95《孝友列传递一百二十》,中华书局,1975年,第5592页。“家、国、礼、法”的关系,在此时也不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学术难题。尽管如此,从唐代的几则官员因为家事而“破坏”国礼的案件中,仍旧可以看到家国礼法关系并不是一个可以绝对化、简单化的概念。贞元八年(792年),将作监元亘负责荐享昭德皇后王氏(?-786年)庙,但斋戒时,适逢其家人忌日,元亘依据《假宁令》“私忌日给假”条例,未参加斋戒。但是此事则遭御史弹劾。德宗皇帝召令尚书省与礼官、法官集议此事。尚书左丞相卢迈(739-789年)认为,“谨按《礼记》云,‘大夫士将祭于公。既视濯而父母死,犹是奉祭也。又按《唐礼》:‘散斋有大功之丧,致斋有周亲丧,斋中疾病即还家,不奉祭祀。皆无忌日不受誓诫之文。虽《假宁令》忌日给假一日,《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今亘以假宁常式,而废摄祭新命,酌其轻重,誓诫则祀之义,校其礼式,忌日乃循常制,详求典据,事缘荐献,不宜以忌日为辞。”依国家礼法典而言,私忌日可以不行斋戒,但是依据《左传春秋》经义则元亘必须受罚,最后集议的结果是,“由是亘坐罚”。参见[宋]王溥:《唐会要》卷23《缘祀裁制·贞元八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55年,第445页。
宋代以后,社会变革以及士大夫挽救礼法时弊的决心使得礼秩得以“下行”,贯彻儒家亲亲尊尊、父慈子孝、夫贤妇随的基本精神,可以说它进入了地方社会的伦理生活,此即30年来明清史学界所谓的“地域社会论”。德国汉学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与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Ping-ti Ho)将其归纳为近世中国家庭“向下的社会流动”理论。明清之际,具有基层功名的社会精英开始深化经营地方与家庭,而中高层官僚家庭的社会流动也开始逐步基层演进。参见Eberhard W., A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3;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266;[美]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由于进入统治阶层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明清之际的精英开始转而卷入地方事务,通过强调儒家礼仪的研究(尤其是丧葬礼)来强化各自家庭与宗族的秩序与伦常,进而确保他们在宗族组织治理中的支配地位。Brook T., “Funerary Ritual and the Building of Lineag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9, 1989, pp.470~471.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随着明代初年朱学被定为一尊,朱熹《家礼》一书中的诸多主张被国家礼制所采纳,使得家族秩序中的祠堂制度、士庶冠昏礼及品官丧礼等通过地方精英们的推动反过来影响国家法制。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宋元以后文献传播水平与速度的提升,《家礼》被视为规范民间社会的唯一经典,其在明清礼学中已然获得了“经”的地位。围绕着《家礼》一书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家礼学”,伴随着家礼书籍的广泛刊刻、流传,在宋代以后的一千年时间里,朱子的礼法思想被中国家庭视为独尊。从而导致出现“二千余年天下相为守法,独康成郑氏及朱子之书耳”以及“自宋以来,民间所尊尚,但知有朱子《家礼》,不知其他”(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本》序)的局面。《家礼》适用于家与宗族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比如,家礼中的孝道观、悌友观、义利观等以及具体的冠、婚、丧、祭仪式;对宗族男子孝行、悌友义举以及其他生活角色的影响和定位;宗族祭祀礼仪模式的建构以及祠庙祭祖的形式与变化;地方志民俗资料以及民间社会中礼生对《家礼》婚丧仪式的吸收等。可以说,《家礼》主导了宋元以来宗族制度与理论的方向,比如宗族形成的原因、宗族乡约化、国法与家礼的关系、家庭宗族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轨迹等。士大夫在国家政治层面,推动国家礼制不断地采纳家礼的礼法制度;在地域社会层面又不断地接受并革新家礼的家族观念。
从中国传统家庭形态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家”在法哲学上总是呈现出一种二元的对立与妥协,“家庭既建立在生物性需求之上,又受某些社会方面限制的制约。因为,如果每一个生物性家庭都形成一个封闭的世界,自行繁衍,社会就无法存在。所以,家庭总是在天性与文化之间来一个妥协。”[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第2卷):现代化的冲击》,袁树仁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6~8页。中国人对礼法作用于家庭的发明,正好对家庭如何在“天性”(常)与“文化”(变)之间妥协的问题作出了解答。其中的“常”是关于家族秩序有效维系的哲学思路,而其中的“变”是关于家族结构及其社会关系所呈现的不同姿态,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和合”,就必须理解礼法的适时性。
可以说,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呈现为一种贵族式的组织架构,表现的是一种倡导门第与私礼意义上的“积极的大家族主义”;宋代以后,中国的家则呈现为一种新官僚政体与“敬宗收族”的礼法制度相结合的“消极的宗法主义”。“由礼仪教化民俗”这一课题也成为宋代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在学术上的兴奋点,“家”的法哲学话语日趋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与“庶民化”意识,同时制礼者宣称庶民修礼认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国家层面“崇化导民”,而事实上也彰显了士族在“起家”的过程中试图永葆家族不堕的用心。
三、当代家内法哲学秩序的失落与重建
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断裂”。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这使得现代人对于家的理解已经在形式上全然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4页。近代之前的中国家族,承续着宋代家礼的基本精神,但是随着近代以来战争的频仍、女权主义的大兴、“国故”的自污情结以及现代性话语的引入,传统家制在极端个人主义的挞伐下,开始上演一出“娜拉离家出走”(Nora)的话剧。现代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家庭被边缘化,重家的合法性也遭到排斥。[加]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彭铟旎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192~193页。国人对于家族、家庭以及家礼大多采取激进的批判姿态,认为维系家族的规范是“吃人的礼教”“家庭乃万恶之源”,熊十力:《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336~337页。 因此,“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汉一:《毁家论》,张枬、王忍之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第917页。
近百年以来,“国家被不断地奉为至上,而家族维系力则极为薄弱”。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民国丛书》,第3编第13册,上海书店,1946年,第96页。“民族社会的单位既不是家庭,又不是个人,而是笼统的社会全体,更准确一些,是挟全体名义来驱策每一个人的国家与政府”。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民国丛书》,第2编第19册,上海书店,1929年,第92页。其中主要表现在外国资本與中国社会的变化,农村贫困与农民家族的缩小、都市中家族制的崩溃、婚姻与家族的法律观一扫而空。陶希圣:《婚姻与家族》,《民国丛书》,第3编第15册,上海书店,1934年,第96~108页。家迅速地自“父子中心”转而为“夫妇中心”,家族制度一经向着横的方向(夫与妻)发展,其必然的结果是轻视家系与消灭家风。上层社会开始出现“奢侈的抑制”(Luxury Check)与“经济的最高额”(Economic Maximum)等忽视代际关系的口号,近代家族制度也只能渐趋欧美式的小家庭模式。李树青:《蜕变中的中国社会》,九思出版社,1978年,第140页。而所谓的宗族制度徒具虚名,既无权力,又无财产。近代以来,宗法制度颓败,后世之人散无友纪,家在整个国家社会中的地位被不断贬低,国人自利其家的意识甚至被认为是政治不昌、国家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国”与“家”呈现二元的、对立的分裂局面,“今日政治之不善,中国人重视其家之习,有以为之累也。国家之任官,将使之行国家之意也。而今之官吏,无不为财来。故缺有肥瘠,差有美恶。彼直商贾耳,安暇奉公?其所以如此者,皆家之累也。今日人人重视其家之习不改,一切皆无可望,亦不独政治也。”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民国丛书》,第5编第19册,上海书店,1929年,第59~60页。
传统家族礼法的衰落在公社化与“文革”时期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有学者将这种冲击称之为“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家庭伦理对家庭成员的“保护”功能遭遇冲击,家庭的依附感被“单位”所取代,转而被卷入“政治动员”的狂流中;家庭成员被“政治符号化”,成为“阶级斗争”中的“揭发”者或“敌视”对象。“儒家伦理被抨击并以集体化公社取代家族农业,集体化时期压抑了家族主义的进取精神”。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三联书店,2000年,第310页。亿万个家庭被狂热地动员起来,造成了中国在一段时间之内进入了无序的状态,传统家礼中那种“爱敬之实”“名分之守”的本体价值转而成为父子反目、兄弟阋墙。而重要的是,今人对于传统“家”构造的想象,被活生生地隔断,国人从此在这一问题上造成了群体的失忆。
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家”几乎已经处于一个失去传统道德与文本制约的境地。经济理性进入家庭,构成对家庭责任的冲击,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导致决策的分散化,个体意识的强化使得“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39、259页。家长权威维系力的衰落,家族成员对大家族主义风习的抵触、诚信丧失、公德沦落、人伦沦丧,而仁爱、宽厚、勤俭、尊长、慈幼等传统被视为草芥,中国千万个家庭“碎片化”、成员“原子化”,城市家庭离婚率不断上升,赡养纠纷、房产纠纷不断增多,而维系农村家庭的组织与人力纤维被隔断,人们正在经历道德与伦常的真空期:道德领域一直处于传统家礼礼法体系被解构的状态,以宗族与信仰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被解体,而新的、富有建设性的家庭秩序却无从重建。
事实上,作为在现实中维持着“同居共财”关系的同宗者的小集团,中国传统的家更多地是从观念上被建构起来的。[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8~60页。中国传统的“家道”,是整个儒法体系中关于“天理节文”与“仪文度数”之间、“治之道”与“治之具”之间、儒法“政治价值”与“政治主张”之间如何自洽、自处的问题。质言之,家内礼法秩序的衰落与人们对家的法哲学的认知模糊有着根本的关联。忽视了“家”的哲学建构,就会导致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最基本的秩序缺位。所以,要重建家内秩序,就要在国家治理与家庭伦常之间,寻求一个基本的平衡。天性是不可以变更的,而文化则随时而变。所谓不能变者,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需要变者,即维系家的礼法哲学要与时俱进,随时代的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这种“常”与“变”的思想,既强调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而在具体政策措施层面主张“应时”,又同时将基本政治价值的追求构建于寻求先王之道的“复古”色彩。
首先,家的法秩序是一套“独行”的、“先在”的系统。所谓“独行”,即“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这是两套并行不悖的程序。士人格、致、修、齐的实践及其适用的规则,都应该首先在家庭内完成,家庭组织及其规则具有指导性。冠、昏、丧、祭之礼施于家是家政,施于国是国政,施于天下是天下之政。家政体现的是父子、兄弟、夫妇在家礼中各自的角色处理。所谓“先在”,即天下之名分以国之名分为先,国之名分以家之名分为先,因此说是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系辞》)这一自然理性之中就已經蕴含着父子、夫妇的家庭伦理,这个伦理是一个先在于国政的系统。
其次,家礼与国政是同一套价值系统。家内秩序之本的基本逻辑是,“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所谓“成教于国”,是指政事之施在其中(家)”。换言之,在我为孝,则天下人皆知孝;在我为弟,则天下人皆知弟,推而广之,所谓孝者事君、弟者事长、慈者使众,事父与事君之理相同,事兄与事长之理相同,慈幼与使众之理相同,三者能修于家,三者自然也能成于国,“此道理皆是我家里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于国。”[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6《大学三·传九章释家齐国治》,中华书局,1986年,第356页。
再次,家为国之本。家庭并不参与国家的治理,家庭之治的目标是植德积善,而治国平天下之事,“卿大夫以下盖无与焉”。之所以不应以家庭伦理参与国家治理,是因为家的秩序是本,国与天下的构造只是对家的参照,故本不可与末。正如朱熹所说,“以家对国与天下而言,则其理虽未尝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无等差矣。”[宋]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3页。所以家礼是一切礼制的先在秩序,一切礼制都应首先以家内秩序伦理作为行动的合法性基础。
总之,要重建当代的家内法哲学秩序,必须在“法义”上确立:(1)“家”是秩序思维、日用伦常的场所,是各类社会规范性价值的源发地;(2)重建“家”作为人性价值观念再生产以及培育公共品质的基本单位;(3)在家庭秩序重建过程中,要保留“爱敬之实”的个体主义德性论而审慎对待宗法共同体的等级观念;(4)国家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合作治理,应当参照家内秩序的逻辑规则并以其为基本前提。
四、结论
中国古代的“家”所蕴含的礼法秩序,是个人、社会、国家形态存在的前提,而并非全然是过去学者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同心圆结构”或“投射/折射”等理论。在神圣的“家”中,指导中国人正确行动的德性得以孕育,规范社会的秩序得以生成。“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规范性源发地,承担着建构“心智心力”与“权力话语”的基本功能,这是对近50年来中国史学界“家族国家观”理论的一个补充和修正。
中国人对“家”的认知与构造,不是依据法权意义上的契约与权义,而是基于礼法意义上的自然关系的表达。家的法哲学表达与演变进路,包含着两汉及魏晋时期的“公私分离”、唐宋时期的“士庶再分”、明清时期的“定于一尊”、近代以来的“离家出走”以及当代社会的“无家可归”。在这种演变过程中,中国人非但不排斥身位在家与族中的主体地位,反而凸显个体仪式是家庭法则的先决条件。由家及族,由族及国,由国及天下关怀,构成一个有序的外扩结构。人本主义社会的道义制裁,不是外在的上帝,而是内在的良知;每个人身体的来源以及对权力的尊奉,不是神道与契约,而是天理与人伦。
“家”的法哲学表达,意味着“义理”与“秩序”分别在“体”与“用”的层面充当着维系家国儒学长盛不衰的角色;家的法哲学的演变,意味着中国古人致力于推动这种二元理论有效地在地域中“下行”与在时空中“播迁”,以此来确保家的永久合法性。质言之,中国传统“家”的法哲学,是一种“父子兄弟足法,而后人法之”的“先家”“重家”思想。
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民族研究院、西南政法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