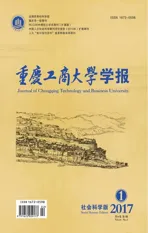论希腊科学精神及其在中世纪的继承*
2017-03-23刘铮
刘 铮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论希腊科学精神及其在中世纪的继承*
刘 铮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希腊的科学精神表现为理性的批判和论辩传统,以及超越功利性的自由学术精神。这一科学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并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和发展。中世纪对希腊科学精神的自觉继承和弘扬乃是促成近代科学诞生的必要条件,中世纪的大翻译运动、大学和神学家-自然哲学家团体以及唯名论者的挑战则为希腊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思想训练。
希腊;科学精神;基督教;中世纪
一、希腊的科学精神
英国科学史学者G·E·R·劳埃德(G.E.R.Lloyd)认为,西方科学最早源于古希腊人,虽然在古希腊并没有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这一词,但古希腊人最早试图通过始终如一的方式来解释自然现象,开辟了古希腊的知识论传统。在劳埃德看来,古希腊的最主要贡献就是“自然的发现”(discovery of nature)[1],他后来又称之为“自然的发明”(invention of nature)。
之所以说古希腊人“发现”自然,乃是因为米利都学派最早地区分了“超自然”和“自然”,认为自然现象受到有规则的因果规律支配,从而把神从自然现象中排除出去了。在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念中,自然界不仅是有活力和有灵魂的,而且也是一个有运动和有规则的世界。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希腊思想家把自然中心灵的存在看作自然界中规则或秩序的源泉,而规则或秩序的存在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2]4
正因为如此,米利都学派开创了理性的批判和辩论传统,这与古希腊城邦中公民的政治生活是分不开的。在早期希腊哲学家那里,相互批判、相互竞争的风气几乎随处可见。因此,在劳埃德看来,“米利都哲学家们取得的成就不是清晰完整的知识体系。……他们的成就在于拒斥了对自然现象的超自然解释,并在那样的情形下开创了理性的批判和辩论活动。”[1]12正因为如此,在古希腊人那里,人们才能通过理性来“发现”自然的规律,从而达至真理。
而之所以说自然是“发明”的,在笔者看来是因为古希腊人对自然的独特理解和观念。正是因为对自然的独特理解和观念,使得古希腊人能够运用理性的精神来探索自然界的运动和规律。古希腊人对自然的独特理解和观念,并不仅仅是区分“自然”与“超自然”,而且也是赋予自然以“本性”的意义。在柯林伍德看来,古希腊人的自然观念并不像我们现代人那样认为自然就是自然物的“集合”(collection),而是一种“原则”(principle),即“本源”或“本性”[2]52。因此,探究自然就意味着探究其不假外求的内在本源;这就意味着自然界作为“自身涌现”的整体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目的,人们通过理性得到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是最高等级意义上的知识,因为它们最接近理念世界的真理。人工物也就不能等同于自然物,人工物只不过是对自然物的拙劣模仿。这种超越功利性的、对知识内在性的探求也就构成了希腊的科学精神。“超越任何功利的考虑、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就是希腊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在其他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这样的精神气质。”[3]正是借助于这种超越功利性的、诉诸理性和具有批判性的自由科学精神,依据于内在知识的演绎推理,古希腊人才发展出了一套依据于数学(几何学)的自然观念和宇宙观念。
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该学派希望从数中找到万事万物的原理。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是“最早试图为有关自然的知识提供量化的数学基础”,并对日后科学的发展至为关键[1]23。甚至,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对数的演绎,认为“天界是一个音阶和一个数”,天体的运动造成和谐而听不见的音乐,整个宇宙即是这种和谐有序的宇宙。这一和谐宇宙观为古代宇宙图景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发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念,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借助几何化的“理型”来解释万事万物的基本结构,正是因为不变的几何“理型”,才造就了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柏拉图相信,科学的目的在于理解变化多端的经验背后不变的抽象定律,而作为最纯粹的关于“形式”之科学的几何学能够为人们揭示出世界的真理。因此,在柏拉图那里,天文学就是精确的数学科学,他区分了纯粹观测的天文学和由“问题出发”的天文学。纯粹观测的天文学圄于感性经验的材料,无法得出理念世界的真理,而从“问题出发”的天文学则是抽象的、数学的天文学。在这种关于抽象的理念科学的结构中,具体的天文现象和通过演绎推理得出来的理念结论相符与否似乎并不太重要,因为“真”意味着必然如此,古希腊人实际上是通过某种解释学的策略来使得实际观测与理念结论相符。这种解释学策略或通过哲学的观念消解,或通过基于几何学的数学模型消解。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人历来有天尊地卑的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天界与地界迥然有别,天界(月上界)是永恒、纯净和不变的,地界(月下界)是有朽、杂乱和变化多端的。天体则镶嵌在天球上做匀速圆周运动,因为“正圆”被看作是最完满的图形,行星周而复始围绕地球运转。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古希腊人往往把经验现象解释成与其理念世界相符合的现象,或者根本不承认经验现象的合法性。比如,古希腊人往往把彗星现象解释为大气现象,从而消解了变化多端的彗星现象与月上界纯净和不变的理念观念的冲突;古希腊人也不承认太阳黑子的存在,认为太阳本身是纯净的天体,所谓黑子无非是人们看花了眼[4]。
上述例子都是通过既有的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自然哲学理念对一些实际观测作出辩解,但是,仅凭既有的自然哲学理念无法完满解释行星的逆行,即古希腊人所谓的七个行星(日、月、金、木、水、火、土)的不规则运动。柏拉图所说的“拯救现象”(save the phenomenon)就是试图从几何学上“拯救”七个行星的不规则运动。柏拉图试图说明的是,“行星的不规则运动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如此,其实是由其本身匀速而整齐的运动组合而成的。”[1]79由此,古希腊人则通过引入“同心球模型”“本轮-均轮”体系以及后来的“偏心匀速点”(equent)等复杂的几何学技术来把看似不规则的行星运动化解为规则运动的组合,从而试图完成柏拉图所谓“拯救现象”的任务。
因此,正是通过这种出于理性自由的内在的演绎推理,使得古希腊人对自然观念和宇宙观念的“发明”得以发展并完成,也奠定了古希腊人超功利的、为求知而求知的自由科学精神。古希腊人的这种科学精神,亦为后世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二、中世纪对希腊科学精神的继承
科学史的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没有作出重大贡献。传统观点所谓中世纪是“黑暗的中世纪”,即是说中世纪并没有继承多少希腊的理性科学精神,基督教和中世纪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体系被视为新科学诞生的主要障碍。
但是,这种传统观点并没有考虑到中世纪科学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形,用现代人把科学和宗教的理解强加到古人身上,并盲目地把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看不到近代早期科学的产生有其深厚的、根源于中世纪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把中世纪看成是黑暗的和“铁板一块”的科学史解读模式无疑是一种“辉格主义”(whiggism)。
在美国科学史家爱德华·格兰特(Edward Grant)看来,不论中世纪是否像迪昂所论证的那样与希腊科学和近代早期科学具有一种“连续性”,至少中世纪的社会-文化背景为近代早期新科学的诞生奠定了背景前提。笔者则认为,格兰特所说的作为“背景前提”的基督教、大翻译运动和大学的诞生为希腊科学精神的继承创造了条件,并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基础。
(一)基督教与希腊科学精神
流俗的观点认为,基督教在打压科学上有很大作用,这其实就是把基督教会的某种反常做法强加到作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督教之上。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西方基督教史的大背景下看,对自然哲学的偶然回击(比如13世纪初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巴黎被禁,或者巴黎主教颁布1277年大谴责)仅仅是相对次要的反常情况。”[5]105
众所周知,基督教是在罗马国家的传统中孕育而生的,“新约全书是用希腊语书写的,因此基督教一开始就已经带有两希文明(希腊和希伯来)相结合的痕迹。”[6]在格兰特看来,基督教传播缓慢的特征使它从一开始就与异教文化(特别是希腊-罗马文化)相互适应,这就使得基督教本身并不排斥异教学术,异教学术反而成为众多基督徒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因而,“希腊罗马文化和学术虽然有时会受到质疑,但并不会被当作敌人,其潜在的用途早已被认识到。”[5]12
而这种潜在的用途就是利用已有的异教成果更好地为解释和理解基督教信仰服务,这一“婢女说”并不是对异教学术的打压,而只是甄定了相对于《圣经》启示和基督信仰而言,异教学术的从属地位。事实上,大翻译运动和大学的诞生为希腊科学精神的复兴和自由学术创造了条件并提供了制度保障。中世纪神权与王权相互独立的体制也始终没有使拉丁西欧形成像拜占庭或者伊斯兰文明那样的政教合一的体制,这是大翻译运动得以迅猛开展和大学得以生根发芽的更根本的社会因素。
(二)大翻译运动与大学的创立
如果非要说中世纪是“黑暗的”,那我们至多只能说中世纪的前500年是黑暗的。蛮族的入侵和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使得拉丁西欧渐渐地疏离了希腊学术精神和学术成果。公元9—10世纪,大量的希腊科学典籍被大规模译成阿拉伯文,使得希腊的学术遗产在阿拉伯世界生根发芽,这份遗产跟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渐渐传回西欧,促成了开端于11世纪、并在12世纪和13世纪达到高潮的大翻译运动。正如格兰特所说:“从1125年到1200年出现了一次真正的拉丁翻译高潮,它使相当数量的希腊和阿拉伯科学重现天日,13世纪还会出现更多的译本。”[5]32
这场大翻译运动使得希腊学术成果——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系统地翻译回西欧并得到系统地研究。吴国盛认为,这场大翻译运动也促成了欧洲在中世纪后半叶的第一次学术复兴,并为三百年后的文艺复兴以及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和观念基础[6]。这里所谓的制度基础,就是大学的产生和发展。
大翻译运动重新激发起了人们的求知欲望,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发展,大学这一行会“联合体”(universitas)得以产生和发展,大学成了自由学术精神的制度保障。在笔者看来,大学对于希腊科学精神的继承有两个方面:一是“经院论辩”成为大学教育之锁钥,这继承了古希腊理性批判和论辩的传统;二是传统的“自由七艺”在大学的艺学院的教育中得以发展更新,这继承了古希腊人超越功利性、为求知而求知的自由科学精神。
具体来说,在中世纪的大学建制中,论辩成为大学生活的常态并逐渐被制度化。论辩更多地可被看成是学术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辩分为常规和非常规两种。常规论辩由教师定期举办,并要求学生参加,在这种论辩的练习中,学生逐渐获得了未来任教的宝贵经验,学生通过答辩裁定后,获得相应学位。非常规论辩即“自由论辩”,自由论辩是面向社会的公开性的论辩,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听众可以提出刁钻的问题为难主管教师,听众不仅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解答问题,很多试探性的回答也被提出了。
正是源于中世纪的大学中广泛开展的论辩传统,才发展出了“疑问”(questio)这一在自然哲学中频频使用的形式,它“源于评注,但在结构方法上又类似于口头论辩(这是中世纪大学教育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它实际上是教师在课堂授课中讲解的问题的文字版本。由于具有论辩的结构,疑问形式的文献和分析几乎已经成了中世纪‘经院方法’的同义词。”[5]156中世纪的自然哲学通常由一系列的疑问形式和议题组成,而数学也在中世纪普遍应用于自然哲学问题,这种对数学的运用通常只是假设性的,与经验研究无关,只是依赖于逻辑论证的“一些基于任意假设的纯形式练习”。也就是说,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对于检验假说性的结论是否符合现实世界也根本没有兴趣;而这种对数学的运用和理解,与古希腊人用数学模型去理解世界的方式不谋而合。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继承了古希腊以降的理性批判和思辨传统。
另一方面,古希腊自由人的传统“七艺”学科(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在中世纪随着大翻译运动也被大大丰富和更新了。在大学的艺学院,课程教育以自由七艺为基础。在中世纪,艺学院的教育与神学院的教育往往有着不同的分工,艺学院教师往往不被允许涉足神学议题,艺学教育的种种逻辑推论——无论与基督信仰有多乖离——只要坚持是“假说”而不实际信仰为真大抵就不会受到什么阻碍。这充分说明了中世纪大学相对地学术自由。因此,中世纪大学的艺学课程得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发展起来,这些课程实际上与社会需求相脱离,是纯粹为了求知而求知、为了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训练。正如格兰特所言:“中世纪大学的艺学课程之所以被发展起来,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实践需要。它源自12、13世纪的翻译活动所带来的希腊-阿拉伯思想遗产。这份遗产由一批理论著作组成,它们需要就其本身的价值进行研究,而不是出于实用或赚钱的目的。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并被波埃修等人加强的古代传统非常强调对学术的热爱,强调为知识本身而获得知识。……中世纪的教师和学生对此都表示赞同,这也相应地决定了中世纪大学的特点。”[5]63
(三)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内在张力
由于艺学院的教师不被允许涉足神学领域,探讨神学议题成为了神学教师的“专利”。又由于大部分神学教师具有艺学硕士学位,他们在艺学和神学领域都具有学术训练,因此他们具有相当的学术自由把自然哲学应用于神学,并把神学应用于自然哲学,并形成格兰特所谓“神学家-自然哲学家”团体。由于具有更多的研究自由,这一“神学家-自然哲学家”团体能够突破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思想教条的束缚,做出大胆的假设和结论,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带来了内在的思想活力,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希腊科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吴国盛认为,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恰恰为经院哲学注入了内在的思想活力,“一方面,经院学者们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正统地位,可以自由地研讨异教学术所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基于上帝全能的唯名论思想,又可以大胆挑战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的种种理性教条。”[6]这是因为,唯实论者的思想理念预设了共相先于个别事物存在,这就意味着上帝通过理念范畴(共相)创造个别事物;在这里,上帝宛如一个理性秩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换句话说,上帝不可能做有违于理性和逻辑之事。但是唯名论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个别事物先于共相存在,共相只不过是人类理性的抽象名称而已;在唯名论者看来,唯实论者的观点会限制上帝的全能,上帝既然是全能的,就能够为所欲为,做出有悖于人类理性和逻辑之事。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唯名论者的想法,提出种种假设性的论题(比如虚空是存在的、可能存在多个世界、宇宙是无限的、世界的中心不是地球等等)在客观上挑战了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教条。
因此,不仅像格兰特所说的那样,大翻译运动、大学的诞生以及神学家-自然哲学家团体是促成近代科学产生的背景前提,而且在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者的挑战也为科学革命提供了神学动机和观念前提。
三、结语
如果说,近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那么,若没有对希腊科学成果和科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科学革命必定不可能发生。换过来说,如果没有中世纪的大翻译运动、大学和神学家-自然哲学家团体作为背景前提的保障,对希腊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从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的思想巨擘们身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对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继承与融合。哥白尼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还是一个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具有太阳崇拜的情节,“正是由于太阳有着超越的完美和价值(它是光和生命之源),哥白尼才把中心位置赋予了太阳”[7]26。开普勒不仅像古希腊先贤那样相信宇宙的数学秩序与和谐,而且他也是一个虔诚和具有异端倾向的基督徒[7]53。伽利略直接宣称自然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上帝就像一位几何学家,把世界彻底数学化[8]63。牛顿一生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神学领域,“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位虔诚的、笃信的基督徒”[8]245。在牛顿那里,宇宙不仅仅是数学化的,而且也有其宗教起源,上帝具有创造和维护宇宙秩序的功能,“正是由于上帝,事物结构之中才会具有那种智慧的秩序和规律性的和谐,从而使事物成为精确认识和虔诚沉思的对象。”[8]250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中世纪对希腊科学精神的自觉继承和弘扬乃是促成近代科学诞生的必要条件,中世纪的大翻译运动、大学和神学家-自然哲学家团体以及唯名论者的挑战则为希腊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思想训练。
总之,正是中世纪对希腊科学精神和科学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建立了背景前提和观念前提。科学不仅有其人文基础,而且有其宗教基础。从科学革命时期的思想巨擘们身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科学与人文、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融合。中国当下的科学素养教育往往遗忘了科学的人文本质和宗教根源,甚至一味把科学与人文、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也就错失了对科学之本质意涵的理解。科学思想史正为我们重新思考科学的本质及其与人文和宗教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1] 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M].孙小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2] 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M].吴国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吴国盛.科学精神的起源[J].科学与社会,2011(1).
[4] 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J].北京大学学报,2015(4).
[5] 格兰特.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M].张卜天,译.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6] 吴国盛.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J].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5(1).
[7] 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M].张卜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 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张卜天,译.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责任编校:朱德东)
On the Greek Scientific Spirit and Its Inheritance during Middle Ages
LIU Zheng
(DepartmentofPhilosophy,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The Greek scientific spirit was included in the traditions of rational criticism and debates, and the free academic spirit beyond any material interest.This kind of scientific spiri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and was able to inherit and develop during the Middle Ages.The Middle Ages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Greek scientific spirit can be seen a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birth of modern science.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the universities, the theologian-natural philosophers’ organizations, and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nominalists not only can be seen as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Greek scientific spirit, but also can be seen as institutional assurance and mental exercise of the Greek scientific spirit.
Greece; scientific spirit; Christianity; Middle Ages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1.016
2016-10-21
刘铮(1989—),男,山东高密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科技史研究。
B502
A
1672- 0598(2017)01- 0117-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