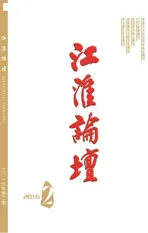论左联政治文化生成的基础*
2016-12-08魏正山
魏正山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论左联政治文化生成的基础*
魏正山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左联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与进步知识分子在国统区群体合力之下产生的一种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诉求,也是将革命的理论及其意识形态扩大为社会共识的有机互动。上海作为左联的发生地,为其政治文化的生成提供了最适宜的理论基础、阶级基础、传播基础及外部基础,这对于左联政治文化生成的发生来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与一种历史合力的内在安排。
左联;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生成基础
左联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与进步知识分子在国统区群体合力之下产生的政治文化现象,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又一个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引领武装军队和“文化军队”的新时代。作为左联政治文化的发生地上海,也取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大量精英知识分子和中共力量相继汇聚于此,在他们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成为左联政治文化生成的理论基石。同时,上海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以及阶级觉悟的逐渐提高,为左联政治文化的生成奠定了阶级力量,而出版行业的繁荣以及租界内法律保障、言论自由形成的公共舆论的批评功能,则为左联政治文化的生成提供了传播进步思想的物质支持和话语空间。这一切对于左联政治文化生成的发生来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与一种历史合力的内在安排。
一、左联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知识分子来说,1927年是一个痛苦和迷惘的年代,也是一个值得深思与反省的年代。政治形势的骤变,引起了人们对革命的重新审视,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政治运动碰壁,凸显了它幼年时期的弱点和不成熟,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及众多革命知识分子无不认识到政治运动必须有理论指导,然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11,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更有利于中国社会接受新的思想,对中国革命来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11。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革命的成功示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性方案,无疑刺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使得“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3]。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就已通过多重途径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深入。1928—1930年间,翻译出版的马恩著作就有《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近40种[4],列宁的著作以及唯物辩证法的研究著作也相继出版。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秘密出版机构无产阶级书店,被查封后又成立华兴书局,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他革命书籍。为积极配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及发行,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就提出:“党必须有计划地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共的书店,学校,通信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5]1929年的中国翻译出版界,刮起了社会科学翻译出版的劲风,“社会科学的书籍,遂如雨后春笋,普遍于全国”[6]。
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理论,更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行动指南融入当时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和革命现实中。1928年前后发生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唯物史观的倡导等一系列理论探究,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社会史领域,其根本指向都是检讨和反思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革命,它的前途将在哪里?中国应该走何种道路,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前提?甚至作为中国革命主体的革命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和主体形态——这些都是“大革命”过程中凸显的问题。一系列与现实交织的论争与思考,既是对革命的呼应,更是相对独立的对革命的思考、反思、想象甚至是批判,不仅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及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抗性的集体表现,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合法空间与理性想象。
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关注之前无暇顾及的文化领域,致力于建设文化领域中的联合战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俄国掀起的“红色革命”在本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它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道路指引和良好的空间氛围,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学工作者竞相追随。1930年3月2日,在中共力量的促使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在上海成立,制止了1928年以来关于“革命文学”在文艺领域内的过激斗争。它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队伍,而且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新进程,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一翼。值得注意的是,“左联”在政治上支持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艺术上致力于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建构框架,正是其政治文化的思想路引,而“介绍外国已有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加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宣传”[7]也自然成为左联所要肩负的使命。左联成立初,鲁迅、冯雪峰等左联盟员就将《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论》、《艺术与文学》、《文艺与批评》、《文学评论》、《致敏娜·考茨基》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论引入中国,并在革命实践和文学实践的互动中,通过“翻译的政治”的方式逐步地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内涵和现实意蕴。特别是左联的第二份决议中“必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研究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及理论和批评”[8]的指向,也从侧面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文艺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作为中国革命思想核心的无产阶级意识,不是一次性获得的认识,而是一种思想机能,把握中国革命“意识”意味着打破一切“意识形态式”地看待现实、思想和行动方式,意味着不断在实践与思想的互动中确立辩证关系。对塑造左联政治文化来说,往往在文化领域产生根本的政治动力,而政治又赋予文化以现实的形态。左联政治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不仅是现实处境的要求和抉择,同时也是革命理论框架下将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理论注入中国革命的实践。这是政治上尚处于年幼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艰苦努力,打碎旧文化,努力走出一条改变中国文化面貌新道路的勇敢前行,左联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也随着左联所肩负的光荣使命,深深地扎根在马克思主义的土壤里,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完成自身政治文化理论的自我生成与历史构建。
二、左联政治文化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外围组织,左联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而当时的上海则是中国工业和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也是与资产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方。1900—1910年,上海有500人以上规模的工厂就有46家,共有工人76051人,其中外资企业18家,雇佣工人36030人,占中国工人总数的48%。[9]时至1920年,上海的机械工人有231485人、手工业工人212833人、运送业工人116250人、服务性行业工人3200人,共计563768人。[10]而当时全国约有工人261万[11],仅上海一地的工人就占全国工人的1/4。又因租界的存在,上海成了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掠夺的大本营,1930年、1931年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分别有42.8%、46%集中在上海。[12]9外国资本的投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如技术、设备、资金、交通、电力等近代工业、商业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使上海形成了较好的投资环境。1932—1933年间,全国各种现代工厂2435家,1200家在上海;上海工人占全国的43%,工业产值占全国的50%。[13]1932年,有67家近代银行的总行设于上海,占所有银行资本的63.8%。[14]1933年,上海直接对外贸易总值也占据了全国53.77%的份额。[12]9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俨然已经成为经济繁华、无产阶级工人人数最多最密集的现代大都会。
不可忽视的是,工人阶级虽然“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5],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却十分低下,每天超负荷工作,收入却非常微薄。1920年的《星期评论》就曾报道:“工厂劳动者的工银,平均差不多只得二角五分至三角,月收不过九十角。至少要假定有两天缺工的损失,月收就只有八十四角。”[16]时至1929年,以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全勤的规划计算,上海男工、女工、童工的平均日工资为0.73元、0.44元、0.34元,平均月工资分别为21.9元、13.2元、10.2元。[17]然而对大部分工人家庭而言,仅依靠男性户主1人的收入已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家中的子女不分年龄都得外出帮同做工。作为无产阶级主体的工人阶级生活依旧贫苦,他们渴望改变现实生活状况,不再遭受剥削和压迫,他们身上所具有革命性是彻底的,这和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彻底的革命性不谋而合。
早在“五四”时期,上海产业工人就已经萌生了阶级意识,“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不下11万人,连同店员、手工业工人7万多人,共18万人。紧接着就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开始‘三罢'斗争”[18]。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震撼了整个中华大地,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传播,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广泛展开。从“五卅”运动开始,上海工人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人运动的情绪也步步高涨,这导致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刀锋转向工人阶级。在白色恐怖之下,大量的产业工人被加以共产党的罪名,工人罢工遭到武力压迫,在国民党组织“工统会”成立的9个月内,上海工人被杀害的有2000多人,被逮捕的有万人以上。[19]面对高压的政治环境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上海的工人阶级仍然坚持自我觉悟的立场。中共六大后,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党中央提出工人运动在行动指导和组织形式上的策略:重视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学会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和能够利用的合法条件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也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1928年下半年,上海发生的94起罢工中,由资本家方面引起的占32%,由工人反抗引起的占60%,斗争结果,工人完全胜利的占25%,相当胜利的占19%,失败的占13%。[20]在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中共在工人中的影响逐步扩大,工人阶级的运动不仅此起彼伏,而且有章有法,他们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获得胜利,并动摇了国民党的高压统治。
可以说,工人阶级作为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作为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最为革命的运动的领导力量,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有了最坚实最可靠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着现代上海的繁荣而日益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他们反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抗争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压迫,他们无所畏惧地走进了历史的长河,与左联的政治文化运动相互辉映,刻画出中国革命现代化进程中最绚丽的景致。
三、左联政治文化的传播基础:上海出版行业的繁荣
上海出版行业的黄金时代与租界的话语环境为30年代左联政治文化的发展搭建了一个现代舞台,成为左联向外界发出声音的重要途径。1930年,上海图书杂志出版机构有145家、印刷机构达200家之多。[21]很多书店都分布在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的各条马路上,除了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的昆仑书店、光华书店、现代书店、开明书店等一批中小型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大出版机构也汇聚于此。这些书局很多都由民间资本投资,租界的商人利用租界特殊的环境,投资左翼文化出版销售事业,左翼的书和杂志成为读者购买的焦点。现代书局发行的《大众文艺》、《拓荒者》,光华书局发行的《萌芽》、《新地》,湖风书局发行的《北斗》,北新书局发行的《沙仑》等左联期刊受到读者的喜爱,有的一出版就会销售一空。很多新开的书店以及当时老牌的出版机构相继出版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书籍,如昆仑书店出版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南强书店出版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1册)等。
相对于图书出版机构,上海的报业发展也进入了大众传播的媒体时代,受众的范围也由社会上层群体扩充到中下层群体。《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等成了许多作家、名家艺术精品的园地。同时,上海还存在着大量的外埠出版机构,截至1932年,上海存有的外来报刊中日报10家(全国共43家)、周报22家(全国共27家)、双周报3家(全国共5家)、月刊21家(全国共23家)、季刊6家(全国共6家)、年刊1家(全国共6家)。[22]此外,1934年,上海报业还出现了英、法、德、日、俄等外文报纸15种之多。出版行业的繁荣,不仅丰富了上海现代都市生活,还为中西不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等多元话语,提供了比较、竞争、交流、融合的舞台,也助力左联积极参与出版的实践过程,在参与话语博弈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现革命话语的现代力量。
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号召战斗的无产阶级,应当“创办自由的报刊”,就是要创办“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23]的报刊,左联成立前,列宁这一思想就已经在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界广为传播。自1930年1月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鲁迅、冯雪峰、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就在上海创办了大型文学杂志《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左联成立后,不仅吸纳了上述期刊,还先后创办了《文艺讲座》、《巴尔底山》、《文化斗争》、《世界文化》、《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等刊物,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主导力量。事实上,左联创办的这些刊物不仅同构了左联政治文化的传播载体,而且也为之后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营造了更加广阔的话语空间。
四、左联政治文化的外部基础:租界内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1930年的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一个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一个号称“东方巴黎”的传奇,一个与传统中国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24]香水、高跟鞋、法兰绒套装、电影院、咖啡馆及跑马场等众多西方现代化的物质和生活方式,以极大的力量吞噬着上海也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西方世界对中国输入商品和生活方式时,也带来了殖民的附属品——租界。从政治上看,作为殖民产物的租界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于法无据,于理难言。在殖民主义者的巧取豪夺下,上海租界成为中国封建政府、军阀统治下的权力薄弱点,成为封建政府、军阀政府与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进步人士之间的缓冲地带,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进步势力的发展。从社会发展来看,租界不仅给上海带来了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造就了上海优越的文人思想和多元的文化品格。租界内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促使相对自由气氛的产生,为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动的空间。租界也成为近代新型文化知识分子的重要聚集地,他们竭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各种文化壁垒,为开辟革命文化的思想阵地积极奔走。
30年代初期左联的组织活动也正是借助上海租界内特殊政治环境逐步发展起来的。1930年2月16日,左联全体筹备委员会在公共租界内的公咖啡馆(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口)秘密集会,商讨成立左联事宜,之后的集会及联络地点也往往选择租界,租界内的“行政管理权及其他一些国家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不受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25]。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政策的国统区之外,上海租界成为左联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中间地带。
上海租界为左联政治文化的存在提供了自由宽松的政治语境,租界当局执行相对言论自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家的创作提供良好的环境。相对于租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华界的政治环境要严酷得多。国民党当局采取高压政策进行文化“围剿”,取缔进步书刊,赤裸裸地以反革命姿态出现,大量剥夺和限制进步文艺作品和刊物的出版。国民党政府在30年代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钳制言论自由的文件,如在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之前,“代表反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一切自由刊物,差不多都遭封闭,《社会科学讲座》、《新思潮》、《文艺讲座》、《萌芽》、《拓荒者》、《大众文艺》、《巴尔底山》等已经明令禁止,此外暗中扣留不准发卖的更不知多少”[26]。1931年10月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25条,对《出版法》的原则和办法加以具体规定;次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发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指出凡宣传共产主义,便被认为是反动的。面对国民党文化高压政策的“围剿”,左联成员和中国共产党采用了灵活多变的策略和方法,通过不断改换刊物的名字和作者的笔名、借用大众通俗读物、宗教宣传、谐音、改变书刊的外在样式、刊登广告、向商业性质的文艺刊物投稿以及把刊物办得“灰色”一点(即邀请非左联成员写文章,如《北斗》刊物)等策略和方法迷惑国民党当局的审查,与国民党当局周旋。经过伪装的书籍和报刊,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增加了国民党审查的难度,为突破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密网提供了可能。由于上海的特殊格局,租界当局和华界当局对思想文化的禁忌各有不同,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也不尽相同,造成了上海思想文化的活跃空间要比中国其他地方更加宽阔,加之上海文化事业的发达和生存环境的优越,以及租界内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共同为左联政治文化的存在构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
左联作为时代文化思想的标杆,在国统区传播了理想,促成了波澜壮阔、蓬勃发展的局面,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这个历史奇迹的背后,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进步知识分子在国统区群体合力下产生的特有的政治文化,一种现代意识与社会建制充分结合的充满“革命现代性”的政治文化。革命现代性光环聚焦下培育出的革命所必须的土壤,以及在其滋润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上海出版行业的繁荣、租界内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都为左联政治文化的生成提供内了动力和现实的可能。历史的事实证明,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进步知识分子在国统区群体合力之下产生的特有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播下了进步的火种,并且在民主革命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集聚了重要力量。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71.
[3]胡适.建国问题引论[J].独立评论,1933,(77).
[4]张太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J].中共党史研究,2011,(7):121.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266.
[6]吴亮平.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意义[J].世界文化, 1930,(1).
[7]潘汉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J].拓荒者,1930,1(3).
[8]冯雪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J].文学导报,1931,1(8).
[9]王关兴.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3):22.
[10]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J].新青年,1920,7(6).
[11]刘明逵,主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22.
[12]唐振常,主编.上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3]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0.
[14]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2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730.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
[16]戴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J].星期评论,1920, (48).
[17]张忠民.近代上海工人阶层的工资与生活——以20世纪30年代调查为中心的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2):6.
[18]苏智良,江文君.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J].历史研究,2011,(3):134.
[19]金应熙.从“四一二”到“九一八”的上海工人运动[J].中山大学学报,1957,(2):76.
[2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41.
[21]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9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5904.
[22]蔡铭泽.《向导》周报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51.
[2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64——665.
[24][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4.
[25]费成康.中国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84.
[26]潘汉年.本刊出版的意义及其使命[J].文化斗争, 1930,(1).
(责任编辑无逸)
D092.6
A
1001-862X(2016)02-0091-00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KS026);2014年度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2014yks115)
魏正山(1986—),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