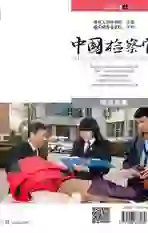《刑法修正案(九)》加大行贿犯罪打击力度规定研究
2016-05-30赵崇杰
赵崇杰
内容摘要:《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具体表现在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体系,将罚金刑纳入其中;严格行贿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降低行贿犯罪逃脱处罚的可能;扩大行贿犯罪的对象范围,有力地回应了严厉打击行贿犯罪的现实需求。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 行贿犯罪 罚金刑 从宽
一、完善行贿犯罪的财产刑规定
《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罚金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也必须与犯罪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相适应。行为人在实施行贿行为时,必然要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因素,同时也受需求法则的支配。决定行贿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有两个因素:一是实施行贿犯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二是预测行贿犯罪将受到的刑罚处罚。现实中,行贿人之所以敢铤而走险,就在于其犯罪成本低于犯罪收益,很多行贿人犯罪后被轻缓处置且不会被判处财产刑。因此,要有效遏制行贿犯罪,关键在于增加行贿人的预期成本,使其行贿成本大于预期的犯罪效益。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罚金刑的修订有两处:一是在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原有刑罚基础上均增加了“并处罚金”的规定。其中对单位行贿罪实行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判处刑罚的同时也并处罚金;二是在第390条有关行贿罪的规定中增加规定“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规定相比以往有很大进步,但仍有完善空间,以后仍需要从健全行贿犯罪刑罚体系的角度考虑,进一步增加罚金刑在行贿犯罪中的适用空间。
在贿赂案件查办过程中,行贿人通过贿赂官员获得了巨大利益,但因立法缺失不能对其进行经济处罚,未免有失公平。增设罚金刑符合刑罚平衡理念和公平正义原则。其一,从刑罚功能上看,行贿犯罪分子在受到人身处罚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受到制裁,增加了犯罪成本,实现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其二,从刑罚体系协调性来看,现行刑法对行贿罪的处罚以短期自由刑为主,把罚金刑引入到行贿犯罪的刑罚体系中,且在各档次法定刑中均规定“并处罚金”,能够充分发挥罚金刑与自由刑并科的互补惩罚功能,使行贿犯罪的刑罚体系更加完备、科学,更利于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
二、严格行贿罪从宽出罪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严格了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将第390条“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特别减免规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这一修改使得行贿犯罪从宽处罚实现了梯次设置,对行贿人的处罚将更加严厉。
第一,从轻或者减轻规定与自首规定相契合。《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后第390条款与此相互呼应,但《刑法》原第390条有关“对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行贿人,都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对行贿犯罪做了降档处罚,无“从轻处罚”这一量刑档次。通过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情况看,没有从轻处罚的规定,既不利于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行贿人科学量刑,又使行贿人在以行贿手段从受贿人处获取利益的同时,通过与司法机关进行“辩诉交易”获得风险成本利益,无形中放纵了行贿犯罪,以致催生更多的腐败犯罪,不利于源头治理。
第二,免除处罚规定与立功规定相契合。《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原第390条规定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就可以免除处罚,较第68条的规定更宽泛,反映了宽纵行贿、严惩受贿的反腐策略,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多行贿犯罪因种种原因被豁免。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免除处罚条件与第68条的规定相一致,要求免除处罚要以具备刑法规定的法定情节为前提,即犯罪较轻的,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小,对其免除刑罚可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基于刑罚的层次衔接角度考虑,设置行贿犯罪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梯次,更能彰显行贿受贿并重打击的立法主旨。
第三,行贿犯罪出罪条件设置严格。《刑法修正案(九)》第390条规定,只有在行贿人犯罪较轻且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免除处罚。而对于主动交代犯罪较轻的行贿人,揭发检举行为只对侦破普通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对侦破重大案件起一般作用,或者行贿人有重大立功表现,但犯罪较重的,均不能免除处罚。此条款的严苛设计摧毁了行贿人认为行贿数额越巨大,交待后立功也就越大,也就越可能免除处罚的梦想,充分反映了刑法重拳打击行贿犯罪的决心,行贿犯罪轻刑化处罚将成为历史。
三、扩大行贿犯罪的入罪对象
《刑法修正案(九)》在第390条后增加一条,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构成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这一规定扩大了行贿人员入罪范围,使行贿犯罪的法网越织越密,彰显出从严打击行贿犯罪的决心。
第一,扩大入罪对象的法理依据。《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现行刑法没有设置相对应的入罪条款。从刑法理论来看,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关系,对合关系犯罪具有对合性、犯罪性、法定性三方面属性,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功能上存在对向性,双方主体各自实施行为,彼此补充,相互呼应,形成统一整体,二者的对合关系要求立法上要配置相应罪名。从罪名完备性上看,行贿受贿在特点、规律上的相似性、关联性,决定了对二者的罪名、刑罚设置的协调性和必要性。考虑当前反腐力度的强化和刑法罪名完备化的现实要求,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利用特殊关系行贿罪被纳入定罪范畴,既符合刑法犯罪对合关系原理,又是反腐败现实的必然要求。
第二,扩大入罪对象的立法渊源。《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刑法修正案(九)》又增加了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这些罪名均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内容设置,既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内在要求,也使我国反腐败立法与国际社会形成有机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公约要求缔约国应将此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构成了将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重要立法依据。
第三,扩大入罪对象的价值所在。《刑法修正案(九)》将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的行贿对象扩展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员及离职工作人员等。其意义在于:其一,此类人群均是会对国家公职人员用权行为产生影响力的人员,将对此类人群行贿行为纳入刑法调整之列,势必对行贿人产生强制威慑力,可遏制贿赂的上游犯罪,对于预防职务犯罪产生积极效果。其二,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依然要求具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构成要件,但随着刑事司法实践不断发生变化,我国法律、法规和各类规章制度的日益完善,以行贿方法获取的能够为法律和政策承认及认可的正当利益会变得越来越少,有利于对行贿犯罪的侦查、取证,也更能实现从整体上预防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