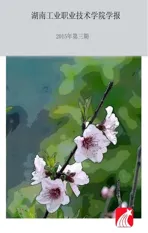从“两个缪见”看“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2015-03-29熊尧
熊 尧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一、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在后人长期的运用及不断升华中,成为后世对文本解读的主要途径之一。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操作来看,很多时候甚至是唯一途径,其根深蒂固的地位自是不言而喻。清人顾镇曾这样表述:“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虞东学诗》)。顾镇对“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结合起来阐释的:通过对文本字面意思的理解(即“意”),再联系作者所处的“世”,这样就可以推导出作者的“志”来。这种对作品的解读方法是我们中小学时期老师教导的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后再结合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阅历来体会文章中心思想的源头。孟子的这种思想用在文学批评中操作步骤是通过文本,读者逆推出作者的真实意图。然而,文字作为创作者思想的载体,有时客观上并不一定完全能够传达作者的创作动机。由此而论,某些时候也会把读者正确还原作者的真实意图引入不正确的道路上。“作家的复杂性决定了创作动机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不同的作家就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目的,因而就有不同的创作动机。”[1]
二、作者创作动机的不确定性
我们先试着来看一下著名文艺理论家瑞恰慈在剑桥大学文学系执教时做的一个教学实验。他把一些除去作者名字的作品打印稿给学生,请他们做完理解并评价后返还,其结果让他大为吃惊:这些有志于文学研究的名牌大学的高才生,虽然受过良好而又系统的传统文学研究的训练,但是对大家们的作品大都持否定态度,反而对那些二三流的诗人却大加肯定。对于这样的结果,瑞恰慈认为传统的先讲作者再论作品的研究方法会诱人产生一种敬重权威的感觉,这种先入为主的权威感定然也就形成对作品的一种公式化的解读。瑞恰慈的这个实验就和“以意逆志”形成了对立。在这个实验中,缺少了“知人论世”的辅助,整个对作品的解读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导致这种“偏差”的原因,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分析:这些著名的作者应该是当代的居多,而且和学生年龄差别也较大,因为已逝的作家的作品对于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学生想必陌生的很少,这些作家的成长经历和接受实验的学生成长经历相对会有隔阂,心理上产生代沟也属正常;那些二三流作家则刚好相反,年龄接近一些会更容易在心里产生共鸣,评价自然也就会更高。
作家的创作动机是否可以“以意”去“逆志”呢?通过上面的实验呈现的现象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再看对“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理解,有人认为“伊人”是梦想中的另一半,有人却认为还可以理解为人生理想;再比如“烽火连三月”,有或是三月份,有或是三个月(形容战事惨烈且持续时间长)的理解;“悲凉楚大夫”,有人为是指屈原,有人说是宋玉。这些不同的理解没有一个完全让人信服的理由,就造成了一些含混的理解。“许多诗歌研究者穷尽毕生之力于析义辨疑上,他们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明确的:必须确定一义,即使证据不足,某些歧解只能存异,但作者只有一义入诗,我们也只能以一义解之,如果一时无法选择,世世代代的文学研究者总有一天能恪尽其职”。[2]这种存异,不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桩公案,而且还让我们在还原作者的真实意图时,显得很是为难。不过在这种存异和为难中,争论的产生却促成了研究的不断深入与一代代研究者的不断涌现和成长,以及研究途径的不断拓宽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这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作者创作动机能否可以由作品推导出来,这也许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仁者智者不同角度的探讨甚至是争持形成了文学研究多样化的发展,同时在此基础上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三、“感受缪见”产生的原因
如果“以意逆志”让我们无法尽窥作者真实想法,使我们产生了感受缪见,这是由于作者自身和读者所处的角度的不同原因引起的。
首先,传统的一部分文人喜欢作态夸大事实得言论。先说陶渊明,一句“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不仅写出自己挨饿,还写出了极大的寒冷,以至于巴不得早点天黑赶紧上床睡觉,这样可以省掉晚饭,可是又因为饥寒交迫而又盼望早点天亮。老实说,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善于经营生活的人:不光不给豆苗除草,导致收入不理想;而且颜延之等人的慷慨解囊也没有让他脱贫。对于他的做法,鲁迅先生曾带着调侃的味道来形容他“很有些酒意了”。再说身居长江主簿的贾岛,明明俸禄丰厚却总喜欢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让旁人描述他“拄杖傍田寻野菜,趁早封书乞米炊”。“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的传统为文观念让相当一部分文人为达到博取同情心的目的不惜夸大事实,这是我们无法真正“以意逆志”的原因之一。
其次,作者无法驾驭自己思想感情也是一个原因。白居易的《长恨歌》一诗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是讲唐皇苦寻倾国之色而多年不得;“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一句讲述的是杨门借助贵妃而显赫。这里分别讲了唐皇好色和贵妃恃宠而骄,可见作者对两人还是颇有微词的。唐皇因贵妃误国,这基本上是大家的共识,单从全诗前面部分来说也当如此解读,可是当我们再往后面看却又不尽然:虽然说了“昭阳殿里恩爱绝”,但是又说“蓬莱宫中日月长”,这就把作者的同情之心表露无遗。诗名起为“长恨”,不知是恨唐皇和贵妃,还是恨反叛者,或者是恨自己无法将自己开始的愤恨之情贯彻到底,更甚至是几者兼而有之。不管是从任何角度去解读,“以意逆志”也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感受缪见”。在实践创作中,临时生发的感情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作者对文章原定感情基调或是整体架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即使可以最大限度地“知人论世”,也无法改变读者猜测作者创作动机的存在的事实。
再者,多种表现方法的运用,一旦读者理解角度与作者的原义产生偏差也会形成感受缪见。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一类的文学作品,表现方法的运用总是层出不穷:
1、互文。“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等,如果读者只是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忽略掉“互文”的因素,理解自然是无法还原作者原意的。
2、倒装。倒装句经常会让一个初涉之人产生莫名的感觉,理解起来糊里糊涂。比如说“甚矣,汝之不慧”一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太过分了,你的不聪明”。再看“多情应笑我”一句若还原成原意就应该是“应笑我多情”。
3、修辞格。李白的诗文常寓神奇瑰丽的夸张于全文中,理解了字面意思,还要进一步剔除夸张的成分。对仗是中国古体诗文常用到的手法之一,“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是为了寻求一个适合的字而下的苦功,从“捻断”中的苦苦推敲,我们不难看出很多时候为了求得对仗工整的目的,作者总会不惜搜肠刮肚地苦觅合适的字词,于是对于违背初衷也就很好理解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所列的三种表现方法只算作是代表,并不能完全陈述引起“感受缪见”的现象,实践操作中我们还会发现很多种让读者稍不注意就无法推断出作者创作动机的表现形式。
另外,其它一些原因也可能会引起读者的感受缪见。“以史证诗”是我们“知人论世”的一个条件,但是“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人物。”[3]鲁迅先生的这句话这是对“以史证诗”的反证,所以读者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王勃《滕王阁序》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句子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普遍的人把“落霞”理解为晚霞,但有人认为此“霞”非云霞之霞,是南昌当地秋天里的一种飞蛾,也即是今天所说的麦蛾。又因为七八月间晚霞映照江水之上造成反光,这些蛾子会循光纷纷堕于江面之上扑腾,江鱼便纷纷争食。而“鹜”本为家鸭,体重不能飞,只能在江面循游,看见江鱼争食蛾子,自然就会争食江鱼。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作者描写的是一条简单的食物链,而不是普遍认为的秋江晚景图。再说“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的诗句,如果不知道“明月”是鸟儿之名,“黄狗”是小虫名字,传说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学者也会闹笑话,一般人就不说了。曲解可怕,有意曲解更是可怕,两者都是属于“感受缪见”,只是出发点不一样而已。
四、避免“意图缪见”与“感受缪见”的路径分析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句话的意思很好理解,它要表达的就是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对同样的作品有不同的解读。鲁迅先生在谈论经典名著《红楼梦》时是这样说的: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读者的立场不同,解读作品的切入点以及目的性不一样,自然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关于能否“以意逆志”的问题,前文曾经略有提及。“知人论世”又能否更好地辅助读者去更精准地解读作品呢?我们不妨来看下面的一段话再作讨论。
善哉,孟子之言《诗》也,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汉人传《诗》,皆用此法,故四家诗皆有序。序者,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4]
文本的存在是客观的,作者的创作动机相对于读者来说也是客观的,而读者所循的探究作者意图的途径却是主观的。在整个探究直至定性的解读过程中,必须一方面要尊重客观事实,另一方面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致力于还原作者的初衷。王国维对孟子的诗学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志”虽在古人,但“逆意”却完全出于自己,所以要让自己所得之意“不失古人之志”。再看他对孟子“知人论世”的阐释:解读一个人的作品,不光要“知其人”,还得“论其世”。那么,“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孟子本人并没有把‘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联系在一起。将这两者在一起的乃现当代学人”。[5]在漫漫的研究过程中,当人们逐渐发现“以意逆志”无法满足“不以文害辞”和“不以辞害志”的时候,于是就把“知人论世”也添加进去了,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来解读文本的今天,我们依然也会发现操作的结果也未必真正如意。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新批评派针对创作者的“意图缪见”和解读者的“感受缪见”,实际上就很好地发现了这种弊端。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好多问题并不是靠着下个定义或者是搞个推论就可以解决的,大多数时候对文本的解读,现实中的我们总会面临着“多项选择”的尴尬。
“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这个词语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尴尬的处境。
归纳演绎可以让我们在更好地解决文本字面意思的同时,严密地执行还原作者动机的标准,同时也有综合分析,这是对纯文本的“沉浸浓郁”,这个过程是客观的。文字所外现的本意解读过之后,有目的性地筛选则是一个“含英咀华”的过程。作为创作者的个体,从其社会属性来说,“知其人”而后“论其世”,需要读者把作者连带其作品放在社会大环境里面去综合考查,以达到正确“逆其志”的终极目标。同时,心理上的换位思考也是很有必要的:“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以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6]不管是作者本人还是其作品,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所以我们加入“以史证诗”的做法很有必要,当然前文提及这些操作方法还是可能导致“感受缪见”,只是相对而言,毕竟大多数史家的笔触都还是公正的。
解读文本是一个重新经历作者思想历程的过程,时空、心路历程、社会历史等的不同,的确对读者重新建构之路形成很大的制约,但也是这种制约,促使我们想方设法,力图真实重现作者思想的火花。综合选取适当的方法,择取不同的角度切入,尽力避免“感受缪见”的产生,这是一个持久性的研究话题,研究之路不止,探索之路也不应停歇。
[1]童庆炳.文学理论要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15.
[2]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141.
[3]鲁迅.鲁迅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74.。
[4]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7.
[5]谭德兴.论“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实践操作及问题[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5):31.
[6]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