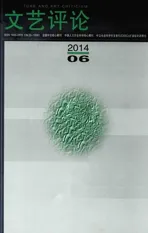论苏雪林作家批评的矛盾色彩
2014-09-29方秀娜
方秀娜
苏雪林是一个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作为二十世纪和冰心、丁玲等人齐名的才女,苏雪林一生都生活在纠结与矛盾之中,因此她“一生都在与生命打苦仗”。她接受了五四的新思想,承认自己受五四影响最大的“便是‘理性主义’”,却又庆幸“虽服膺理性主义,却还知选择应走的路”;她像五四时期所有的新女性一样,崇尚自由和独立,却又为了孝顺自己的母亲而接受了封建家庭包办的无爱婚姻;她向往过爱情,欣赏好友庐隐对婚姻的大胆追求,而她也曾有过热烈的爱恋,却又亲手扼杀了那段美好的爱情,将自己置身于道德理想所建的“地上花园”里,不敢越雷池一步;她以五四文化新女性的身份出现,却猛烈地抨击着同时期五四作家们那种诉说自我内心欲求与冲动,崇尚个性的文学作品;她自命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却倾其一生投身于“反鲁”事业,并对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口诛笔伐,完全丧失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客观和理智。究其原因,或许可以解释为性格使然,苏雪林生性洒脱、率真、直爽,喜欢逆潮流而行,常常表现出有悖于常人的认知,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性格使她经常做出常人难以琢磨的“怪举”;或许可以解释为传统思想的影响,致使她虽然身处五四,却没能够完全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最终成为一个“行为很旧、思想很新”的“半吊子新学家”;或是缠绕她大半生的难以释怀的恩怨纠葛,使她在理想信仰上选择了另外一种走向,从此踏上了“反鲁反共”的不复之路。这种生性中率性偏激与批评家固有的冷静自持并存的矛盾复杂性,使苏雪林的作家批评表现出了草率的情感宣泄与冷静的理性思考相交织的矛盾复杂色彩。
一、有失公允的主观感受式言说
纵观苏雪林作家批评的整体,呈现出的还是公允、客观、公正的特性。作为新文学的实践者,苏雪林深知文学创作者筚路蓝缕的艰辛,她特别赞赏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作家,对于新文学创作的尝试者和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各流派的代表人物,苏雪林都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与赞赏。但这种客观公允的批评态度并没有被苏雪林一以贯之,出于个人好恶、道德立场、价值观念、政治走向等因素,使她对一些作家的批评完全处于情绪失控状态,表现的极为偏执、苛刻和草率。
(一)个性驱使的激进批评
1.敬仰之极的夸美之辞
苏雪林是一个不善于控制个人情感的批评家。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面对自己肯定的批评对象,便难以控制其欣赏、夸赞的情感,批评对象所呈现出来的被她认可的方面,会引起苏雪林的强烈的赞赏,而她又时常任这种情感随意发泄,因此便时常会呈现出情感化的批评特征。所以她的作家批评常常会被人视为个人情感的抒发,而并非有理有据的正面评论。
苏雪林具有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但同时,她却缺少一个批评家更应具备重要能力,那便是控制自己爱憎的能力。面对自己喜爱和崇敬的作家,苏雪林从不压制内心的敬爱之情,而且一定会在字里行间将这种喜爱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胡适,苏雪林是既充满了热烈的敬仰之情,又满怀对恩师的感恩之心。她评价胡适“这个扭转三千年文学史的局面,推动新时代的大轮,在五四学术界放出万丈光芒的胡适博士,将来自能在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上获得极崇高的地位”①这段文字,对于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地位,以及对胡适个人学识、才华的认可都溢于言表,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对胡适的顶礼膜拜和无限崇敬之情。对于她同样崇敬的周作人先生,则有这样的论断:“近年小品散文的盛况似乎已被那些突飞猛进的长短篇小说所代替了。而且从前那些小品文成绩也已被猛烈的时代潮流,冲洗得黯然无色了。但中国有一座屹立狂澜永不动摇,而且颜色愈洗濯愈鲜明的孤傲的山峰,这便是周作人先生的作品”②这段总结概括式的结论,刚劲有力,一语中的,确实叫人拍案叫绝。但同时,我们又不难透过这段语言表象,参透其内在的含义,即在小品文创作方面,周作人的地位唯恐无人能及,表现对小品文未来发展的悲观预感。这就漠视了除周作人之外一些小品文作家的杰出贡献。周作人的小品文成就确实卓著,对小品文的贡献也是不容小觑,但是绝不是空前绝后的。
徐志摩是苏雪林笔下极尽夸美和赞誉的作家之一。对于徐志摩,苏雪林不仅仅是喜爱,更多的还是一种钦佩之情。她虽与徐志摩只见过两次面,也没有过多的交谈,但苏雪林却将其视为“诗哲”,并被徐志摩深深的吸引,对他“十分钦佩”。③因此,苏雪林在对徐志摩诗歌的批评的时候,这种喜爱的情感便不自觉地引导着苏雪林的批评,并先入为主地成为她批评写作的主导情感,因此在批评过程中,只要遇到志摩诗中有可圈可点之处,她便决不放过,甚至不惜花大量的笔墨和篇幅予以高度褒扬。即便是稍有瑕疵,苏雪林也从不直接表述,即便指出来也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寥寥几笔,不肯留下过多的痕迹。只有在将徐志摩与其他的作家进行比较批评时,苏雪林才肯正面去面对徐志摩诗歌的不足之处。
在《徐志摩的诗》一文中,苏雪林“徐志摩诗的形式”和“徐志摩诗的精神”两个方面对徐志摩的诗进行了论述,并且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在论及徐志摩诗歌精神方面,她提出徐志摩的诗歌表现了人生美的追求和真是人人格的表现。她指出:徐志摩在诗中所寻求的人生美,不但为了安慰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把徐志摩诗中表现的主题进一步的升华开来。无论是论及徐志摩诗的形式方面还是精神方面,只要涉及到具体诗作,苏雪林都难以控制其对徐氏的喜爱钦佩之情,不断地以肯定的态度进行详实的解读和诠释。最后,苏雪林强调“徐志摩是新诗的奠基石,他在新诗界像后主在词界一样占着重要地位,一样的不朽!”④这样的赞颂贯通古今,空前绝后。此时,徐志摩个人对中国新诗的作用被苏雪林无限地夸大,却忽视了曾与徐志摩一同在文坛奋斗过的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等作家的杰出贡献,将其列入二流作家之列。徐志摩是以诗歌的成就著称文学界的,他的散文相对于诗歌来说,便稍显逊色。但苏雪林仍旧是专门写了一篇《徐志摩的散文》,高度评价徐志摩是小品散文的名手。文中,苏雪林从徐志摩散文注重音节、感情丰富以及对“新月诗派”成员的影响了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徐志摩散文的突出特点和对小品散文的贡献。对于一些认为志摩情感性文字具有装腔作势的特征的说辞,苏雪林也会帮其进行辩解“志摩文字以纯真的人格做骨子,所以虽然文字有些‘装腔作势’,并不惹人憎恶。”⑤甚至对于徐志摩自评其文章具有“跑野马”的毛病,苏雪林也是宽容的对待,而且还借梁实秋的话“他的‘跑野马’的文笔不但不算毛病,反觉得可爱了。”为其开脱。⑥
苏雪林对于自己喜爱的作家不仅会极尽夸美之词地大加赞赏,当这些作家受到冷落、抨击或非议的时候,苏雪林总是会挺身而出,极力为他们辩护。对于“新文艺读者眼光之迟钝,欣赏力之薄弱,到了不可原谅的程度。”⑦她感到非常悲痛。冰心的小诗深深地折服了苏雪林。在对冰心的《繁星五四》进行批评时,苏雪林抑制不住内心冲动的情感,将潜藏在心灵深处的赞赏之情和盘托出,使其评论文章的篇幅大大的超过原诗的篇幅。对于冰心“以哲学家的眼,冷静地关照宇宙……以诗人的慧心体会出之,即便是“一朵云、一片石、一阵浪花的呜咽……”,“甚至连一秒钟间所得于轨道边花石的印象,也能变成这一段神奇的字”。⑧苏雪林感慨“这几句诗的意义,有时连数万言的哲学家讲义也解释不出来,她只以十余字便清清楚楚表出了。”⑨也为其他评论者对于冰心文字的非议与偏见进行了有力的辩解。
2.憎恶之下的口诛笔伐
苏雪林对创造社作家,尤其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极为厌恶。在苏雪林看来,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文学艺术的标准尚处于不断完善发展的时期,人们对于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观点的文学作品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只能依照个人的兴趣喜好来进行评析。这在这样一种时期,那些善于自我吹捧的、擅长滋事谩骂的、作品的内容带有强烈刺激性色彩的、作品质量粗制滥造但却数量奇多的作家,往往能够迎合大众的口味,从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对于读者中出现的“浅薄”、“荒唐颓废”分子,让苏雪林十分愤慨,而那些对于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但不去做去伪存真的工作,反而大加歌颂,这更是苏雪林完全不能接受的,她称这些人是“盲目的批评家”,“连评判的常识也没有”⑩苏雪林认为郁达夫谈性欲问题、表现性的苦闷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病态,因此她称郁达夫为“色情狂”。对于陈文钊认为郁达夫“初期的创作背景,性的苦闷,是其骨干。这种苦闷自然不是大夫个人的,每一个人在青年期从生理的发展,必然会发生这种作用……而像达夫这种病态,在一时成为青年苦闷的典型。”(11)的论述,苏雪林认为要么就是陈文钊在作违心的言论,要么就是他青天白日里闭着眼睛说瞎话。(12)于是,万般无奈的苏雪林最终把这样她自认为不正常现象的原因归结到中国国民性上,认为是这些人的作品正中了中国人对于闺阃和情色事情的好奇与向往,因此才会使这样的作品红极一时。
浪漫文学是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史的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受个性趋势的苏雪林将对创造社的憎恶之感无端的扩大、蔓延,最终甚至转向对浪漫文学的厌恶,并进一步演变成为对所有“浪漫”因素的憎恶。她甚至认为是“浪漫”扰乱了原本澄澈的中国文学史,使文学史失去原本的庄严、厚重,变得随意、轻浮。在《王统照与落华生的小说》一文中,苏雪林认为王统照早年的作品多存在“肉多于骨”的毛病,而且觉得他的作品故事情节“缺乏一种紧张的空气”,她将王统照这一时期的作品称之为带有浪漫色彩的作品。而在这之后的《山雨》则开始倾向新写实主义,所以苏雪林觉得《山雨》比之前的作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对于《山雨》中存在的艺术上的松懈、琐碎、重复的毛病,苏雪林仍将其归结为浪漫造成的;对于落华生的小说,苏雪林认为是超越王统照的。她还认为沈从文的作品表达思想的方式就是“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而这种强加式的灌输和中国国民的整体状况是不相适应的,因此也就无法达到沈氏所料想的效果。苏雪林高度肯定了巴金是当代作家中最富情感的一个,他的情感之热烈以至于使他燃烧。但是由于巴金作品中的这种热情太无节制,是作品“不知不觉带着浪漫色彩”(13)的原因造成的。在《幽默作家老舍》一文中,苏雪林对老舍的幽默风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在最后之处,她也指出了老舍作品的艺术缺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老舍描写人物有时带着浪漫的意味。《离婚》中的丁二爷原是个傻瓜,但他后来居然能暗杀小赵救了张大哥一家”(14)这种浪漫的艺术处理,使得老舍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略显荒唐。
在论述郭沫若的诗歌时,苏雪林全篇尽是讽刺挖苦之词,将郭沫若批判得体无完肤。她从布局的缺点和造句的缺点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郭沫若作品艺术不甚讲究。”(15)在论及布局缺点方面,苏雪林又从郭沫若诗歌用笔太直率无含蓄不尽之致、结构太简单和不知变化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论及造句用字的缺点方面,苏雪林主要从郭沫若诗歌句法字法不修饰,常有笨拙、粗疏、甚至文理不通之处展开了具体的论述。并将其原因归结为“这或许是由于他的旧诗词根抵太坏之故。”(16)
在论及郁达夫的小说时,苏雪林更是丝毫不掩饰其厌恶的情绪,憎恶的词句通篇皆是。在《郁达夫及其作品》一文的开篇处,苏雪林就言辞激烈地抨击了诸多位创造社的作家及其作品。在对郁达夫进行具体论述时,也是首先指出了郁达夫擅长写作的表现“性欲”的作品这之所以受欢迎,是钻了周作人所说的中国人多少患有一点“山魈风”的毛病的空子。苏雪林认为,郁达夫对性的苦闷的描写是对“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17)的再现,而非弗洛伊德所说的“性”作为情感的源泉的角度。苏雪林总结郁达夫的作品除了性的苦闷,便是写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巢、下等娼妓、偷窃、诈骗,以及其他各种堕落行径。而郁达夫对这些题材的关注角度和表现手法,在苏雪林看来都是有悖于她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是被苏雪林所不耻和厌恶的。为了充分证明自己的论述具有可信度,苏雪林将郁达夫小说中缺乏心理学依据的人物行为与佛朗士的《黛丝》中人物行为进行对比。通过这种对比的方法,将郁达夫小说人物内心揭示的缺点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每个作家创作都有其自身需要表达的情感和用意,不管苏雪林如何不喜欢郁达夫的小说,如何憎恶郁达夫本人,她都不应该仅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想来歪曲作者原本的创作动机,这完全是一种极端情绪化的表现。
(二)政治走向的歪曲批评
苏雪林的一生是矛盾复杂的。我们很难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粗浅而简单地下结论。她不是政界人士,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但对政治之事却非常关注,并且参与其中。她从不标榜自己政治进步,但在关系民族危亡的抗战关头却慷慨解囊,把自己靠创作赚得并且节衣缩食省下来的五十三两三钱黄金捐给了国家。由于苏雪林保守的思想观念以及与鲁迅难以释怀的恩怨纠葛,使她始终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成见,反而走向了与共产主义对立的立场,“她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过激的运动,是赤化。”(18)她甚至“认为是新文艺充当了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工具,是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相互利用的结果。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利用鲁迅在抢夺文坛的控制权,为宣传共产主义服务,鲁迅则在利用共产党在文艺界的影响奠定他的文坛霸主地位。”(19)苏雪林对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认识,使她走向了与之背道而驰的信仰之路。在她的作家批评中,对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极尽污蔑、诋毁之辞,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作家批评中隐含着的强烈的政治走向。
1.丧失理智的诋毁批评
政治上的反共倾向使她在评论某些作家时有失公允。尤其是对于鲁迅这样一位民族斗士,苏雪林对他的评论并没有做到一个批评家应有的理智和公平,抓住了鲁迅的品格道德等私人问题不肯罢休,半辈子都从事着“反鲁事业”,近乎是泼妇似的无理谩骂和人身攻击,使其评论文章也大打折扣。
这种丧失理智的诋毁批评突出地表现在苏雪林对鲁迅的评价方面。苏雪林对鲁迅的这种诋毁和攻击,似乎已经超越了文学批评的界限,转化成了人身攻击。1936年11月12日,苏雪林写了一封《与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曾大骂过鲁迅:“诚不能不呼之为站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布其罪状,告诸天下后世,使人人加以唾骂”。(20)这封信苏雪林拜托胡适转交给蔡孑民。1936年11月18日,在苏雪林写给胡适的信中再一次以极端偏激的词语发表了对鲁迅见解:“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迎、基督都比他不上。”(21)所以,胡适看了此信后,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他“很同情”苏雪林对鲁迅的“愤慨”,但同时他又表示对苏雪林攻击鲁迅“私人行为”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只讨论鲁迅的思想和信仰;对苏雪林的谩骂之语,胡适批评其太动火气,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22)
苏雪林没有听从恩师胡适的意见,将这封信与之前写给蔡氏的那封于第二年在《奔涛》半月刊上发表出去。这两封信件一经问世,使整个文坛都为之震动了,人们无法接受苏雪林对于鲁迅的攻击与谩骂,这使苏雪林成为了整个文坛进步人士的攻击对象。60年代,苏雪林从大陆到台湾定居后,还曾写成了《鲁迅传论》,后收入到《我论鲁迅》一书中。在这本书中,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更是体无完肤、无孔不入。
苏雪林攻击鲁迅的另外一点便是将鲁迅视为“极端“虚无主义”,在“虚无主义者”眼中,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一个是可以相信的。她认为鲁迅的创作小说带有“虚无哲学”的色彩,她称鲁迅是“一切希望都没有,围绕他周围的既没有一个好人,对中国民族更以为病入膏肓,无以救药。”(23)鲁迅对旧文化的反思与对人的个体存在的反省所表现出的野性的力量,在她看来是异端邪说的表演。她叹道:“一个人的思想阴暗虚无到这种地步,也可谓叹观止矣。”(24)苏雪林对中国古典文学是绝对敬仰和尊重的,她绝不容许任何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之音。因此,对鲁迅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批判旧时代的精神和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成“吃人”的历史,都特别反感,她认为鲁迅最擅长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中国人。这种心理便是处于鲁迅的变态心理,既然是处于病态心理,便无法令人信服。
对于鲁迅加入左联一事,苏雪林更是给出了一番叫人难以置信的理由。她认为鲁迅加入左联“并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并没有忽然不惜自相矛盾,认为文艺真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其实他也有私人企图。”(25)苏雪林理解鲁迅的“私人企图”是因为鲁迅心理有极度的病态,这种病态使他仇恨心理极强,他嫉妒学问、才华、名望、地位比他高的人,“必欲去之以为快,不得不转为仇恨。”(26)所以,鲁迅打算连结创造社诸人共同为破坏封建社会而努力,而鲁迅看重的则是创造社诸作家的心理是很容易推测出来的,这也正是鲁迅选择创造社作为自己结盟对象的一个重要方面。苏雪林对鲁迅的评论缺少学术性和科学性,除了人身攻击和扣政治帽子,没有多少实事求是的态度。
2.污蔑人格的苛刻批评
在论述鲁迅性格时,苏雪林认为鲁迅的性格“是那么的阴贼、峻刻、多疑、善妒、气量偏狭、复仇心强烈坚韧,处处令人可怕”,(27)紧接着,苏雪林分析了鲁迅的相关作品,最后得出结论:鲁迅的确具有这种性格。但因苏雪林憎恶情感支配着她,所以类似的分析只是苏雪林的主观臆断。如在证明鲁迅“阴贼”性格时,苏雪林举出了鲁迅幼时因“隐鼠”失踪便以“谋害”的罪名加罪于保姆的事件。但苏雪林并没有停止分析,而又拿《史记》中张汤幼时掘鼠的故事相提并论,从对鲁迅“阴暗”性格的分析到后来对鲁迅的人身攻击,苏雪林逐渐陷入无法自拔的“反鲁”泥淖。使苏雪林关于鲁迅的文章丧失了学术价值,因而也失去了论辩的意义。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偏见,是如何诱使一个有才华的批评家逐步走上了背离公正立场,歪曲客观事实的歧路。”(28)
苏雪林在后来写的《鲁迅加盟左联前后的作为》中,对鲁迅的憎恶更加强烈,情感情绪化现象也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在论及鲁迅当了左翼文坛盟主之后,对陈西莹、胡适的“开罪”,特别是鲁迅骂胡适为“‘伪学者’、‘金元博士’、‘高等华人’、‘王权拥护者’、‘杀戮知识分子的刽子手”。(29)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迫于国内的形势,苏雪林选择离开大陆,远赴台湾。然而,她并没有停止对鲁迅的谩骂。来到台湾之后的苏雪林,仍然继续着“反鲁”事业,从50年代开始,直至60年代中期,苏雪林共写了18篇“反鲁”文章,后结集出版《我论鲁迅》一书。在这本书中,苏雪林对鲁迅的谩骂可谓是口无遮拦、犀利苛刻、言辞激烈,毫不留情,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而且,她在这本书中将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共匪”。很显然,苏雪林已然将对鲁迅的憎恶转而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其中,1958年,她写了一篇比较较刻薄的《琵琶鲍鱼之成神者》,借古时无知人们将琵琶和鲍鱼视为神明供奉的故事,进行发挥“即猥琐之物,在某种条件下,亦可成神”,“鲁迅便是琵琶鲍鱼之成神者,惟琵琶鲍鱼均系无意造成,而鲁迅则是共匪有心塑造的偶像而已。”(30)在这之后,苏雪林还写过一篇更加“疯狂”的文章《对战斗文艺的我见——论共匪的文艺政策及当前战斗文艺的任务》,“这大约是配合当时台湾当局‘反攻大陆’需要建言”,说“鲁迅心里具有十分病态。他颇像外国一种猘犬,咬住人砍下他的头还不肯放。他最爱说‘复仇’二字,……鲁迅骂陈源教授,足足骂了十年,一直骂到自己进了棺材才罢。这样不近人情之事,实为古今中外文坛罕见之例。”(31)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苏雪林半点文人的面目了,有的全部是仇恨和辱骂。直到1959年,苏雪林又写了《新文坛四十年》,这片文章中苏雪林已经不再评论文艺,而变成了政论文。她在文中将中国共产党称为“魔鬼”,“大陆现在由魔鬼统治,文学也已成为魔鬼宣传的工具”(32)她甚至在文中提出“清除鲁迅余毒,反对共匪政权,从来不敢懈驰。”(33)将“反鲁”与“反共”共同作为她的“事业”。
苏雪林对鲁迅的认识完全是来自于带有主观情绪的偏见,缺乏清醒、客观的深刻分析,苏雪林对鲁迅人格、性格以及加入左联动机的评价都是粗鲁、拙劣的,最终,也只能使她对鲁迅的谩骂与攻击成为后人嗤之以鼻的笑料。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名族斗士,在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高尚的民族气节,以及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揭示,鲁迅的精神对整个国家、民族和一个时代的作用与影响都是苏雪林根本无法理解的。苏雪林没有深刻认识到鲁迅的作品和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崇高地位。鲁迅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现象。
二、批评家的冷静与坚守
苏雪林的作家评论虽然带有强烈的主观偏执色彩。但同时,一方面苏雪林的作家评论是她在武汉大学教书时为教学之需而作,为了向学生呈现一个真实、客观的文学史状况,苏雪林在对作品评价时能够从不同角度挖掘,力求做到公正公平。另一方面,苏雪林毕竟是一个批评家,且是一个学术研究者,所以他具备一个批评家应有的素质和眼光,能够秉持一个批评家的理性。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她能够客观冷静地将对作家本人的爱憎与作品区别对待,能够以宽容的态度,从审美的角度和艺术价值方面去审视作品,固守着客观的艺术标准和审美标准,不盲从、不跟随,坚持着特立独行的个人批评写作。使她的批评写作又具有很强烈的理性色彩。
(一)以文论文的客观批评
苏雪林虽然是一个不善于控制个人个性情感的批评家,但抛却个人的好恶来讲,她的大部分文学批评都能够坚持比较客观公允的原则,力求做到以文论文,苏雪林具有尚武的性格特点,且又是一个正直、率性的人,所以她从不会趋炎附势,也不会为了迎合某人、某事而放弃自己得观念和追求。因此,无论批评对象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还是名不见经传小人物,她都不会刻意地奉承或是轻视。而对于她所批评的作品,也不会因为作者的身份、地位、名望而盲目抬高其地位,或是轻蔑地贬低其价值。
胡适是苏雪林最为敬佩的作家,除了源于胡适的文学成就,还因为苏雪林一生都将胡适视为恩师。她认为胡适扭转了三千年文学史的局面,推动了新的时代车轮向前转动,并且断言“将来自能在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上获得极高的地位”。(34)即便这样,对于胡适先生创作的筚路蓝缕、启山林之功的《尝试集》,苏雪林也并没有全盘肯定,一味的高唱赞歌。她评价胡适的《尝试集》“明白清晰、富于写实精神、极具哲理化”,写的是极好的。但是苏雪林并没有被个人对胡适的敬仰和崇拜蒙蔽了批评家冷峻的双眼,她还是抛却了对胡适的个人情感,理性地发现胡适的诗太过于注重哲理性,而缺乏想象和情感。最后,苏雪林指出:“像胡先生那样一个头脑冷静,理性过于发达的哲学家,做诗人是不合条件的。”(35)许钦文一出现在文坛上,便以小说集《故乡》被读者们所接受,甚至鲁迅对其也有大加赞赏,认为在描写青年心理问题上,许钦文胜过自己。苏雪林对于许钦文作品中对于青年人内心世界的描写,尤其是对五四运动后青年男女恋爱心理的揭示是非常认可的。徐志摩同样是苏雪林十分喜爱和敬佩的作家之一,虽然在评论志摩诗时,苏雪林没有指出什么缺点,但在评论闻一多诗歌的文章中,苏雪林却明确地指出了徐志摩诗的不足之处。这种用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不足证明属于自己反对阵营作家诗歌的长处的做法,确实是值得称颂的。
苏雪林能够坚持以文论文的批评原则,即便是面对自己最为厌恶的左翼作家时,她也能够将个人的情感好恶搁置一旁,坚持从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角度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品。用苏雪林自己的话来说,“以艺术人品为重,艺术优良,人品也还高尚,虽属“左倾”人士如闻一多、叶绍钧、郑振铎、田汉等在我笔下,仍多恕辞”。(36)在对闻一多的诗歌述评时,苏雪林对闻一多的《死水》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并没有因为闻一多的左联身份而影响苏雪林对其诗歌诸多优点的揭示。苏雪林称叶绍钧是“多产而作风却极其精炼纯粹的作家”,苏雪林对于叶绍钧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对“爱、生趣、愉快”因素的揭示是极为积极向上的。叶绍钧创作的《火灾》、《被忘却者》则被苏雪林视为“五四时代新生的气象和那时代人的人生观的代表。”(37)而长篇小说《倪焕之》苏雪林则认为是叶绍钧思想转变后的作品。苏雪林认为《倪焕之》“虽亦有随意串插的情节,但写来及其亲切有味。(38)作品中对于五四运动的描写可谓是绘声绘色、淋漓尽致,绝对配得上茅盾给出的“扛鼎之作”的美誉。(39)对于田汉的剧作,苏雪林也是大加褒扬。她高度赞赏田汉的出众才华,认为“田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剧作家。五四他即成为时代的骄儿,到抗战前夕,他的光芒不唯没有消失,还有日益眩耀之势。”(40)苏雪林指出田汉剧作具有描写极有力量,富于感染性;情节安排之妥当与对话之紧凑;善于利用演员之特长与场面之变化莫测等特点(41)。苏雪林甚至认为田汉是中国新式话剧的“顶梁柱”对其剧作特点进行了细致而富有溢美之词的评论,文末处,苏雪林又将田汉誉为戏剧界的十项全能。
(二)宽容的批评态度
苏雪林的文学批评有着可贵的宽容态度。苏雪林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的代表作家,她所崇尚的风格是清新隽永,富有抒情意味。然而她从不以自己的风格特色衡量别人的作品。早年间留学法国的经历,对于苏雪林文艺思想、审美角度和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洲社会开放、自由、民主的先进思想正好切合了苏雪林率真、坦荡、自然的性情。从欧洲回到祖国后,苏雪林又与同样有过留学经历、有着开放思想的陈源、凌叔华、袁昌英等人密切往来,她们对欧洲进步思想的接受和理解,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苏雪林。这两方面的作用,使苏雪林一方面摆脱了当时社会对于文学功利性的推崇的影响,看重从审美特性上看待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使她无论对待与自己价值观念相背离的左翼作家,还是与自己来往密切、观点相近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作家,以及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新感觉派作家,都没有局限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与观念,而是秉持着宽容的眼光,并从自己独特的审美立场出发,对其进行客观中肯的评价。对于和自己风格完全不同的鲁迅小说的辛辣冷峻、周作人小品文的平淡清涩,她都大加赞赏。
对于沈从文小说中体现出的犷悍、雄强的野蛮气质,她也颇具赞美之词;她还对被当时文坛视为“怪诗”的李金发等人的诗予以介绍、鼓吹,肯定他们对中国新诗坛的贡献。苏雪林还在评论了沈从文小说的优缺点之后,真诚地希望并热情地预言:作家只要好好地收集人生经验,细细磨琢文笔,一定会有创作的辉煌时代。(42)在这里,苏雪林严格地做到了实事求是地开展文学批评。客观公允而又有理论深度的批评,对于引导读者准确地欣赏作品,帮助作家总结创作得失,进一步提高创作水平乃至促进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苏雪林对此问题的认识及她在文学批评中体现出来的宽容精神,正是在文学批评领域树立了榜样,对于当时文学创作的繁荣做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叶绍钧的作品》一文中,她说:“五四左右以创作小说引人注意除了鲁迅、冰心,便要推叶绍钧了。他是一个多产而作风却极其精练纯粹的作家。”(43)并且对其题材选择予以肯定,即便后期创作有“左倾”色彩,还对其艺术上的特点给予高度评价。
苏雪林对左翼作家虽然大多是对立和排斥的,但是对一部分左翼作家还是相当宽容的,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政治倾向而予以全盘的否定。例如,对于张资平,苏雪林的整体情感是偏向否定和憎恶的,对于张资平小说批评的大多数内容在批评张资平其不足之处,但在结尾处却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在论及茅盾作品时,从表面上看,苏雪林是“勉强”找出了茅盾作品中存在的弱点,但在结尾处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弱点却并没有影响到苏雪林对茅盾的高度评价“像茅盾就可算现代中国‘文学界的巨人’,就不说是‘巨人’,欲可说是左翼文坛的巨头了。”(44)足可见苏雪林宽容之处。对于田汉的剧作,苏雪林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她认为“田汉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剧作家。五四他即成为时代的骄儿,到抗战前夕,他的光芒不唯没有消失,还有日益眩耀之势。”苏雪林认为田汉是中国新话剧的“顶梁柱”,对其剧作特点进行了细致而富有溢美之词的评论,文末提出:“说田汉是戏剧界十项全能,也可当之无愧。”(45)
(三)学理性的理性批评
苏雪林是一个理性思维能力较强的人,在为完成教学任务而编撰的现代作家论中,常常采用学者的冷静和理性思考来关照研究对象,她能够在对批评对象进行深入细腻的综合阐述、评价后,再将其条分缕析、分门别类的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并且运用得特别娴熟。由此,苏雪林在对新文学作家进行的批评中,常常将所批评的对象置于批评者理性目光的审视下,体现出其科学严谨与细致周到的学术品格,因此,极具实用性。正如在苏雪林自言“仅有客观的分析,而缺少主观的批评”(46)的《周作人先生研究》里,苏雪林主要从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趣味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在逐条阐释和实实在在的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基础上,苏雪林得出了作为思想家的周作人所写下的好文字和作为文学家的周作人“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和“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47)的飘逸而深刻的小品散文风格。
《沈从文论》是苏雪林所做的被后人所称道的作家论之典范的作品。在对沈从文进行具体批评中,苏雪林在对研究对象全面、清晰、综合的审视中,对其作出了极为周全、详细、系统的理性评论。她从沈从文作品的题材内容、哲学思想和艺术特点等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综合性考察。首先,简单、明了地总结了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后,便以简洁、明快、利落的笔触将其作品分门别类地划为四类,接下来,便逐类依次进行分析评价。其次,苏雪林发掘了沈从文作品中所蕴藉的哲学思想。她准确无误的地指出沈从文不成系统的论述,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替自己鼓吹,实则是想借助笔墨的力量,实现他救助民族的理想。在这种细致深刻的理性化解析和科学严谨的论证中,苏雪林睿智而理智地发现了沈从文很想将湘西民族特有的“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48)的理想和欲求,其一针见血的精辟之论,着实令人叹服。
在对沈从文作品的艺术特点进行评论时,苏雪林则独具慧眼的发现了在新文学界以“文体作家”著称的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的成败得失。她在细致地评介沈从文作品的诸多长处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明确指出了沈氏创作的弊病。从批评者对研究对象优点与不足的一一列举中,我们能够看出苏雪林作家批评全面、细致、周到的风格。在当时的批评界,沈从文的作品被冠以“空想”的帽子加以诋毁,并一味“否定了他的作品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49)在这样的批评环境里,苏雪林通过对其作品深入细致的逐层推介和适度解析,以机智、巧妙而又理性的分析性批评,客观地给出了沈从文早期作品的价值所在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样一来,在一味否定之声中出现的苏雪林关于沈从文作品客观、真准、翔实的批评,其特殊的意义就此显现了出来。
苏雪林特立独行的个性就决定了她是一个决不跟从的批评家。在具体批评中,面对不同的观点,苏雪林亦有自己的判断,不人云亦云。如苏雪林对周作人、俞平伯、鲁迅等批评对象的判断,就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论及周作人的历史观念时,苏雪林并不因周作人曾经是自己的老师,有所顾虑和偏见,而是坚持了不赞同周作人的观点。除此之外,苏雪林还用了大量的篇幅,列举了西方众多国家的事例说明“死鬼僵尸之为物,岂惟中国有之,各民族莫不有之”,而且还举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相同类型的人物,并对此提出质疑,以此证明中华民族并不是像周作人所说那样卑劣低下。在对大量的事实进行分析、书评之后,苏雪林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对于俞平伯散文喜谈哲学的特点,苏雪林也表示出不同的观点。对于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写到的乡民谈话不用绍兴土白时,苏雪林认为“《阿Q正传》之不用绍兴土白,正是鲁迅特识。”(50)
苏雪林无疑是一个矛盾、复杂、纠结的人物,那种批评家固有的客观冷静和批评家最应摒弃的偏执激进在她的批评文章当中竟然能够同时存在。她的身上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她以富于理性的思考和创作,也曾给中国文坛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曾条分缕析地对作家作品做出过客观、公正、宽容的评价,使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了解作家的创作风格和作品的艺术价值。她对一些作家的宽容评价,给了作家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使一些处于成长阶段的作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缺点,给了他们为文学继续坚持的动力。苏雪林对当时部分作家的客观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促进现代作家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并由此确立了她在中国现代作家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然而,与此同时,她又时刻表现出了批评家最不应该有的冲动、偏激和有失公允,她那种凭借个人一己好恶对某些作家的攻击和辱骂,已经使她文人的素养面目全非,文学批评应该固守的冷静与客观已经被她的个人情感占据。同时,由这种偏执激进而衍生、升级的带有政治指向的文学批评,更使苏雪林的文学研究之路扭曲变质,从而走向了无边的政治泥沼。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苏雪林言辞激烈、偏执苛刻的表述,却恰恰体现出了其“不顾及自己宽容中庸的道德外表”(51),的率性真诚的批评态度。因此,虽说这种缺乏批评者应有的冷静和理智的批评带有个人的一己好恶和极端情绪,但是这种批评却也因其率性和真诚而具备某种特殊的个性色彩。
①②⑦⑩(11)(12)(13)(14)(34)(37)(40)(42)(43)(45)(46)(47)(48)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8、235-236、182、326、320、320、334、341、9、309、366、305、306、376、235、252、3008 页
③(35)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 346、327页。
④⑤ ⑥⑧ ⑨(15) (16)(17) (25)(26) (27)(29) (38)(39)(41)(44)(52) 苏雪 林《中 国 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258、259、80、80、90、91、316、603、、603、208、604、305、432、504-507、408、298 页。
(18)(19)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170、171页。
(20)(21)(22)(23)(24)(30)(31)(32)(33) 苏雪林《我论鲁迅》,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4、63、67、15、17、133、139、149、152页。
(28)左志英《一个真实的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
(36)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自序》,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49)金介甫《沈从文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51)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