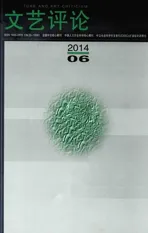也论陶渊明、李白饮酒诗蕴涵的生命意识
2014-09-29樊婧
樊 婧
一般地说,我们在考察诗人的诗歌创作与生涯时,“认识基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然,这并非对任何一个诗人都很明显,但是对于某些个性特征比较明显的诗人来说,这种意识观念则是不可或缺的,并且系统地贯穿其一生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诗歌创作中),陶渊明强烈的“归隐”意识以及李白微弱的“归隐”意识和强烈的“流浪”意识,就是如此。
一
众所周知,陶渊明与李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一位是农民的儿子,一位是浪人的骨肉;一位是温文儒雅的文人,一位是放荡不羁的才子;一位是在朝为官,毅然放弃,一位是乡野白衣,极力入仕;一位归隐田园,独享其乐,一位幕府为僚,自娱其向。二人纵有诸多的不同,惟有满腔忧世的情怀是相同的。还有特有的嗜好是相同的—那就是喝酒与写诗,古人云:豪放之士固要“醉卧沙场”,隐逸之人也爱“举杯邀月”。所以我们的诗人便常常以酒为写作题材,并在诗中蕴涵了浓浓的人文情怀。如李白在《襄阳曲》中写道:“鸬鹚勺,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①向我们充分地展现了一个放荡不羁的豪放之士。而陶渊明的一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②就给我们说明了追求自由的无限乐趣。总之,文化作品中的“酒”通常只是“形”,放浪形骸之形,而其“神”(思想境界)则隐含于“形”中,这里的“形”特指诗歌,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以便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诗歌内在的“神”韵。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任何意识观念的产生都是同现有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出身寒微,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生活平淡而别有一番风味,但他一直存有报效国家的志向。然而在当时极度重视门阀的社会里,这种愿望是很难实现的。虽然陶渊明后来入仕,可是做的都是小官,不足以让他展示自己的才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且家庭地位的低下最终造成了他日后政治上的尴尬处境,也成为他几次出仕又入仕,最终归隐的原因之一。其次,陶渊明刚正耿直,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③而他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④这也就是陶渊明自始至终的“归隐”意识,这种意识更多的体现在他的饮酒诗(《饮酒》、《止酒》、《述酒》等)中。他的饮酒诗大多写于他已经退隐躬耕田垄,思想已经渐趋成熟和平淡时。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时代塑造了陶渊明,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里曾经指出:“到了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是陶潜。”陶渊明一生嗜酒,有酒则饮,饮则必醉。在其《五柳先生传》中道:“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⑤临了最后,他就酬觞赋诗,以乐其志。《饮酒》是组诗,共20首,写于陶潜四十岁以前。据他自己说,是在醉酒后,诗兴大发而作。王安石曾赞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句诗是“自诗似来无此句”。虽然这些诗是酒后所作,却不以酒入诗,堪为“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与李白似有相同,只不过李白是以酒为诗罢了。
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其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⑥苏东坡曾赞誉它境与意会,最为佳妙。据说当时曾有传本作“望南山”,苏东坡认为它意境全无,神气索然。以“望”的有意识比之“见”的无意识,而无意识更显自然,“见”字之神也在于此。陶渊明的“归隐”意识也于字里行间显现无疑,似乎无人工的雕刻。其实这也正体现了他自然为真的意念。陶渊明在大自然中归隐,鸟,花,以及山林间的点点滴滴都成为他的最爱,这里与他所处的纷繁芜杂的朝廷政治生活大相径庭,使他重新对生活充满信心,有了欣赏自然的情趣,也有了对仕途生活的重新审视。他在《饮酒》其九中写到:“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在其四中写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⑦用以描写自己隐居的快乐和决心。以至后面的出仕机会,他都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也与李白用尽办法不得入仕,有丝毫机会决不放弃的心态是不同的。因为他已经更加厌倦了政治,这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出来:“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生去旧京,峡中纳遗薰。”⑧陶渊明在涤洁纯净的自然环境中,身心也经过了洗涤,这使他看透了朝廷官场,他本期望为民做事,一生能有所功绩,然而全都事与愿违,他矛盾的心情在隐居的生活里慢慢得到平静,他不想再心起波澜,因此坚决放弃了“为他人做嫁衣裳”且不得好的出仕机会。温汝能评此诗说:“题名《述酒》绝不言酒,盖古人借以寄慨,不欲明言,故诗句与题义不相蒙者往大痛。”⑨他的愁怀是靠自然和酒来消解的。他在《还旧居》中写道:“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⑩死且不怕,还怕独自身处归隐吗?这就使他更容易超脱于世俗,也是他与其他归隐之士的一点区别。同时,他身处一个篡乱的时代,生活中避免不了危险。常醒者小心翼翼,何等愚蠢;独醉者悠然自得,何等聪慧!因此陶渊明毅然地走上了归隐的道路。
任何意识观念也与他当时社会已有的意识观念有关,有时甚至影响某人的一生。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表现饮酒的诗人,而他所处的时代儒家思想衰落,道家思想空前活跃,玄学流行。陶渊明深受其影响,富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同时他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却并不沉溺于老庄玄谈中,因为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他还受到佛教的熏陶,参悟人生与佛教暗合,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的,他不相信来世。正应合了《饮酒》其六中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11)。思想境界越来越高,平和之心也越显突出,后来陶渊明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后世如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文学家、政治家在仕途失意后,往往也都回归到陶渊明,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酒也已成为陶渊明吟咏的一个人格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因为酒可以让他们短暂的忘记痛苦,得到精神上的超脱与解放,从而体悟人生的真谛。陶渊明饮酒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可以说酒也是他归隐心境的一大寄托。陶渊明归隐并怡然自乐,甘于寂寞的走完一生,这是一种别人都无法比拟的人格境界。就是充满豪情,颇为自负的青莲居士也得甘拜下风,但是他却在“不甘寂寞”中创造出人生又一种高尚的人格境界。
三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然而,他又处于安史之乱中,天才诗人的气质被兵荒马乱所侵扰,也勾动了诗人原本心中就有的满腔的报国情怀,从而也成为他四处漂泊的一个契机。李白所处的时代是由安定转为动乱的,它与陶渊明所处的易代环境是不同的,因此二人心中所产生的思想意识也就不尽相同。大家都知道,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不过从种种资料及其本人诗作“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等等。表明他应该是生活在一个富裕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隐居与漫游、神仙道教、任侠中度过的,这与他家所处蜀中是分不开的。蜀中是一个多山水之地,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12)许多教徒,浪人,侠士,纵横家也多喜欢把自己寓居在山水里,尤其是道教气氛极其浓郁,这就使身居蜀地的李白耳濡目染,逐渐培养成自己独有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气质。虽然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但他同样有强烈的积极入世思想,与其他文人不同的是他不屑以科举的方式进入朝廷,也不愿从军边塞,而想直接凭借干谒走上仕途。于是他以安陆为中心,历江夏,襄阳,洛阳,北上太原,南下隋州,又回到洛阳,进行着自己的干谒、漫游生活。他以一种迫切强烈的心情上书安州裴长史,韩朝宗,希求荐用。结果是大失所望,看到得只是官场的黑暗,最终落得被拒之门外的下场。于是他带着受伤的心情再次漫游,从梁,宋而洛阳,襄阳,然后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但是李白并不安分,强烈的功名心使他隐而想出,天宝元年,玄宗召其入京,李白遂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心态奔赴朝廷,试图以自己的才能“济苍生,安社稷”。这段日子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但不久,他就为朝中权贵所谗毁,被迫离开长安。强烈的待遇反差使得他的心情落差很大,后来他沿黄河东下,来到洛阳,结识杜甫。二人同游梁,宋,又遇高适。后又寄家东鲁,南下吴越,北上蓟门。近十年的漫游使他的心情更为复杂,“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可是尽管他对朝廷充满了不满与失望,但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入世,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没有消退。尽管他不为他人所容,但他宽容了世俗,后来他又因反叛罪长流夜郎,乾元二年,遇赦放回,流寓南方,最终病势于当涂,葬于青山,年仅62岁。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李白在二十五六岁离开蜀中后,再未回归一度作为“故乡”的蜀地。通过这条李白的求仕路线,我们可以看出李白诗中的微弱的“归隐”意识与强烈的“流浪意识”,也显示出李白与通常意义上的流浪者不同的是他有明确的目标和坎坷的“朝圣”之路。就如李白的《行路难》所说:“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思是说,酒和菜的价格是昂贵的,但我吃不下去,只好放下了酒杯和筷子。想渡黄河但冰封流阻,想登太行却积雪满山。看看四周都是岔路,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诗人以行路的艰难比喻世路的险阻,倾吐出不被重用的愤慨之情,从而成为他流浪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李白诗作,可以看出他的饮酒诗(《将进酒》,《山人劝酒》,《对酒》,《金陵酒肆留别》……)也正好反映了其“归隐”与“流浪”两种意识,与陶渊明不同的是李白的酒诗很多都是作于朋友离别时,这使他的诗作别有一番凄楚的风味,也更能体现出李白流浪时孤寂徘徊的心态,我们不禁眼前浮现出一个四处漂泊的游子形象。
李白近似于陶渊明,他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立抵卿相”,待到建功立业后便功成身退,归隐江湖。换言之,他不是一位持久的责任承担者,而是临时的责任承担者,然而这是不切实际的。神仙道教信仰在李白思想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道家和道教信仰给了他一种极强的自我解脱的能力,因此我们看李白最突出的人格特点就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其次,任侠四处游历和豪爽的性情也给了他很大程度的影响,成为他敢于独自流浪,无所顾忌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正是盛唐的风采。
酒是李白的一大最爱,在人们赋予李白“诗仙”之名的同时,也赠予了他另一个美名—“酒仙”,传说李白只有在喝酒时才能写出好诗,事实证明酒确实是他创作的源泉,李肇在《国史补》中记载道:“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13)像他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14)正是他乘着酒兴疾笔而书的,用他的诗句来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诗外的酒与诗中的酒已被他融汇在一起了。他对于酒也有自己的见解“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从中也可以感觉到恃才放旷的李白愤世的悲怆。然而我们从他这些诗句中只是体会到他隐约的“归隐”意识,更多得感受到的是其浓烈的“流浪”意识。李白有着超凡的豁达,他在一路“流浪”的过程中把自己深深地融入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又借着自己饮酒的豪情,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联想,过滤着他的精神思想和意识潜质,从而使自己在一次次的愿望落空时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
四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陶渊明与李白虽然都写了不少的酒诗,但其中所反映的意识是不一样的。二人虽都谈归隐,但陶渊明是在静中谈隐,且在彻底放弃仕途后又彻底归隐;而李白则是在动中穿隐,即在四处漂泊的行程中短暂归隐,因此李白的酒诗就比陶渊明的多了些“流浪”意识,且以“流浪”意识为主导。为什么李白同样具有陶渊明的“归隐意识”,尽管它很微弱。而陶渊明却没有李白的“流浪意识”,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呢?我想是因为时代造就了他们,陶渊明更加正统一些,他本身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尽管当时同样各种思想盛行,但他接受的大都是儒家的教条思想,他的生活意识比起李白就有些固步自封,似乎永远不会打开冲破世俗的那道门槛。他的生活环境已经决定了他不可能像李白一样,思想及其行为四处漂泊。他为了完成自己被赋予的官职责任,就必须每天上朝下朝,过着非常有规律的生活,他的忠君爱国思想使他先前没有思考过要彻底地改变它,也许是因为离开朝廷后,他找不到更好地报效国家的办法。所以当他被朝廷无情地抛弃后,他只有选择“归隐”,这与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因为从他的诗文中我们体会更多的是真淳和淡泊,没有像李白那样有过分的张扬和张力。金代元好问曾在《论诗绝句》中评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他的诗总是在平淡之中颇具真情实感,这可以从其作品省净的语言和平和的语气体会出来。封建社会文人一般都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是他的悄然归隐,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的“穷则不独善其身”,他的退隐并非是故作高蹈,走博取名利的“终南捷径”,而是真正出于真心本意,要坚决抛却乌纱帽,遵循个性,寻找自由,为我们昭示了一个伟大的忠君爱国的士大夫形象。他的“归隐意识”并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直至最终被朝廷抛弃才产生的,而是一直以来都在其脑海中储存的,如写景的《癸卯岁十二月中作》:“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就是陶渊明在做官的时候所写的,他虽人处官场,却时时挂念着他的园林,要回到他的农耕生活中去。人生总有众多的失意与得意,在陶渊明失意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要“归园田居”,这是他心里的潜意识(心理学上指不知不觉、没有意识的心理活动,是有机体对外界刺激的本能反应),陶渊明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这些也正是他与李白不同的意识观念的渊源。同样,李白身上特有的“艺术家”气质,让他比陶渊明更加洒脱,作品也更加富有张力,尤其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他的饮酒诗之所以也具有“归隐意识”,与陶渊明相同的一点是,或者说是与每个人都相同的就是人生的失意,对于他二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官场的失意,因此他二人经常借酒消愁,借酒抒怀,写下一首首酣畅淋漓的饮酒诗。在这其中他们一定想的是要尽快逃离这个苦难的旋涡。因此“归隐”的念头也就随着他们喝酒一次次在脑海中闪现。最终陶渊明比较幸运地遂了心愿,其实自身内心却是无限难过。李白的生性让他不甘于停下来,尽管他一次次地想过安定,可是到了最后他还是走上了“流浪”的漂泊道路。因为就像李白自己在诗中写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一杯杯的水酒只会暂时麻痹他们的苦恼神经,一旦酒醒,又再次陷入痛苦的深渊。归隐也是一种暂时的逃避,他们始终是与这个社会分不开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说陶渊明“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其实李白又何尝不是呢?李白与陶渊明的饮酒还有些不同,他虽然更多的是在失意时喝酒写诗,但是他经常在高兴的时候也痛快得挥笔,陶渊明总是显得很恬淡,其则一出自然,对于世事,真似无所在意;而李白总是非常地豪放,似乎没有他要顾及的事情。李白的“流浪”是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父亲带着全家从碎叶到四川绵州昌隆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四处壮游,四十岁以前都是遨游天下,逍遥自在的时候,“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穿行于祖国众多的大山名川,也造就了他豪爽的性情,同时注定了他与祖国一草一木的感情。山水灵氛陶冶了诗人的性灵,庄骚诗魄启迪了诗人的哲悟。《下终南山遇斛斯山人宿置酒》:“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吾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造成李白流浪的另一个原因是李白本性的狂妄,段成式在其著作《酉阳杂俎》中记载:“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他的脾气与众不合,且当时与贺知章、裴周南、崔宗之等浪迹纵酒,如此怎能不碰壁呢?陶渊明与李白的一生都与大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不同的是陶渊明接触的是所居地的山水田园这些自然物,诗文多表达一种幽静之美;而李白则是在流浪漂泊的过程中接触祖国的大山大河,因此他的诗文总是体现了大自然的壮阔之美。李白从小受其父—只有“客”这一通称的异民族移民李客的影响,被乡贡制度排斥在外,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李白的自我感觉中产生“疏离感”,自己似乎在流浪。直至以安陆为中心自我推荐努力及其失败,使得他的“寄人篱下”之感加深,从而使“流浪”意识也进一步加强,一直到最后客死他乡。还是著名诗人艾青说的好:“酒,使聪明的人更聪明,糊涂的人更糊涂。”两人身上同俱的浪漫气息使得“造饮辄尽,期在必醉”的陶渊明爱酒,爱得痴;“举杯邀明月”的李太白爱酒,爱得狂。但是酒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消解他们的愁怀。《止酒》中说:“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但是酒却成为陶渊明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让陶渊明能在醉境中见其真心。“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酒的世界却成了李白避世的世外桃源。在酒的世界里,诗人可以尽情游乐,不受任何封建教条的束缚,也不必向封建统治者低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何等的逍遥不羁!“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对自我的充分肯定!正是李白诗中的酒,造就出诗中的李白。而陶之酒恬淡静穆,自然真朴而又韵味淳厚。虽然陶渊明没有李白的那种热烈,但是他安然自如,悠然自得,展示了文人与才子气质的区别。
朱光潜先生曾对陶渊明给过这么的评价,“酒对于他好象是一种武器,他拿在手里和命运挑战。”我认为对李白来说,也是很合适的。他们以酒入诗,写意人生,一位“诗化隐逸人生”,一位“诗化激情人生”,不仅写出了诗中的酒味,读来一种清冽的醇香;而且阐释了人生真谛,令人回味无穷。
①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0页。
②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③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④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240页。
⑤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9页。
⑥《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⑦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⑧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⑨[日]松浦友久著,刘维治等译《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页。
⑩(14)李白撰、杨镰校点《李太白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0-250、840页。
(11)(12)陶渊明撰,袁行霈编校《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 247、200-300页。
(13)[日]冈村繁著,陆晓光译《陶渊明李白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