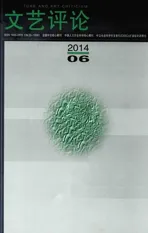杜甫咏物诗中的“物理”与“性灵”
2014-09-29王建生
王建生
伟大的文学家杜甫,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进行孜孜不倦的探求,为后世留下许多名篇杰构。据浦起龙《少陵编年诗目谱》,杜甫现存诗作1458首,始于25岁,终于59岁。乾元二年(759),四十八岁的杜甫从同谷入蜀,此后便“飘泊西南天地间”①。客居秦州、成都、夔州、湖湘等地时,杜甫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详观物态,细推物理,陶冶其诗性精神。通过咏物诗,所了解的杜甫,不再是“醉里眉攒万国愁”②,一味的忧叹,而是与自然万物亲密接触。自然、物态、物理,触动着他的灵感,抚慰着他的用世情怀,诗人那种静观、涵养,浸润于诗意内外。
一、忧郁心境的调剂
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客居秦州。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共创作十六首咏物诗:《天河》、《初月》、《捣衣》、《归燕》、《促织》、《萤火》、《蒹葭》、《苦竹》、《除架》、《废畦》、《夕烽》、《秋笛》、《空囊》、《病马》、《蕃剑》、《铜瓶》。这十六首咏物诗构成大型咏物组诗,缥缈者如天河、秋月,微小者如萤火、促织,甚至无生命的存在体如废畦、空囊等,都进入杜甫的视野。在对这些大小不一的事物的题咏中,寄寓了杜甫诗性情怀;这一点,钟伯敬总结得很到位:
少陵如《苦竹》、《蒹葭》、《胡马》、《病马》、《孤雁》、《促织》、《萤火》、《归雁》、《鹦鹉》、《白小》、《猿》、《鸡》、《麂》诸诗,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劝诫者,有计议者,有用我语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蠢者灵,细者巨,恒者奇,默者辨,咏物至此,神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著手矣。③
诚然,在十六首咏物诗中,杜甫本人的情感得以自觉流露,而这种情感又是被压缩过的,所以在诗中的表露很平和、细缓。如《促织》:“促织甚微细,哀音可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意相亲。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④浦起龙注云:“哀音为一诗之主……为‘哀音’加意推原,则闻之而悲,在作客被废之人为尤甚。感以其类,故深也,丝管不足拟矣。”“音在促织,哀在衷肠。以哀心听之,便派与促织去,《离骚》同旨。”⑤人情、物意交融在一起,很难分辨出是“哀心”聆听“哀音”,还是“哀音”触动“哀心”。之所以称之为“自觉”,言其有意为之,就十六首而言,虽所咏之物个个不同,却表现出总体一致的风格,咏物写心,委婉地寄寓自己的多样情感,而总体效果却是物意与人情水乳浑融。
检点杜甫此前的诗作,未见如此集中创作咏物诗的现象。他如此自觉地创作咏物组诗,与其心境的变化密不可分。客居秦州,开始踏上飘泊之旅,“此作客之始,为东都旧庐残毁之故,自是长别两京矣”⑥。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引起了杜甫心境的变化。因为“长别两京”,就意味着告别政治文化中心。时年杜甫四十八岁,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抱负,有“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⑦的才华,却不得不收起大展宏图的双翼,内心深处的酸涩、凄楚不待言表,积郁遂深,该如何调适呢?杜甫调节这种心境的表证,就是联章体遣兴诗的大量创作。秦州时期,杜甫共创作了五组(十八首)联章体诗。如《遣兴五首》之一:“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古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陇阺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杨伦评“第一首虽有两古人作骨,却多说自家话”⑧。出于调节心境的需要,除了联章体的遣兴之作,杜甫还尝试用咏物诗的形式,来排遣抑郁。从这个角度来讲,秦州咏物诗充当了杜甫忧郁心境的调适剂。
秦州咏物诗的创作,大大开拓诗歌题材,其前虽也有咏马、咏月之作,却有一种昂扬的少年精神在其中,就其咏对象而言,大都具有精神激励意义。而秦州后的咏物诗,其对象更为宽泛,而且更着眼于物意人情之间的沟通,这也是秦州后咏物诗的总体特征。如《病马》诗中,老马衰病而不被弃,与诗人哀怜情感相吻合,即是如此。在寻求意情相通的意旨下,“物”不在于形体之大小,可以是日月风雪,也可以是花鸟虫鱼,即便是微不足道之物,彼时彼境,杜甫亦能找到物意关联点;将情感积淀后通过物意传达出来。
二、咏物诗的精进之路
从同谷入蜀后,杜甫寓居成都,过上了相对安适的生活。相对闲暇平静的草堂生活,让诗人有充裕的时间,带着诗兴的眼光观物、观世、观我,从而诞生诸多清新灵动的诗作。如《江头五咏》组诗:《丁香》、《丽春》、《栀子》、《鸂鶒》、《花鸭》。浦起龙评:“江头之五物,即是草堂之一老,时而自防,时而自惜,时而自悔,时而自宽,时而自警,非观我、观世,备尝交惕者,不能为此言。先儒每困于流离中,炼于身心学问,此诗应有合焉。”⑨诗人情感蕴涵在物意之中,诗意中分明有一个“我”,咏物与自咏自喻完美的统一。《栀子》诗:“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伤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⑩在杜甫眼中,栀子有着与众不同的风姿、情韵;而能发现并赏识栀子之风情,不正是诗人性情的映现吗?就其所咏之物而言,杜甫善于抓住最有特征的点而透视其全貌,如《梅雨》中“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11)二句,将江南梅雨时节淅淅沥沥,连日不开的特征概括出来,其中也体现了北方人对南方风土节候的静观细察。从成都时期开始,杜甫的咏物诗朝更加精微的方向发展。不仅咏物诗出现精微之作,许多咏物句亦精微迭现,让人目不暇接,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12),又“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13),无限情致,尽从“繁”、“嫩”出。体物至此,足以“惊风雨”,“泣鬼神”。
到达夔州之后,杜甫的咏物诗创作进入高峰期,约有50首咏物诗诞生。黄白山评价道:“前后咏物诗,合作一处读,始见杜公本领之大,体物之精,命意之远。说物理物情,即从人事世法勘入,故觉篇篇寓意,含蓄无垠。”(14)夔州时期咏物诗达到自然化工的境界。故李子德评价说“何处得其微妙,贯乎化工矣”(15)。试举两例以证之:
《雨》:“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时。轻箑须相向,纤絺恐自疑。烟添才有色,风引更如丝。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16)此诗大历元年(766)春云安作。首联说时节,颔联言天气闷热,竟用起了扇子,反衬所用非其时,颈联写绵绵细雨,尾联虚笔一晃,让人顿生无穷遐想。
《江梅》:“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绝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雪树元同色,江风亦自波。故园不可见,巫岫郁嵯峨。”(17)该诗乃大历二年(767)春于夔州西阁作。由梅花及春意、客愁,次及雪树江风,落笔于故园、巫岫,这种跳跃性的物象与空间切换,使“风景不殊河山之异”的今昔感喟,跃然而出。它如《见萤火》、《月圆》、《吹笛》、《庭草》、《树间》、《白露》等,都可称得上咏物之杰构。
到达夔州后,同题咏物诗的批量创作,显示出杜甫独特的创造力,敏锐的洞察力及非凡的想象力。月、雨成为反复吟咏的对象,咏月七次十首,咏雨十三次十七首。我们不得不惊叹杜甫同中求异,另辟蹊径的艺术构造能力,所咏之月,个个清辉,在月光的抚慰之下,有写不尽的羁旅行愁,碾不碎的还乡梦。同题同旨的约束下,“江月”与“圆月”又是如何超脱共性,成就其独特性呢?以《江月》一首为例证明:“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天边长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团清影,银河没半轮。谁家挑锦字?烛灭翠眉嚬。”(18)浦起龙注云:上四,琅然清圆;五、六,无尘气;七、八,更不即不离。月得江而弥光,光满楼而动思,思由“作客”,客故“霑巾”,触之者“江月”,为所触者客“思”也。“玉露”、“银河”,旁笔写景。(19)
同题多咏的艺术魅力,在咏雨诗中也得到很好的展示。云安春雨“烟添才有色,风引更如丝”(20),夔州雨“风吹沧江去,雨洒石壁来”(21),写急雨“行云递崇高,飞雨霭而至”(22),写绵绵细雨则“青山澹无姿,白露谁能数。片片水上云,萧萧沙中雨”(23),写密雨则“骤看浮峡过,密作渡江来”(24),写晨雨“小雨晨光内,初来叶上闻。雾交才洒地,风折旋随云”(25),写夜雨“山雨夜复密,回风吹早秋。野凉侵闭户,江满带维舟”(26),咏江雨则“乱波纷披已打岸,弱云狼藉不禁风。宠光蕙菜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27),咏寒雨则“朔风鸣淅淅,寒雨下霏霏”(28)等等。这种对雨全方位多视角的描述,只有心入其境,心神与自然的冥合,才能产生如此杰作。有第一等襟怀,有第一等洞察力,方有第一等诗人。才学、识见及诗性感观,都是这类诗创作所具备的材料,否则,就会跌入呆滞、重复的低谷。在杜甫咏月、咏雨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心灵的律动,这是杜甫咏物诗创作的三昧。
说理、议论的参与,是杜甫夔州咏物诗另一显著特点。《鹦鹉》、《孤雁》、《鸥》、《猿》、《麂》、《鸡》、《黄鱼》、《白小》八首,已或多或少的加入议论成分。触物感怀,感而发之,本是一种通行的诗文写作规律。由物到情感是一种很自然的表露,而由物到议论,超越个体情感,则是一种突破。一旦进入议论层面,个人情怀已上升到一定高度,民胞物与,所感发的多是大众情怀或普世性的道理。这既需要情感的转换,更需要相当广阔的胸襟与怀抱。当然,在杜甫这里,我们看到议论的火花,星星点点,灵光乍现,给人一种阅读的冲击、震撼。以杜甫咏物诗数例,以见证杜甫议论之风采。
《鹦鹉》末句“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29)诗歌结句写别离之故,感慨遥深。“就剪羽解嘲,言正不须丰满见奇,有怜而收汝者,将复损之,不如息意于此。”(30)“解嘲”抑或“感慨”,均针对世事人心而发议论,见解明确,发人深省。
《猿》“惯习元从众,全生或用奇”(31),因猿啼而发议论,借猿智能远患,来说明涉世之难。《麂》“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32),浦起龙评曰:“五六名言,汉、晋间士人之祸,十字括之。”(33)仇兆鳌注云:“后半慨世,不离咏物,而却不徒咏物,此之谓大手笔。”(34)感慨议论的强化,使全诗境界阔大。王士祯云:“咏物诗最难超脱,超脱而复精切,则尤难也。”(35)杜甫能跳出一己之私,放眼古今,故能有超脱世俗之见。
《白小》“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如?”句,朱鹤龄评曰:“一鱼虽小而不尽取之,岂得为义乎?”(36)拾卵而不尽取,深深的触动杜甫民胞物与的情怀,所以尾句之议论,实际上包含斥责、呼吁等复杂的情感。
杜甫夔州咏物诗那种行云流水式的笔法,突兀峭拔的警句,水到渠成的情韵,使咏物诗的创作进入自然天成的佳境。这恰好与杜甫总体诗艺的圆熟合拍。黄庭坚有一番经典评论:“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耳。”(37)进入夔州后,杜甫诗歌尤其是律诗的技艺浑然天成,“不烦绳削而自合”。杜甫咏物诗能有如此成就,与杜诗艺术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纵观杜甫从秦州到夔州时期的咏物诗,可以看出他诗艺精进的过程。
三、“细推物理”、“陶冶性灵”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对杜甫咏物诗有一段精当的评论:
咏物起自六朝,唐初沿袭,虽风华竟爽,而独造未闻。惟杜公诸作,自开堂奥,尽削前规。如咏月则“关山随地阔,河汉近人流”;咏雨则“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咏雪则“暗度南楼月,寒深北诸云”;咏夜则“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皆精深奇邃,前无古人。(38)
胡评“自开堂奥”、“尽削前规”、“精深奇邃,前无古人”,诚不为过。杜甫咏物诗确实是一道奇峰,它劈开了一个新的天地。“物”决非消遣之玩偶,而是兼融物理人情,酝育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单不说他那近百首咏物诗,即便那些散落于各体诗作中的咏物写景句,亦包含人情物理,杜诗中触目皆是,聊举数例,以兹证实:“鲜鲫银丝鲙,香芹碧涧羹。”(39)“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40)“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41)“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42)
杜甫已自觉的将“物理”纳入写作的轨道,“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43),“挥金应物理,拖玉岂吾身?”(44)“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45),又“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46),“物情尤可见,词客未能忘”(47),等等。“物理”,在杜甫的诗集中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它既指有形之物的生长荣枯,如花开花落、北雁南飞等等,又蕴含着自然界损益变动,生生不息,兴衰更替的规律,乃至当下人情冷暖,世态薄厚,名利的羁锁,生途的艰涩……足够让一社会人躁动不安,形劳神伤。忠君爱国,仁民爱物牵动杜甫的用世情怀,疲惫着那颗忧伤的心灵,“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48),“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49),“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50)。物,舒平诗人眉宇间的忧愁;物,润泽诗人跳动的心灵。故凝眸望去,物物含情,“沙晚低风蝶,天晴喜浴凫”(51),“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52),“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53)。
物之理并非终极目的,诗人由物理上升到浮生之理,顺应此理,不悖不逆,从而达到物理、生理与人情的自然融合,他明言:“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54)杨伦评此句“言欲识浮生之理,即观物情可见”。又,“自喜逐生理,花时甘缊袍”(55),如此“体物”,以求“自适”、“自觉”,即追求心灵的安适和内心境界的提升。
因对“物理”的关注,带动诗人对物情、物态、物色的静观细摩。物色方面:“物色兼生意,凄凉忆去年”(56);“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流与老夫”(57);又杨伦评《江村》“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称“二句物色之幽”(58)。“物色”近于物类,杜诗中,物的品类之盛,让人称叹。物情,含人情而非人情,王国维云:“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59)人之情一经物之润泽,已非人情,读者亦不觉是人情,荡漾着自然的清新与活力,让人流连,让人劳神。“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60),“狎鸥轻白浪,归雁喜青天”(61),“细草留连侵坐软,残花怅望近人开”(62),“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班”(63),“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64),缘不论一笑一喜,一愁一恋,物情、人情几难分辨,又何须分辨?
植根于物我同视的情谊,以物为友伴,“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65)。淡出世俗的物累,看到一个清新澄明的灵物天地,静的、动的、静中有动的、动中含静的,百态俱见。以咏雨诗为例:写平静之细雨“青山澹无姿,白露谁能数。片片水上云,萧萧沙中雨”(66);写暴风骤雨“峡云行清绕,烟雾相徘徊。风吹沧江去,雨洒石壁来”(67)。至于咏物句中动静态的例证,举不胜举,此不赘述。
与物理相关捩,便是诗人“性灵”的陶冶。凡伟大之诗人,必具多方面之才能。就杜甫而言,既有体民忠君的怀抱,又有亲和自然的情调,若千诗一旨,何以成为伟大诗人!通过咏物诗及咏物句,我们看到诗人生命的律动,感受到他对自然、人事永不疲倦的叮咛、追索。物,在诗人的炼炉中燃烧,点亮诗人心香一角,那是别样的杜甫,不是“三吏”“三别”式的悲吟,而是在遣兴,在涵养心性。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68)
“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69)
“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劳。”(70)
在咏物诗中,诗人的心性陶醉在自然物中,性灵的舒展与物象的描摹相牵连,同步运行。何谓性灵?一为精神,一为情感。紧绷心弦的,舒缓平和的,不一而足。物在精神或情感的促动下,对情感的发抒起着缓冲作用,这在《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等以讽谕为旨的咏物诗中,表现更突出。将己之情转化融注在“物“之中,然后由物托出,经此曲折运动,委婉平和,不露锋芒。如《病柏》一首:“有柏生崇冈,童童状车盖。偃蹇龙虎姿,主当风云会。神明依正值,故老多再拜。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出非不得地,蟠据亦高大。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鸮志意满,养子穿穴内。客从何乡来?伫立久吁怪。静求元精理,浩荡难依赖。”(71)李西崖认为,这首诗乃伤悼房琯之作。至于喜怒哀乐等情感,在咏物中有广泛的体现,如《丁香》末二句“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杨评“若护若诫深婉可味”(72)。
就整体而言,咏物诗中愁、忧的感情成分比较多,这与杜甫经历、志意有关。黄庭坚二句诗说得好,“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73)。乐也好,愁也罢,一旦经过“物”的洗涤过滤,所散发出来的都是诗性的情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74)、“凭几看鱼乐,回鞭急鸟栖”(75)、“隐几看帆席,云山涌坐隅”(76)等等,超脱单纯物象描摹,弥漫着情感的氤氲,闪烁着跳动的性灵,这也是杜诗魅力所在。
咏物诗的发展源远流长,《诗经》鸟兽草木,《楚辞》中香草美人,虽为零星散句,远非后世连篇咏物可比,然状物贴切,又兼比意,基本上奠定后代咏物之格局。后世咏物,多从物、意两方面进行开拓:写物则力求真切神似,托意则求隐委圆融。由先秦的言志、意,到六朝的类化情志,及至唐代,则为个体情怀,极尽曲折,渐至佳境。杜甫咏物诗超越前人,自开堂奥,即使在同时代人中,亦卓然特出,截断众流。举同一时期李白与之相比,杜甫咏物诗的典范意义更为卓著。李白感兴散漫之人,咏物诗数量少,远没有杜甫的耐心与工巧,兴象随至,无拘无束,感情的激流奔腾横溢,所以并无规矩可寻,如《南轩松》:“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幂。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霞,直上数千尺。”(77)杜诗除了情感的荡漾外,还有物态具象的刻画。其咏物诗物与情、形与神的有效结合,都为后世咏物诗甚至咏物词提供了范本。总之,杜甫在咏物诗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地位,其作用重在启后,其意义是多重的、广泛的。
①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杜诗镜铨》卷十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50页。
②(73)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山谷外集》卷十六,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42页。
③杨伦《杜诗镜铨》卷六《归雁》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2页。
④⑦⑧⑩(11)(12)(13)(16)(17)(18)(20)(21)(22)(23)(24)(25)(26)(27)(28)(29)(31)(32)(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4)(75)(76)杨伦 《杜诗镜铨》,第 257-258、25、234、386、317、345、355、580、737、666、580、626、626、627、742、743、782、747、857、828、830、830、64、178、341、357、180、671、922、277、271、952、952、963、445、467、778、813、277、446、968、320、355、446、447、504、890、968、627、626、817、739、1012、370、385、344、782、971页。
⑤⑥⑨(19)(30)(33)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96、27、431、504、523、525页。
(14)(15)(36)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七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2、830、832页。
(34)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33页。
(35)王世贞《分甘余话》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页。
(37)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二,《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
(38)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页。
(59)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77)李白《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