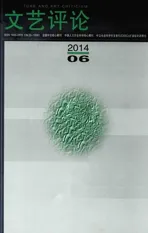《左传》卜筮与《周易》的美学传播
2014-09-29高方
高方
卜筮是人类文化原始时期遗留下来的预知吉凶的方式,是先民历时久远的精神遗存,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能看到它或隐或显的影子。春秋时期,在“天命”思想的援引和指导下,卜筮以一种极其普遍的方式存在着,《周易》就是人们所采用的重要工具和依据之一。那些因占卜而产生的颇具文学色彩的卦辞、繇辞(爻辞)等卜筮之辞也随着占卜活动在民间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并对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一、遇事则卜的春秋习俗
春秋人在很大程度上相信神灵和鬼魂的存在。《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内史过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虢之史嚚也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僖公十年秋天,狐突在去曲沃的路上遇到了太子申生的鬼魂,约定七天后附于巫的身上传达天帝使夷吾“敝于韩”的命令。所以晋惠公夷吾在秦晋之战中败于韩原应验此说之后,秦人才会说“晋之妖梦是践”。僖公十五年夷伯之庙遭受雷击,左氏认为其有不为人知的罪过而受到天谴。昭公十八年郑国大火之后,子产也曾一度忙着“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除了人的行为,僖公二十八年甚至还出现了主动“索贿”的河神。①
正因为人们相信鬼神的存在,才会生成一种与之相关的特定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认识,于是每遇重大事件就要以卜筮决之,卜筮就成了人们生活中必要的组成,《尚书·洪范》“稽疑”条下即言“择建立卜筮人”,其原则是“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②。卜人在其时的地位也是相当受人重视的。隐公十一年滕侯和薛侯同时来鲁国朝拜,于是在位次先后上发生了争执。薛侯的理由是“我先封”,滕侯则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卜正”即是卜官之长,可同天人沟通,预料吉凶祸福,且为周之同姓,于是在取得薛侯的理解后这次朝会“乃长滕侯”。
关于《周易》,金景芳先生早就说过:“周易是具有卜筮形式和哲学内容的矛盾的统一体,它有荒诞的一面,也有正确的一面”,“蓍卦本为卜筮而设,而其内容实体现了哲学思想。这个哲学思想和古代希腊哲学一样,是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宇宙观。但是一经变成公式,把它应用於卜筮,它就不可避免地又有了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性质。”③自汉代经学兴起后,《周易》就被称作《易经》,“易学”则成了解释其经传的专门学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易》为开卷第一编,《周易》便从此成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扬雄也说:“六经之大莫如《易》。”随着儒家经典数量的不断增加,《易经》又被称为“群经之首”。
作为后世各种占卦术的源头和渊薮,《周易》在春秋《左传》之中的出场频率也是极高的。《左传》中首次出现《周易》之名与《周易》之筮是在庄公二十二年: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敬仲名完,是陈厉公之子,因陈国内乱而奔齐改为田氏,卒谥敬仲,代齐之田常为其八世孙。敬仲年少时,周朝太史携《周易》来见陈厉公,陈厉公请其为敬仲占筮。这说明《周易》之类的典籍当时尚由周王朝集中管理并未广泛散落于诸侯之国,且占卜之术还由专门人士来完成,人们也还十分相信占筮结果的预言功能。但当敬仲奔齐并到了娶妻之年的时候,“懿氏卜妻敬仲”所用就是隆重的龟卜之法,“其妻占之”则告诉我们占卜人不再是专门的神职人员,而可以由大夫之妻即一个普通的女子来充当,而其所得的“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大吉之兆竟然也能和周太史当年的《周易》之筮相吻合。到了陈国覆亡的时候,敬仲的五世孙陈无宇开始在齐国昌大,八世孙田常则在战国之时专政于齐,都验证了《周易》之筮的准确无误。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生活几乎无事不行占卜,立君要卜(僖公十五年)、祭祀要卜(僖公十九年、三十一年)、迁都要卜(文公十三年)、嫁女要卜(庄公二十二年、僖公十五年)、立夫人要卜(僖公四年)、有孕要卜(僖公十七年)、疾病要卜(僖公二十八年)、下葬要卜(宣公八年)。战争之中更是卜得十分仔细,是否作战要卜(僖公十五年)、是否追击要卜(襄公十年)、使何人驾车要卜(襄公二十四年)、使何人追敌也要卜(文公十一年)。僖公十九年卫国大旱,“卜有事于山川”是卜祭祀,僖公三十一年告诉我们“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向筮史行贿说明此次所行是“筮”而不是“卜”;文公十一年“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于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昭公十八年吴伐楚,楚人“卜战,不吉”,便不欲战;昭公三年,晏子甚至引谚语告诉我们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连选什么样的人做邻居都是要由占卜来决定的。昭公五年说:“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
巫、祝、卜、史均通于占卜之术,而且无不得益于家族承传,但后来一些看起来和占卜没有什么关系的某些“来历不明”的人也能参与其中。如庄公二十二年的“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襄公十年的“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等等。卜筮之外春秋时还有一种独特的占星之术。例如《左传》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就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他的预言。昭公十七年,鲁申须、郑梓慎、郑裨灶更是依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的天文现象,同时预言“宋卫郑将同日火”,而他们的预言第二年就应验了。
二、卜以决疑的民之初心
《白虎通》云:“龟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见兆也。筮也者,信也,见其卦也。”④《礼记》云:“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⑤由此可知卜筮之法都是为了“决民疑”。
僖公十七年补记当年事,说晋惠公之妻梁嬴怀胎十月却未能及时生产,于是使“卜招父与其子卜之”,占卜显示“将生一男一女,男为人臣,女为人妾”的结论,梁嬴果然生了一对龙凤胎,并不信邪地按照卦义给他们分别取名为“圉”和“妾”。而最后的人生结果也是其子圉西质于秦,其女妾为宦女,无不与卦义相合。这一事例不但告诉我们占卜的结果十分准确,而且透露给我们知道卜人是一个父子相袭的职业。僖公十五年晋惠公于韩原之役被秦人俘获放归后,对群臣说:“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就是让大家卜定日期立子圉为君,古人认为“大事卜,小事筮”,言“卜”而不言“筮”明立君为大事也。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行卜法而不行筮法,是因为迁都也是大事。而僖公十五年追记当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可见嫁女虽也行占卜之事却算不得大事。其繇辞“士刲羊”“女承筐”等语见于今本《周易》,其释义则出于史苏之口,而晋献公未从史苏之占执意嫁伯姬于秦穆公也表明了春秋人对天意的不完全认同。
事实上,还有一些占卜并不全赖神力,而是建立在经验和见识的基础之上,可以算是人力和神力的结合。晋国卜偃的事迹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左传》闵公元年晋献公作二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灭耿、灭霍、灭魏,回来后把魏地赐给毕万并任命他作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僖公二年虢公在桑田打败了戎人,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僖公十四年秋天沙鹿山崩塌,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僖公三十二年冬天,为晋文公出殡时灵柩中发出牛鸣一般的声音,卜偃让大夫们下拜,说:“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以上四例都只记了卜偃之言,而未记他有占卜的行为。并且从他的言论看,多是出自于一个智者的敏锐思考,而非神的意旨的决断。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卜偃已摆脱了沟通天人的工具属性,而直接成为了人和神的结合体,其预言的准确和神性的存在是建立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的。
宣公十二年郑楚有战,晋人准备救援郑国却听说郑国与楚人结盟,于是打算攻打郑国。先縠不肯审时度势一意孤行率军渡过黄河后,荀首说:“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谓之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他的理论并非来自占卜,而是来自《周易》之文的智慧启迪。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此处也是运用《周易》哲理所作出的准确判断,同是非卦之思。
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从楚国回来,告诉子展说:“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昭公元年晋侯有疾,秦国医和判断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当赵孟问其“何谓蛊”时,医和回答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在与赵简子论“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这一话题时说道:“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震上乾下即为大壮之卦,以论季氏自公子季友至季文子、季武子的功业。此处和上面的例子一样,都不是占卜得来的爻辞,而是将《周易》中展现的哲理应用于现实的生活,以使人们有悟、有感。
《左传》所叙的神鬼虚妄之事中,也不乏神不能主宰人事的记录。成公五年赵婴因为与赵庄姬私通而被自己的兄弟放逐到齐国,此前赵婴曾梦到天使对自己说:“祭余,余福女。”就是说天神说你祭祀我我就会降福于你,可赵婴这样做了却仍旧没有避免被放逐的结果。士贞伯借此事一语道破人神之间的关系,他说:“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僖公二十一年鲁国大旱,鲁僖公认为是巫师和上天沟通不利,并且因为上天可怜那些仰面突胸的畸形人,怕雨水灌入他们的鼻子所以不肯下雨造成大旱,就想要烧死他们。臧文仲不但用“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作为理由劝阻了鲁僖公,而且建议他从人事的角度来“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最大限度地降低旱灾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襄公十年宋平公在楚丘设享礼宴请晋悼公,席间使用了《桑林》之舞。因为《桑林》之舞属于天子之乐,晋悼公虽辞谢却未能成功制止。回国途中走到雍地时晋悼公生病,占卜的结果是桑林之神在作祟。荀偃、士丐想用祭祀的方法攘灾,荀罃却说:“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于彼加之。”不但谴责鬼神之无礼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而晋悼公的病也自己好了。
三、取象譬喻的卜辞之美
古人说“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却也说“大事先筮而后卜”⑥。僖公四年记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时就是这样:“卜之,不吉;筮之,吉。”晋献公于是决定“从筮”。卜人的建议则是“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并以占卜所得的不吉之辞来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
这段记载从多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卜筮的多条信息:一是诸侯立夫人要通过卜筮来决定吉凶;二是“卜法”与“筮法”可以同时使用;三是卜法通常比筮法更加灵验,即所谓“筮短龟长”;四是卜筮时已有现成的繇辞可供参考;五是卜筮的结果不是一定要遵从,而是可以由人来作出最后的决断,并已经表现出了对天命的怀疑和否定。这里我们主要说繇辞。
僖公四年的这条繇辞是:“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大致意为:“专宠一定会产生变乱,将要夺走您的肥羊。香草和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还会有臭气传扬。”这条繇辞以杂言写成,兼具押韵特点,在拟写方式上擅用比喻,不但先以“羭”贴切地将申生比作献公之肥羊,而且能够以“薰”“莸”喻申生、骊姬等人之品性并体现流芳遗臭之意,可见构思之精巧、表义之恰切。
庄公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得到的繇辞是:“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这条繇辞音韵优美,全用四言,首二句兴中有比兼用叠字,将其与《诗》中的史诗类作品置于一处恐怕也难分轩轾,体现了高超的写作技巧与写作水平。
僖公十五年晋国韩简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虽然他的目的在于说明“象在数先”,却也在无意中为我们揭示了占卜与取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前为晋怀公占卜所得的繇辞是:“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晋怀公在此战中被秦人俘获,证明他与“雄狐”之间是一种显在的比喻关系。襄公十年郑国皇耳率师侵卫战败时,卫国大夫孙文子卜追之,其繇辞为:“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当卫夫人定姜作出追击的决定后,卫人抓住了郑国的主帅皇耳,皇耳与“雄”之间也是一种显在的比喻关系。两条关于战争的繇辞都以“雄狐”或“雄”为喻,说明了繇辞写作中有着相似的取象原则。结合其他实例去看,则会发现比喻修辞在春秋繇辞中的运用十分普遍。例如,哀公十七年卫庄公“亲筮之”所得的繇辞也存在着这样的特点:“如鱼赪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在品味《左传》繇辞之美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有着明确的文化源头。
刘大均先生说:“《周易》这部书,讲的是象、数、理、占,揭示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对立与统一的法则,并运用这一世界观,运用八卦模拟表达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的各种信息。”⑦但人们说起《周易》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往往是它的“象”,然后才是数字、道理和占卜。《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下》亦曾直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而“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韩非子·解老》释“象”曰:“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周易》的产生远远早于《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它所先取之“象”是远古先民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所发现的生活要素和生活本质,来自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基本需要和诗性观察。而将客观生活呈之于“象”,也表明了先民最简单也最直接的目的“立象以尽意”。如《说卦传》释“乾”卦时即言:“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孔颖达《五经正义》解释说:“乾既为天,天动运转,故为圆也。为君、为父,取其尊道而为万物之始也。为玉、为金,取其刚之清明也。为大赤,取其盛阳之色也。为良马,取其行健之善也。为老马,取其行健之久也。为瘠马,取其行健之甚,瘠马多骨也。为驳马,言此马有牙如据能食虎豹。《尔雅》云:‘据牙食虎豹。’此之谓也。王赓云:‘驳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为木果,取其果实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这些都说明《周易》的意蕴表达是建立在“象”的基础之上的。《周易》之象来源于先贤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睿智选择,风雷雨雪、山川河野、夫妇君臣、衣食庭邑无不入于明达之眼而用于传示自然之理。“《周易》当中的卦象由于经过《辞》尤其《传》的解释已不单是定吉凶的象征,而是成为概括世界万事万物的模式,有其更广泛的象征意义了。”⑧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不可方物也。”⑨昭公二十九年晋国出现了“龙见于绛郊”的奇景,蔡墨在和魏献子的对话中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上述内容除最后一条见于今本《周易》的《坤》卦之外,均见于《乾》卦,从初爻到六爻,自下而上是讲“龙”由“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到“亢龙有悔”的整个过程。傅道彬先生认为,“这里描绘的是苍龙星由冬及春、由春及秋的秩然有序的运动变化,意义上是层层递进的。爻辞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意义是跨越爻位而联系在一起的”,并认为其“韵律和谐”,有着“丰富的诗的蕴涵”。⑩事实上,卜筮中出现的那些春秋人或是更早些时候巫祝卜史等人所拟的繇辞都是其时语言的精粹,都饱含着诗的因素,甚至包含着诗的要素。也正因如此,卜筮才成为其时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
章学诚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也。”(11)春秋时期,人们的精神领域已经相当开阔,精神世界也相当丰富。文化储备早已成为一池丰盈的春水,文学的和煦之风吹进城墙宫殿,也盘旋于城郭田野。在金声玉振之中,高庭清酒之间,砖木石瓦之上,人们手捧《周易》虔诚卜筮乞求上天的垂怜。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迷信,而是春秋生活最真实的景象,也正是春秋的卜筮生活为我们留下了质朴的祈愿、庄重的仪典和优美的卜辞。
①《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南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②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2页。
③金景芳《易论》,《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
④《白虎通·蓍龟》。
⑤《礼记·曲礼》上。
⑥《周礼·筮人》。
⑦刘大钧《〈周易〉浅说》,《山东图书馆季刊》,2006年第4期。
⑧黄广华《〈周易〉成象说》,《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
⑨(11)章学诚《文史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 页
⑩傅道彬《〈诗〉外诗论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