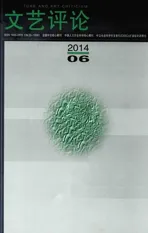论阳明心学对黄省曾人格心态和文学思想的影响
2014-09-29吴琼
吴 琼
黄省曾(1490—1546),字勉之,号五岳山人,是明中期一位博学多才的文人。他的一生贯穿弘治、正德、嘉靖三个时期,其与明中期文坛的许多名流都有密切而频繁的交往,而其复杂的人格心态与独特的文学思想则与阳明先生所倡之心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黄省曾倾心于阳明心学对其任心自适的人格心态之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儒家提供给士人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外向型选择,士人自然可以用儒家种种理论进行修身,自我提升,但其最终的旨归是为了服务国家;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哲学,尽管它也强调经世致用,但其更多的是讲求通过理来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善人格境界,用外在的理来指导人生实践。而阳明心学与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要坚持儒者救世济民的传统责任,二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虚明灵觉,不受外物沾染,获得良知之超越境界。因此,阳明心学便为包括黄省曾在内的诸多士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天地,他们即使在不能通过科举跻身仕途、振耀王庭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生命的丰足、自我的快适,仍然能够实现不朽的人生情结。因此,在接触阳明心学后,黄省曾的人格心态无疑更向着任真自适一面倾斜。
“无可无不可”的超越境界使黄省曾终于能够从履考不中的现实中解脱出来,原来,著书立说以成一家之言一样可以获得人生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甚至可以获得不朽的名声。出处进退之间不必再受更多的委屈和折磨,适时获取实惠的人生乐趣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座右铭》中,黄省曾重新对自己的人生下了定义:“虚静养天龄,宣节与候通。恬淡而卓守,砥厉戒圜同。出也泽九方,处则乐而终。”①这出处进退皆能自得其乐的人生理想便是直接受到阳明心学影响的结果。
黄省曾一生酷爱遨游山水,每到一地赏景,必赋诗以助兴。心学之良知境界作用于外在的山水,便使黄省曾形成了对生生万物的真切体验、丰富了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感受,同时也使这种自适之乐不再仅限于对客观景物的欣赏,更使其内心之情境得以充实和饱满。因此,黄省曾才反复申述自己必周游五岳的原因:“小子所以长思缅虑而必之乎五岳也。五岳之地,仆岂徒之?盖将撰造一家之言,登诸竹简,藏诸名山,以付于来哲耳。不亦俊伟光世也哉!……夫五岳小子必游,游且必以圣贤之道发之于文,以成一家之言。归于故乡,仍亲农作于南海,以窃附乎向长、梁鸿之末,则仆之志愿毕矣。”②
成就一家之言同黼黻盛世一样,都可以实现俊伟光世的人生理想,而将圣贤之道发之于文,又是黄省曾一生所追求之最高目标,因此,省曾从心学处受惠可谓多矣!吴中的隐逸传统在这里又可以与心学之自得境界相联,徜徉山川、躬耕陇亩不再仅是消极避世的自全之法,而是实现人生理想后实实在在的欣然快适。
在黄省曾的文学创作中,他多次提及这种“潇洒”、“洒然”、“宴然”的心境:
山人种竹当清轩,攀弄修篁心洒然。春摇红日醉芳醑,夜扫明河横素弦。泠风萧飒听来好,翠影婵娟对可怜。平生制得玄洲曲,借尔吹箫秦女边。③
落日惠山生紫烟,参差龙剎俯江天。清觞碧草金岩上,潇洒春空挥五弦。④
珠璧穷暮天,赋诗吾自怜。孤独凄在眼,岁除无一钱。颜色凋青镜,贱贫心宴然。室人莫交谪,听我鸣清弦。⑤
在前两首诗中,黄省曾将良知的超越境界与自然山水结合,形成了一种意态风流、飘逸潇洒的生命情状,那攀弄修竹、制曲吹箫的生活情趣,那落日紫烟、碧草金岩的美好画卷,没有透彻领悟良知境界之人是无法安然享受这人生之乐的。而第三首诗则展现了省曾生活的另外一面。除夕之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热舞欢歌,而此时的黄省曾却因为家无余钱而处在困顿之中。这一冷一热的对比更突出了诗人生活的凄苦。然而,此诗的情感基调却不是立足于这孤独凄冷的氛围之中,而是在颈联实现了一个转折,“贱贫心宴然”说出的正是省曾富贵贫穷都不能动于心的人格境界。诗人此言不光是自宽自慰,还要抚慰自己的家人,让他们在清雅的琴音中共同感受这种毁誉富贵不萦于怀的超然境界。
当黄省曾成圣的志向受阻,无法实现儒家入世的人生理想时,吴中根深蒂固的隐逸传统便占了上风。他也像唐寅、祝允明等人一样,追求世俗的享乐生活,但他却绝不风流放荡。因为黄省曾始终还在关心着世运和文坛的动向,他在接受阳明心学后,更是把重心放在了著述问学等事上,因为这一样可以实现成圣的志向和不朽的理想。因此,他的任真自适中更多的是古之君子的作风,这与完全耽溺于物质享受中之人是不同的。
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黄省曾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主观性灵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观念。这种文学思想的形成,又与其接受心学所形成的人格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哲学体系,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士人在明中期生存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和困境,而阳明选择的解决方式就是改造士人心态。可以说,阳明并没有以解决任何实际的文学问题为主观目的,尽管他对文学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但那也只是作为一种陪衬出现的。然而,心学对文学所造成的客观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心学主张关注个体情感、个体生命之价值,阳明拈出“良知”这个哲学概念,首先就是强调“良知不在心外”,它是心之本体,心之虚灵明觉。因此,对良知的强调实际就是要求遵循本心、从心灵出发观照万事万物。反映在文学思想中,就是左东岭所说的:“良知说对其(王阳明)诗学观念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心与物的关系上。”⑥就黄省曾来说,他一生酷爱山水之游,心学首先就通过山水自然进入到他的内心,使其进入到一种虚明灵觉的主观境界中,由对外在景物单纯的欣赏而转入到审视自己内心的情感、体悟生命之真谛。他笔下的山水自然、人情物态,丰富饱满,他不再把自然当成纯粹的承载客体,而是注重人与自然冥合无间的情感体验,“水寻沧海去,云抱碧山来”⑦,“日含山气落,云抱水容移”⑧,“芳草无心迷客径,桃花着意带流川”⑨等诗将云、日、水、芳草、桃花等自然物象拟人化,使之具有浓浓的人情味和情感意识。在虚明灵觉的良知境界中,一切都是真诚自然的,主观心灵的洒落和豁达成就了一种真实适意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而这种心境又利于培养对文学的审美情趣,感受艺术的真和美。
黄省曾注重主体心灵与客观物象之间的融合,而又要时时突出那一念之灵明,强调主观性灵作用于客体时所达成的文学效果。个体在观照自然万象时,感受到的是生生不息的生之体验,内心回归到一种原初的状态之中,没有任何伪饰和狡诈。因之,人的内心体验和情感也便跃动鲜活起来,这是建立在心与物统合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观念,正因物之真切无伪,主观之心灵要想达成虚灵明觉之状态,便亦只有真实地反映、还原客体世界,从而便形成了一种重视主观性灵的文学观念,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一种真实自然的价值形态。
在黄省曾看来,诗与文的本质相同,首先都是以阐发性情志趣为旨归的:
诗者,神解也,天动也,性玄也。本于情流,弗由人造。故虞书显为言志,泗夏标之嗟叹,盖重词复语不出,初源迭韵,盈篇悉形,一虑观之,三百自可了。如古人构唱,直写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态各畅,无事雕模;若末世风颓,横添私刻,矜虫斗鹤,递相述师,如图缯翦锦,饰画虽妍,割强先露,故实虽富,根荄愈衰,千葩万蕊不如一荣之真也。⑩
夫文者,所以发阐性灵、叙诏伦则、形写人纪、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声谐而节会,乃玄黄之英华,而神理之自然。譬彼霞辉星彩,匪绘而焕,龙章凤色,不绣而奇,岂出造为?精机妙吐而已。(11)
黄省曾把诗定义为“神解”、“天动”、“性玄”,是从诗歌本身的自然属性出发的;而文所具有的“发阐性灵、叙诏伦则、形写人纪、彰泄天化”之功能,也是从重视文学审美功能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的。在黄省曾看来,诗和文一样,都是用来表现个体主观之性情的,它们从自我心底的最深处发源,从而是最真实的;要求直抒胸臆,不假雕饰,自然而然地喷薄而出,因而又是最自然的。这实际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学本质之真实,因此强调创作时的情感基调就应是真实自然、发自本心的;二是表现方法应真实自然,即文中所云之霞辉星彩、龙章凤色,都不是因为刻意雕饰而彰显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容不得半分虚假伪饰。文学需要形式技巧,但是这种技巧性的修饰不能妨碍文学本质之真诚,否则便不如没有了。黄省曾在对比古今后发出感慨:“千葩万蕊不如一荣之真也!”实际就是要求文学应以表现主观真诚之性灵为目的和旨归,强调一种重视主体性灵的文学思想。
黄省曾自己的创作实践充分体现了他重视主观性灵的文学思想,如五律《春泛镜湖》:“佳丽摇新望,云空鸟不稀。树春花欲语,山暮日知归。小棹浮群象,澄波暎客衣。暝余还镜里,天月借清辉。”(12)这首诗写得清丽自然,不带一丝烟火气,可谓学谢而又超谢。诗人赋予自然景物以人之情感和意识,使他们时时处处都能与诗人进行交流和沟通,这种交流不再是单向的、被动的,而是双向互动的,物亦有人之情感,春天了,它们也有想说话的冲动,也会如人一样进行感知,有欣然、有喜悦,也会舍不得诗人离去。此诗体现了黄省曾对山水自然之爱,以及其闲适自如的心态。最重要的是,这首诗受阳明心学的影响颇深,诗中的景物都被赋予了人的意志和感情,它们不再是纯粹的客观物象,而是融入了诗人主观之心性,为其涂上了一抹心灵和情感的色彩。
又如,五律《南星草堂杂兴》:“花泻最澄溪,霞横不断陴。日含山气落,云抱水容移。游盖自兹远,归琴何太迟。修杨弥望夹,随步领风吹。”(13)首联和颔联共写了花、霞、日、云、山、水等景物,但又不是简单地将它们平直堆砌起来,而是赋予这些自然景物以人的意识和知觉,这又是心学重主观性灵之文学观念的体现。首联中“泻”、“横”二字动态地将落花与晚霞各自之特点展示了出来。落花飘洒在澄溪之上,晚霞横亘在山与山之间,日光随着时间的流逝,含着迷迷蒙蒙的山气,缓缓下落;天边的云彩怀抱着清清泠泠的水气,随风飘移。这一幕美景是诗人自己的主观体验,却完整的通过山水云日传达出了一种人之情态和感觉,人与自然冥合无间,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状态。颈联和尾联由景过渡到人,诗人处此胜景之间,只盼能携一具清琴,于山间微风漫步,静享天人合一之妙。这首诗不仅表现了黄省曾刻画山水之功,更重要的是他传达出的情感体验和和乐境界。
这样的例子在黄省曾的诗歌中还有很多。由此可见,黄省曾重视主观性灵的文学观是在阳明心学“良知”说影响下形成的。但黄省曾又对这种影响作了一些自己的生发和改造,因为阳明心学首先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出现的,它与文学之间毕竟还有着种种差距。尤其是阳明主观上不愿意过多的涉及文学创作,并以诗文小技的观念指导自己、影响别人。因此,“良知”说所能体现的诗学观念就是有限的,或者说是不自觉的。黄省曾则不然,他对阳明心学最大之体悟就在于将“良知”和“情识”联系起来,把良知所承载的生命境界、审美情趣、精神品格等用一种更为直观、更为具象的诗学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文学观渗透进黄省曾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对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观照,在山水自然中体验真实情感,又用自然之情指引着个体感受万物生生之亲和。
黄省曾较阳明更像一个风流儒雅的文人墨客,而始终不是一个可以翻云覆雨的政治家。省曾受心学之良知境界影响而形成的重主观性灵的文学思想是他毕生的追求和理想,他一直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前进。如果不能振耀王庭,那就去成就一家之言,在山水之乐中笑傲人生。这未必是心学的全部内容,但却是黄省曾人生的真谛。因此,他才更重视文学的审美本质、重视文学怡情悦性的功能,这些都是直接得益于心学所培育的良知境界。阳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创作出那么多富有画面感和艺术美的空灵诗作。然而,阳明的文学思想是不够完整和彻底的,从哲学的良知境界到文学的审美本质这显然需要一个糅合和发展的过程,缺乏明确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不可能完美地完成这一转换的。因此,黄省曾强调在文学创作中重视主观之性灵,便不只是一种学习和吸收,更是一种转化和完成。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⑩(11)(12)(13)黄省曾《五岳山人集》,明嘉靖刻本,卷四《座右铭》、卷三十《答蔡羽书》、卷十六《对竹轩下》、卷十八《月夜偕高令公次登惠山饮第二泉》、卷六《除夕》、卷十七《二泉》、卷十一《南星草堂杂兴》、卷十六《集陆郡伯园》、卷二十五《诗言龙凤集序》、卷二十六《李先生文集序》、卷十二《春泛镜湖》、卷十一《南星草堂杂兴》。
⑥左东岭《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诗学观念》,《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