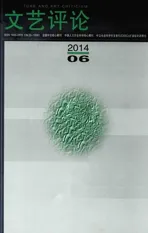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
2014-09-29郭艳华
郭艳华
北宋是诗歌新变、词体成熟、散文繁盛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新型文学格局的形成深受特定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在北宋167年的发展历程中,民族之间的纷争与融合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内容,而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则是北宋民族关系的一条主线。北宋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过宋夏战争的困扰,文人也因此深受这场持久战争的影响。在宋夏战争的影响和支配下,北宋文人有了更多的时代感受与历史经验,文学创作因之有了更加广阔的现实内容和丰富的时代内涵。不论是战事诗的勃发,豪放词的成熟,还是政论散文的繁盛,都与宋夏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北宋立国到靖康前的170年间,中国境内的民族关系格局大体呈宋、辽、夏三朝鼎立之势,这一局势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文学发展的走向,它对于实用主义文学观和北宋文学精神品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文学审美风格的形成及变化之间也有着深刻的联系。”①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无疑是支配北宋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导因素,当我们把审视历史的眼光定格在宋夏对峙百余年,就会发现北宋文人的创作热情与文学的现实指向,是随着宋夏战争的发生发展而彼此消长,而且北宋重要的文人几乎人人都写过反映宋夏战争的文学作品,从而深刻影响着文学格局的分布与审美风貌的形成,由此可见民族关系格局对北宋文学时代精神内涵的深远影响。
一、宋夏战争与北宋“战事诗”的勃发
现实性与议论化是北宋诗歌的总体特点,这一诗学风貌的形成与特殊的政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复杂的民族关系则占主导因素。在167年的历史进程中,北宋始终处在与辽、金、西夏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对峙的政治格局中。在此过程中,北宋与西夏的并立时间最为长久,且“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约占四分之三以上。”②宋夏战争持续的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斗争之惨烈,是以往战争中颇为少见的。仁宗朝是政治与文学变革的高峰阶段,也是宋夏战争最为严酷的时期。严重的边患危机激发了士大夫文人浓郁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上书谈论军事得失,寻求救弊之策,以致“天下言兵者不可胜计”,③从而掀起了一股救弊时政、富国强兵的爱国热潮,饱读经书的儒学之士由此正式走向北宋的政治舞台。面对宋夏战争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危机,北宋文人或娓娓叙说、或慷慨陈词、或滔滔雄辩、或精细剖析,将宋夏战争过程中的种种实况予以真实记录,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战事诗”。所谓的“战事诗”,是专指对特定作战双方战况的再现与持续描写,它具有双向性与延续性的特点,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边塞诗。自《诗经》开始,历代都有记录战争情况的诗歌,并形成了强大的边塞题材,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能够像宋夏战事诗那样,既全面系统,又真实动情地记录延续百余年的战争情况,因而较之前代的战争诗可谓有集大成之意义。
通过检阅《全宋诗》,可知和宋夏战事相关的诗歌近千首,内容涉及战争场面、百姓疾苦、文人忧患、边塞风光等各个方面,作品集中展现了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给北宋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具有以诗存史的现实价值。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历时22年。自景祐元年(1034)宋夏交战至庆历四年(1044)议和,两方战争更是频繁爆发,屡战屡败的惨败结果让北宋朝廷不堪重负。仁宗、英宗朝是北宋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时期,在与西夏之间的数次大规模战争中均以失败而告终。面对国家陷入空前的战争危机中,北宋文人开始将创作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冗官冗费、苟安积弱等困扰北宋社会的重大诗社会问题,都成为文人所关注的焦点。不论是范仲淹、韩琦、富弼这样主持过军国大政,且亲历边塞、曾领军与西夏战斗过的朝廷重臣,还是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文坛领袖,亦或是梅尧臣、苏舜钦这样的著名文士,无不对宋夏战事投向关注的目光,宋夏战争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成为当时文人儒士的中心议题,由此形成了政治与文学的交互渗透,宋夏“战事诗”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勃发,并成为北宋诗歌创作内容的重要部分。
宋夏战事诗的表现范围非常广泛,凡是和宋夏战事相关的内容都包罗其中。除了像以往边塞诗那样注重对军营生活和战地风光的描写以外,宋夏战事诗更加侧重于对战争过程中敌我双方的作战情况的再现,战争带给无辜百姓的灾难苦痛,以及对统治者无心作战、消极妥协态度的揭露与批判,这些内容都无不被诗人们广泛涉猎,随之诗歌也被大量的议论所占据,散文化的议论方式可谓无处不在。如梅尧臣《董著作尝为参谋归话西事》中以“大将罪专辙,举军皆感伤。归来出万死,羸马亦催藏”,揭示了英勇将帅无端获罪的不公待遇;其另一首《猛虎行》对朝中主和派不顾国家安危的丑恶嘴脸予以讽刺:“有虎始离穴,熊黑安敢当……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诗人借对猛虎嚣张跋扈、任意横行的描述,揭露和痛斥权奸“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的恶劣本质;石介在《寄赵庶明推官》中言道:“四十年来赞太平,君王耳畔管箫声。定襄地域俄连震,莱牧男儿忽议兵。明日边烽高百尺,同时御府出三旌”,指斥北宋朝廷大敌当前却依然歌舞升平、不思进取,最终延误战机的轻敌行为;欧阳修的《寄秦州田元均》一诗中以“由来边将用儒臣,坐以威名抚汉军。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藩无事着耕耘”等句,对北宋朝廷不思进取、坐以待毙的消极懈怠予以尖锐的指责。此外,如梅尧臣的《汝坟贫女》、《田家语》、《对雪》、《猛虎行》,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吴越大旱》、《庆州败》、《乙卯冬大寒有感》、《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宋祁的《感事寄子明中丞》,欧阳修的《食糟民》、《边户》,韩琦的《荣归堂》,王安石的《收盐》、《兼并》、《感事》、《河北民》,苏轼的《和子由苦寒见寄》、《和王晋卿》、《闻捷》、《闻洮西捷报》、《郭纶》、《吴中田妇叹》、《荔枝叹》、《和子由蚕市》等代表作品,或再现战争的残酷场面,或揭露军队赏罚不公,或揭示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都无不与宋夏战争这一引发社会危机的核心问题息息相关。
在宋夏战争牵引下,北宋文人以诗文干预政治、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目的更加明确,作品的辐射面也更为广远。上到治国方略、军事部署,下到民生哀怨、百姓疾苦,都切实地拓展了议政诗文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形成有宋一代诗学风貌的主流特色。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说:“最早的《诗经》,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等,无不以社会之良心自期。不过,在唐朝以前的诗里,这种意识是有限的,只有到了宋诗,尤其在大家的诗里,才显得普遍起来。宋代诗人而不作批判社会与政治之诗的,可说很少。”④的确如此,那些引领北宋政治与文学革新方向的文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都亲身经历了宋夏战争最为激烈严酷的时期,他们对战争所带来的种种破坏性的后果都有着深切的感受。不论是亲历战争现场,记录实战情况;还是根据耳闻,抒发对战争的感受,都体现出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密切关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论是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军事见解的发表,还是对战争场面的再现,以及导致战争失败造成社会灾难深层原因的探寻,都一一涵涉在文人笔下,客观描述与主观批判交替进行,诗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干预现实的工具。于是,唐诗那种以抒情见长的表达方式在宋诗中则被散文化的议论方式所替代。在以批判时政、歌咏民生为旨归的宋夏战事诗中,诗人们更是大发议论,纵横捭阖,将深沉忧愤、峥嵘跌宕的内心情感融注到理性的议论之中。可以说,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艺术特质同样也是宋夏战争背景下的艺术产物。
二、宋夏战争与北宋豪放词风的全面建构
词体在晚唐成熟,至北宋达到繁荣阶段,其间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婉约词一直居于主流风格。然而随着宋夏战争的频繁爆发,士大夫文人创作视野和人生体验都因之而发生了改变,并拓展了新的创作视域——边塞战争与军旅生活。于是关心国家安危、慨叹国耻国难的豪放之作开始不断涌现。其中,不论是浅斟低唱的沉吟,还是雄肆粗厉的高唱,都与历经百年的宋夏战争有着密切关系。北宋豪放词的作者多是经历宋夏战争,且关注现实政治、忧国忧民、积极有为的仁人志士,他们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注入词体,以原本应歌娱乐的小词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化,抒发振兴家国、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主义豪情,从而打破词体的娇娆柔媚之态,大大加强了词体的现实功能。对国家社稷安危的强烈关注使得北宋词人打破诗尊词卑的狭小观念,从而将创作目光投向风起云涌的广阔社会,与战争相关的边塞风光、登临伤别、怀古咏史、报国志向等内容开始涌现词坛,由此掀起了豪放词的创作高潮。不论是塞外边地的战争景象,词人对家国社稷的忧患情怀,还是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无从实现的内心悲怨,都开始大量涌现在词人笔下,词体这一风貌的转变与宋夏战争这一影响北宋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事件密不可分。
作为北宋豪放词的先驱,范仲淹一生正值宋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到他晚年时,宋夏矛盾愈趋激化。在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其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不仅走上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文记录了他们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所闻、所见、所感。范仲淹虽然存词只有五首,但却能够摆脱浮艳华靡的传统词风,将边塞将士戍边的情景,以及忧国思乡的深沉感情注入词中,为宋词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渔家傲》、《苏幕遮》两首作品就是他在西北军中的感怀之作,真切展现了边防将士们忧国怀乡的深情,以及词人对离乡久戍将士们的深切同情,可谓在剪红刻翠的软媚词风之外另辟一隅。尽管词体的艳科性质和娱乐功能一直潜在地支配着北宋词人的创作观念,然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⑤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创作规律,没有一种文体能够逾越时代精神的影响而独立存在。继范仲淹之后,引时事入词逐渐成为一个时期普遍的创作倾向,并在其他词人笔下也有广泛的表现。如刘潜《六洲歌头》中的“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驱龙虎,鞭寰宇,斩长鲸”,借项羽的慷慨气概表达自己对英雄的崇敬与向往,其中不乏力主抗击外族的期待;沈唐《望海潮》中的“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箫鼓沸天,弓刀似水,连营十万貔貅,金骑走长楸”,将“川容如画”的中原大地与“刀弓似水”的战争场面做对比,流露出对不义战争的严厉谴责,从而引发人们对于战争的思考。虽然北宋前中期直接描写边塞风云的词学作品并不很多,但“这种豪放词风所体现的阳刚之气和壮伟之美,无疑正是一个弱势民族在强族压迫下急需的精神素质。”⑥由于词体声情体制的限制,表现重大社会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北宋词的创作中数量有限,难与婉约词平分秋色,但这已经能够说明时代精神对文学体式的强大影响力,同时我们也能够深切感受到宋夏战争带给词人创作上的艺术敏感,这也潜在地推动着词体的内质演变。
北宋中后期是豪放词的确立和深化期,同时也是宋夏战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在经历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战役的惨败后,北宋词人逐渐从宋初承平的温柔乡中清醒过来,并开始通过变革寻求出路,王安石、苏轼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改革精神的文人,这种精神也必然会反映在词体创作中。王安石以词体来咏史怀古,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表达革除时弊、重振国威的迫切愿望,其《桂枝香》、《千秋岁引》就寓涵此意。程千帆先生把王安石和范仲淹并列,认为“范仲淹和王安石等只是偶尔填词,范词现存5首,王词现存27首,但他们的艺术风格不同于晏、欧等词家,不妨说是苏轼开创豪放派的先驱和同调。”⑦程先生之所以将范、王二人视为豪放词的先驱,正是因为他们以政治改革领袖的气魄冲破了词体纤柔狭小的牵绊,使其承载着更为广阔而实用的现实内容。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豪放词开始在改革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高潮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不论是为国立功的热望,对百姓深受战争之苦的同情,还是对战争的憎恶以及统一祖国的愿望等,都开始成为词人们所关注的现实内容。豪放词发展到苏轼那里,则呈现出自觉的创作状态。苏轼现存词340余首,豪放词虽只占其作品的五分之一,但却能够打破词体固有的抒情程式和创作定势,用“以诗为词”的创作理念拓展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吊古伤今、政治怀抱、指陈时政成为苏轼豪放词的标志性内容,而这都与宋夏战争密切相关。其《南乡子·赠行》、《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望江南·超然台作》等作品正是宋夏战争背景下的感怀之作。在《南乡子》一词中,苏轼虚构了一个万舰待发、“旌旗满江湖”的壮阔场面,“帕手腰刀”的“丈夫”正整装待发,开赴战场。与驰骋疆场的将士相比,词人只能自嘲是纸上谈兵的“迂儒”,悲怆之情流于笔端,并发出“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的无奈与悲痛之声。此外,《满江红》中的“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行香子》中的“君臣一梦,今古空名”;《望江南》中的“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等无不是激愤感伤之情的深情表露,映射出苟安局面下文人失落无望的内心悲凉。较之前期豪放词风的含蓄委婉来讲,苏轼笔下豪放词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得到进一步加强,深刻展现宋夏战争背景下的时代精神与文人风貌,从而为词体创作开辟了更加健康、开阔的创作道路。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是记录这个时代历史动变的晴雨表,宋词创作同样如此。作为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一部分,词体的创作主题与历史内涵都会受到其实政治格局的影响。由于政治与文学的亲缘关系,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必然影响词人的审美心理与主题取向,从而“使北宋词在风花雪月、羁旅行役之外,又增加了边塞、和战、朝政、民生、学问、事功等经世济民的广阔内容。小词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己小我之事,不再仅仅抒写个人情怀遭遇,它开始有了更深沉的思想性”。⑧从不寐流泪的“白发将军”到“射天狼”的爱国志士,从“少年任侠”的英雄豪杰到“宣威西夏”的战地将领,一群心系国家命运的仁人志士谱写出一曲曲或悲壮苍凉,或豪迈劲健的慷慨悲歌,给满溢着脂粉气的北宋词坛凭添了几分豪壮之气。不论是山河受创的家国之痛,壮志难酬的精神苦闷,还是激昂壮烈的民族精神,如彭腾不息的江河之水一样融贯于整个北宋词的发展过程之中,慷慨苍凉的词情也在时代矛盾的激流中也愈加浓烈,发人深省。北宋豪放词的延续与不断发展亦说明时代精神对文学体式的强大影响力,而宋夏战争无疑是其建构与成熟的重要历史动因。
三、宋夏战争与北宋政论散文的繁盛
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顶峰,这已经是古今学界所公允的定论。从吕祖谦所编的《宋文鉴》、庄仲方所辑的《南宋文范》,以及今人所编的《全宋文》等散文总集来看,宋代散文数量繁富,佳作纷呈,风格流派众多,可谓集前代之大成。宋代散文之所以有着如此之高的成就和地位,除了以上数量和风格上的成就以外,还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点,这依然与宋夏战事有着密切关系。宋夏战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积弊激发了北宋文人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政的热情,其创作心态与价值取向因之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言纳说为忠,”⑨将道德精神的建构与政治理想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文人一方面致力于探求政教根本,另一方面则担负起经国救世的社会责任,双方的合力造就了经学、史学、文学的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繁盛局面。在此背景下,北宋文人士大夫开始要求用文学来反映现实,他们将深沉的忧患思想与高昂的士人风貌融合在一起,以积极有为的创作心态展现济世安邦的政治抱负与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由此得到空前强化。由此,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事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策论、奏议的形式发表和宋夏战事相关的各种见解,从而将政论性文体的创作推向高峰。
作为政治的参与者、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者,以及文学的创作者,读书、治学、从政、议政成为北宋中期文人士大夫的主要生活内容,而如何挽救受到战争重创的国家危亡,成为当时文人儒士的中心议题。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感的激励下,一些重臣兼文士,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王安石等都直接或间接参与边事,他们积极进言献策,发表对战争的见解与救国方略。欧阳修对宋夏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做了这样的概括:“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困矣;所需者财用,今财用乏矣。”⑩范仲淹更是“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11);司马光不仅有《论北边事宜》、《远谋》等陈述自己对边事意见的政论奏疏,而且明确提出“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谓盗窃”(12)的立身标准,对士大夫们高扬自我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了要求;就连邵雍这位三十年居于洛阳“安乐窝”中潜心做学问的道学家,亦表露出“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边塞四首》其一)的御敌决心;理学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3)的豪言壮语同样是宋夏战争背景下的时代呐喊,鲜明体现着宋代士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品格,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一诗就以“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来概括北宋中期文人的精神风貌。在揽时事、发议论的过程中,促成了种种或力主革新、或因循保守的政治见解层出不穷,而宋夏战争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成为当时文人儒士的中心议题,由此形成了政治与文学的交互渗透。
据现代学者统计:“以单篇文章或专题形式记宋夏之事的汉文西夏文献多存在于宋人文集以及宋人编著的一些历史文献中,这些文集和历史文献许多流传至今,所以被文集和历史文献所编入的汉文西夏文献也得以保存了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夏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如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胡宿的《文恭集》、宋祁的《景文集》、包拯的《孝肃包公奏议》、尹洙的《河南先生集》、欧阳修的《欧阳修全集》、夏竦的《文庄集》、韩琦的《韩魏公文集》、苏轼的《苏轼文集》、苏辙的《栾城集》等文集中都存有多篇与西夏相关的文献,存在于宋人文集中的这些文献多为宋臣上奏的各种奏议。(14)这些奏议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宋夏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内容。在北宋对西夏作战期间,宋仁宗就向广大文臣们征询对夏良策,仅一年时间内就收到近万条建策。存在于其他历史文献中的专题西夏文献主要有诏令、奏议和历史专题。明代黄淮、杨士奇所撰编集的《历代名臣奏议》350卷,其中宋代奏议约占十分之七。奏议类文体作为大臣向皇帝进言的参政议政之辞,大多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思考与反映,政治色彩很强。诏令专题最为集中的是《宋大诏令集·政事门》中的《西夏》部分,共辑录了北宋降于夏的66条诏令,这些诏令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宋朝封建中央集权政府对宋夏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奏议专题最为集中的是在《宋朝诸臣奏议·边防门》中的《辽夏》部分,收录了宋臣80篇左右的西夏专题奏议,宋臣主要围绕宋夏关系这一主题来申明各自的立场、观点,这些宋臣包括田锡、张齐贤、杨亿、庞籍、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司马光、余靖、苏辙、范纯粹、范纯仁、张舜民等。历史专题主要有《东都事略》卷一二七、一二八《西夏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西夏扣关》,《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五《安边御寇·西夏》,《隆平集》卷二十《夏国赵保吉传》等。这些专题以叙西夏历史地理沿革为主,或详或略,内容多寡不一。综合研究这些单篇或专题文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宋朝统治集团和一般文人对宋夏关系的基本立场和看法。深陷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现实的难题摆在富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文人面前,他们必须直接面对并且思考这些现实存在的危机,并做出解答,而包含奏议、书说、诏令、传状等用来议政说理的散文无疑成为他们发表治国方略、针砭时弊的最强有力的阵地。
面对北宋王朝“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识战阵”(15)的社会现实,以诗歌反映宋夏战争所带来的政局弊端和民生困厄,成为诗人们普遍的创作倾向。也正因如此,宋夏战争所辐射到的所有社会问题,北宋中期诗人都能够通过议论、散文为诗的方式予以真实再现。面对国家所面临的内外危机,文人笔下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促使朝廷勤政修德,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并削减租赋,减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负担,从而通过有利改革,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其中王禹偁的《三谏书序》、《端拱篇》、《待漏院记》、《御戎十策》、《应诏言事疏》、《唐河店妪传》等名篇;柳开的《代王昭君谢汉帝疏》、《上言时政表》、《默书》、《与张员外书》、《贺枢密副使富谏议启》等作品都直接针对民族战争引发的相关问题而发表见解和议论。随着宋夏战争的不断激化,谈论兵事成为北宋文人笔下的重要内容,并广泛存在于奏议、策论、札子、碑志、传记等各种文体中。韩琦的《陈用兵练卒疏》、《请鄜庆渭三路添兵疏》;张方平的《平戎十策》;程颢的《论霸王札子》、《谏新法疏》;程颐的《上仁宗皇帝书》;欧阳修的《论乞谕陕西将官札子》〈庆历三年〉、《论元昊来人请不赐御筵札子》;尹洙的《谏时政疏》、《息戍》、《兵制》;李觏的《富国》、《安民》、《强兵》、《庆历民言》;司马光的《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札子》、《辞免裁减国用札子》、《论召陕西边臣札子》、《论北边事宜》、《论西夏札子》、《谏西征疏》、《西边剳子》、《乞不拒绝西人请地剳子》、《论召陕西边臣剳子》等奏札都是他对边患问题的认识和主张。此外,宋夏战事也促发了政论文的兴盛,如苏轼的《思治论》、《进策》等文,希望通过富国强兵、巩固边防来挽救社会的政治危机;苏辙的《夏论》、《周论》、《六国论》、《秦论》、《唐论》、《尧舜》、《汉高帝》、《汉文帝》、《唐高祖》等文章,都是他回顾历史、感发现实的力作。秦观在作科举士子之时就已经对宋夏作战情况予以关注,创作了包括《将帅》、《谋主》、《兵法》、《人才》、《边防》在内的五十篇策论文,主要内容针对北宋朝廷与西夏历次战争胜败得失而展开,对宋夏之间的关系形势作了客观深刻的分析,渗透着强烈的报国热情;陈师道的《兵法》、《奇正》、《将才》、《将心》等文,都是从儒家经邦济事观念出发,评论时政得失,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应对西夏的战略措施。可以说,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北宋文人始终把国家兴衰、民族忧患、民生疾苦作为关注的重心问题,从而展现他们的济世情怀与忧患精神。通过聚焦于宋夏战争的方方面面,北宋文人充分贯彻了要求文学反映现实,革除社会弊病的诗文革新主张,完全摒弃了宋初诗坛总体上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虚浮风气,从而为北宋文学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创作格局。
历史上不乏战争,历朝历代都曾有过边关动荡的时期,但像宋代士人这样以如此饱满的激情和深沉的理性来凝视和思考战争事件的,可谓是一道独特的景观。当我们把审视历史的眼光定格在宋夏对峙百余年,就会发现北宋文人的创作热情与文学的现实指向,是随着宋夏战争的发生发展而彼此消长,而且北宋重要的文人几乎人人都写过反映宋夏战争的文学作品,从而深刻影响着文学格局的分布与审美风貌的形成。当我们以宋夏战争作为主线将北宋文学的发展进程贯串起来,则真正窥见了北宋文人和他的时代是怎样的荣辱共存,这种民族忧患意识显示出了宋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时代文学的主要思想特征,这是决定宋代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发展线索,也是深入探求宋代文学精神底蕴的重要背景。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文学与政治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但绝对不是直线型、简单化的,而是以创作主体为核心中介,以文化思潮与审美风尚为依托,从而在一个立体化、复杂化的历史空间中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宋夏战争对北宋文学格局与审美风貌的影响就是最好的说明。
①赵维江《宋辽夏鼎立格局下的北宋文学进程》,《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②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绪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苏舜钦《论西事状苏》,《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④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联经出版社1977年版,第26页。
⑤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页。
⑥傅璇琮、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⑦程千帆《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⑧朱崇才《宋学与北宋词坛的新变及平衡》,《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⑨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⑩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11)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277页。
(12)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5页。
(13)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
(14)胡玉冰《汉文西夏文献述要》,《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5)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