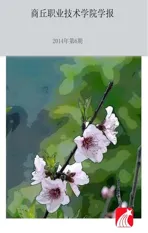魔幻化与民族性
——《百年孤独》与《红高粱家族》作品比较
2014-04-10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魔幻化与民族性
——《百年孤独》与《红高粱家族》作品比较
李文英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的成名作,也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一颗璀璨的明星;《红高粱家族》是莫言非常有名的作品,也是中国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代表作之一。前者魔幻色彩浓厚,后者在这一方面有所继承。与此同时,两部作品在生死观问题、主色调的选择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也都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性成分。
魔幻化;民族性;马尔克斯;莫言
新时期小说所获得的活力与开拓性发展,是在与域外文学不断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在众多刺激性因素中,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寻根”小说代表作家莫言的创作深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他既有对马尔克斯的接纳与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
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登上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盛坛。魔幻现实主义,顾名思义,是魔幻与现实的统一,是现实的生活内容与虚幻的艺术情境并置共存,但又无损于真实性。与其他艺术流派一样,魔幻现实主义也以现实为依据。其独特之处在于通过作家的想象把具体的现实上升为幻化的理想,创造出一种带有虚幻或魔幻色彩的新“现实”。
莫言,中国八十年代“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家。其小说风格的形成与马尔克斯有直接联系。莫言曾说,马尔克斯“用一个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的温暖的精神家园……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峰,充满同情地鸟瞰纷纷攘攘的人类世界。”莫言借鉴这种认识方式,在生活感悟、艺术表达上自觉地站在民族心理的高度去审视现实,遵循魔幻现实主义“变现实为魔幻而又不失其真”的原理,用一颗悲悯之心去寻找汉民族失落的精神家园,并以象征、暗示、隐喻等陌生化技巧,阐释和建构一个独特文学世界。
一、魔幻化
马尔克斯作品中魔幻色彩随处可见。在《百年孤独》中,神奇事件比比皆是,充满了小说每个角落,其中不乏对神话传说的模拟。马尔克斯以拉美大陆独特的现实和人们的审美习惯为基础,博采众长,广泛地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将人们所熟知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融入到拉美的现实生活中,使作品的形象让读者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激活读者的想象思维,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使之完全融入作品的艺术境界中。
马尔克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借助想象的意象,抓住事物的某些特点加以夸大强调,达到荒诞离奇、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在《百年孤独》中,庇拉·特内拉可以从扑克牌中得知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失眠症引发了健忘症,人们先是忘掉过去的事情,后来连物品的名称也忘了,甚至乱认爸爸妈妈;霍塞·阿卡迪奥被枪杀后,鲜血流过几条街给她母亲报信;佩特拉·科特的性欲可以使六畜兴旺,加快牲畜的繁殖,“让她骑马在牧场里溜一圈,就足以让所有打上她家烙印动物都无可挽救地陷于疯狂繁殖的灾难之中”;乌苏拉死的那天,镇上的鸟儿都像得了瘟疫一样一群群死去;奥雷良诺在娘肚子里就会哭,睁着眼睛出世;姑母与侄子乱伦,生下的长猪尾巴的男婴被一群蚂蚁活活吃掉;马贡多被一阵风刮走……作者通过荒诞夸张的描写将这一系列光怪陆离的景象同马贡多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并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一种遇到任何情况,哪怕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将这些看作不可思议的事件混入马贡多最平常不过的现实,他将拉美大陆的魔幻现实揉以现代派技巧去铺陈描述,让人们浮游于荒诞的境遇之中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真实可信。
事实上,这一切看似非现实的东西恰恰正是拉丁美洲的现实,小说作者只是借助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拉美人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信仰融入其中。他以真实的事件与现象为基础,借助想象与幻想,抓住事物的特点加以夸大或渲染,造成一种离奇感,从而加强魔幻效果。正如卡彭铁尔所说:“魔幻现实主义忠实地表现了拉丁美洲的神奇现实,这一神奇现实既非光怪陆离的自然现象,更非作者凭空想象,而是迷离恍惚的意识形态,是信仰,是拉丁美洲人的信仰对客观现实的突变、启明或夸张。”[1]389总而言之,马尔克斯运用现代派的文学创作形式,反映了拉丁美洲具有魔幻色彩的现实。
莫言作品的魔幻色彩没有马尔克斯的浓厚,或者说比较隐晦,但仍然多处可见。《红高粱家族》中第三章“狗道”部分给狗赋予了人的性格。“我”家的三条狗(红狗、黑狗、绿狗)充当了领导,在狗的内部展开了一场类似于人类的血腥斗争。负者黑狗眼睛里流露出祈求的光芒,一头扎进河里自杀了,赢者红狗发出庆典般的嗥叫。第五章“奇死”部分,奶奶为了能押中“押花会”的“会名”,带着父亲去死小孩夼里称死小孩的经历,“是我奶奶的富于‘魔幻色彩’的天才脑袋的骇人听闻的创造。”二奶奶死了之后还能大叫大骂,发出像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的声音,直到邀请李山人使用法术驱邪才让二奶奶咽了最后一口气。“她(二奶奶)以她诡奇超拔的死亡过程,唤起了我们高密东北乡人心灵深处某种昏睡着的神秘感情。这种神秘感情……成为一种把握未知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细读作品可见,作者通过对反常人物和事件的怪诞描写,以滑稽、夸张为主要特征,从而揭示出魔幻色彩独特的表达效果。
莫言承认,他的小说魔幻色彩很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古代的鬼怪故事。莫言说:“鬼怪故事往上一接,就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联系起来了。”[2]58莫言的小说创作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在与王尧的对话录中,莫言谈到,“我也尝试写过类似于《聊斋志异》的短篇,如果要用《聊斋志异》的方式写长篇巨著肯定是不行的,但在我的长篇里也涉及神鬼这样的情节。”[2]58
通过对两部作品魔幻色彩的文本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怪诞在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用怪诞的描述手法来揭露人性中那些可怕和可恶的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实主义中容纳了现代派表现技巧,营造了小说创作的新格局,是莫言《红高粱家族》艺术上的一个成功之处。整个红高粱家族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森林般的红高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而《红高粱家族》中每一个人物与画面都充满了深刻的寓意。这一“神话模式”的运用,借鉴马尔克斯的魔幻技巧,也凝聚了创作者的“新鲜血液”。
二、民族性
《百年孤独》与《红高粱家族》两部作品以各自的民族特质为基点,打上了深厚的民族性烙印。关于民族性的叙写,将以下面三点为例进行论述。
(一)生死观
在拉丁美洲民族的生死观中,生与死没有绝对的界限,死亡是另一种“生命”,可以在残废中延伸。亡灵也有感情,也有听、说、忆、思的能力。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死人也会衰老,也可以与活着的人进行交谈……墨尔基阿德斯几次重生,死后还常常回到实验室指导奥雷良诺破解羊皮书,普罗登肖死后多年又老得“白发苍苍,动作颤巍巍”,还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一直谈到天亮等等。在马贡多,活人与亡魂的交往非常自然,就仿佛他们依旧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并且共同经历着生老病死。在作者笔下,往往人鬼不分,生死无别,人可以死而复生,鬼可以从阴返阳,扑朔迷离,古怪稀奇,这种描写充满魔幻色彩的同时,也体现了印第安生死观。这种古老的印第安生死观,无疑还带着原始的荒蛮和愚昧。这一文化传统揭示了一个事实,即马贡多闭塞、落后、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体现着另外一种生死观,即它渗透着一种向死悦生的“红高粱精神”。戴凤莲临终前发出一段炽情的“天问”,在和死亡之神牵手前的昏迷中,戴凤莲并没有突然等待生命分分秒秒地耗尽,却在弥留之际回顾了自己激情四溢的生命旅程。天赐的情人与她在那片荒成血海的高粱地里尽情欢爱。那是生命内在性的呼唤,任情任性。在肉体饱受痛苦的垂死之际,戴凤莲的灵魂依然如一颗疯生疯长的红高粱自由自在无所拘束,为生命最后的瞬间涂满传奇异彩。那洋溢着生命本质和原欲色彩的狂放与迷醉情态已将蜷伏在所谓传统规范下的封建道德伦理踏实地踩在脚下。正如尼采所言,“不论在哪里,只要听到了狄奥尼索斯(酒神)的声音,阿波罗(日神)的规范便归于乌有了。”[3]125戴凤莲摒弃弱质的生命情态,以生命原欲的冲动、扩张和迷狂挤退了伦理道德和政治意识,尽情演绎诠释了尼采界说的“酒神精神”:“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的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包含着毁灭的喜悦。”[3]128无疑,莫言的小说世界是一个酒神精神的境界,是感性的解放,是一种狂欢化的艺术思维。
(二)主色调的选择
如同我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视黑色为不吉利的象征一样,印第安民族传统把黄色为凶兆。在《百年孤独》中,黄色被用来作为腐败、没落、死亡以及一切祸害的象征,墨尔基阿德斯被淹死前“假牙上已长满了黄色的水生小植物”;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死时,天下起了黄花雨,“镇上下了整整一夜,小黄花盖满了屋顶,堵住了门口,闷死睡在露天的动物……”;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梅梅的男友,他的身边总是飞满了黄蝴蝶,梅梅在看到他之前总能先看到很多黄色的蝴蝶,结果马乌里肖·巴比洛尼亚被子弹打穿了脊梁骨,后半辈子一直蜷缩在床上,孤独地度过了一生;黄色的香蕉也是马贡多衰亡的象征,美国人在马贡多成立了香蕉公司,马贡多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殖民地,还有香蕉公司黄色的火车头、黄玫瑰等等,这些“黄色”均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增加了作品的魔幻色彩。黄色几乎无处不在,它一直贯穿小说始终,频繁地暗示着马贡多这百年历史的不幸和布恩地亚家族命定的悲剧。
相比于马尔克斯作品中的黄色,莫言则更喜欢写红色。红是中国的一个吉祥的象征,红色是所有颜色的原色调。莫言笔下的色彩其底色是红色,如写奶奶穿的衣服是红色的,高粱是红色的,性格也可以是红色的,“我爷爷辈的好汉们,都是高密东北乡般鲜红的性格,非我们这些孱弱后辈能比”……就连写死神,也说它有着“高粱般金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这些色彩,与其说是意象派的,不如说是民间的。这些色彩诉诸于人的感觉、视觉,具有强烈刺激性。以血一样的红高粱为背景,在其中演绎的是英雄传奇、爱情传奇,因此,红色的深层隐喻是性、情爱、激情和生命力。莫言对红高粱进行过无数次的描写和赞美。血染的红高粱,散逸着苦涩微甘气味的红高粱,辉煌、凄绝、忧郁、庄严的红高粱,是强烈生命意识的主体象征。有学者称“红高粱”为《红高粱家族》的“生命图腾”,它自始至终陪伴着小说里的每个人物,它的气息熏染着每个人的灵魂。不难发现,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与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一种生命力的传达。
莫言小说中还写到血的鲜红。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写到许多充满鲜血的斗争场面,这种充满民族集体主义精神的鲜红热血,被莫言书写得淋漓尽致。血腥的斗争暗含着潜在的民族意识。在罗汉大爷被活剥之后仍不停止的詈骂声中,得到空前的惨厉和强烈的表现。我们不赞成缺乏深意的血淋淋的描写,但在这里,这惊天动地的惨剧,这残暴与罪孽,这壮烈的仇恨与反抗,又何须掩饰呢?雷达说得好,“掩饰它,便是忘记我们民族历史上‘满是血痕’却又璀璨光辉的一章,无血痕即无灿烂,越惨厉便越强韧,越真便越美,打破和谐的噪音里正有民族魂的悸动和腾跃。”此外,《红高粱家族》中写到,在“我”家的三条狗的斗争中,最终红狗战胜了黑狗,这胜者与败者的颜色选择,“红”战胜“黑”的意义,潜意识也揭示出作者对红色的偏爱。
马尔克斯和莫言两位作家,对不同颜色的选择,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所持的人生观的差异。马尔克斯选择的是消极色调,无疑增加了小说的悲剧气氛。最后,马贡多小镇也灰飞烟灭,被一阵风刮走,从此无影无踪。这不得不让人在黄色的笼罩之下反省,在百年孤独后,是一无所有还是换来了拉美人民精神上的反思?莫言选择的是积极色调。红色的描写,其实渗透了作者的主观色彩,寄托了作家的理想,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这其中也隐含了莫言对生命意识的张扬和无限感叹,它缘于对狂野雄强的生命力的推崇和赞美。
(三)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民族性的体现,还体现在其所表现出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中国学者在介绍《百年孤独》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声明其思想内容的政治倾向和进步色彩。比如陈光孚在《“魔幻现实主义”评介》一文称《百年孤独》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具有“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积极意义”[4]138。通过勾勒在马贡多成立香蕉公司的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以及马贡多的兴衰史和对每一个人物精神的极度空虚和寂寞的描写,向人们剖析了拉丁美洲贫困落后的原因。邓小平说“落后就要挨打。”人们从落后和外国列强的掠夺中觉醒,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走向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小说具有抨击时政流弊,鞭挞社会不平,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意义,体现了很强的渴求民族独立之愿望。
《红高粱家族》以抗日战争为社会背景,来表达大无畏的民族精神。与以往的红色经典不同,莫言所歌颂的对象——爷爷余占鳌,却是高密东北乡有名的土匪。关于这一角色身份的选择,曾有学者评价说,“莫言想从余占鳌这个勇猛剽悍的土匪身上发掘一种失传已久的强力精神,寻找中华民族深处的蕴藏着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然而,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一个没有任何理念和信仰的土匪来承担,连莫言自己恐怕也没有信心。”[5]71也许,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小说人物余占鳌说过一句话:“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此话便可以用来驳斥上述论断。
诚然,如果用阶级观点、主流意识形态那套法则来分析土匪,分析余占鳌,就会陷入到困境里去。但莫言小说创作的意义,正在于他依据人类学的博大和原始的精神对传统伦理学的冲破,反对艺术拘泥于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价值与判断。这体现出在莫言的思想中艺术的观念不应该被意识形态化了的道德所压制。这一点与马尔克斯创作中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他们力求摆脱传统的道德思维定势,故意推翻传统的陈旧与腐败,在人物塑造中冲破非善即恶、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颖的能吸引读者的创作理念。就是这帮可能被一些人称为“土匪”的人,却能在那片刺目、妖冶的高粱地里用鲜血和白骨开辟战场,写下了高密东北乡惊天动地的一页。《红高粱家族》中的“土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变成了真正的“英雄”。
《红高粱家族》中浓厚的民族性,还可从“我”奶奶等人身上也得到很大的体现。“我”奶奶则是一个反封建主义的典型形象。她以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美,来反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作品中,莫言写到:“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做,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我”奶奶甚至说:“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凡此种种,均可以看出,作者实际上是在与中国传统封建道德叫板。有学者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化的审美特征,是个拥有“个性解放”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民间传统文化与封建社会主流意识抗衡的野性思维的展现,这种反礼教的人道之举充满了刚正不阿的民族气概。莫言在此巧妙地把我国传统俗文化的精髓运用于他的小说创作中。
三、结语
在博大而浩瀚的拉美混血文化为底蕴的基石上,马尔克斯用《百年孤独》再现了拉丁美洲战后百年的现实,从中思考民族的命运。他以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将拉美人的意识、信仰融入到活生生的现实当中,并以精湛的艺术技巧使之同现实发生联系,一方面作为映照现实的镜子,另一方面作为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阶梯。这正是《百年孤独》独特艺术魅力的根源所在。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体现出的拯救意识使怪诞描写发挥了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意义。怪诞手法的使用,就其本质而言,用鲜活的民间资源拯救日趋萎缩的民族生命力。莫言以《红高粱家族》,展示了二十世纪上半期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以及祖先生机勃勃的生命激情,寄寓了反击和拯救中国人思想退化的理想。他不是机械地模仿或沿袭了《百年孤独》的创作路子,而是立足于民族的根基,以冷峻的现实主义为基调,以丰富的民族文化为背景,从而催生出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
[1] 阿莱霍·卡彭铁尔.这个世界的王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 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尼 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87.
[4]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评介[J].文艺研究,1980(5).
[5] 王永兵.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死亡叙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6(4).
[责任编辑袁培尧]
2014-09-17
李文英(1985- ),女,广东清远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I207.42
:A
:1671-8127(2014)06-005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