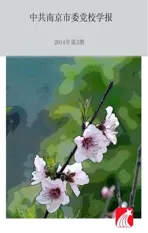证人宣誓制度研究*
2014-02-02凌高锦
凌高锦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重庆 410122)
2013年11月,甘肃酒泉市瓜州县法院推行实施了“证人保证书”制度。开庭前,法官依法告知出庭证人相关权利义务后,证人要在法院制作的“证人保证书”上签名备案,而且保证书以“誓言”的形式,由证人向法庭作出“保证向法庭如实陈述、提供有关情况,如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愿负法律责任”的保证。自2013年以来,该法院在适用证人宣誓制度进行审理的500多起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有130件,其中有141名证人出庭作证,且未发生因证人作伪证导致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至目前案件上诉率比上年度下降3个百分点。而将这一制度引入司法审判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早在2002年5月24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审理一起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中,首次启用证人宣誓制度。证人宣誓的主要内容为“就所知悉的案件事实如实向法庭陈述、如实回答各方当事人及法庭的提问,决不作伪证,如故意隐瞒、歪曲事实,甘愿接受法律制裁。”
此外,2001年11月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在最高法院鼓励各地法院改革创新的背景下,认真组织有关人士反复论证,试行了《证人宣誓规则》,①并以我国三大程序法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依据,在一起民事纠纷案件的庭审中首次施行证人宣誓制度。
当证人宣读誓词,向法庭保证如实作证并对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这一幕幕庄严的场面出现在法庭上时,很多人也许会对这种形式感到新奇,也许会去探究这一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及程序规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有诉讼法制度的“空白”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②并没有使得更多的学者停下脚步对此予以深入的关注。上述实践中存在的例证都只是各地法院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的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其本身也是证人宣誓制度在中国诉讼实践中的现实“表达”,并未形成制度化规定,有待我们的进一步探究。
从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者大多把视角都集中在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制以及证人证言、证人权利义务等方面,很少关注到庭审程序中,如何解决证人如实作证,即如何构建证人宣誓制度的问题。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并不具备建立证人宣誓制度的基础,进而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③就证人宣誓制度的理解与适用,这些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理论研究上的误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一、证人宣誓制度之基本范畴
(一)证人宣誓制度之历史沿革
证人宣誓制度(Oath)是指证人在作证之前,向法庭郑重声明其如实提供证词,通过一定的仪式,或虽无仪式但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其责任感的方式进行的,来加重证人担保其如实作证的心理负担的古老的证据制度。不可否认的是,宣誓仪式自其产生到被引入诉讼程序中作为一项制度以来,其制度内涵、功能等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历史时期:
1.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证人宣誓制度就已被作为审判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了规定。[2]当时,其得以构建的基础在于“在信神最深之社会,一般人民,信神之全知全能而敬畏之,欺神者必受责罚,故古代多以宣誓为判断诉之曲直,罪之有无为最确实之方法”。[3]但这种仪式的表达,“并不是出于道德的原因,而仅仅出于盲目的迷信。”[4]
与这种完全依托于人们对神的敬畏和宗教信仰的宣誓制度相适应,当时的证人宣誓必须由三个要素构成:首先,它必须是一种讲真话的庄严的许诺或宣告;其次,这种许诺必须是向那些能够对许诺有保证的神做出的;最后,宣誓者必须信仰超自然力的存在,相信作了伪证后会受到神的惩罚。可见,这一阶段,宣誓作为一种仪式本身“得以存在的原初根据,就在于它能够赋予人们宗教品质。”[5]并且将这种仪式视为发现案件“真实”的一种有效的手段。正是在这样观念以及宗教的信仰的背景下,使得宣誓制度的产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此外,在当时宗教与法律一体,甚至宗教在整个制度体系中对法律起到绝对的支配作用的条件下,宣誓是被作为一种司法化的仪式出现在法庭上的。它本身就有一套必须严格执行的,既定的程序和方法,并且其中的规定操作起来十分繁琐,严格的规则使得任何与程序、方法不符的行为都被视为无效,甚至遭受到惩罚。同时,宣誓本身所具有的魅力还在于被直接作为一种证据用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为真。④
2.在封建制时期,尽管宗教信仰依然成为统治者维护其专制统治政权的工具,而且在整个社会制度体系构建中,仍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水平的发展,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潮的兴起,使得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传统上一直将宗教信仰视为证人宣誓制度之根基所在的认识也面临着挑战,受到了批判。在一些宗教信仰较为普及的西方国家,立法在规定原则上应以宗教信仰起誓的基础上,又专门设置了郑重承诺制度以替代以宗教信仰起誓。⑤而且,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并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宗教,许多国家在证人宣誓类型的规定上,也逐渐呈现出一种统一化的趋势。⑥
3.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由过去的蒙昧、无知走向了理性和科学,宗教不再是世俗社会的主宰者,而逐渐转变为世俗民众的精神归宿。客观上使得证人宣誓制度所赖以构建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无法再完全依托宗教信仰为其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无法固守其在传统司法制度中所占据的领地,并不得不面对现实作出一些制度上的调整。
证人宣誓制度经过教会法的改造之后发生了质的转变,现代意义上的证人宣誓制度开始形成。在现代诉讼程序中,无论当事人提出证据的形式如何,都必须严格按照程序,在经过宣誓之后提出。而且,在具体的法庭审判中,证人宣誓的作用不再是发现案件真实的主要手段,而成为保证证言真实性的程序设置。
那种绝对的以证人宣誓的方式所得到的证言并不能保证案件事实得以真实再现,而更多的时候需要借助于其他证明制度来查清案件事实,使得证人宣誓制度日益式微,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同时,与传统制度中所蕴含的“虚无的”“神罚”观念相比,现代各国的证人宣誓制度并不再强调宣誓需要以宗教信仰为前提,也不因为不进行宣誓而否定证人作证的资格,主要是通过“实定法”所规定的民事制裁或刑事罪名等措施来强制证人的内心世界,以敦促其如实作证。
(二)关于宗教信仰作为证人宣誓制度基础的反思
证人宣誓制度是根植于宗教信仰以及基于此的宗教文明的沃土之上的,所以才产生了“盖宣誓,源于宗教信仰,基于人类对神忠诚之精神而产生”这样的认识。[6]而关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诚然,宗教信仰在早期历史上是一直作为宣誓制度存在的文化基础,并且影响着,甚至是决定着证人宣誓之后所做证言本身的真实性问题。笔者认为,证人宣誓制度的实质是,通过一种庄严、神圣的仪式所产生“外力”,来作用于证人的内心并使其产生发自内心的畏惧感,从而将其所知道的案件事实如实陈述给法官。这也正是早期社会中,宗教信仰成为宣誓制度存在的基础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原因。但是从这一历史视角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已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遭受到了彻底的“涤荡”。现代社会,随着宗教信仰的类型以及群体也趋于多样化,或许仍将宗教一种文化因素作为讨论证人宣誓制度基础的认识,已经是一种理论上的误区了。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适应现实生活多元,信仰内涵不断丰富、多元的现实,我们应该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信仰的涵义。一个民族,只要有信仰,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主义信仰,抑或是文化信仰,都能凝聚民族精神,产生强大的道德力。“宗教信仰并不是道德力量产生的唯一来源,一个社会的道德也并不一定要以宗教作为唯一的基础,尤其是不一定要以某一种宗教作为唯一的基础”。[7]在认识宣誓制度之基础一问题上,我们也不可以将宗教信仰局限于宣誓制度构建的唯一条件。
目前,中国人并不是说没有自己的信仰,而是在思想观念多元的前提下,每一个体的认识和观念都有很大的差异。在理论上,我们的信仰观念可以被划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制度化的信仰。这样的信仰类型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政治信仰,团体信仰等等;二是普化的信仰。⑦而我们所需要强调的是,信仰的多元化本身就为证人宣誓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提供了可能性。不可否认,也正是这样的认识才能够让我们从更为广泛的领域,以更为开放的视角来解读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并且为证人宣誓制度得以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奠定现实的基础。
二、构建证人宣誓制度之必要性
证人宣誓制度作为一项古老的预防法则,其顺应历史变迁,虽在制度内涵和形式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但是仍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立法所采纳,其本身的价值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实践中许多人却以该制度不符合中国现实以及文化传统上的冲突为由,认为我国不具有建立该制度的土壤,进而否定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甚至其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理性价值所在。笔者认为,此类观点值得商榷。证人作证前进行宣誓,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我们应该在具体分析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以及深厚的文化信仰基础,并结合我国司法制度改革之现状,从而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客观的评价。
(一)制度功能分析
1.证人宣誓具有仪式功能。
证人宣誓作为证人作证前履行的最后一道程序,以其形式上的严肃性和程序上的规范性,对证人作证前和作证过程中的心理起到一定的约束和警醒的作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证人如实作证的。从而使得宣誓在“可以成为情感的渠道并表达情感,引导和强化行为模式,支持或推翻现状,导致变化,或恢复和谐与平衡”[8]方面发挥作用。
2.证人宣誓具有证明功能。
纵观宣誓制度历史,其作为法官审理裁判的前置程序,在于通过宣誓来查明当事人之间系争请求之原因事实存在与否或者被告有罪与否。因为人们囿于“积善余庆,积恶余殃”⑧这一朴素的善恶报应观,“相信他所信仰的超凡之物在其有生之年或死后将会惩罚虚假宣誓行为”,[9]相信有最后的审判(冥罚),即作伪誓会遭受到冥罚。[10]因此不敢随意说谎话作证,才使得宣誓制度起到了其本应具有的证明作用。
此外,宣誓制度本身的功能还在于对声明人所作的证言本身产生积极影响,即当法官采信了证人证言时,之前所进行的庄严的宣誓仪式会极大地增加证言本身的价值所在。
3.证人宣誓具有威慑功能。
“宣誓的目的,并非请上帝注意证人,而是让证人注意上帝;并非上帝惩罚作伪证的人,而是让证人深信上帝完全可以做到”。[11]传统认为,宣誓制度本质上是以证人相信其宣誓后,如果说谎的话就会遭受到神的惩罚这一信念为基础的,并且,如果证人进行了宣誓,其才能够得到法官的信任并且其证言才可以被采纳。[12]而现代证人宣誓的威慑功能主要通过法律规定的伪证罪来实现。许多国家都规定,在证人宣誓之前或宣誓后询问前,法官或其他主持宣誓仪式的人应告知证人其作伪证可能招致的惩罚。通过这种外在的惩罚对证人的内心世界产生强制,使其因惧怕伪证的处罚而如实作证。如《加拿大刑法》规定:“在司法程序中作证,明知其证据不实,而故意导致审判错误,提供不实证据的,为伪证罪。”[13]
4.证人宣誓制度在现代诉讼中作为保证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一种制度,其独特的对证人的内心规范作用仍不可忽视的。
通过宣誓仪式的进行,将证人诉讼外的社会角色转换为诉讼内的法律角色,并内在地强化了证人对这一角色转换的认知,大大减轻证人的心理在无意识层面对外在要求的对抗,更有利于其对证人角色的理解、认同和内化。[14]
(二)经济价值分析
现代证人宣誓是一项简便易行的制度,相对于交叉询问、补强证据规则等其他保障制度而言,其所耗费的司法资源极小,只需在每个证人作证之前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和较低的司法成本即可完成。面对我国诉讼实践中证人翻证、伪证多发,司法资源极度匮乏的现实,通过证人宣誓制度可以在最小的司法成本投入和提醒证人如实作证,以获取真实证言之间获取更大的司法效益。
事实上,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如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是可以建立起以相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证人宣誓制度,而在其他地区则可以确立起不依赖于宗教信仰的证人宣誓,这也符合证人宣誓制度发展的一般趋势。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在我国建立证人宣誓制度,而是如何构建一个适合我国的证人宣誓制度。
三、构建我国的证人宣誓制度
随着历史的变迁,宣誓制度在适应现实需要变化的同时,其自身也有了深刻的发展和变化,逐渐由内在的心灵强制变化为外在的制度规制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其自身制度的独立性,进而脱离于宗教的绝对支配从而独立地发展成为了一项制度。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都未有宣誓制度的规定。⑨虽然刑事诉讼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了法官在审理案件之前告知证人如实作证以及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的告知制度和证人签署保证书的制度,但是其与宣誓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仅仅提醒证人知晓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却不具有唤醒其良知、理性和道义,加深证人责任感的“强制力”,⑩无法取代宣誓制度本身独具特色的魅力。而且,这种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的制度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证人宣誓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应用于诉讼当中,由证人于作证前进行宣誓,强化和明确了证人作证的法律责任,最大程度上发挥提高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体现诉讼的正义和法律的尊严的功用不言而喻;同时也为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填补法律制度空白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在修订诉讼法律时,应该对证人宣誓制度予以规定。
(一)宣誓的主体构建
首先对于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宣誓能力。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应当排除在宣誓主体之外。如日本民诉法第201条亦规定:“证人,除另有规定外,应当使其宣誓。未满16周岁的人或者不能理解宣誓意义的人作为证人询问时,不得使其宣誓。对于询问不行使本法第196条所规定的拒绝证言权利的证人时,不得使其宣誓。证人对自己或与自己有本法第196条规定的关系人显著利害关系的事项受到询问时,可以拒绝宣誓。
其次对于精神有障碍或者缺陷的人是否具有宣誓的能力,笔者认为证人若患有精神障碍或者存在智力缺陷,即其意思能力本身或有欠缺,故不得令其宣誓。⑪
再次鉴定人和勘验人都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他们就案件中所涉及的专门问题或者是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判断和勘验、检查以及出具鉴定意见,属于广义上的证人证言,也应当成为宣誓的主体。
最后是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被告人亲属不能成为宣誓的主体。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将证人出庭作证和如实作证规定为证人的一项公法上的义务,并未区分规定作证主体的例外,⑫也没有规定免誓的相关规则。但是实践中又面临着这样的窘境:证人往往拒绝出庭作证,或者虽出庭作证但是作伪证,而法律对此并没有有效的制裁措施或配套制度来予以规制。笔者认为,为保证作证要求的合理性,同时保护家庭亲属关系的稳定与和谐,立法在今后的修订中应当规定赋予特殊主体以免誓的权利,避免将无辜的利益群体推向要么违背良心作证,要么拒证的困境,所以这类人也不能成为宣誓的主体。
诚然,更为棘手的问题还在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能否作为宣誓的主体。《德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了关于被害人及其家属是否免誓的问题,由法官斟酌决定。而我国,理论上对此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肯定说”认为我国的证人宣誓制度适用于广义上的证人,特别是被害人作证前也应当宣誓。而“否定说”认为基于被害人的特殊身份,其在刑事诉讼中不需要进行宣誓。[15]
笔者赞成“否定说”的观点。首先,被害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属于当事人的范畴,因此持有将被害人归为广义的证人范围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次,基于被害人的特殊地位,其因先前受到被告人犯罪行为的伤害,故而在案件事实的陈述过程中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实难想象。但是这些不实陈述本身并不一味等同于虚假陈述,往往是可以在法律规定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而且纵有有虚假陈述之故意,亦有罚款或司法拘留等措施予以规制。因此,将被害人作为宣誓主体的考虑,实属无益。对于被害人作证的问题,笔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审判长训示制度,⑬通过在作证前,由审判长告知被害人真实陈述的义务和故意作虚假陈述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实无规定被害人作为宣誓主体之必要。
(二)宣誓的程序构建
在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宣誓程序的合理设置是发挥宣誓制度功效的前提条件。
首先,在案件正式进入开庭审理阶段之前,法官应该依法告知证人宣誓的义务,并提醒证人应当如实陈述事实,以及作伪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且仪式的进行由审判长来组织和掌握。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就明确规定了证人的具结义务,证人应确切保证其陈述均属真实,具结即系为保证。[16]同时,规定了审判长命证人具结时,应郑重其仪式,应告知具结之义务及伪证之处罚。⑭
其次,从仪式“过渡”功能的角度来看,证人宣誓仪式能够缓解证人角色转换的不适应性,实现日常状态下的人到诉讼状态下的证人的平稳过渡。因此证人宣誓开始的时间可以采取大多数国家的法例,在证人合法地进入法庭后和法官或者相关人员询问证人之前进行。这种过渡功能使得证人从喧嚣的世俗社会进入到法庭的庄严界域当中,内化地增强了其在诉讼程序中角色的认同,减少了证人对外来压力的无意识抵抗,[17]帮助其平衡这种心理障碍,完成角色的转换。
再次,是参照国外的立法例对于宣誓的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就有关的案件事实和争议的问题有权陈述自己的主张和依据,并相互进行辩驳、论证。新民事诉讼法第68条也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宣誓本身只是最大限度实现对证人如实陈述的可能性,却无法保证其真实地、客观地作出陈述。即使是经过宣誓仪式后有证人所作出的证言本身,也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充分的质证、辩论,在此条件下方可成为法官裁判的依据和基础。
最后,法律还应当对宣誓主体资格的排除以及证人拒绝宣誓时的处罚措施进行明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首先明确了“证人,除另有规定外,应当使其宣誓”。其次,宣誓主体资格的排除以及证人拒绝宣誓时的处罚措施在本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证人拒绝宣誓,那么法官可以要求其释明;⑮甚至在其拒绝宣誓理由不成立的情况下,可以依法对其处以罚款、罚金或者拘留。⑯
(三)宣誓书的内容的构建
首先,关于宣誓书的内容,笔者认为,我国宣誓书可以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证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职业、有无宗教信仰、与被证明人的关系等等。至于宣誓词,我国幅员广阔,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差异较大,所以我们在适用宣誓制度的时候,应该尊重证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以及对宣誓誓词的认同感。因此,宣誓誓词内容应当体现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
其次,誓词内容的规定要规范完备。实践中,各地法院在证人宣誓词内容方面所做的规定和样式基本上还是趋同的,只是在个别用词上有所不同。例如,誓词中出现的“所知悉的案件事实如实向法庭陈述、如实回答各方当事人及法庭的提问,决不作伪证,如故意隐瞒、歪曲事实,甘愿接受法律制裁”;还有“我向法庭宣誓:以我的人格及良知担保,我将忠实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保证如实陈述,毫无隐瞒。如违背此誓言,则愿受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神灵的惩罚、法律的制裁以及心灵道德的谴责等内容”;再有“我愿意出庭履行法律规定的公民作证义务,我所提供的证据是真实的,如有伪造,愿意依法承担罚款、拘留或刑事责任。”等例证。
可以看出,各地法院在证人宣誓誓词方面的规定还是比较明确和具体的,不仅指明了证人应该如实陈述,不作伪证这一基本原则;而且誓词内容上还将证人违背誓言,作伪证所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进行了明确。
(四)证人宣誓的形式
宣誓主体信仰的多样化决定了宣誓形式的多样化。首先,证人宣誓的形式应当由法律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并结合证人的信仰来决定允许证人以其所信仰的并为我国法律所允许的宗教起誓,只有能在良心上对证人产生拘束力的词句或仪式才能成为证人宣誓的形式。⑰如在英国,按照1754年的判例,证人可以使用符合他的宗教的宣誓形式作证。《1978年宣誓法》允许证人按照对他有约束力的方式作宣誓。
其次,为了加强宣誓的仪式效果和警醒作用,证人的宣誓必须单独进行。
再次,在具体的证人宣誓的形式上,由证人站在宣誓台前或者证人席上,面对审判席,左手按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⑱或者基于其特定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内容,宣读作证誓词。
最后,证人应该采用朗读宣誓词的方式进行宣誓。在证人跟读或宣读誓词以前,法官应告知证人宣誓的意义和其所承担的义务,告知其提供伪证的法律后果,在得到证人明确表示清楚的答复后,法官才可以允许证人开始宣誓。宣誓可以由书记员领读誓词,宣誓人跟读,也可以由宣誓人根据宣誓书自行宣读。领读、跟读、自行宣读都必须声音清晰明亮,语气庄重。法官及法庭所有其他成员应当全体起立,由法官引导证人按照事前所确定的形式进行宣誓或证人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宣誓。
(五)证人宣誓制与伪证罪的关系
目前,证人宣誓制度并未在相关诉讼实践中得到运用。因此,笔者在考量对证人如实陈述事实进行提前预防——证人宣誓。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观察的视角放在另一个层面:如果证人进行了宣誓,但却未能按照其所保证的内容真实陈述,则如何从刑法方面对其进行规制。因此,有必要将证人宣誓与伪证罪联系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证人宣誓的威慑功能和提醒功能。[18]
笔者认为,设置证人宣誓制度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唤醒证人内心的良知,和对法律的信仰,增强其如实作证的责任感,从而最大程度上实现其如实陈述的可能性。而构成伪证罪的犯罪主体,⑲即证人的范围却不仅仅只包括经过了宣誓的证人,还包括依法不需要宣誓的证人。只要符合伪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就可以对其施以刑罚,进行制裁。从这个逻辑来思考,对于未经过宣誓程序的证人都有惩罚其作伪证的法律依据,那么对于经过宣誓的证人,法律已经给予了其如实作证的空间和机会,“让证人知道法院是如何依赖证人在法院中的作证。此乃最后的机会,提醒证人,假若他们远离真理,那么,社会的谴责就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19]甚至是刑罚的制裁。
四、结语
任何社会为了合理地解决纠纷,都必然需要规定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即解决纠纷的程式、规则和方法。[20]事实上,对于宣誓制度能否在我国诉讼制度中得以构建的问题,任何浅尝辄止,不予理性分析其价值所在而武断地进行否定的论断都是不科学的。对宣誓制度本质的认识,应该从其本身所具有的功用和价值来进行可行性分析,而不可以局限于仪式本身,看上去“流于形式”的过程,其背后却蕴含着作为其存在的、鲜为人理解的道德基础——信仰和普化的社会心理。纵观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以及中国古大典籍中,都存在着将宣誓制度作为提醒证人如实作证,增强其作证义务和责任感的手段的规定。
随着司法实践的推动,人们在思想上也逐渐对这一制度有了认识。而且随着中国民主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意识不断增强,以及现阶段信仰类型的多元化都为建立和完善证人宣誓制度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注释:
①根据该院的证人宣誓规则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证人在法庭作证时应当宣誓或作出具结保证;证人宣誓由审判长(独任审判员)主持,书记员负责监誓。证人应在宣誓台前面对审判席宣誓,并在签署证人宣誓书后进行法庭作证程序”。
②但是经过笔者的考察,在中国的夏、商时期,相关的法律制度中出现过关于宣誓制度的一些规定。根据《周礼》:“前者,依誓礼以结方语之约束;后者,歃牲血而立神誓;盟约之辞,则载之于策,或藏之官府,以供将来之勘证。”另外,诉讼中也有所谓“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凡盟诅各以其地域之众庶,共有牲而致焉,既盟则司盟共祈酒脯。”参见[日]岁积陈重著,黄尊三译《法律进化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③有学者从中国目前宗教信仰、历史文化背景的缺失和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不完善的角度出发,认为现阶段不具有构建证人宣誓制度的基础。参见赵蕾:论民事诉讼中不宜建立证人宣誓制度,《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年第27卷,第208页;王钺焜:我国建立证人宣誓制度的探讨,《河南城建学院学报》,2010年第19卷,第4期,第91-92页。
④《苏美尔法典》:“引诱自由民之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知之者,则引诱此女之人应对神发誓云:‘彼知实情,过应在彼。’”引自陈一云主编:《证据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⑤如英国《1978年宣誓法》第5条规定:“应当允许任何拒绝宣誓的人以郑重承诺代替宣誓”,而且“郑重承诺与宣誓具有同样的效力和后果”。参见何挺:证人宣誓:历史沿革和功能考察—兼论构建我国的证人宣誓制度,《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7年第1辑,第250页。
⑥许多国家法律认为,宣誓就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并且将宣誓作为证人能否具备作证资格的前提条件。
⑦有学者对此的认识是,将宗教类型划分为两类:即制度化的宗教和普化的宗教。参见张吉喜:证人宣誓与仪式—证人宣誓制度的另类解读,《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2期;魏强:论宣誓制度在我国诉讼中的构建,《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2卷第3期。笔者对此的思考是,可以将这种对宗教的解释扩大到对信仰内涵的解读,我们的生活中所存在的信仰的形态也可以包括两类:一类是制度化的信仰,如共产主义信仰,法律信仰,团体信仰等等;另一类则是普化的信仰,包括民间存在的祭祀,风水,算命和纯粹的敬畏心理等形式。
⑧《易经·坤卦·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另见南朝宋·释法明《答李交州难佛不见形》:“积善余庆,积恶余殃,虽新新生灭,交臂代谢,善恶之业,不得不受。”西汉·刘向《说苑·谈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⑨《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可见,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关于宣誓制度的规定,而且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没有规定。
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1条第2款规定:“证人、鉴定人作证前,应当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说明鉴定意见,并在保证书上签名。”
⑪《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3条:“证人在作证前要声明如实提供证词,通过宣誓或虽不宣誓但以某种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的方式进行”。其中就明确了证人宣誓制度所具有的实质性功能。
⑫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14条:“以未满十六岁或因精神障碍不解具结意义及效果之人为证人者,不得令其具结。以下列各款之人为证人者,得不令其具结:一、有第三百零七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清晰而不拒绝证言者。二、当事人之受雇人或同居人。三、就诉讼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者。”
⑬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则有关于证人拒证权的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63条:“第52条第1款所称被指控人的亲属有权拒绝宣誓;应告知该权利。”该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的订婚人;2.被指控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存在;3.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是旁系二等血亲或者二等姻亲。”又如《韩国民事诉讼法》第294条和295条。
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1条第1款规定:“证人、鉴定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核实其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关系,并告知其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⑮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12条第1款规定:“审判长于询问前,应命证人个别具结。但其应否具结有疑义者,于询问后行之。”第2款规定:“审判长于证人具结前,应告以具结之义务及伪证之处罚”。
⑯《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5款规定:“本法第198条和第199条规定,准用于证人拒绝宣誓的情况”。而在其第198条和第199条的规定中,就明确了负有释明的义务。
⑰《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5款也规定了在证人拒证的情况下,且无正当理由时,准用第192条和第193条的规定,由法官课以罚款、罚金或拘留。
⑱何挺.证人宣誓:历史沿革和功能考察——兼论构建我国的证人宣誓制度[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7(1):253-257。
⑲由于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世界上部分国家存在着将宣誓的形式作了其他特殊要求的情形。如英国规定,证人宣誓时,需要双手捧着《圣经》。
⑳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参见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51页。
[1]See.HAMISH STEWART.RCNALDA MURPHY.STEVEN PENNEY.MARILYN PILKINGTON.JAMES STRIBOPOULOS.Evidence.A Canadian Casebook,The Principled Approach to Hearsay,P.227.
[2]摩奴法典[M].马香雪.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41.
[3][日]岁积陈重.法律进化论[M].黄尊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8.
[4][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30.
[5]孙长永,纪虎.宗教化的法律仪式[J].学术研究.2004,(6).
[6]陈朴生.刑事证据法[M].台湾: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1979.378.
[7]陈少林.宣誓的启示—信仰、道德与法制[J].法学评论.2009,(5).
[8][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73.
[9][美]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可证据论[M].汤伟建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36.
[10]赵蕾.论民事诉讼中不宜建立证人宣誓制度[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27).
[11]See.Wigmore Evidence.1816.Theory of Oath(Chadboum Rev.1976).
[12]See.HAMISHSTEWART.RCNALDA MURPHY.STEVEN PENNEY.MARILYN PILKINGTON.JAMES STRIBOPOULOS.Evidence.A Canadian Casebook,The Principled Approach to Hearsay,P.227.
[13]刘永红,任雪丽.略论证人宣誓制度不适宜我国[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4,(2).
[14]张吉喜.证人宣誓与仪式—证人宣誓制度的另类解读[J].社会科学家,2007,(2).
[15]刘善春.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25.
[16]魏强.论宣誓制度在我国诉讼中的构建[M].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
[17]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62.
[18]廖中洪.中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
[19]廖中洪.中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2.
[20][美]弗洛伊德·菲尼,[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岳礼玲.一个案例 两种制度——美德刑事司法比较[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