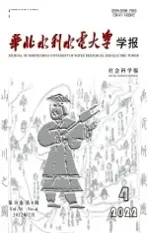现象学:教育现象学的哲学基础
2011-08-15王萍
王萍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现象学:教育现象学的哲学基础
王萍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教育现象学与现象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现象学从理论现象学中汲取营养,是实践现象学流派的组成部分。现象学为教育现象学提供了哲学基础,决定了教育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和研究范式,也为教育现象学提供了本体论的借鉴。
现象学;教育现象学;哲学基础
随着研究的日渐丰富,教育现象学作为“一门新型教育学的可能”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认同。但是,教育现象学与现象学有着何种关系?教育现象学与现象学运动有着什么关联?现象学运动又能对教育现象学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至今并未被明确回答。在教育现象学快速发展的今天,梳理与反思这类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正日益凸显。只有理清脉络,教育现象学才能在学术地图中寻得一己之地,才能汲取营养茁壮成长。
一、现象学概略
现象学的英文是phenomenology,是20世纪初产生于德国的一种哲学流派和思潮,创始人为胡塞尔(Hussel,E.)。其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即“通过回到原始的意识现象,描述和分析观念(包括本质的观念、范畴)的构成过程,以此获得有关观念的规定性(意义)的实在性的明证”[1](P1635)。这一描述性界定阐明了现象学的性质、特点和任务。若从其所指范围看,现象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现象学亦即胡塞尔的现象学,它随着胡塞尔《逻辑研究》的发表而问世。广义的现象学即现象学运动,是“西方现代研究、阐述和应用现象学哲学有关的学术思潮及学术活动的总称”[2](P1637)。本研究所指为广义现象学,教育现象学从现象学运动中汲取营养而形成。完全描述现象学运动的全貌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此我们无意也无力展示现象学运动全貌,只能粗线条勾勒现象学运动。
1901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胡塞尔发表了《逻辑研究》一书,在德国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著文评论此书,一些学生转学到胡塞尔所在的哥廷根大学学习,由此产生了一种哲学——现象学,也产生了影响持久、深远的现象学运动。现象学运动通过1913年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得以滥觞,并通过这份刊物而得以体现。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出版预告及创刊号的卷首上,这种精神有具体的文字体现:“这些编者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体系。使他们联合起来的是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只有返回到直接直观这个最初的来源,回到由直接直观得来的对本质结构的洞察,我们才能运用伟大的哲学传统及其概念和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观地阐明这些概念,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重新陈述这些问题,因而最终至少在原则上解决这些问题。”[3](P40)胡塞尔将这种精神称为“面对实事本身”,海德格尔(Heidegger,M.)将其概括为“走向实事本身”的现象学座右铭。正是在现象学精神的指引下,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汇集于现象学运动的长河,成就了现象学及现象学运动。
现象学运动起源于德国,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象学的影响就传到法国,并受到法国哲学界的极大关注,甚至促成了现象学中心的转移——由德国转移到法国。现象学移至法国是其国际化历程中的重要步骤。并且,现象学在法国得到了独具特色的新发展,如法国现象学很容易渗透到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社会学、历史哲学等研究领域,增强了对实践的指导。此后,现象学运动进一步扩大,1939年成立了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现象学学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涌现了更多现象学学会和小组,如美国的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学会(1962年)、英国现象学学会(1967年)、德国现象学研究会(1973年)等。如果说学会将一大批现象学研究者聚集起来,那么,档案馆则为研究现象学提供了资料。比利时卢汶天主教大学率先建立了胡塞尔档案馆,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先后建立。这为现象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使现象学除了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得到传播和发展之外,还在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俄国、印度、日本、中国等地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与积极研究。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施奈德教授(Schneider,H.W.)所说:“胡塞尔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大陆的哲学,这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获得了支配地位,而是因为任何哲学现在都企图顺应现象学的方法,并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它现在是高雅的批评的绝对必要的条件。”[3](P1)施耐德教授从对其他哲学产生影响的角度谈论了现象学。其实,现象学的影响远不止于哲学,还影响了艺术、文学、心理学等学科,也影响了教育现象学的产生及发展。
二、教育现象学对现象学的脉络传承
现象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理论现象学与实践现象学两大传统。教育现象学从理论现象学中汲取理论营养,是实践现象学的组成部分,它们构筑了教育现象学与现象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理论现象学主要有以胡塞尔为代表的超验现象学派;以海德格尔、萨特(Jean-Paul Sartre)、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派;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为代表的语言现象学派;以来宾纳斯(Levinas,E.)为代表的伦理现象学派;以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利科尔(Ricoeur.P.)为代表的解释现象学派等。虽然各学派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它们遵循共同的现象学原则,即“回到实事本身”。现象学运动更像是一棵伸展着的大树,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有如树根,其他的学派有如伸展开来的树枝,树枝依赖树根供给营养,树根依赖树枝得以展现,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撑、相互超越。与此同时,这些现象学学派又共同构筑坚实的理论土壤,为实践现象学提供滋养。如超验现象学派的“悬置”、“还原”与“生活世界”;存在主义现象学“走向事情本身”和“此在”;解释现象学对生活文本的解读、反思;伦理现象学的规范性;语言现象学对语言描述作用的分析等[4],这些对教育现象学及教育现象学研究具有理论支撑或方法论的价值。
实践现象学是与超验现象学、存在现象学、语言现象学、伦理现象学、解释现象学并存的另外一枝。之所以在现象学发展过程中出现实践现象学,是因为现象学作为哲学,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教给人们一种思维的态度和方法。实践现象学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它从现象学运动的多个学派中借鉴方法与观点。有现象学家宣称“只能通过现象学实践自身获得对现象学的正确理解”[5](P3)。实践现象学流派更是认为,现象学的重要作用不在于思考、思辨,而在于实践,同时提出了响亮的“做”现象学的口号。正是在“做”现象学理念的指引下,教育现象学将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悬置”、“还原”、“体验”、“解释”等理念,作为指导实践的准则,在临床心理学、医学、教育学、护理等学科领域中运用,并涌现一大批代表人物,如精神病专家宾斯万格(Binswanger)和范登伯格(Van Den Berg,J.H.)、临床心理学家拜腾狄克(Buytendijk,F.J.J.)和林肖腾(Linschoten,J.)、教育学家兰格威尔德(Langeveld,M.J.)和博尔诺(Bollnow,O.F.)等。
实践现象学流派中的教育学家兰格威尔德正是教育现象学的创始人。1944年,乌特勒支学院的兰格威尔德在其作品《教育学的科学本性》中提出了教育现象学的概念,教育现象学的基本思想在这本著作中得以体现,如强调教育学的规范性、关注儿童和成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研究教育生活体验等,从而奠定了其教育现象学创始人的地位。因该书所提倡的观点与传统教育学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之处,给人们带来一些新鲜观点,受到广泛关注。这本书从1946至1979先后15次出版。兰格威尔德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在于提醒人们:“教育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其研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知道事情是怎样的,而且是为了了解近期或长期实践之内人们应该怎样做。”[6](P39-64)这一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克里克曾提出的理想一致,这也是教育现象学的一种必然追求。兰格威尔德将教育现象学的研究称为“家庭、厨房、街道”的研究,认为“家庭、厨房、街道”恰恰是实践的“真对象”,只有从“真对象”的实践中才可以探索出知识的奥秘、联系和最本真的东西。教育现象学者怀着这样的信念,关注家庭、厨房、街道等生活场所中所发生的事件,以期通过自己的研究引起人们对其教育意义或价值的重视。兰格威尔德在阐明教育现象学思想的同时,也进行了具体的教育现象学研究,如《儿童生活中的“秘密场所”》对于阁楼等秘密场所相对于儿童而言的意义进行了研究,确立了教育现象学研究空间体验这一基本方向。在兰格威尔德之后,教育现象学研究开始成为乌特勒支学院一些成员的共同事业,如比克曼(Beekman,T.)、莱维林(Levering,B.)等都进行了教育现象学的研究,以致促成了与北美现象学研究的对接。20世纪70年代,北美开始形成现象学研究的传统,尤其是在奥克(Aoki,T.)、范梅南(Van Manen,M.)、肯尼斯(Kenneth,J.)、卡森(Carson,T.)等人的领导下,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了众多的教育现象学研究,在他们的推动下,教育现象学更是得到了国际化的发展,被更多人所关注和了解,逐渐成为“一门新的教育学的可能”。
三、现象学对教育现象学的影响
教育现象学的产生及发展离不开现象学的影响,但现象学对教育现象学的影响又是内在的、深入骨髓的。因为哲学意味着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意味着高度抽象与概括,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意味着一种丰厚的底蕴和支撑。现象学决定了教育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和研究范式,也为教育现象学提供了本体论的借鉴。
现象学为教育现象学提供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基本原则。现象学运动之所以能将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学派归为一体,就在于“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与原则,这一原则是现象学之所以成为现象学的重要标志,也是现象学为教育现象学所提供的哲学基础。“回到事物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象学哲学中内涵最丰富、发展最充分的一个理念,虽然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愿意响应这一号召,践行这一原则。现象学对“回到事物本身”的执着精神,影响了教育现象学同样遵从“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提倡回到教育现象本身研究教育问题。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回到事物本身”同样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理想,只有回到事物本身,才有可能真正了解该事物,认识该事物,并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教育现象学方法之所以是一种别样的研究视角,就在于其重新返回教育的本真,在教育生活体验中追寻教育意义。这是对“回到事物本身”的一种回应。
现象学决定了教育现象学的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现象学是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之一,其本身也充盈着对人文思维的执着追求。教育现象学以现象学为哲学基础,秉承了现象学浓郁的人文特性,并且教育现象学的研究符合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要求。“人文主义研究范式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7]这说明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要素包括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整体性探究、解释性理解。教育现象学研究具备这三个要素。第一,教育现象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是有价值关联的。在教育现象学研究中,虽然有“悬置”、“加括弧”的要求,但这仅仅是提醒研究者尽可能不带任何偏见、不受任何权威影响地接近事物本身,至于具体研究过程中对现象的解释、对现象意义的理解等都受研究者本人生活背景、经验等的影响。并且,教育现象学强调研究者关注并理解他人在真实教育情境中的体验,在此,研究者本人就是研究的工具。第二,教育现象学研究强调直观把握,是对事物的整体性探究。教育现象学研究中将现象看作一个整体,强调透过感性直观、范畴直观等方法把握事物。教育现象学的研究不是研究单个现象本身,也不是对众多单个对象的归纳总结,而是需要靠直觉、洞察等把握现象的主题和意义,这是对现象的一种整体性探究。第三,教育现象学的研究是对教育现象的解释性理解。理解在现象学那里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被提高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理解成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不是对客观知识的说明,而是人生经验的表达方式。研究者会以掺入个人的情感、态度和体验的方式理解事物,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文本。教育现象学继承了现象学对理解的重视,强调对教育情境中的他人的解释性理解,强调对教育文本的解释性理解。
现象学为教育现象学提供本体论借鉴。自胡塞尔始,尤其是经过海德格尔的发展,现象学试图重新构建关于存在的本体论,试图借助超感觉和超理性的直觉建立概念体系。现象学“既不承认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预先假定,也不承认传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而要求重新考察开端的绝对明证性”[8]。最终,现象学将这种绝对明证性确定为“事物本身”。这样的本体论带来一种新观点:现象本身即为本质。在现象之外,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本质,现象本身可以自我显现,现象会向我们显现其自身,而无需我们赋予其另外的本质。因此,对现象的领会和理解是存在的基本形式。这样的本体论给教育现象学一定的启示:教育活动也是一种现象,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教育现象也即生活。因此,我们应回到教育现象本身去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现象本身即其本质。这将是对传统教育学的一种颠覆。传统教育学提倡研究教育现象,解释教育规律,本质先于现象而存在,需要去发现。教育现象学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也许教育的本质就是教育自身所显现出来的,我们需要关注这种显现。
现象学哲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其对教育现象学的影响可以说具有较大的间接性。但这种影响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正是在现象学运动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才开始将现象学理论及方法引入教育领域开展研究,才产生了教育现象学。但不可忽视的是,教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有着独特的教育立场,现象学为教育现象学提供哲学基础,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1]冯契.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2]哲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哲学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M].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李树英,王萍.教育现象学的两个基本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
[5]Ihde,D.Experimental phenomenology:An introduction[M].Albany:SUNY Press,1986.
[6]Van Manen,M.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and the question ofmeaning.In D.Vandenberg(Ed.),Phenomenology and Educational Discourse[M].Durban:Heinemann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1996.
[7]孙家明.论西方教育研究的范式演进[J].成功(教育),2008,(11).
[8]金延,张有奎.现象学方法的反思[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3).
Phenomenology: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WANG P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Henan University,Kaifeng475004,China)
There are countless ties between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and phenomenology.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absorbs nutrient froMtheoretical phenomenology and is a component of practical phenomenology.Phenomenology i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Phenomenology determin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and the paradigMof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Furthermore,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takes examples froMthe ontology of phenomenology.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Phenomenology;Philosophical basis
G40-06
A
1008—4444(2011)05—0162—04
2011-05-16
王萍(1981—),女,河南方城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讲师,教育学博士。
(责任编辑:宋孝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