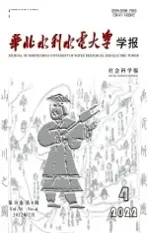王蒙小说中的文体跨界现象
2011-08-15龙学家
龙学家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王蒙小说中的文体跨界现象
龙学家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王蒙小说的美学价值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体现在故事的叙述上,而是体现在深切的抒情与警策的议论上。按照文体要求,议论与抒情在小说中只应该配合故事的叙述出现,但是王蒙小说中的议论抒情却喧宾夺主,占有过量的篇幅,存在明显的文体跨界现象。
杂文手法;文体跨界;多元价值取向
一、综合了抒情散文与文艺性政论的小说叙事
小说是一种叙事文学,叙事文学必定要讲故事。抒情散文是抒情文学家族中的一员,中国一直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抒情的本志在于表达主体的内心情感。文艺性政论的内涵指向较明确,是指带有文学色彩的议论政策和政治生活的散文。王蒙小说中的议论多与政治相关,是因为王蒙小说主要描绘政治生活。王蒙的小说身兼三任,在小说叙事中掺杂有相当数量的脱离主线情节的抒情和议论,所以,王蒙的小说不仅是单纯的叙事文学,而且还跨了抒情散文与文艺性政论的界限。
童庆炳在他的著作《文体与文体创造》中,参照中国古典文论详尽地阐述了文体论中体裁、语言体式、个人风格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体裁从根本上制约了文学创作,所谓“写诗要象诗,写小说要像小说,不能不遵体制随意乱写,如果体制得不到大体的遵守,势必产生非驴非马的东西。非驴非马的‘四不象’在动物界是允许存在的,但在创作中则不允许存在”[1](P11)。他在批评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时,提出了“小说杂语文体”这一独特的概念。他说:“翻开‘季节系列’,触目都是王蒙式的语言的游戏、语言的狂欢,那种看似非正规而又正规、看来似通非通、非通又通、似连非连、似不连又连的句子满篇都是:白话、古代诗词、现代诗歌、政策条文、苏联歌曲、流行口号、毛泽东语录、成语、流行谚语、民间俚语等夹杂在一起;幽默、排比、反讽、比喻、象征、议论、调侃、戏谑等交叉使用,可这—切又都能连成一气,且蕴涵丰富,信息量大,形象鲜明,生气盎然,风味独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小说的统一的杂语文体。”[2]童先生的定义针对的是王蒙小说中的语言特色和行文的修辞表现手法。这么庞杂的分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的语言和几乎囊括所有修辞的表现手法要想黏合在一起,势必得依靠王蒙自己独特的叙事、抒情、议论三合一的表述方式。
王蒙小说打破了人们对小说的固有期待,在正常的故事讲述之外,不单单有大篇幅的抒情,还掺入了大段的议论,在故事的框架上把政论与抒情散文奇特地链接在了一起,兴之所至的王蒙打破了体裁间的差别,各种体裁在同一时空集体呈现,有研究者将之称为“经纬交错的小说新结构”[3]。在这种观点中,对现实的抒情与议论统统被归为心理活动,所以论者认为王蒙的小说以故事情节为经,以心理活动为纬,经线保证了故事的流动性,而小说深刻的内涵又沿纬线以抒情和议论的方式展开。在王蒙的代表作——被称为季节系列的四部小说中,第一部《恋爱的季节》还重在情节的编织,到了最后一部《狂欢的季节》,小说的重心转移到对“文革”的评议,情节和人物都只充当了一个由头,或者是论题。
小说从讲故事的文体变成了说理兼抒情的文体,真可谓是王蒙的一种创造。王培元用“一个人远游”来概括王蒙此类小说的模式[5]。这里,“一个人”就是议论主人公、抒情主人公,他的主观感情凌驾于故事之上,他可以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也可以是故事的叙述者。例如中篇小说《杂色》,故事情节几乎没有,写了因政治原因被困新疆的内地知识分子曹千里到夏季牧场的一次公干,一路上经过了七个地方:过塔尔河(河水很急,老马喝水),进补锅匠村(在供销社买了点东西),进山(进山前进遇到一条黑狗),然后走傍山石路(路上不断下马与哈萨克牧民施礼),进入草地(遇到暴风骤雨),最后来到一个名叫“独一松”的地方(饿了,在毡房里喝马奶)。这样简单的情节不足以支撑一部中篇小说,《杂色》中出彩的是曹千里的评论。曹千里一路走一路想,主观之情与客观物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感情丰厚复杂,过去的回忆、现实的遭际与将来的展望于同一时空内展现,牢骚与激情共存,自弃与奋发并列。高行健在1982年就读出《杂色》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于王蒙赋予曹千里的王蒙式的机智的自嘲[6]。通过曹千里,王蒙写出了一代虽命运浮沉却不甘末流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心境。
“一个人远游”与“经纬交错的小说新结构”都共同昭示,故事因素在王蒙小说中退居次要位置,作为小说,其艺术价值主要不是建立在故事的描述上、情节的编织上,而是建立在论说之上。《杂色》1981年载于《收获》第3期,那时的王蒙刚刚重返文坛,还在摸索自己的文风,到了写作《季节系列小说》时,王蒙的文风终于形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夹叙夹议的宏大文体”[4](P145)。这样的文体是越界的文体,行文表现手法上倚重抒情与议论,其艺术美感有相当一部分体现在抒情的真挚和议论的警策上,作为小说当行本色的故事叙述在文本中被稀释掉了,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就成了“叙事+主观抒情+杂文式的议论=王蒙小说”。
二、文体跨界背后的思想内涵
王蒙是一个用笔思考的作家,他的作品背后有他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1994年前后爆发的“二王之争”,王蒙在那场论战中显得势单力薄。十多年过去了,近几年来,反而有不少学者发表文章重提往事,重新理解王蒙的用意,阐释王蒙的哲学思想。笔者认为,王蒙这种“夹叙夹议的宏大文体”是其独特的哲学思想的表达工具,王蒙小说的文体跨界现象可以从其哲学思想中找到原因。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王蒙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多元”思想,矛头直接指向长期在我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二元对立”思想。
众所周知,把共和国的那段历史当作写作资源的不仅有王蒙,还有一个庞大的“知青族”和“五七族”作家群,他们与王蒙有相同的历史背景,但表现方式却迥然不同。有不少作家升华自己的受苦经历,将那段岁月当成人生的一份最宝贵的财富,将自己过往的经历神圣化,以此完成对现实苦难的超越。在《绿化树》中,张贤亮让主人公忍受饥饿的折磨,性苦闷的折磨,在马克思著作的指引下,主人公的精神反而在苦难中得到了提升,他在极左政治造成的苦难中修行,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成”,章永磷体现出一种悲壮的崇高美。从维熙以其右派经历写出了《走向混沌》这部小说,跟张贤亮一样,从维熙也有意识地神化右派的受苦经历,肉体的苦难升华了崇高的精神。其他作家都有类似的倾向,支撑他们创作的哲学思想正是“二元对立”。
王蒙小说中的价值取向却是多元的。王蒙既批判极左的政治,又嘲笑右派知识分子庸常的一面。在《失态的季节》中,王蒙讲述,原来1957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的右派还保留了城中的职位和薪水,当他们放假回城的时候,累积的薪水一齐补发给他们,所以这帮右派分子拿着这笔为数不少的钱在北京城中很是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吃西餐、看电影、逛商场,只是怕被其他的下放在一处的右派撞上,因为这样会留给对方自己“仍有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口实。王蒙写道:“在农村人们最喜欢问的就是钱。‘一个月挣多少钱?’无数次这样问他。领导上规定不准说实话,不准说出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在乡下如果给一个农民这么多钱叫他赴汤蹈火也罢低头认罪也罢死命改造也罢他们会打破头抢着去的。为这么多钱割掉一个手指头农民也会乐意的。”[7](P8)下放右派对物质享受的难分难舍以及与本地农民巨大的条件反差,主要不是以故事的形式得以“显示”的,而是由小说主人公和叙述者“论说”出来的。这样的小说结构可以用“一事一议一感”来描述,情节滔滔汩汩向前发展,针对具体事件,就有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者直接由叙述者出来发表意见或者抒情。“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8](P389)这句话是《夜的眼》中的主人公陈杲听见别人谈论民主后的心里所想。当时陈杲刚刚开完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贝尔格莱德、新加坡、民主,之后又要连夜到一位领导家“走后门”。这句话出现在这样的情节设置中极富哲理性。王蒙在小说中大量地运用警策的哲理性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评价,使他的小说犹如杂文一般深刻。
多元的王蒙像是一个智慧老人,也正是因为王蒙太爱在小说中思考,议论抒情冲淡了故事叙述,所以伤害了现实主义文学塑造典型人物的金科玉律。王蒙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支撑自己的写作方式。在《关于塑造典型人物》中,王蒙争辩道,既然人物形象可以称为典型,那么一种情绪一种心境能不能被冠以典型之名呢[9](P189)?例如短篇小说《夜的眼》就营造了一种气氛。刚刚结束了“文革”,中华大地百废待兴,但是也给人一种乱纷纷的感觉。“夜的眼”暗指路灯,光亮可人但又照得眼花,“夜的眼”本身也给人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社会越变越好,但是,依然有不和谐之处——陈杲找人办事却被索要“人事”。
《关于塑造典型人物》写于1982年,从那时开始,王蒙已经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新文体进行辩护,这是王蒙文体创新的开始。支撑王蒙小说的不是故事,而是多元哲学和随之而来的情感。他的艺术重心由塑造“典型人物”转移到心理意识层面的“典型情绪”、“典型心境”,通常这种情绪和心境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借助抒情和议论表达出来。这样的写作方式解放了王蒙被文学体裁的条条框框所限制的笔杆,其文学创作最大程度地与自己广博而又深刻的思考相契合。
世人评论王蒙的小说往往标注“意识流”这个关键词,其实这与抒情和议论的运用互为因果关系。“意识流”是说王蒙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曾是学界一个热门的话题。王蒙最初借鉴西方意识流技巧,不是盲目地求新求变,而是西方的意识流技法契合了他文学表达的理想。王蒙是一位重感受重思考的小说家,这在小说家族中多少显得有点儿特立独行,但是,西方的意识流小说给摸索中的王蒙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成功范本。意识流小说淡出了故事因素,用潜意识建构人类世界。王蒙没有走这么远,他只是发现了人的内心可以成为情感和思考的载体,直接书写自己的情感和思考的方式比编故事的方式更直接也更符合他的艺术个性。所以,在《春之声》、《夜的眼》等篇什之后,“意识流”已经在王蒙小说中消退,但王蒙却在“意识流”的启发下将艺术的重心由外部世界转入内心活动,这也成为他代表性的风格。
三、结语
王蒙小说的主角是王蒙的思想,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王蒙逐渐坚持一种多元的价值观。在多元价值观的表达方式上,他选择了以故事为辅、直接抒发为主的写作方法。童庆炳认为,一种新文体是否美,取决于它的内容与形式是否统一[1](P287)。王蒙的此类小说以他熟悉的政治生活为题材,根据自己的多元哲学对这一题材进行提炼加工,基于小说的内容,王蒙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思辨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多元的价值观,势必会造成要表现的内容无法再只用编故事的方法表达,所以,王蒙选择了这种跨界的小说为其内容的载体。
[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童庆炳.历史维度与语言维度的双重胜利[J].文艺研究,2001,(4).
[3]陈孝英,李晶.“经”“纬”交错的小说新结构——试论王蒙对小说结构的探索[J].当代作家评论,1984,(1).
[4]王蒙.狂欢的季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王培元.“一个人远游”:王蒙小说的一个模式[J].当代作家评论,1995,(6).
[6]高行健.读王蒙的《杂色》[J].读书,1982,(10).
[7]王蒙.失态的季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8]王蒙.王蒙文集(第五卷)·夜的眼[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9]王蒙.王蒙文集(第七卷)·关于塑造典型人物[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Crossover Phenomenon in Wang Meng’s Novel Style
LONG Xue-jia
(College of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 large partof the aesthetic value in Wang Meng’s novel is not reflected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story,but it is reflected in the deep emotion and literary comments.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ylistic requirements,comment and lyric in the novel should only cooperate with the narration in the novels ofWang Meng,but they take possession of excessive length,so the author thinks there is obvious stylistic crossover phenomenon in Wang Meng’s novels.
Essay style,Cross-over phenomenon,Multiple values
I206
A
1008—4444(2011)05—0120—03
2011-07-12
龙学家(1986—),男,四川威远人,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