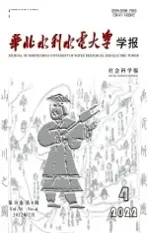清代科举试诗改革背景下李贺诗的接受状况
2011-08-15杨鉴生吴留营
杨鉴生,吴留营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清代科举试诗改革背景下李贺诗的接受状况
杨鉴生,吴留营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诗歌选本往往反映出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貌。《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诗,受其选诗标准、宗旨定位和所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所制。清代科举试诗促成了诗学的复兴,古典诗歌则因现实的需要而面临新时代的扬弃。
清代;科举改革;李贺
世称“诗鬼”的李贺是中唐诗坛年少才高而英年早逝的杰出诗人。乾隆中期科举试诗改革掀起了编选诗歌选本的热潮。优秀诗歌在选本中缺席,引人发问,促人深思。笔者以《唐诗三百首》为例,就科举试诗改革背景下李贺诗在特定选本中的接受情况作一论述。
一、李贺诗与清代试帖诗体制
李贺诗继承发展屈原、李白等人的浪漫主义色彩,亦取法于韩愈诗文理论,形成独具一格的“长吉体”。历来评者对其褒贬不一,欣赏者谓之奇思妙语、巧夺天工,抨击者论其师心作怪、艰涩难解。
李贺及其诗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杜牧曾为《李贺集》作序,赞曰:“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垅,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1](卷7,李贺集序)陆龟蒙、李商隐都曾为李贺作传。唐代即兴起仿学李贺诗之风。《旧唐书·李贺传》载:“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2](卷137,P3773)宋欧阳修《春寒效李长吉体》、秦观《拟李贺》等摹拟长吉体者不一而足。明胡应麟亦称:“元末诗人,竟师长吉。”[3](内编卷三,P56)清方扶南曾作高度评价:“学其长句者,义山死,飞卿浮,宋元入俗。”[4](P292)吴闿生亦赞曰:“昌谷诗上继杜韩,下开玉谿,雄深俊伟,包有万变,其规意度,卓然成一大家,非唐之他家所能及。”[5]足见李贺诗在历代诗学界之瞩目地位。
科举制自隋代兴起,唐代发展完善,历经宋元明清,沿用不衰,只是科考内容时有变化。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制动刀,唐代以来的诗赋科目被取消,诗歌由此走下高台,光环褪去,备受冷落。然而,诗歌始终是古代社会教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清初,诗歌被边缘化的现实不只为学者所忧虑,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重视。为改革八股取士之弊,康熙曾两次推动科举试诗改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6](卷108,P3151),遂正式恢复科举试诗科目。科举指挥棒指向的变化,促成了一次不小的诗歌复兴热潮,学诗、论诗、编诗、写诗之风盛行一时。诸如毛张建《试贴唐诗》,徐曰琏、沈士骏《唐律清丽集》,李因培《唐诗观澜集》,纪昀《唐人诗律说》等应试诗集纷纷涌现。沈德潜也重订《唐诗别裁集》,并在序言中说:“五言试贴,前选略见,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入春秋闱者导夫先路也。”[7](重订版序)处于此背景下的编者蘅塘,自然也不能置身其外。《唐诗三百首》虽未明言专门服务于科举应试,但所选五言律诗最多,其中也收录了一些奉和应制之作,如岑参《奉和贾至早朝大明宫之作》、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等诗篇,显然是应现实之需。
科举终究是官方取士的政治活动,必须体现统治阶层的意志。虽然科举试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八股拘泥,考生有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但试诗题目均出自经、史、子、集,评卷标准形式上要求使用五言六韵、八韵的排律,较之唐代,规制更为严格。试帖诗亦八股化,试诗题目或为前人诗句,或为成语典故,且题目之字须在首、颔两联中点出;韵脚在平声各韵中出一字,出韵、倒韵、重韵、凑韵、僻韵、哑韵、同义韵和异义韵均不能用;除首尾两联不用对偶外,其余各联均须“铢两悉称”;此外,考生应熟稔用典,既能判明诗题典出何处,行文扣题,又须在制诗时灵活用典,忌用牵强生涩之典。内容上则要求清正典雅、辞清理醇。“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复经礼部奏议,应再饬考试各官凡岁科两次以及乡会衡文,务取清真雅正,以为多士程式。”[8](P13)鉴于此,唐诗选本的编者亦心领神会,自觉掌握分寸,别裁选诗。
而李贺的诗并不合应试体制。唐高宗时,进士科开始加试诗赋。玄宗时,正式把诗赋定为科举的必试科目,且进士科重在考诗赋,由此,“以诗取士”的风气便骤然兴起,写诗作赋成为人们做官的一种敲门砖。唐代州府试的诗,一般是给定题目和用韵的五言六韵律诗,其间也偶有八韵者。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李贺参加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汉章帝曾作《灵台十二月诗》,各以其月祀奏之;古乐府中亦有《月节折杨柳歌》,自正月至十二月皆有吟咏。在考场上加以闰月,可见李贺对汉乐府诗作的深谙与喜爱。清人王源曾评曰:“读汉魏乐府,乃知长吉章法一本乐府。”[9](卷15,听雨轩序)事实上,李贺在题材上偏爱乐府诗,所创该体仅被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的就多达46首。李贺应试诗章法结构与科考的要求限制显得格格不入。现就其体制举一例分析。
正月
上楼迎春新春归,暗黄著柳宫漏迟。
薄薄淡霭弄野姿,寒绿幽风生短丝。
锦床晓卧玉肌冷,露脸未开对朝暝。
官街柳带不堪折,早晚菖蒲胜绾结。
全诗是一种平和的叙述,既无开门见山,亦无卒章显志,颔联颈联顺意而下,没有讲求对仗。在平仄上,第一句仄字开头,六字皆平,与第二句的平仄相杂而不相符。在用韵上,联尾各字究其中古发音亦不甚严格,清方扶南评李贺“诗亦深思,但非试帖所宜。有唐人试帖行世,可鉴也。”[4](卷1,P299)可辅此证。通观十三首诗更是长短不一、音节各异,可见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为应试诗中仅有的特例,是当时科考诗体的别格。李贺《赠陈商》中的“学为尧舜文,时人责衰偶。”对堕入程式、偏重声韵的诗风十分反感。唐赵璘《因话录》中亦有云:“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10](卷3,商部下)擅古体歌行的李贺显然不符科举试诗的程式,其应试诗尚且如此,其余尤甚。清代科举试诗袭唐制沿用五律,且章法结构、韵律和对仗要求更严,李贺诗更不宜作为试贴诗范式为学童仿习。
二、李贺诗与《唐诗三百首》的题材韵律
中唐以降,格律诗的创作数量大大超过了古体诗,而且诗歌的整体艺术价值较之前期也有很大提高。反映在蘅塘的选本里,格律诗占了约四分之三的篇幅。这是由科举试贴选用律诗为体式相促而成的。蘅塘选诗对字数、句数、平仄、用韵都有严格的要求,所选近体诗无一首有孤平、三平调等弊病,律诗的对仗也极其工整。
《唐诗三百首》对体裁要求比较严格,编者将所选诗歌按体裁明确分为七卷,被各卷收录之作都有清晰而明确的诗体。沈德潜认为:“诗贵浑浑灏灝,元气结成。”[7](原序)所以,他选诗的艺术标准是“有不著圈点而气味浑成者,收之;有佳句可传而中多败阙着,汰之”[7](凡例)。这一点内化在蘅塘选诗的标准里,诗歌“脍炙人口尤要者”[11](凡例),每首诗读来朗朗上口,浑然一体,不因只注重炼字炼句而忽视整体诗风。
而李贺诗歌多为古体诗,虽有少数的格律诗,但诗中平仄、用韵也不甚严格。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李贺所作诗歌多沿袭古乐府、齐梁宫体,并受《楚辞》影响甚深,因此,在诗歌的格律方面不甚着力,平仄、用韵、对仗甚至体裁上都形成一种散漫无章之态。“李长吉七古,虽幽僻多鬼气,其源实自《楚辞》来,哀艳荒怪之语殊不可废,惜成章者少耳。”[12](P987)二是李贺作诗常常诗囊选句,连句连词成篇,导致字句之间缺乏平仄上的粘对、韵律上的切合。因此,他的诗歌有句无篇,在章法上散乱零碎,在结构上缺乏完整性。三是完全出于对“元和体”的憎恶。“元和体”是中唐大诗人元稹、白居易所创的诗歌体式,在中唐广泛流传。“元和体”注重形式,妨害了讽喻之意的表达,并导致后来纤丽浮荡诗风的形成,因而引起韩愈、孟郊等人的憎恶。李贺与韩愈交往甚密,又颇受其“以文为诗”主张的影响,因此,其诗在形式上要求不严。
“长吉诗无七言近体,亦是千古一恨事”[13](P1048),清方扶南亦评“长吉诗但无七律,其五律颇多,而选家诸本未采,大抵视为齐梁格诗”[4](P291),且“李贺古诗或不拘韵,律诗多用古韵,此唐人所未有者;又仄韵上、去二声杂用,正合诗余”[14](卷26,P263)。如众所熟知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此题为乐府旧题,是一首拟古诗,介于古体诗与近体诗之间,从体制上可以说是一种半自由诗体,深究各联尾字中古音,可以发现此诗并不押韵,在平仄上没有粘对,在对仗上也不工整。全诗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景物的罗列,加以融合和渲染,因此并没有追求格律上的契合。从李贺的诗歌和前人对其评价中,可以推而总之,李贺诗少有韵律工整之作,读来往往苦涩拗口。这显然与《唐诗三百首》诗歌格律体裁上的选编要求相违背。
三、李贺诗风格与清代文治方略
考察清代科举试诗改革要义,亦可从御选唐诗着手,二者共同体现了清代文治方略。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我国古典文化集大成的总结阶段。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古代经典的一次告别演出,是一种必然。文化集成自然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驱动,但更多地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息息相关。清初,根基未稳的满清统治者迫切需要汉族臣民尤其是士人对其统治地位的承认抑或是默认。事实证明,单纯的杀戮显然不是治国安邦的长久之计,非治本之策,且又埋下更深的仇恨,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汉族士人的控制则更胜一筹。为防止文人以纸笔诗文鼓动人们的反满情绪,标榜尊崇儒道、稽古右文的清廷组织人力,提供财力,对历代图书典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集成。一时间,大批文化精英在宫阁馆室里聚合。在终日整理图书典籍的过程中,销蚀的不只是时间岁月,亦是对满清新朝的抵触情绪。
另者,皇帝往往亲总此事,屡屡莅临指导工作,这些文士依据帝王的旨意来决定图书的增删去留,日渐自觉地倒伏在帝王划定的圈子里,而文人内心“学以晋仕”的意识也使这些沦落的前朝士人因重沐皇恩而对清廷感恩戴德,乐为所用。
更为甚者,皇帝亲自别裁编选诗文,成为清代文治一大特色。康熙、乾隆、道光等在位期间,除授意指导选本编订工作外,都曾亲自操刀,遴选唐宋诗歌集成御选标本,从而更直接更深刻地影响选家编者编选标准和诗文创作的笔端指向。康熙在《御选唐诗序》中云:“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15](卷首)乾隆选定《唐宋诗醇》以成“共识风雅之正轨”[16](P3151),其以温柔敦厚的诗歌正风化俗、平和人心之意昭然若揭。最高统治者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的文化意指,成为整个文坛的标尺准绳。无论是科举试诗、选本编撰还是诗文创作、品评,所有的文学活动都在围墙里平和演进。清人梁章钜在《制艺丛话·例言》中云:“国朝自康熙以逮今兹,中间制艺流派不无小异,而清真雅正之轨则屡变而不离其宗。”[8](例言)文人士子无论分属何种学派,均须与朝廷文治思想保持高度一致。朝廷和主流文坛所崇尚的“清真雅正”之风影响整个清代中前期。思想情感健康纯正、表达形式委婉平和之诗得以存活、传扬,而消极偏激、离经叛道之类诗文则因与之格格不入而遭冷落摒弃。
李贺诗风显然不符清代文治崇尚的清真雅正精神。“长吉歌行,新意险语,自有苍生以来所绝无者。”[17](新集卷六)求新意、出险语,其诗往往有意向一个偏僻的方向放纵。“贺有异才,而不入于大道,惜乎其所之之迷也。”[18](P1422)由此可知,这种诗并不追求大雅,甚至有些刻意走歪邪古怪之路,因此很难符合主流诗歌的标尺。从意象上到用字上,从叙述上到想象上,李贺诗无不透出一种超乎凡人、浮于尘世的独特性。“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时时山精鬼火出焉;苦涩如枯林朔吹,阴崖冻雪,见者靡不惨然。”[19](卷4,P1217)有人说他继承了太白的想象之奇,但李贺的想象力更是超然天外,让人觉得陌生且不易理解。有人说他继承了韩愈的用字之诡,这种用字的诡奇更是生涩难见。更有人说他是屈原之转世,楚《骚》之苗裔。“李长吉诗,每近《天问》,《招魂》,楚《骚》之苗裔也;特语语求工,而波澜堂庑又窄,所以有山节藻棁之诮。”[20](PP26)因此,其诗往往给人一种来自异界的陌生感,来自天外的惊奇感,来自鬼域的冷涩感。“篇章以平夷恬淡为上,怪险蹶趋为下,如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21](卷1,P455)从宋人张表臣的评论可以看出,文风广袤、兼收并蓄的宋代尚不能将其置之廊庙,清代清真雅正的文风更不能容。结合诗句“银浦流云学水声”、“老鱼跳波瘦蛟舞”、“美人懒态胭脂愁”等中的“银浦流云”、“老鱼”、“胭脂愁”这类语言不可谓之不险,但在长吉诗中屡屡出现;又如“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枯荣不等嗔天公”这些语言更是出乎世人的顺天思想与传统观念,其诗与清代文治思想相去甚远,不为主流诗坛和整体文学风气所容。《唐人试律说》、《御选唐宋诗醇》等试贴诗选和御选诗集均避选李贺诗。身为学官,肩负引导学子启蒙、晋仕的蘅塘自是深谙当局文治要旨,毅然将李贺诗弃于案角,略过不提。
综上所述,独具风格的李贺诗在历代虽为诸多文人所追捧、仿习,但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其地位和接受视野有所变化。除启蒙读物定位、情感教育功用等既定框架外,《唐诗三百首》亦受科举试诗改革背景因素所制,故而有字难韵险、消极偏激之嫌的李贺诗见弃集外。
[1]杜牧著,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序[A].姚文燮,王琦,方扶南.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吴闿生.跋李长吉诗评注[J].四存月刊,1922,(12).
[6]赵尔巽.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梁章钜.制艺丛话[M].上海:上海书店,2001.
[9]王源.居业堂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0]赵璘.因话录[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1]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施补华.岘佣说诗[A].清诗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78.
[13]叶矫然.龙性堂诗话[A].清诗话续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5]玄烨.御选唐诗[M].(清)康熙五十二年内府刊本,1713.
[16]永瑢,等.御选唐宋诗醇提要[A].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十)[C].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陆时雍.诗镜总论[A].历代诗话续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3.
[19]谢榛.四溟诗话[A].历代诗话续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沈德潜.说诗晬语[A].清诗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1]张表臣.珊瑚钩诗话[A].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0.
Acceptance Satus of Li He’s PoeM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PoeMin Qing Dynasty
YANG Jian-sheng,WU Liu-ying
(Literature School,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Shangqiu476000,China)
Poetry anthology often reflects the social style under the specific era culture background,“300 Tang poems”do not elect LiHe's poems in it,because of its standards,Purpose,positioning and social background.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ic reforms in Qing dynasty contributed to the revival of the poetics,classical poetry faces a challenge by the new era because of reality needs.
Qing dynasty;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ic reforms;Li He
I207.2
A
1008—4444(2011)05—0113—04
2011-05-21
杨鉴生(1969—),男,福建宁德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后。
(责任编辑:王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