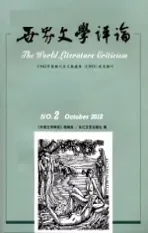《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内心密语之解读
2011-08-15黄燕红
黄燕红
“没有回忆的人是一具尸首”(伏尔科夫5)。这是肖斯塔科维奇《见证》的整理者,俄罗斯学者伏尔科夫在该书序中的一句话。
肖斯塔科维奇是20世纪前苏联伟大的音乐家,他的创作遍及各种音乐题材。《见证》是他在去世前四年之内对音乐研究家伏尔科夫口授的。这些手稿被偷运到美国,每一章节上都有其亲笔签名。在这本回忆录的开篇这样写道:“关于往事,必须说真话,否者就什么也别说。追忆往事十分困难,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我不想在这些废墟上建造新的波将金村,我们要努力只讲真话”(伏尔科夫31)。
肖斯塔科维奇是个音乐家,音乐家思维有异于常人,就像酒神精神和苏格拉底精神的对立。相对巴赫的虔诚崇高,莫扎特的明媚风流,贝多芬的咆哮伟岸,马勒的忧郁敏感,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有着可怕的美。由于斯大林的残暴统治,肖斯塔科维奇一直生活在恐怖和悲剧的阴影中,“等候处决是折磨他一辈子的主题”(伏尔科夫241)。聆听他的音乐,细读该回忆录,我们看到的是多么似曾相识、触目惊心的场景,看到了阴霾笼罩下俄罗斯大地上人民的屈辱、痛苦和血泪。在那个强权时代,浸淫在漫长的黑夜中,不是肉体的毁灭就是灵魂的消亡。那种无法述说,无法呻吟,无法呐喊,无法哭泣,无法解脱,只有屈服顺从,压抑扭曲的生活折磨着肖斯塔科维奇。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强权政治系痛苦煎熬。《见证》所记录的就像黑暗中渐次远去的烛光,仿佛旗子无法言说旗杆,尽管在风中飘舞,却佯装自己是没有负担的破布。
1934年1月22日,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在列宁格勒的首演大获成功,并在之后的两年里盛演不衰。然而前苏联官方并不认同这部歌剧,以这部歌剧有太多不和谐音为理由展开了批判。斯大林最后以有伤风化且太过标榜利己主义下令禁演这部歌剧。肖斯塔科维奇顿时成了“人民的敌人”(伏尔科夫162)。虽然没有被捕,但随后的日子艰辛难熬。但当他从噩梦中醒来,却不再是一身冷汗而是立刻成熟。他的命运就像盾牌一样,似乎专门是为了对付打击而来。自这个事件后,每当受到官方的批判,肖斯塔科维奇便更加严厉地自我批评,把自己批得体无完肤。在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他的无奈:“左琴科有一个他深信不疑的理论:乞丐一成为乞丐就马上不发愁了,蟑螂并不因为自己是蟑螂而感到极为苦恼。我完全同意。日子总要过下去”(伏尔科夫163)。
其实,在肖斯塔科维奇受到这一事件冲击之前还创作了第四交响曲,由于当时苏联开展了轰轰烈烈且残酷的肃反运动,他意识到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便毅然撤回了正在排练的这首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有着忧伤的旋律,神经质的狂乱和悲剧性的结局,这些特点与马勒音乐精神极为相近。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内容会被戴上悲观色彩和颓废的帽子,问世便注定夭折。肖斯塔科维奇将之撤出无疑是明智之举。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五年禁锢,这部交响曲终于得以面世。我们只有了解第四交响曲的创作背景和内核,才能真正理解第五交响曲的动机,因为他们在根本上有很多共通之处。
之后的日子里,肖斯塔科维奇通过创作一些所谓恰如其分的作品而幸免于即将来临的官方清算。他的《第五交响曲》作为苏维埃共和国二十周年庆典节目在列宁格勒首演。当时苏联评论界反应十分强烈,将其第五定位为明快、光辉、欢欣、乐观、有生命力的优美音乐。肖斯塔科维奇终于因为这部交响曲重获当局的恩宠。
诞生于卫国战争中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使他的声誉达到了顶峰。斯大林将这一作品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1942年7月19号纽约举行了盛大的首演,继而世界上几千家电台转播了这场音乐会。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诠释可谓五花八门,但基本都归结到反法西斯几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上。但是在《见证》这本书里,作曲家本人却对伏尔科夫说:“《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伏尔科夫210)。肖斯塔科维奇所指的另一类敌人显然是斯大林的法西斯暴政,这一主题其实是暴政下牺牲的几百万人的追悼之歌。
可是好景不长,肖斯塔科维奇在1948年创作的第九交响曲又给他制造了祸端。这部作品被官方认为不够红也不够革命,肖斯塔科维奇再次没落。直到斯大林逝世,艺术解禁才给他带来一线生机。
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包括他的室内乐,尤其是他的十五部弦乐四重奏,所表达的深度与境界已经超过了乐圣贝多芬。如果说交响乐是对时代的回应,那么他的弦乐四重奏则是他内心的密语,与自己,与灰暗命运的交谈。而且在很多地方我们不必将之理解为神经质的语言,而是应该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将之理解为健朗强劲的怀疑。肖斯塔科维奇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与贝多芬大不相同:前者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集权统治,其生存状况极其险恶,不仅时刻面临这肉体上的死亡,更可怕的是还面临这精神上的死亡;后者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时期,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一理想的憧憬,如同号角激荡人们的心灵。相对肖斯塔科维奇,贝多芬的生存状况要宽松得多,除了疾病给他带来痛苦外,并无精神死亡的压抑。
何为精神死亡?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哀莫大于心死。翻开世界音乐史,我们不难发现,在音乐中对死亡问题的探寻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马勒,穆索尔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比较而言,马勒所探索的死亡属于宗教意义上的问题,即人死后能否进入天国;穆索尔斯基所探讨的死亡属于世俗意义上的问题,即战争、疾病和社会之不公正;而肖斯塔科维奇所探讨的死亡属于哲学意义上的问题,即人类所面临的比肉体死亡更为可怕的精神死亡。回到肖斯塔科维奇的《C大调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所表现的其实就是一个双重主体:纳粹德国的侵略战争导致了人们肉体上的死亡,古拉格集中营的摧残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死亡。作曲家自己在《见证》里给我们的答案是:“我是应为被大卫的《诗篇》深深打动而开始写《第七交响曲》的:这首交响曲表达了其他内容,但是《诗篇》是推动力。大卫对血有些精辟的议论,说上帝为血而报仇,上帝没有忘记受害者的呼声”(伏尔科夫242)。圣经之《诗篇》中犹太民族那种由悲到喜以及个人哀叹与民众挽歌之相互渗透,那种呼救,绝望和信念无疑在遭遇相同的作曲家心灵深处产生巨大震动。于是,我们在《第七交响曲》的慢乐章中听到了庄严和肃穆,在宣叙调中感受到了一种深切的悼念,体验到了从生命个体的忧怨到民族乃至人类悲怆。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肖斯塔科维奇去世时,《纽约时报》在讣告中这样写道“一位有时受到严厉的思想意识批判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伏尔科夫27)。也有西方舆论认为他和马雅可夫斯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依附在斯大林体制下的御用艺术家。还有人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有着非常复杂的个性,他有时候会撒谎,但是在音乐中,却是完全诚实的。
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肖斯塔科维奇可谓是一个异教。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共产党员,他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宗教情怀,表现在他所创作的音乐中,则到处弥漫着耶稣基督式的悲天悯人与灵魂的拷问。他的音乐是20世纪乌托邦悲剧的伟大见证。
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见证》,严琼芳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