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敦群培诗词思想管窥*
2023-11-30久迈
久 迈
根敦群培(1903—1951)是近现代西藏著名学者,他的人文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藏学的发展。在其坎坷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当中,除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几部文史论著之外,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诗词通俗优美、朴实无华,在西藏文学史上堪称佳作。1947年因“西藏革命党”事件,(1)关于“西藏革命党”事件,参见陈谦平的《西藏革命党与中国革命党关系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9—97页)、张晓红的《“西藏革命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等文。根敦群培被捕入狱,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查抄,致使许多作品在此期间散佚。1990年,根敦群培的弟子霍康·索朗边巴将其著作整理编纂成三册出版,(2)霍康·索郎边巴主编:《格敦群培著作》(藏文),第2册,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本文所用根敦群培诗词,均取自该文献,由笔者翻译成汉文,译文注重原意理解,表达上忽略韵文格式。集中收录了根敦群培的九首诗与十组杂诗,其他著作中也有一些即兴的诗偈,这些大概反映出根敦群培诗词的全貌。
关于根敦群培诗词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有所涉猎。在国内,夏吾才让早先关注根敦群培诗词,认为其诗词含有爱国主义、宗教批判、自由主义、女权思想等;(3)夏吾才让:《根敦群培与其诗词研究》,交巴李加主编:《根敦群培研究》(藏文),第1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20页。后继相关论述多承此说,并以之印证根敦群培的人文精神。在国外,唐纳德·小洛培兹收集、整理、英译根敦群培诗词作品,编著《消失在林中的智慧—根敦群培的104首诗》,导论中对诗词创作来源和内容特点作了简要解读,认为“他的大多数韵文都具有自传的特征”。(4)唐纳德·小洛培兹:《根敦群培诗词研究》,杜永彬译,《中国藏学》2012年第S2期,第47—57页。综合这些观点,从具体的思想特点归纳整体的思想特质,从静态的思想表现中演绎动态的思想变化,则可以发现诗词是深入研究根敦群培思想的关键。根敦群培的诗词富含哲理,隐现个人的社会观念,将那些零散的诗文贯穿到他的人生历程当中,则可窥测他从一名藏传佛教学僧嬗变为一名西藏人文学者的思想历程。
一、佛教出世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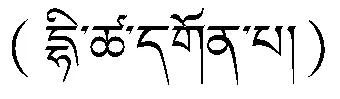
嘎曲以上至那曲以下,虽然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人,只要仔细想想,我们学问僧才是最值得自豪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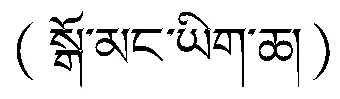
当我去了外地以后,有些百般无聊的阿喀,说我也是因为狂妄自大,终被乃琼护法驱逐。
如果是位正直的护法,怎么可能会让那些,去往各地经商茶酒与肉,如此胡作非为者留住。
卷起贝叶似的法裙,手执刀剑棍棒等器具,本该驱逐这些人,而现在却越来越多。
又说既然无半点信仰,就将此人驱赶到别处,那么为何不驱逐那些,不净生命鸟虫等畜牲。
威武的乃琼护法神,怎么可能会驱逐那些,历经艰苦与磨难,闻求佛法的人们?
或衣冠楚楚的毁法者,或衣食简朴的毁法者,我等看来虽然不相同,佛陀看来并无区别。
那么与其驱逐那些,闻知因明的佼佼者,则不如驱逐那些,经商酒肉的狂妄者。
是否如此自己细考虑,问问那些阿喀格西们,如此言者是我学问僧,智慧之狮根敦群培者。
拉卜楞僧人指责根敦群培狂妄自大,这一点确实有迹可寻。1921年根敦群培离开底擦寺时,就声称像小湖一样的底擦寺已经容不下他这条渴望在大海中畅游的大鱼了。仅此一斑足见他的确是一位个性张扬之人。人们常说,行为决定习惯,性格决定命运。根敦群培这种随性率真的行为方式与桀骜不驯的性格特点,一方面成就了他以后与众不同的思想特点,另一方面也注定了其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生。
从以上回信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拉卜楞寺院中,不但有像根敦群培一样潜心追求佛法的学问僧,也有披着袈裟四处经商务世的“世俗僧”,且这种“世俗僧”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根敦群培反对这种面似求出世,而实际上完全入世的行为,痛斥他们才是真正的毁法者,扬言应该逐出寺院。宗教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然需要经济的基础支撑。拉卜楞寺默许僧人的经商等行为,并未明确反对僧人的世俗活动,客观上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如果僧侣没有坚定的宗教信念,则这种“合理性”就会导致价值偏离,促使世俗追求融入宗教生活,反而使宗教成为世俗价值的附庸。
从以上回信中记载的“世俗僧”增多趋势,反映出这种现象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因此,根敦群培坚持佛教的出世价值,认为出家为僧便意味着放弃世俗追求,不应从事逐利之事。他蔑视那些忙于经商务世的僧人,言语间表现出对他们的轻慢与不屑。另有一首嵌字诗《阿却的历史》中,根敦群培更是用辛辣、嘲讽的语言批判那些打着宗教行善的幌子,专为自己敛财的世俗僧。
在富丽堂皇的房屋中央,摆上丰富各样的美味佳肴,应邀而来享用随唱诵一首,感叹谁人比我阿却更加幸福!远离喧嚣诵经修善的同时,安然坐在熟悉的供养者家中,悉数索取上好的衣食用品,有谁堪比渔夫般的阿却们?背负行囊奔走于各个地方,也很难挣得一个铜子儿,如今看这得到的牛羊财富,有谁比我阿却更加厉害?
明朝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中说:“有在家出家者,有出家在家者,有在家在家者,有出家出家者。处于族舍,具有父母妻子,而心恒在道,不染尘世者,在家出家者也;处于伽蓝(即寺庙),无父母妻子之累,而营营名利,无异俗人者,出家在家者也;处于俗舍,终身缠缚,无一念解脱者,在家在家者也;处于伽蓝,终身精进,无一念退堕者,出家出家者也。故古人有身心出家四句,意正如此。虽然出家出家者,上士也无论诶。与其为出家在家者,宁为在家在家者!何以故?袈裟下失人身,下者又下者也!”。(10)陈耳东、陈笑呐、陈英呐编著:《佛教文化的关键词——汉传佛教常用词语解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2页。可见,身在佛门而心在尘世,以出世之身行入世之事,这是佛家最为不齿的行为。世俗价值不能融入佛教真理——这个观念贯穿了根敦群培的一生,也成了其人文思想产生的基础。
1927年,根敦群培离开拉卜楞寺,前往西藏拉萨哲蚌寺求学。无独有偶,也是因为质疑贡乾教材中的佛学观点,他与寺内僧人产生分歧,还曾遭到蒙古僧人的殴打。(11)霍康·索郎边巴:《更敦群培大师传·清净显相》,交巴李加主编:《更敦群培研究》(藏文),第1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5页。有学者认为这是根敦群培后来离开哲蚌寺的原因,笔者对之并不苟同。根敦群培才华出众,对佛教因明学运用自如,在佛学辩论中所向无敌,堪称是哲蚌寺最有前途的学问僧。但是,在临近格西答辩前期,他接受了印度学者罗睺罗的邀请,前往印度等地学习考察。对此,根敦群培说:“佛陀的教义已经领会,对此不加以舍求修行,而去追逐格西的虚名又有何用?于是我放弃了拉然巴学位答辩”。(12)甘伯·喜绕嘉措:《更敦群培传略》,交巴李加主编:《更敦群培研究》(藏文),第1辑,第6页。当时在西藏格鲁派三大寺院中,考取格西学位已然成为僧人求取功名的重要途径。显然,根敦群培看到学问僧的这种世俗目的之后,断然放弃了格西答辩的机会。这与此前离开拉卜楞寺一样,他坚持佛教出世价值,绝不迁就世俗观念介入其中。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拉卜楞寺求学期间,根敦群培作为一名学问僧感到自豪,并以此蔑视那些“世俗僧”的务世行为。而此时在哲蚌寺,看到学问僧同样有其世俗目的之后,他对于当下的佛法实践失去信心。根敦群培在斯里兰卡游学期间的一首诗中,表达了自己摆脱这种宗教藩篱的深切愿望。(13)又说这是根敦群培回归宁玛派的标志,这一点还需商榷。
……
将向往高位的基体让火焚烧,把讨厌的僧影扔进灰坑,身随所想就像疯子一般,要是能得到流浪的宽容。将因明三支城墙彻底损毁,让八边宗见的心结自行解去,所有现象以为是无基离根,要是从心底能得到自由快乐。
在政教合一的西藏社会中,僧人的宗教追求与世俗追求趋向统一,或陷于佛教信仰的很多僧人并不能感到佛教的这种畸变,而根敦群培认为这种追名逐利的行为完全是对佛法的亵渎。从底擦寺到拉卜楞寺,再到哲蚌寺,在西藏的整个求学生涯中,根敦群培以身作则维护佛教的出世价值,他的举止行为看似“离经叛道”,实是为藏传佛教“正本清源”,因为“出世”才是佛教的“初心”。
二、社会思想发端
根敦群培32岁时,应印度学者罗睺罗邀请出游印度等地,前后两次返藏进行考察,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他对西藏宗教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1936年10月,他在《明镜》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俗语嵌字诗》的诗,其思想变化从中可见一斑:
加尔各答、尼泊尔、北京,抑或是雪域圣城拉萨,这些各方各地的人们,在我看来本性其实都一样。不喜欢喧嚣嘈杂的环境,举止显得谦逊大方,每当看见金钱财富,都与渔夫的心别无二致。大人贵族喜欢别人奉承,平常人喜欢狡诈欺弄,现代人喜欢吸烟喝酒,年轻人喜欢性感漂亮。热爱自己的祖先亲人,痛恨与己不同的外族,犹如牛一般的我们人类,心灵之根怎会如此相似。去杂日朝圣是为了填饱肚子,不畏寒暑努力是为了争得名气,念诵释迦经典是为了收取工费,总而言之都是为了金钱财富。法帽、袈裟、经幡抑或华盖,各类食品供祭与法会,我们所做的一切及一切,除了奇特的演出外别无所见。就像进入牛羊的牢圈,无论何地都无幸福可言,直至这血肉之躯消亡,不得不在这个世间留住。直言不讳便是如此,哎呀唯恐别人又会发怒。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此时根敦群培已经彻底从宗教的身份藩篱中走出来,开始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西藏宗教的社会性质。他发现,西藏现有的佛教信仰具有强烈的世俗目的,其功利性质与正统佛教价值相去甚远,人们的行为“总而言之都是为了金钱财富”。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佛教信仰深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佛教已经畸变为经济运行的载体,也在信仰的掩盖下成为很多人谋取利益的手段。因而,根敦群培从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揭露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的虚伪性。“我们所做的一切及一切,除了奇特的演出外别无所见”。这种针对宗教的社会批判意识,为其人文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础。
根敦群培在印度游学时,正值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高涨时期,反对殖民主义的社会思潮深深感染了他。在此期间,他将代表传统印度精神的文学作品《沙恭达罗》《罗摩衍那》《薄伽梵歌》等翻译成藏文,并以诗词谴责英国的殖民统治:
食肉的狼和食草的兔子,与其在一起商议吃喝问题,不如暂时待在自己的同类中,保持各自的行为为善。让那些牧民吃猪肉,让那些农民喝酥油,若不喜欢就不要强迫,若喜欢就不能强行阻止。
当时的英国殖民者野心勃勃,他们在占据印度的同时,还伸手干预西藏地方事务,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对英国人的这种行为,根敦群培更是深恶痛绝,他以诗文警告西藏地方上层:
在洁白无瑕的布幕之上,用电光展现各类景象,虚幻女王的哭笑之影,为三界众生尽现演出。虽然没有利他的慈悲之心,但善于运用科学之幻影,将正直的人指向歪道,请当心那些黄发猴人。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之际,根敦群培“醉心于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思想,从而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在西藏进行一次重大改革乃至发动一场革命”。(14)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466页。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认为根敦群培加入了西藏革命党,并认为他是西藏革命党的第四位成员。1945年,邦达·绕嘎让根敦群培经由不丹和达旺到西藏去朝圣,他化装成一名朝圣的僧人乞丐,但实际上是去绘制西藏尤其是藏族人居住的北部地区的地图。(15)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第466页。根敦群培是否加入了西藏革命党,因为没有直接的考证材料,学者们观点不尽相同。但说他加入了西藏革命者的行列,这是不争的事实。
经过多元文明的洗礼与世界范围内革命思潮的影响,根敦群培终于从一个佛教学僧蜕变成一位人文学者。他明确意识到,若是在西藏进行社会变革,首先必须要对思想领域进行革命。他在另一首诗中这样批判西藏社会:
……
将一切藏于内心自诩深沉,以为怀疑一切便是智慧聪明,将所有陈旧看成是神的惯例,将所有新颖视为魔鬼幻现,所有的新奇以为是恶的先兆,这是佛教之地吐蕃的习俗,也是传至今天我们的习惯。
根敦群培认为西藏社会之所以如此落后,主要是因为宗教思想的长期禁锢。下层民众对神的信仰根深蒂固,社会上的迷信色彩异常浓烈;上层唯恐危害到佛教统治利益,拒绝异质文化输入传播。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们的思想显得极为迂腐,没有一丝推陈出新的观念。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社会,统治者的意志必然异化为神的意志,而神的意志自然也会成为统治者的意志。毫无疑问,当西藏社会遭遇变革的历史契机时,所有的矛头也必然指向政教合一制度以及相应的思想领域。
三、人文主义滥觞
根敦群培对政教合一制度的西藏社会深有感触,他认为赤松德赞建立的是一个世俗政权,“采用的是法王阿育王(Dharmaraja Asoka)的佛教思想。现在,在西藏,我们已把佛法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这就产生了问题,假如我们把糖和盐混合在一起,那怎么能食用呢?”(16)杜永彬:《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332页。。根敦群培从佛教学僧嬗变为人文学者,先从历史思想领域解构西藏社会。1945年,根敦群培从南亚回到西藏后,专心从事《白史》撰写工作,他在《白史》补遗中赋有一偈,体现了自己的史书与以往史书之间的不同:
不以偏见沦为“红”,不以献媚变为“青”,不以后言沦为“黄”,因此这便是“白史”。
西藏史书,有用颜色来做书名的传统。以上所谓“红”约指蔡巴·贡噶多吉所著《红史》,书中引用汉文史料较多,汉藏关系记述较详(后有班钦·索南扎巴的修订本《新红史》);所谓“青”约指郭译师·循奴贝所著《青史》,书中对格鲁派以前的藏传佛教流派及密法传承记载较为翔实。根敦群培认为这些史书有“偏见”、“献媚”之嫌,一是指在史料上偏向于汉籍,二是指史书完全为宗教服务。而后来的史书多又以格鲁宗派源流为重,亦有“黄(格鲁派)”的偏颇。所以,根敦群培立志要破除这些因素,以不染之“白”的原则去撰写他的史书。他在导论中说:“这里所要叙述的主题是有关赞普父子治世的诸多历史,以及如何运用武力进行统治和领土扩张的情形。至于赞普和王后不同寻常的传记,以及如何弘扬佛法的业绩,已为众所共知,于此不再赘述。”(17)更敦群培:《更敦群培文集精要》,格桑曲批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概言之,根敦群培要撰写的是吐蕃时期政治历史,他力求摆脱宗教和神话传说类的影响,表现出人文主义史观。
恩格斯说:“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44页。当根敦群培从佛教学僧嬗变为人文学者后,又从宗教思想领域解构西藏社会。根敦群培在一首偈语中说:
疯癫的思维不知道自己的面目,居然去度量天地政教的大小,竟把时常所见的虚妄现象,当成是一生皈依的人们。
人类的认识都是虚妄不实的,但是人类思维本身并不清楚这一点,总是将自己的认识当成是真理的来源。若以此作为进入佛法的基础和途径,则如同丈量天地之间的距离,不但不可能,结果必然是将世俗现象当成皈依的对象。根敦群培通过这种“异端”理论表达其佛学思想,他在《中观精要论》中批判格鲁派“名言量”学说,其中有二十一首偈语,总概全部思想观点。笔者选取其中三偈分析:
宗喀巴大师说,在承许万法无自性的前提下可以抉择世俗认识为“量”,以此推求“缘起”证得“性空”,此即“名言量”学说。根敦群培以为世俗认识并不能成为胜义佛教的“量”。他说:
有无依心说知识,真假缘境言正量,既是彼此相立存,名言量成无以信。
所有的知识都是人类认识的反映,但问有、无等认识是否准确,是否为量(真理),则又由认识的对象(境)来决定。这就好比雪是白色的,是人类的眼识所见,但说眼识是否为“量”,又要看它认识的雪是不是白色来确定。如此,能量和所量之间相待而立,原本无以为“量”。而以这种逻辑去论证“性空”,则就像用白色去证明眼识为“量”一样,因为“自性”本身并不存在(无自性是前提),所以“实执”(执自性有)是不正确的认识,是“非量”(非真理)。反过来说,因为“实执”非“量”,他所认识的对象“自性”自然为“无”,是不存在的。根敦群培认为“名言量”在逻辑上存在谬误。
“名言量”学说认可世俗认识有“正量”,但否定其中“实有”认识。根敦群培举例批判说:
敌人真有是实执,敌人相害为正量,俱可生恨无分别,名言量成无以信。
根据“名言量”思路,“实执”是无明增益的结果,其对境根本不存在。如果将敌人执为“真有、实有(自性有)”,这种“实执”也没有对境可言,所以是“非量”。但是,又认为伤害者敌人是存在的,是“有”,因为自己确有被伤害的结果,这是“正量”。根敦群培说,无论是执敌人为“自性有”,还是执敌人为“有”,对于遇害者来说都会产生恨意。用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则“实执”和“量”在这里趋于一处,很难分清彼此了。宗喀巴大师说:“故自寻求时,境上有性,正理能破,非破其有。说诸正理惟为寻求自性为胜,故彼正理,是为寻求自性有无。说正理破,亦是破除自性之义,故当分辨彼二差别。”(19)宗喀巴:《宗喀巴大师集》第1卷,法尊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419页。如此对“自性有”与“有”做了区分后,又说未入胜义道者难以分辨“有”与“自性有”的区别。那么,就只能认可世俗认知中“量”与“自性”很难区分。
对于“名言量”的批判,根敦群培更有一段精辟的偈语:
所有能用有益识,分类置之为正量,犹如海市隐去后,大漠又见蜃楼起。
说为了论证“自性”不存在,重新捡起世俗关于“有”或“无”的观念,以此建立“名言量”,这就像努力把一种虚幻的景象否定之后,又重新构筑起一道虚幻的景象。那么,中观思想依然没能跳出世俗观念,依然在有和无的认识中徘徊。宗教学家威尔逊说:“宗教立足于超越世俗的愿望,一切宗教信仰都要求人们达到一种被称为‘信仰的飞跃’的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有一个需要突破的临界点。虽然有人企望实现这种‘信仰的飞跃’,但却难于突破这个临界点,因为他们缺少那种欲罢不能的动力,因此,只能始终在经验范围内徘徊。”。(20)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梁鸿飞、王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根敦群培认为,既然中观思想建立在名言量之上,那么也就只能在世俗思想内迂回,根本无法进入法界一步。“总之,我们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无论胜义、世俗都非要能够说清楚、想明白,尤其要说清楚为止,这样,一旦获得与其相应的理论,就自以为结合正理和教理找到了终极真理,其实是‘喜酒者得酒,喜肉者得肉’,只是获得了与自己的意愿相合的理论而已,怎么会是得到了佛菩萨的境地呢?”。(21)霍康·索郎边巴主编:《格敦群培著作》(藏文),第2册,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所以,越是相信世俗的正理,就越是无法得到出世的意义。正如庄子所说“有涯待无涯,殆也。”人的经验理性不能成为追求超越性宗教的基础。
纵观根敦群培一生的思想历程,可以发现他的人文精神是“宗教”与“社会”两个维度展开的结果。从宗教角度来看,根敦群培恪守不求名利的“日绰巴”精神,始终以身作则维护佛教的出世价值。在《中观精要论》中根敦群培批判“名言量”学说,否定世俗认识成为胜义认识的“量”,将人的理性限定在经验认识之中,让宗教回归超越性信仰——这种宗教对于世俗的扬弃为人文精神提供了发生空间。从社会维度看,根敦群培自南亚游学后,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他的人文意识不断被激起,他以旁观者的角度反思西藏社会,认为宗教是西藏社会发展的最大羁绊,并经过西藏革命党投入西藏的改革实践。在《白史》中根敦群培将宗教等神秘因素从历史叙事中剔除,通过自己的史观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通过两个维度的观察,隐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之意趣,或许这就是根敦群培人文思想的最后归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