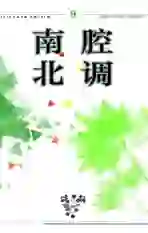张一弓:时代变迁中的 “变”与“不变”
2023-10-12刘宏志
刘宏志
20世纪80年代初,张一弓凭借他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强势登上文坛。之后,他又创作《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嘎斯》《黑娃照相》等一系列小说,连续获得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可以说,张一弓刚登上文坛,便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很快他便沉寂下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虽然也发表过几部中短篇小说,但是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一直到21世纪,他出版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重新宣告当初那个优秀作家的归来。不过,《远去的驿站》这部小说在写作手法、表达内容等方面,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一弓那些引起重大反响的小说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如果我们把张一弓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作为他创作的开端,把他的《远去的驿站》作为他创作的结尾的话,可以发现,在这时代的变迁中,张一弓的创作有他一开始的坚守,也有最后的超越。今天,我们在这个拉长的时空中重新审视张一弓创作的历程,审视张一弓创作中的“变”与“不变”,或许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家创作与时代的关系。

一、时代变迁与张一弓的求“变”
新时期伊始,张一弓凭借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一系列直击社会问题、书写当下社会现实的小说冲上文坛,并且迅速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但是,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等待着‘文革’后主流文学作家的,并非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通衢。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历史的转折,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探索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双重挑战,不得不在革命传统和历史失误、文学创新和流行时尚、大众需求和审美惰性之间作出审慎的分辨和艰难的选择。” [1]具体来说,张一弓是在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浪潮中一举成名的,他的写作立场、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内容等,都非常符合第一个文学浪潮的要求,这也迅速把他推向当时文学的潮头。但是,文学的变革是迅速而猝不及防的,随着新时期第二个文学浪潮——“八五”文学新潮的到来,张一弓被突然出现的文坛新秀挤出文坛中心。这当然也意味着,张一弓遇到巨大的艺术挑战——他所习惯的艺术创作方式似乎突然落伍了,而改变自己的艺术创作方式,则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自己遭遇的困境,张一弓很早就意识到了,并且也开始认真思考,并试图作出改变。“他在认真地思索,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自己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苦恼中思索,在思索中苦恼。‘我的写法是否过时了?是否文学召唤了我又抛弃了我?是否时代变化太快,不再需要我为它呐喊了?’他又在怀疑和否定自己了。”[2]站在历史的高度,反观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的变革,我们会发现这里的确有明显的时代变革的影响。新时期伊始,旧问题亟需清算,新现象亟需关注,社会百废待兴,社会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个时候,实现社会变革的需求是压倒性的需求,社会上各个艺术门类都需要为这个问题服务。而且,文学艺术为社会变革服务不是某一个机构硬性的命令,而是社会全体民众自发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篇小说可以引起社会轰动的原因。张一弓的小说,聚焦社会问题,急切地表达着作家对过去问题的批判,对新生活的向往,表达着作家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分析,这种书写,正好切中时代的脉搏,所以,那个勇于承担、富有英雄主义气息的“犯人”李铜钟才能引发全国众多读者的共鸣。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也要慢慢地归位于文学本身,社会对小说的社会性的要求逐渐弱化,而对小说的艺术性的要求则不断上升,这也就导致张一弓的创作在不知不觉中偏离时代的中心。简言之,张一弓没有变,但是时代发生变化了,于是,张一弓就落伍于时代了。要想赶上时代,张一弓必须对自己的创作作出必要的调整。
张一弓的创作历程,就是他不断求变的过程。张一弓作出的第一个调整是创作导向和叙事话语的转变。为什么写小说?对于张一弓来说,这原本并不是一个问题。他一开始就非常清晰地确定自己写作小说的动机,那就是为社会服务。 他曾这样说:“我不是说,我在每一篇习作中都要表现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塑造出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但在我的创作指导思想和总的倾向上,我将尽力掌握生活中的美、丑对立及其在斗争中互相消长的辩证法。”[3]从张一弓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一弓明确地把自己的写作和社会需要勾连起来,即自己的写作,就是为了表达社会重大现实。所以,对于他來说,把握好社会重大的矛盾冲突,并且有正确的立场,就是写好作品的首要前提。而且,对于创作中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关系,张一弓也作出自己的选择,他说:“生活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一定要对文学从属于什么的问题作出毫不含糊的回答,那么,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文学从属于生活。这儿所说的生活,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4]从张一弓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是他对文学的社会价值关注超过对其审美价值的关注,二是他对表现社会生活和群体命运的兴趣超过对于表现个体心灵的兴趣。”[5]对于所要表达的重大社会问题,张一弓也有一个集中的关注,那就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他对于表达农民问题,有强烈的使命感:“我从16岁就开始思考‘三农’问题……我要为改变当代农民的命运而呐喊。”[6]正因为有如此清晰而鲜明的立场,张一弓对自己的创作表达什么,要呈现时代的什么,也有着清晰的把握:“我总在提醒自己:要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我国农村作一些忠实的‘记录’。如果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记录我对我国农民一段严酷的历史命运的痛苦思考,那么,《赵镢头的遗嘱》则试图记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民表现出来的充满智慧和勇敢的历史主动性,他们对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道路的发现,以及他们为了肯定自己的发现而进行的斗争;《张铁匠的罗曼史》《寻找》《瓜园里的风波》则是农民刚刚赢得一个新的历史命运,而又负载着旧有的历史忧伤的亦喜亦惧的心理状态的纪实;《黑娃照相》仅仅是一个即兴的‘人物速写’,写下了‘过去他身上留下的穷乏所形成的心理的和外表的印痕与被生活唤醒的对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对美好未来的确信;《流泪的红蜡烛》是迅速变动着的农村现实生活传递给我的一个使我喜悦而惆怅的新的讯息,这是一幅富裕和愚昧掺杂一起的色彩极不协调的图画,它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物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而精神生活依然‘贫困’的矛盾……我还应当提一提《最后一票》,这个短篇是从政治生活的角度,记录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被唤醒的、此后都被遗忘了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激发出来的民主要求的第一声呐喊。”[7]一个作家,对自己的小说分别表现哪些问题,回应哪些社会关切,认知如此明确而肯定。这就说明,此时的作家张一弓,其实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的认知者,是一个自觉把回应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指向的写作者,更带有社会科学家的气质。而且,从张一弓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张一弓是以问题小说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书写,也确实是把自己当作时代的秘书:“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当我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后,才不无惶恐地意识到,我是在力不从心地做着这样的秘书工作了。”[8]
张一弓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秘书,关注时代重大问题,关注时代变革中的重大事件,由于他很早就从事农村报道工作,对农民又有着特别的关注和情感,决心为改变农民的命运而呐喊,所以,他对时代的重大关注又集中到农民、农村问题上。以上可以说是对张一弓早期创作的一个简单归纳。我们也可以看到,新时期伊始,由于国家、社会层面对极左年代清算的需求,以及农村改革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张一弓的这些基本创作指向与其对应的叙事话语就正好与时代精神相契合,这也让他站在时代的潮头。但是,随着“八五”文学新潮的到来,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对文学内涵的政治要求在减弱,对其艺术创新的要求在提高,对文学的社会价值的要求在减弱,对其文学价值的要求在提高。这样,在新的时期,这些原本带给张一弓文学荣耀的叙事指向,就反过来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一弓就开始自己艰难的文学转型之路,他先后发表《死吻》《都市里的牧羊人》《夜惊》《孤猎》《黑蝴蝶》《都市里的野美人》等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和之前的叙事有着明显的区别。事实上,对于张一弓来说,此时叙事的转型,不仅仅是叙事指向的改变,还包括叙事话语的转变。他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发表的小说,采用的是“政治—社会”话语,小说围绕社会热点事件进行。但是在“八五”文学新潮之后,文坛流行的是寻根文学,是现代派小说,是先锋小说,这些小说的叙事话语都明显脱离既往的“政治—社会”话语范畴。所以,对于张一弓来说,小说叙事的转变,同时包含创作导向和叙事话语的转变,这显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张一弓所遭遇的问题,也是当时他那一代作家所遭遇的普遍性问题,这些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功完成话语转型的,并不多见。对于自己的创作困境,以及自己面临的问题,张一弓有着清晰的认知,所以,在进行新的艺术探索的时候,他才会说自己“如同一个胎位不正的产妇,正经历着难产的折腾”[9]。的确,张一弓在当时经历难产的折腾,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直到21世纪开始,张一弓也就创作上述有限的几篇中短篇小说而已。但是,经历《死吻》《孤猎》《夜惊》等小说的不是非常成功的叙事探索之后,我们发现,张一弓创作的《远去的驿站》,已经成功地脱离原来习惯的“政治—社会”话语范式,以对生命的关注切入历史之中,去书写个体生命在历史风云中的沉浮。小说更加关注的是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普通的个体生命,表达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这和张一弓早期强调关注、书写社会重大政治事件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
张一弓小说叙事的第二个变化是对小说叙事方式作出调整。张一弓早期的小说颇受欢迎,和张一弓小说的叙事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有论者分析张一弓早期写作的特点:“他对生活中不同寻常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敏感和兴趣,善于抓住它们作深入开掘、提炼为起伏多变的戏剧性情节……构成张一弓小说戏剧性情节的矛盾冲突,常常是十分尖锐的。他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他的作品往往一开篇就进入何去何从的抉择关头,并且很快让矛盾激化,使他的人物在生死攸关、成败安危在此一举的严重时刻表现出精神上的强有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从而唤起读者的正义感和崇高感。”[10]这种书写方式让张一弓的小说带有很强烈的戏剧化色彩,也能在短时间内引发读者的崇高感,从而对读者产生情感的影响,但是这种书写也有自己的硬伤,即可能会为了戏剧化效果的需要,影响人物塑造的合理性,从而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之前很多文章都分析过的赵镢头之死这样一个情节安排。作家为了安排小说情节的高潮,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在小说中为赵镢头安排的结局是最后自杀。但是赵镢头并没有必死的理由,所以这个情节并不合理。这样的处理,显然影响对赵镢头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另外,这种对戏剧化高潮场面建构的强调,也决定张一弓的小说都会采用一个封闭的叙事结构,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结构中,围绕一个核心的矛盾进行不断渲染,才能够建构出戏剧情节的高潮。但是,这也同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即表达内容会受到叙事结构的限制,作家无法在小说中呈现更为丰富、驳杂的东西。对于自己创作艺术上存在的问题,张一弓也非常清楚,他在谈及自己小说的时候,一方面强调情节对他小说的作用:“内容决定形式。我的小说反映在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生活,从而要求我在小说中把批判精神与高昂理想结合起来,这使我不敢小视情节的作用。” [11]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对特异事件和对外部情节结构的偏爱,也无疑是我习作中的一个局限。它不仅限制我在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里选取素材的可能性,而且不能使我对人物的心理状态作出直接的透视,揭示人物内心的真实,这就损害人物的丰满型和生动性。因此,在《黑娃照相》《寻找》等习作中……吸收西方小说中心理结构的方法,以打破这种局限……我也没有勇气离开外部的情节结构……”[12]从张一弓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明显意识到自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这其实也是张一弓之后陷入长期的困惑和难产的原因所在。不过,我们从他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可以看到,小说艺术上存在的上述问题显然都得到有效的解决。在这部小说中,张一弓不再追求情节戏剧化,而是煞费苦心设计一个散文化结构,从而完成对更为广阔的叙事内容的包蕴。张一弓说:“最大的挑战就是长篇小说用散文的结构。我所要写的三个主要人物父亲、舅父、姨夫的生活原型,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纠葛的……我又遇到新的问题,就是必须用虚构的故事把本来无纠葛的三个人物纠葛起来……后来才想到,干脆不要这个撑起一部长篇的故事框架,就靠第一人称的作者用自己的回忆,而且用他童年和老年的两个视角来贯穿,这就是现在的散文化结构。”[13]《远去的驿站》的这个结构安排,让作家可以相对自由地在情节主线中安排进更多的情节,从而涵盖更为丰富、驳杂的生活,这是张一弓对他过去小说结构的一次有效突破。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完成从紧密围绕情节构建一个封闭的故事到打破封闭叙事结构这样一个叙事变化的,不仅仅是张一弓一个人。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叙事,基本是遵循之前的经典现实主义叙事方法,强调在一个封闭的叙事空间内完成对一个完整事件的叙述。但是,后来的现代主义等叙事方法开始对小说叙事产生巨大影响,作家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恪守一个封闭的叙事空间会直接影响小说表达的广度和深度,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很多作家都已经逐渐抛弃传统的封闭物理空间叙事。当然,这种转型对于张一弓来说更为艰难,因為他之前小说的所有的成功经验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封闭叙事空间的建构上,而他在21世纪伊始的《远去的驿站》的成功,也证明张一弓艰难转型的成功。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张一弓的写作有着强烈的理性色彩,他用他的理性来捕捉对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并将之结构成小说。他的敏感,他的理性,以及他社会价值优先的文学立场,在新时期之初是他小说的优势,这个优势也成就那个以反思文学而蜚声文坛的张一弓。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曾经的优势反而变成他小说创作的劣势,成为阻碍他前进的障碍,张一弓在艰难跋涉中,终于超越这些局限,并最终成就新的自己。
二、求索中的坚守
张一弓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人,虽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张一弓并没有停止在艺术的道路上精益求精。有论者曾经指出张一弓早期小说变化的过程:“张一弓创作的这种融汇倾向是渐次自觉发展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政治思想上的开拓精神与艺术手法的循规蹈矩所造成的不协调,便是初期创作这种不自觉的标志;之后的《春妞》《流星》则显示作家在艺术融汇上的长足进步……张一弓感知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式在悄悄发生变化。由单线条的自然主义的感知方式和叙述方式,逐渐走向立体的经验结构和叙述结构。”[14]如果说在早期,张一弓小说叙事的变化还是在既往的“政治—社会”话语范畴内在一些具体叙事手法上进行调整的话,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一弓创作的《夜惊》《孤猎》等小说,则完全脱离“政治—社会”话语范畴,以一种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去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认知。所以,纵观张一弓的创作史,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它就是张一弓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不过,张一弓的小说书写,也一直坚守一些基本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质是张一弓前期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远去的驿站》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张一弓的小说始终保持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情怀,这是张一弓小说的重要特质,也是他的小说总能带给人感动的重要原因所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这并不妨碍批评家们不断指出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诸多缺失。至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之后的作品,更是不断被批评家指摘。如有人认为,张一弓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够鲜明,“继‘李铜钟’之后,逐渐忽视了人,忽视了有性格的人的塑造”[15],甚至认为连《张铁匠的罗曼史》《赵镢头的遗嘱》这样的小说,人物也是有问题的,“活动在这里的人物一个个仿佛是提线木偶,任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16]。也有人指出,张一弓小说中的人物,“人物思想与性格的基调十分鲜明和强烈,然而却缺乏应有的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人物有足够的力度却缺乏丰富的内涵和精微的分寸感。”[17]应该说,这些分析都有合理之处,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张一弓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这并不影响张一弓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带给读者巨大的感动。无论是李铜钟,还是赵镢头、张铁匠、高山兰、郭亮、春妞,这些人物都有着引发读者感动的巨大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家成功地把自己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情怀嫁接到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从而引发读者的感动。李铜钟勇于承担责任,宁愿冒着入狱的风险也要打开国库,取粮食给乡亲们的行为是英雄行为;赵镢头以死明志,用自己的生命为乡亲们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呼喊是英雄行为;张铁匠不向命运屈服,不屈不挠地寻找自己的妻子,春妞儿拒绝命运的安排,冒着流言蜚语和各种困难坚持学开车走出自己的新的道路,同样也带有英雄主义的气息。或许这些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在自己的选择中一往无前地努力,毫不犹豫地坚守,无所畏惧地承担,都有着典型的英雄主义气息,能够带给读者感动。这也是张一弓小说虽然被诟病有概念化倾向、过于理性化,但是依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的原因所在。
成名之后的张一弓虽然在努力寻找自己写作的新的道路,但是,这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情怀,却始终在他的作品中存在。他在转型期创作的中篇小说《孤猎》表现英雄的困惑,《夜惊》则暗示着对一个民族英雄意识退化的悲哀。他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虽然只是回忆历史中的一些普通人物,但是,这些普通人物身上其实也都带有英雄主义的气息。在小说重点叙述的几个人物中,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也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他却一直在执着地寻找流失在民间的古典乐曲。他的行为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在报上公开谴责:“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是他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选择。父亲或许是一个普通人,在全民抗日战争时期,他也没有成为一个抗日的英雄,但是他对自己选择的事业的坚守,显然也让他具有英雄主义的气息。小说中的大舅孟诚,虽然是一个国民党员,但是又并不完全遵守国民党纪律,同时,他也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同时也并不为任何政治集团所喜欢。最终,他虽然为革命、为抗日战争付出很多,却也被自己信任的同志暗杀于乱草丛中。这个人物,也不是传统的英雄形象,还带有几分自由主义的色彩,但是他的精神,的确也有英雄主义的气息。姨夫贺胜则是主动参加革命,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出生入死,小说还着重叙述姨夫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传奇经历。姨夫贺胜为了理想积极参加革命,并且为了革命出生入死,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行为上,显然都符合英雄的要求。上述这三个人物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对自己选择的道路的坚守,在国家危亡之际勇于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都让他们具有英雄主义的气息。另外,小说中的薛姨、王疯子等人物,也都带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气息。小说人物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气息,给这部小说增加浪漫主义的因子,带给小说动人的力量。
张一弓小说中另外一个始终保有的特质是对社会、历史旋涡中个体生命的关注,是他积极入世的忧国忧民的创作立场。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张一弓继承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关心普通民众命运的人道主义传统……对于张一弓来说,文学不只是一种审美创造,而且是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他的社会政治热情通过另一个突破口的宣泄和迸发。所以,张一弓常常‘心甘情愿地写一些可能速朽的文学’,甚至宁可把自己的一些作品称作‘一个驻队干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记录’。”[18]张一弓的这种文学立场在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中被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关于李铜钟的书写,关于赵镢头、黑娃、春妮儿的书写,固然有为这个社会的某种问题或者某种新动向发言的指向,是他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方式,但是,毋庸置疑,这些人物的塑造也表明作家对社会变革中这些独特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和认同。这种书写是指向历史、社会中的个体生命,对之进行关怀的人道主义立场的表现。张一弓的这个书写立场在“八五”文学新潮后受到一定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一弓放弃自己习惯的“政治—社会”话语操作,不去书写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不去针对社会中具体的某类人发言,而是创作《夜惊》《孤猎》等明显带有寻根倾向的小说。《夜惊》讲述农民打窑洞打出来一个大禹的石雕。村民们不知道这是大禹,但是都觉得这个石雕高大俊美,是理想的“人样”。接下来,女人们由这个石雕的高大俊美,而纷纷不满意自己的男人,男人则由此发现自己的丑陋,并痛恨石雕,且砸碎石雕。后来外村的石匠告诉他们,这是大禹的石雕,村人们则开始懊悔自己忘掉祖宗。《孤猎》写一个曾经捉过二百多只豹子的英雄猎手和一个寡妇相爱,可他觉得是不对的,为了克制自己的欲望,他离开寡妇,离开这个地方。结果导致这个地方遭野兽肆虐。猎人得到消息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却发现和他相爱的寡妇已经和一个只会打兔子的猎人离开了。失去爱人的猎人冲进狼群和野狼搏斗,最终被狼吃掉。从叙事风格看,这两部小说和张一弓既往的写作有着巨大的差异,显然是受到当时文坛流行的寻根文学的影响而创作的。这两部小说中当然也包含着张一弓英雄主义的情怀,却缺少对时代、社会影响下的具体生命的关注。不过,这种书写显然更像是张一弓的一次创作实验,并没有成为他之后延续的写作方向。在《远去的驿站》中,我们发现,张一弓创作的叙事特点又重新回归,那就是对普通民众命运的关注,对历史、时代旋涡中个体生命的关注。事实上,《远去的驿站》这部小说之所以动人,不仅仅是因为小说具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情怀,还因为小说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小说中的父亲、姨夫、舅舅,以及王疯子、薛姨这些人,在历史动荡的年代,作出自己的时代选擇并为了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然而,他们或者不被人理解,被人嘲弄,或者直接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这些个体生命在历史中的悲喜剧的展开,显然能带给读者更多的关于历史、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考。
如果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作为张一弓创作的起点,《远去的驿站》作为张一弓小说创作的终点的话,两相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巨大的不同。但是,巨大的不同不是一天形成的,其实是张一弓在不断地变动和不断地调整中,一步步完成的。从张一弓创作的坚守中,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张一弓最有情怀的、最擅长表达的,依然是在历史、社会旋涡中的个体生命,依然是人和历史、社会的碰撞。这或许也说明张一弓的文学立场,归根结底,他的文学是要表达人生的,文学是要为表达人生、社会服务的。
三、结 语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一弓突然在文坛成名,并且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在80年代后期,一直到21世纪,张一弓似乎又从文坛消失了,没有作品出现。张一弓的消失,自然和张一弓担任作协主席以及创办《热风》杂志有关,但是,恐怕也和他没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小說表达方式,没有解决好自己的创作转型有关。从《远去的驿站》我们可以发现,张一弓已经成功超越自我,更新自己的话语方式,让自己的写作进入一个新的境地。从张一弓的坚守与超越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坛大气候、时代变化对一个作家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亦可以看到一个优秀的作家,在时代转型过程中,为了不落伍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当然,从张一弓的坚守与超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天然的气质与价值立场,还是会最终决定作家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5][18]曹增渝.用激情和理性浇筑当代英雄——兼论张一弓对主流文学的意义[J]. 小说评论,1992(4).
[2]张宇. 张一弓的命运之神[J]. 中国作家,1985(2).
[3][7][8][11][12]张一弓.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J].文学评论,1983(3).
[4]转引自曹增渝.用激情和理性浇筑当代英雄——兼论张一弓对主流文学的意义[J]. 小说评论,1992(4).
[6][13]苗梅玲.孤独的身影与浪漫的灵魂——张一弓访谈[J].东京文学,2012(4).
[9]张一弓. 猎人在捕猎沉重的人生[J]. 中篇小说选刊,1988(1).
[10][17]刘思谦.张一弓创作论[J]. 文学评论,1983(3).
[14]陈继会.张一弓:寻找与超越[J]. 当代作家评论,1987(4).
[15][16]周桐淦.失去的和缺少的——读《听从时代的召唤》致张一弓同志[J].文学评论,1983(5).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