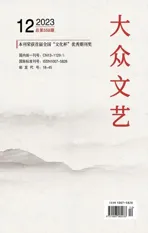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幸福生活”观念剖析
——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文本解读
2023-09-01张卉洁
张卉洁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长沙 410000)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著作中,彰显着人们对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其把幸福看作至善的、最高的目标追求。亚氏“幸福生活”从经验生活的中道角度出发,综合考察人类德性的需求与要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致力探析人类“美好生活”如何可能,其伦理核心在于人如何过上“好生活”,伦理基点落脚于“人”本身及其“人的生活”本身,因而,深入解析亚里士多德“幸福生活”的内涵,对人类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一、亚里士多德“幸福生活”的基本内涵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生活观念基于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幸福观”的考察而形成,更为深入的探析了人类伦理生活的行为规范与道德目标,展现出独特的伦理特征。
1.古希腊先诸的“幸福生活”观
通过对生活的深入思考,苏格拉底首次提出了“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1],苏格拉底对此的回答是“好生活”,“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2],苏格拉底的“活的好”不是简单的物质生活,而是人类对幸福生活永无止境的追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幸福。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幸福生活”的观念上不同于老师苏格拉底的“好生活”,柏拉图对哲学王理想国的向往,正是他所欲求的“幸福生活”。柏拉图的理想生活,是在哲学王的统一领导之下,每位成员各司其职,国家分配财产乃至家庭,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是一种“理想生活”,不是个人的幸福生活,而是全社会文明和精神高度发展情况之下,每个个体都应自觉的恪守自身岗位、地位所具有的道德品质,从而凝聚成为“最优解”的国家,强调着公共性与秩序。
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幸福生活,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进行了更为详细和系统的论述,全书的核心就是对幸福生活的讨论,认为“善”是每个人追求的终极目的,人在符合德性的生活中成就真正幸福,即“至善”的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说一个事物自身即是善,就是说它在总体上对于人是善的或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完善性。当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一种目的不再为着其他别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就是最好的终点也是终极的目的”,那么这个让人类穷极一生追求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人们都同意,这就是幸福”[3]。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生活分为三种:享乐式的感官生活、公民大会式的政治生活、沉浸于理性的深思生活。享乐式的生活是肉体的快乐、是动物式的欲求,政治的生活则将追求荣誉与德性放在首位,但这些都不是最完善的,最幸福的生活是沉思的生活,因为幸福在合于我们自身中那个最好部分的德性的东西,它是最完美的活动,是具有神性的,而我们的灵魂中只有“努斯”是神性的东西,沉思就是一种符合努斯的德性生活,所以沉思的幸福是最高的幸福,因而他得出,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生活不是单纯的思考就等于幸福,而是通过理性思考而过着德性生活的人,才是幸福的人,强调着人的深层次精神追求,同时也承认了人们的“享乐”生活,承认了物质对于幸福生活的重要性。
2.亚里士多德幸福生活观念的特征
城邦生活的前提性:“城邦”在古希腊人心中有着崇高地位,在亚里士多德眼中更是幸福生活的基础性前提,“凡人由于本性或出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4]。亚里士多德认为,生存在城邦中的才是“公民”,而不生存在城邦的人是“非人”,是无家可归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生活中,成为城邦共同体的一员是拥抱幸福生活的前提性条件。
德性和幸福的统一性:过具有德性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幸福生活的基本性要求,也是其幸福生活的本质性特征。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一定意义上也被叫作德性幸福观,德性是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生活即幸福生活,“幸福的生活似乎就是合德性的生活”[3],亚氏将幸福生活与德性生活直接的等同起来,并将幸福看作是德性所追求的最高的善,这种幸福不是来自简单的肉欲生活,也并非简单的消遣性快乐,而是通过符合德性的沉思生活达成的。
快乐的必不可少性:谈论“幸福”一定离不开对“快乐”的讨论,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快乐是一种善,对快乐抱着尊重的态度,“快乐伴随着并充实完善着幸福实现活动本身”[3]。幸福是离不开快乐的,“多数人都认为幸福包含着快乐”[3],只不过对什么样的快乐才能达到幸福的定义与追求不同,虽然大多数追求的只是同样的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多数人追求的实际上是同一种快乐,虽然他们口头上或是心里并不认为自己追求的那些快乐与他人一致,但实际上,肉体快乐是“我们接触得最多且人人都能享受的快乐”[3],享乐的肉体快乐总是大多数人必不可少的必然追求的快乐。但无论是什么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兽类和人类都追求快乐,这就表明它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最高善”[3]。
二、亚里士多德“幸福生活”的实现方式
亚里士多德对“人类过何种生活”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对于“人类如何过上这种生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析,为人类如何过上幸福生活提供了路径指引,具体是:关于沉思的理论智慧、关于躬行的实践智慧以及关于适度的中道智慧。
1.理论智慧:理论智慧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最高智慧,即最高的理智德性。亚里士多德不认可其师柏拉图提出的独立于具体事物的“善”,但亚里士多德承认具体世界需要通过理念才能真正得到认识,因此亚里士多德在理念的最高级上继承了柏拉图理念世界的思想。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研究的前期并未明确的区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认为实践智慧从某种程度是从属于理论智慧的一部分,直到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才明确地做出区分。
理论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由努斯和科学的结合,是与沉思密切相关的德性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智慧是对普遍性和那出于必然的事物的把握,其强调的是事物的“必然性”,认为理论智慧是不受客观世界影响的,“理智本身是不动的,动的只是指向某种目的实践的理智。”[3]理论智慧与必然性的“科学”相连,因而,它也关涉永恒,“科学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因此,它是永恒的。因为,每种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事物都是永恒的。”[3]理论智慧是永恒的,是关涉努斯、直觉和判断的智慧,彰显着“理性思考”的力量,强调“科学”的智慧,是自然直觉对科学的思考。正如前文所言,亚氏最高的幸福生活是沉思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正是指涉沉浸于科学性思考的永恒理论智慧。“爱智慧”的理性活动是人类最高级、最长久、最平稳的合乎德性的活动,相比于其他的快乐,沉思的快乐最容易让人感到最大的快乐,因为这种快乐是最纯粹、最纯净的快乐,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那些获得了智慧的人比在追求它的人享有更大的快乐。[3]由此可见,理论智慧是追求幸福生活的首要部分,是人类通过实践智慧追求幸福的生活的前提智慧。
2.实践智慧:通晓一切的理论智慧为实践智慧给予了启示,防止其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沼。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实践智慧,并详细论述了关于实践智慧不同品质的详细定义,显然,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智慧的核心要素,正是通过实践智慧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幸福美好生活。张彭松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就是在‘实践智慧’的指引下,依循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探究方法,平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伦理态度,研究人们该如何按德性方式生活,增益幸福。”[5]
实践智慧不同于理论智慧指涉的是确定性的事物,实践智慧是针对现实复杂世界的具体德性选择,根据经验和习惯,做出最符合逻各斯的决定。亚里士多德十分看重德性选择,“选择比行为更难判断一个人的品质。”[3]实践智慧就是关于选择好的、选择正确的德性智慧。实践智慧作为针对具体事物和情感选择的智慧,必然具有非确定性的特征,“实践与便利问题就像健康问题一样,并不包含什么确定不变的东西。”[3]因而,实践是一个可变的范畴,只有通过习惯习得的经验,以此获得正确的德性规范及德性习惯。“习惯”和“道德”在希腊语中曾用同一个词表示,人们正是从习惯中获得的好的品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提醒着人们养成好的道德习惯,亚氏将养成良好德性习惯而其行为倾向于做符合德性事情的人们称之为“好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告诉我们,作为实践者,其根本意义不在于成事,而在于成人,根本目的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做人,实践智慧正是在关注人们德性生活时,去追求最高的善,是追求幸福生活的实际行动和行为指导。
3.中道智慧:中道智慧展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智慧的集中,同时也贯穿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全书内容,亚氏在论述每个具体德性时都论述其过度和不足的一面,从而论述其适中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亚里士多德全部德性乃至全部智慧,都强调了中道智慧,可以说,亚氏的中道智慧是其伦理学的指导性部分。事实上,实践智慧的伦理内核也离不开“中度”二字,实践智慧必须在符合逻各斯的德性行为上避免其过度和不足,强调人在具体的行为领域和情感抉择中要把握适度的德性能力。“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这意思是,过度与不及都破坏完美,唯有适度才保存完美。”[3]我们只有将自己的感情和行为都控制在中度的范围里,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被人称赞的“善”的人,“在感情和实践中过度与不及都是错误,适度则是成功并受人称赞。”[3]亚里士多德在书中直白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选择适度,避免过度与不及。”[3]并且指出我们“不能随便说自己或他人做的事合于中道。离去中道,也就是走向某一极端,这时我们就必须矫正。”[3]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通过中道智慧才能实现其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并且也指出在复杂的情感中,实现中道并不是易事,因此我们才需要不断的努力将德性生活变成习惯生活,在适度与中道的理性中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三、亚里士多德“幸福生活”的局限性与启示性
亚氏的幸福观内涵丰富,当今对亚里士多德“幸福生活”研究的热度只增不减。然而,亚氏的智慧终究是来自遥远的古希腊时期,其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受到时代思维的限制,在考察其正向意义的同时必须探析其不足之处,才能更为理智且公正地看待亚氏的伦理价值,并使其发挥最大的时代意义。
1.局限性
等级分明的阶级性。考察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生活必须放在古希腊的时代背景中,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显露出明显的阶级性。一方面,亚氏认为幸福是需要外在条件,当缺失一定的外在条件,例如地位和财富时,幸福生活就变得遥不可及乃至不可能。另一方面,平等不存在每个人中。“父亲同子女的关系、男人同女人的关系、主人同奴隶的关系是一些基本的相互区别的关系,这些关系都含着某种天然的不平等,因为奴隶完全没有思考能力,妇女有但是不充分,儿童也有但是不成熟。”[3]亚里士多德否认奴隶、妇女和儿童的平等人权,这对我们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美好生活背道而驰。人人平等是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天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亚氏的思想在这个方面,对当代人追求幸福生活具有不平等的阻碍性。
沦为空谈的不现实性。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生活虽然关涉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承认了肉欲的快乐,但是他对幸福生活的实际操作与追求标准上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现实性,在实践上仍然难以施行,具有现实主义的理想性特征。亚氏对慷慨、大方、大度、温和、友善、诚实、机智、羞耻的具体德性做出了相对具体的论述,然而其具体的实践描述模糊,并对个体的德性选择和道德抉择上具有相对高的要求,更加倾向于通过“初心”来考量是否符合德性生活。然而,在如今的美好生活时代,我们辩证的认为做事的出发点及其过程与结果的考衡均具有重要意义。
2.启示性
寻求利益与幸福的平衡。利益常常是人行为处事的出发点,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是人之本性,追求幸福更是人人都渴望的美好愿景。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在当今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详细考察了利益和幸福的关系,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了独有的智慧。亚氏将“沉思的智慧”看作是通往最高幸福的秘诀,即,善用“理性思考”的能力,进而在利益和幸福之间寻找一条平衡之路。亚氏强调通过“理论智慧”的引导,探寻幸福的正确方向;通过“实践智慧”的带领,内外兼修,养成良好的德性习惯,能够面对利益做出正确的德性选择,从而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够正确处理利益与幸福关系,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启示方案。
确立理性的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科技与资本的发展中,现代生活充满着诱惑,快节奏的生活让一些群体尤其是青少年迷失在肉欲的快乐中,在此背景下,亚里士多德强调理性的德性生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亚氏告诫人们,肉欲的快乐只是低级的快乐,人类若想追求长久、平稳的高级快乐,只能通过理性的沉思生活才能达成。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在正视欲望的同时,能够做到“克己复礼”,通过理性的思考、阅历的丰富、情操的培育,来确认自己的人生定位,追求真正的、持久的幸福生活。
余论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伦理学界的经典著作,其幸福观为构建人类美好生活道路提供了伦理启示,其伦理智慧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生活的构建及其社会道德个体的塑造仍然具有深刻的价值指导意义。反复探析《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伦理价值绝非多此一举,其伦理指引能够唤醒现代人的道德认知、指引世界现代化下的理性生活,进而激励人类不断向幸福的美好生活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