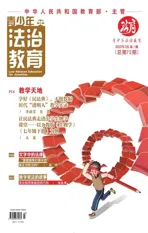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的教义学阐释 *
2023-05-30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孙鹏庆
文/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孙鹏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曾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但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案件频发,学界对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需要调整的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因此,为满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现实需求以及回应社会的期待,《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标志着刑事责任年龄迎来重大调整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新的核准追诉程序——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根据这一规定,十二至十四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在符合罪名和情节要求且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前提下,需要承担相应刑责。由此观之,明确该规范的适用前提尤为重要。但是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的设立具有即时属性,现存立法并未得到充分的解释,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该条款是否能有效运用于实践的疑问,也被动产生了因没有明晰规范内容和程序设计而导致程序失灵与滥用的制度风险,故而亟待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现以作参考。本文的基本逻辑便是通过解读实体法规范,进而厘清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的内涵。
一、规范阐释:背景、本意与目的
规范的背景、本意与目的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契合的关系,解释规范需要就规范制定的时代背景、立法本意以及其所追求的实践效果予以明确。这意味着阐释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需要立足于该款规范制定的背景,探求其立法本意及目的。
(一)规范之背景:社会、实践与理论的三重图景
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的颁布,是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刑事立法积极化的必然结果,未成年人恶性案件频发是其实践层面的诱因,学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充分研究则为其提供了肥沃的理论土壤。
1. 社会背景:社会转型下刑事立法的积极倾向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风险激增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带来刑法发展中犯罪化扩张的态势。基于此,刑法立法预防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意图明显。①姜涛:《社会风险的刑法调控及其模式改造》,《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换言之,是因为某一类的犯罪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危害和社会关注,以至于需要立法予以规制,以维护社会的平稳运行。②[美]史蒂文·瓦戈:《法律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在此背景下,刑法的工具性特征更加突出。③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2020年,我国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新增条文13条,修改条文34条,涉及当下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重大和新型问题。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转型社会中风险激增的客观现实也引起了未成年人犯罪高发、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案例增多等情况。因此,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
2. 实践背景:低龄未成年人重罪案件频发
根据有关数据,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总案件的比例虽在不断下降,有未成年人犯罪式微的倾向,但是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即恶性化和复杂化。许多曾经主要由成年人实施的恶性犯罪,未成年人渐渐地也成为实施主体,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严重且犯罪情节恶劣。④宋英辉、何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被媒体报道后,立即引发了公众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关注,也影响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工作。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在互联网上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期间,人们针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过积极探讨,提出了8,000多条意见,这些意见主要集中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最终,在草案三审稿中对此予以调整,并最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成为现行法律规范。
3. 理论背景:充分的域内外研究基础
目前,针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判定的研究领域主要存在“降低说”“不变说”和“弹性说”,我国以此为基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调整。而综观世界各国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将其设置为十四周岁以下的国家不在少数。并且,基于刑事责任年龄设置的不同,与之相关的域外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催生和发展出了诸如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国家亲权理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少年法庭理论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工作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域外理论与实践资料。
(二)规范之本意:涉罪低龄未成年人的保护条款
探求出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的立法本意,才能从根本上明确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的规范属性。可以明确的是,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的立法本意是保护未成年人。立足于客观实际,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不仅是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频发问题的回应,也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社会治理作用的强化。而且通过诉讼程序进一步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不仅是少年司法对未成年人进行“双向保护”原则的规范体现,也回应了当今社会在司法实践中要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的现实要求。
1. 规范理念:“双向保护”原则的规范体现
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是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应依照“双向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优先保护和特殊保护。“双向保护”原则被认为源于《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第1.4条之规定,其主要内涵为少年司法要注重少年政策适用的社会效果,追求社会效益与未成年人权益的均衡状态。①深圳市福田区法学会、张宏城主编;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编:《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 0版新模式》,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而我国《刑法》第十七条对主观恶意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未成年人通过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经由国家公权力对其进行教育与惩罚的规定,不但能起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还能对涉事未成年人的权益进行保护。另外,感化、教育和挽救未成年人也是程序适用的重点,由此实现社会效益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平衡。因此,我国的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过程体现出了刑法具有的引导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并对其进行保护的功能。另外,通过“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一表述,从程序设置方面也贯彻了严格限制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理念。故而,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可以被视为涉罪未成年人的保护条款。
2. 实践保护:有利于规避利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之情形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利用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漏洞实施犯罪之情形,设立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有利于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实践中一些犯罪团伙会利用未成年人来实施犯罪,以逃避刑法对其的制裁。②彭新林:《理性看待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个别下调》,《民主与法制时报》2021年2月4日第6版。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处于十二到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其身心尚未充分发育,看待世界的方式还比较单一,并且缺乏良好的自制能力与判断能力,容易被犯罪团伙利用;从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来看,实施犯罪对其自身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不可逆的。③庄永廉等:《如何履行好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检察职责》,《人民检察》2020年第9期。犯罪团伙利用未成年人规避刑事责任的客观现实,从侧面反映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是十分艰巨的。因此,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并设立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无疑是防止犯罪团伙将未成年人当作犯罪工具实施犯罪、进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有力之举。
(三)规范之目的:公正司法,防止错诉
从规范本意出发,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实质为未成年人保护条款。那么,在我国社会高度转型、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频发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理论研究充分的背景下,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产生了这样一个条款?该条款颁布后又会达成何种社会效果呢?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制定的目的是维护我国少年司法的公正,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统一追诉标准,实施后将达成防止错诉的社会效果。
1. 根本目的:达到公正司法的理想状态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在公正司法的要求下,公平与正义的理念应当贯穿司法适用的全过程以及结果。④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然而在实践中,全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不充分的。例如,有些地方的实务部门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不考虑其具有的特殊与重要属性,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在他们眼中也缺乏价值。不仅如此,社会舆论以及学界也存在着严惩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张,认为不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对待。这样的观念、看法导致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制度以及刑事诉讼程序无法有效适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犯罪率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会意识滞后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在法律层面主要体现在法律无法及时回应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并在新的法律规范尚未制定时,出现了所谓的“失范”状态。①[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66页。基于恶性案件低龄化以及低龄未成年人权益受损日益严重的现实情况,原有的刑事责任年龄之规定已经无法回应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新课题、新要求,于是便有必要通过刑事立法确立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明确核准追诉的对象、罪行条件以及核准主体,从而达到公正司法之理想状态。
2. 实践目的:防止错诉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是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的程序体现,它意味着未成年人重罪案件只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能予以追诉。这样的程序设计,既严格限制了检察机关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涉重罪未成年人的严管,彰显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厚爱。也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让此类案件的追诉标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统一与规范,由此保证对追诉低龄未成年人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体现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的权威性与公正性,使属于追诉范围者经过公正的程序予以追诉,让不属于追诉范围者不被追诉,从而有效防止错诉,实现司法公正。
二、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的程序要素
站在刑法教义学的立场,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应扩大解释为故意杀人行为和故意伤害行为,这是程序启动的行为要素;程序启动的结果要素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则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达到核准追诉程序要求的情节要素。

(一)行为要素:故意杀人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
根据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触犯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在满足危害结果和情节要求的情况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那么,如果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与强奸、抢劫行为等恶性犯罪行为想象竞合,或者具备强奸罪与抢劫罪等恶性犯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或者加重情节,此时应当如何处置?又如实施了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其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行为,对此又该如何处理,能否适用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有学者指出这是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没有解决的地方,即条款存在体系内部不协调、与其他法条之间存在体系严重失衡的问题。①刘宪权、石雄:《对刑法修正案调整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商榷》,《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年第1期。但是,事实上该条款不仅保持了规范体系内部的协调,而且也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情况。
一方面,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理解为故意伤害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是刑法解释体系性要求的体现。原因有二:第一,从核准追诉条款所处的条文位置来看,其位于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理应与前款④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规范解释上保持一致;第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的规定,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所以,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中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也应当扩大解释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行为。换言之,只要低龄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在满足《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虽然并未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但也应当适用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承担刑事责任。
另一方面,将故意伤害行为、故意杀人行为作为核准罪名的解释也符合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情况。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更偏向于暴力型的人身财产犯罪,手段也更为残忍。因此,我国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使得低龄未成年人经过核准追诉程序后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是立足于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实践所作出的科学举措。
(二)结果要素:致人死亡或者采取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的结果要素应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死亡,第二层是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二者并列。实际上,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危害结果的解释,学界仍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致人死亡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虽是两种结果,但二者的社会危害性一致,即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行为,即便并未造成死亡的结果,但如果是犯罪嫌疑人采取了特别残忍手段导致受害者重伤造成严重残疾,那么他仍然要承担刑事责任。②彭文华、傅亮:《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年第1期。不过,对此有学者持相反的看法,认为低龄未成年人故意实施杀人行为,必须造成死亡结果才可能被科处刑罚,如果只造成重伤致残疾结果,行为人则无须承担相应责任。③胡云腾、徐文文:《〈刑法修正案(十一)〉若干问题解读》,《法治研究》2021年第2期。这两种观点,笔者倾向第一种,原因有二:一是从规范的表述来看,“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之间通过使用顿号表示其为并列关系,在此之后的结果要求,应是对两个行为的同一规定;二是从规范的具体适用出发,如果低龄未成年人以伤害的故意,采取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危害结果,即使杀人未遂,也理应承担刑事责任。故而,致人死亡结果与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结果是并列关系,都可由故意杀人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所致。综上所述,低龄未成年人适用核准追诉程序的罪行具体要求有以下四种:一是故意杀人死亡既遂;二是故意杀人未遂,但是采取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结果;三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四是故意伤害且采取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结果。
其中,“致人死亡”“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等评价标准相对客观,不存在解释上的歧义。但是,对于“特别残忍手段”等应进一步明确其具体含义的标准。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该标准进行判断。第一,从杀人手段判断。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残忍凶杀手段远远超出了人性和伦理的范畴时,应该将其视为“特别残忍手段”。第二,从被害人的感受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段越残忍,受害者就越痛苦,这种给受害人带来特别痛苦的方式,应当被认定为“特别残忍手段”。第三,从社会公众的可接受度判断。使用非常规方法杀死受害者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也应当被认定为“特别残忍手段”。综上,“特别残忍手段”标准的判断核心是行为对于道德观念和社会公序良俗的背离。①车浩:《论被害人同意在故意伤害罪中的界限——以我国刑法第234条第2款中段为中心》,《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因此,在对低龄未成年人涉罪案件进行“特别残忍手段”审查时,应对行为人手段的非道德性进行判断。
(三)情节要素:需要综合衡量的“情节恶劣”
使用“情节恶劣”的表述意味着要科学地适用未成年人核准追诉程序,要注重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考察,基于此,把握其判断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规范本身的逻辑出发进行认知,“情节恶劣”应当是对故意杀人行为和故意伤害行为的情节要求。作为我国法定的犯罪情节之一“情节恶劣”,对行为人刑事责任有消极的影响,即情节越恶劣,行为人可能被科处的刑罚就越重。因此,若将“情节恶劣”作为某个行为的限制条件,则提高了对该行为入罪或者量刑的门槛。根据未成年人核准追诉条款的立法本意和目的,条款中“情节恶劣”应当是对故意杀人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的限制条件,具体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故意杀人既遂,情节恶劣的;二是故意杀人未遂但是采取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三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四是故意伤害且采取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
笔者以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第一,从低龄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上去判断。如果低龄未成年人动机卑劣、手段残酷,且毁灭罪证、嫁祸于人,屡教不改属于累犯的,应当被认定为“情节恶劣”。但如果出于防卫自身安全或维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利益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情节恶劣”。第二,从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去判断。如果造成多人死伤的,或者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父母等近亲属、残害婴幼儿的,则可以视为情节恶劣。第三,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去判断。如果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在该片地区形成持续性的恶劣影响,便可以视为情节恶劣。这要求核准机关结合案件事实、社会影响以及未成年人主观恶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