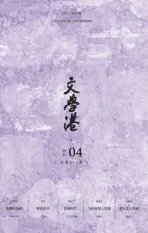红楼大观 (之四)
2023-04-15张亦辉
张亦辉
19.大观园和题对额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
这是川端康成的小说 《雪国》的开头。雪国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地方,具体而言就是位于日本海沿岸中部、本州岛北部的新潟县越后汤泽,作者只要描写一下这个地方,就可以让人物在其中活动了。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小说、电影都是如此。
我们读狄更斯的小说,伦敦熟悉的街道为小说提供了现成的叙事空间与背景。我们看那么多与巴黎有关的电影,那些历史悠久的著名的景点与建筑无疑成了吸引观众的亮点。
《红楼梦》却很特别。
贾府里本没有大观园,曹雪芹需要借元春省亲为由,为宝玉与众姐妹凭空筑造一个大观园,一个本来不存在于人世的生活空间,一个无中生有的活动舞台,一个乌托邦,一个准太虚幻境。也就是说,里边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榭,实际上都是曹雪芹自己一手筹画起造的,所谓老明公山子野无疑只是假托。
实际上,除了曹雪芹本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建筑师能够造出大观园!因为,筑造大观园,除了要懂建筑学、园林学、植物学等,他还必须懂心理学与人格理论,大观园里的每一处馆、院、苑、庵等都是为即将入住其间的人物量身定做的,建筑的风格特点与人物的个性气质之间卯榫契合天衣无缝,如怡红院之于宝玉,潇湘馆之于黛玉,蘅芜苑之于宝钗,秋爽斋之于探春,稻香村之于李纨,栊翠庵之于妙玉…… (马尔克斯在 《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简约地叙述了女主人公与她的房子之间的契应关系: “在整幢房子里,一位讲究实际的妇女的智慧和热情清晰可见。”)
我想,这才是我们欣赏大观园的重点与要点。也是曹雪芹建造大观园的难度系数或心血所在。
曹雪芹建造大观园的过程,堪比于上帝的创世。
上帝创世其实只是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活,祂只是命名。这是天,这是地。
同样,曹雪芹创造大观园,也不是用砖瓦草木,而是用文字和叙述。
可要把偌大一个大观园描画叙述出来,介绍给读者,殊非易事。常规方法是风景描写,但景点众多,亭台绵延,连篇累牍的风景描写一定会重复冗长,读者一定会不耐烦。
所以,曹雪芹就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巧妙方法:让宝玉进园题对额。表面上是 “试才”,实际上是叙事的需要,是介绍大观园的修辞策略:通过题对额,化静态啰嗦的风景描写为动态起伏的故事情节。
当然,题对额的整个过程,不仅动态,而且张致变化多有悬念,贾政与宝玉与清客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充满戏剧性与张力,读起来的效果,有如群口相声,也有如一个个逗趣的舞台小品。整个过程峰回路转,移步换景,柳暗花明,好戏连台,谐趣横生,没有一丝枯燥与板滞,而且人物的个性 (考官贾政的迂腐与考生宝玉的灵气)也借机得到了展示,可谓一举多得。
20.荷包
法国作家加缪在未竞之作 《第一个人》的一条自注中说:
“小说要充满肉体与物体。”
因为文学是人学,自然少不了肉体;而物体则通向细节,可以让叙事变得具体结实,并散发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小玛德莱娜点心、 《尤利西斯》中的猪腰子、《喧哗与骚动》中的钟表、 《百年孤独》中的冰块等,都是耳熟能详的卓越的文学细节。
我们来看看,曹雪芹如何借助一个小小的荷包的细节,拉开了宝黛之间波诡云谲的证情大戏之序幕。
宝玉顺利通过了大观园题对额的考试,无疑,这是他这辈子考得最好的一次。从大观园出来,小厮纷纷上前祝贺宝玉 “得了这样的彩头”,便趁机哄抢了宝玉身上的所佩之物,荷包扇囊,尽行解去。也可见宝玉与小厮们没高没低的亲昵关系。
黛玉见此情景,却不高兴了:
“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
说完,黛玉赌气回房,还将前日宝玉烦她做的那个香袋——才做了一半——赌气拿过来就铰,等宝玉赶过来阻止,却早剪破了。
在黛玉看来,宝玉丢的当然不是荷包,而是她对他的一片情意;而她剪破香袋,一方面实施了对宝玉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无疑让她自己更加生气了。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相爱的人由于过于在乎对方,所以就特别容易因为细枝末节而生气,因为芝麻大的原因生西瓜那么大的气,特别容易从小生气走向大生气,从生对方的气走向生自己的气。
曹雪芹的叙事没有停留在揭示这样的恋爱原理上,而是走向了宝黛之间独特而空前的证情戏码。
所谓证情,其实就是让情感经历一番误会、纠葛与挫折之后走向更深更浓更真的情感。
我们很快便看到,原来黛玉是冤枉了宝玉,宝玉并没有把荷包给别人。他一边生气着黛玉的生气,一边就从里面红袄襟上将黛玉所给的那个荷包解了下来,递与黛玉:
“你瞧瞧,这是什么!我那一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
这既出乎黛玉的意料,也出乎读者的意料。叙事就显得兜折多变迂曲有致。
黛玉一下子从正确主动的一方,逆转为错误被动的一方,而且是双倍的错:怀疑并责怪宝玉把荷包给别人是错的,用剪破香袋惩罚宝玉则是错上加错。
但黛玉并没有认错,她当然不肯认错,她的个性决定了这一点。她只是 “又愧又气,低头一言不发”。
宝玉这时候却不干了:
“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待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奉还,何如?”说着,掷向他怀中便走。
宝玉其实有点得理不饶人了。 “你是懒待给我东西”,显然不是事实,而是气话和借题发挥;再把荷包掷还黛玉,则更显得意气用事:
黛玉见如此,越发气起来,声咽气堵,又汪汪的滚下泪来,拿起荷包来又剪。
叙述了黛玉剪香袋之后,紧接着又叙述她要剪荷包,这就是曹雪芹叙事的卓异与膂力。一般作家定会逃逸一样避开这样的重复 (其实是复沓),但殊不知,黛玉这 “二剪”,剪出的是别样的倔犟与任性,剪出的是证情过程的跌宕与纠结。
好在宝玉这回有所准备,及时抢回了荷包,没有让黛玉剪成。如果真把荷包又剪破了,那倒没有意思了,那就真是笨拙的重复了。曹雪芹当然不会让自己犯这样的错误。
一部 《红楼》,荷包这样的物品细节还有很多,简直星罗棋布于文本空间里,如前面的宫花,后面小红遗失的手帕、蒋玉菡送给宝玉的大红汗巾子、晴雯补的雀金裘、蔷薇硝以及傻大姐捡到的绣春囊……
每个小细节,皆是一篇大文章。
21.来了,来了!
人民文学最新版的 《红楼梦》,依旧根据底本把第十七、第十八这两回合在了一起。其实从阅读角度,不妨果断地把它分为两回,就像第一回 “列一位看官”前面那段批注文字完全可以索性放进脚注或尾注里去。
第十七、第十八两回应该从哪里分开呢?
己卯本以及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都是从 “不能表白”处切分的。窃以为,从文脉与语感的角度,从情节的连续性与内容的完整度来考量, “不能表白”后的那一段,即 “当下又有人回”到 “宝钗便说: ‘咱们别在这里碍手碍脚,找探丫头去。’说着,同宝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闲顽,无话。”这一段,应接续在第十七回,这样才能呼应并补全 “荷包”证情结束时的那句 “可巧宝钗亦在那里”,否则,叙事内容上就会有脱节感与缺失感。
另外,现在进行时的 “当下”两字,显然需要紧跟前面的情节;而 “无话”两字有暂停感或悬停感,更适宜用作回末缀语。
尔后的第十八回,才重打鼓另开张,进入紧锣密鼓的省亲情节,并形成叙事时间上快速递进与叙事节奏上的阶梯发展:
王夫人等日日忙乱,直到十月将尽,幸皆全备……
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贾妃省亲……
展眼元宵在迩……
至十五日五鼓……
省亲的豪华场面与瑰丽情景,当然不是炫耀,而是为了呼应秦氏托梦凤姐时所说的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曹雪芹特别能驾驭盛况空前的场面与宏大热闹的情景 (这一点特别像托尔斯泰,叙述一场尸横遍野的惨烈战争就像炒了一盘菜,真仿佛拥有如椽巨笔和洪荒之力),加上他从小就经历并熟悉那样的场景,所以,他的叙述既宏观繁阜又微观细致。记得台湾学者黄一农就专门介绍过那把 “曲柄七凤黄金伞”与元妃身份的一致性。
元妃前后三次或叹息 “奢华过费”,或规劝 “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或嘱咐“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几乎是贾府盛极而衰的预告或预兆。
当然,元妃与家人相见的情景也写得似喜却悲,辛酸恸人。
但整个省亲回合中,我自己最喜欢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曹雪芹叙事之神鬼莫测与不可逆料的地方,不是元妃如何驾到如何热闹,而是之前贾母与贾赦带领众人在西街门外与荣府大门外怎样迎接和等待。
先是五鼓时分,贾赦等在西街门外等待,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迎接, “正等得不耐烦”,忽一太监坐大马而来,说:
“早多着呢!末初刻用过晚膳,末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酉初刻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戌初才起身呢。”
于是贾母等在凤姐安排下,只好先回屋暂且自便,另派人领太监们去吃酒饭。
此情此景,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谁在人生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等待与渴盼,带着一份按捺不住的兴头与激动?结果却是 “早多着呢”。
于是只好先回家等着。
可是不久之后,外面就传来跑马之声和拍手之声,然后,我们隔着书页都能清晰地听到那喊叫声:
“来了,来了!”
贾赦就领合族子侄重新来到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重新到大门外迎接。但却 “半日静悄悄的”。这真空般的 “半日”,这风暴眼般的 “静悄悄”,真是太让人提着胆悬着心了!
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至西街门外下了马,将马赶出了围訞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得隐隐细乐之声……
那皇家的仪仗与排场,那无与伦比的威赫与庄严,这才如梦似幻般轮番绽现在众人面前。
瞻望勿及,忽焉而至。好事多磨,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曹雪芹真乃叙事天才造梦大师也。
另外须留意的,是省亲过程中,元妃让众姐妹题咏时的一处细节。只要细心阅读宝钗与黛玉两人的诗,便可预知元妃后来为什么偏爱宝钗了。宝钗的诗句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难掩比兴恭维之意;而黛玉的诗句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则几乎只是直陈其事而已。
22.游离与逸出
写小说就是写人物。莫言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的很多作家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红楼梦》的一大成就便是创造了众多活生生的人物 (根据统计口径不同,从四百多个到九百多个再到三千多个不等)。曹雪芹 “造人”的功夫堪比女娲,造一个就活一个!区别只是,女娲用泥土抟人,而曹雪芹用笔墨造人。
英国作家福斯特把文学人物分成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 (译得不够妥贴,圆形人物并没有突出其非平面的立体的性质),前者大概指个性简单、确定的人物,后者则指个性复杂、变化的人物。按此分类,狄更斯或 《水浒传》的人物属于扁平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或 《红楼梦》的人物则属于圆形人物。
一部 《红楼梦》,除了邢夫人、迎春、贾环等偏于扁平人物,大多数人物均是有深度或厚度的立体人物。相比而言,张爱玲在叙述上得益于 《红楼梦》很多,但她的人物相对扁平,缺乏 《红楼梦》人物的深度和厚度。
我们来看看最重要的人物贾宝玉。
从小说的神话开篇,到接下来的具体叙事之中,贾宝玉的人设其实早已基本确定:他的前生是神瑛侍者,有补天之石或美玉附身,他讨厌功名利禄,喜爱水做的女孩,是母亲嘴里的混世魔王,是一个不识农具为何物稼穑为何事的公子哥儿,也是个多情到情不自禁的痴儿(与燕子说话、哭杏等),当然,还是一个秉有绝对之善的宅心仁厚者 (比如贾环一次次加害于他却从不记恨在心)……在这个意义上,贾宝玉很容易成为一个扁平的理想化的人物。
但随着叙事的展开与细节的刻画,曹雪芹不断给贾宝玉这个人物增添人性的维度,赋予个性的深度,从而让他渐次摆脱基本的人设(对那些水做的女孩,对其他许多人物,曹雪芹也都是这么做的。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等,相当于人设与人物画像,曹雪芹在后面的叙事中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人设演化为人性,让她们从画像上走下来,变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孩)。
比如,平时对什么都不在乎,给人大大咧咧的浑不吝印象的贾宝玉,却常常表现出他的细心与体贴。送刘姥姥成窑茶杯,为平儿理妆,发现庸医给晴雯开的药方中有虎狼药,让燕儿给莺儿赔礼时专门嘱咐不要让宝钗听到等,都是这方面的细节与案例。
比如,天不怕地不怕、爱耍性子的宝玉,其实有胆怯与懦弱的一面,他有点像哈姆雷特,差不多是一个情感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在金钏、晴雯等遇难的关键时刻不敢站出来,而只是在死者已矣时去悼念祭祀。
再比如,宝玉时或会表现出没心没肺的自私的一面,完全不顾家庭之收支与盛衰。第六十二回,宝玉与黛玉闲聊,黛玉说起探春管家的不易,并说荣府出的多进的少,不省俭的话怕后手不接。宝玉却道:
“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这次重读 《红楼梦》,最大的收获,是发现宝玉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游离与逸出。
比如,元春封妃合家欢庆之时,宝玉却游离在外, “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心里只惦记着秦钟的病;比如,第十九回荣府刚刚忙完省亲大事,曹雪芹指出凤姐“第一个事多任重”之后,接着就强调宝玉逸出如局外人: “第一个极无事最闲暇的”。
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每逢过年过节、庆生筵宴等闹热场合,宝玉经常独自个儿地逃避游离出去,就像云无心以出岫,就像在某种离心力作用下脱轨而去的小行星。具体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形:
一是有事的游离。如第四十三回凤姐生日那天,宝玉一大早就从后门出去,与茗烟两个到城外庙里祭祀金钏去了。
二是有事没事之间的游离。第十九回省亲之后,全家人在看戏、放花灯,宝玉深感无聊,就带着茗烟到城外去看回家吃年茶的袭人了,还喜欢上了袭人的那个姨妹子。
三是完全没事的游离。荣国府元宵夜宴那回,大家都在看戏,用大簸箩撒钱,只听 “满台钱响”。正在热闹之际, “宝玉因下席往外走”。贾母问他往哪里去,叫他当心爆竹和火纸,宝玉回道: “不往远去,只出去就来。”他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也许只是不喜欢这样的热闹,只是想一个人出去躲躲清静,他到大观园里胡乱转了一圈,撒了泡尿而已。
宝玉的游离行为,固然是日常生活中偶发的无聊所致,或青春期的生命厌倦之表现,或受到油然而至的虚无感的驱使。他的游离习惯,恰好对应存在之荒诞,契合整部小说万境归空的主旨。
但似乎又远不止于此。
宝玉游离并逸出,至少在这样一些岔开的悬浮般的时刻,仿佛是那个游历了人世体验了繁华与冷落的神瑛使者已然斟破了红尘,想要返回自己的前生;也仿佛是宝玉最后出家的预演与预叙;又仿佛是小说人物脱离了作家的控制,摆脱了基本的人设,自行其是,自行出离。
通过游离与逸出,宝玉似乎还无意间成为几个世纪后的 “零余者”与 “局外人”的文学先驱。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谁也无法确知,宝玉到底为何游离因何逸出,也许连他自己也未必明白未必清楚。他的行为始终像一个谜,特别像文本中的一个灰洞。另外,颇堪玩味的是,宝玉的游离习惯,与黛玉的那个习惯巧妙对称恰成镜像:就像王子猷在 “雪夜访戴”里最终 “造门不前而返”,黛玉也经常这样,每每如斯,她来到某处门外 (比如怡红院),却由于偶然性原因,或听闻里边的声音消息,犹豫一阵后,遂打消了进去的念头。
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他们俩一个曾是神瑛侍者,一个曾是绛珠仙草,一个经常离去,一个不肯进去。说到底,他俩毕竟都不完全是真正的红尘中人呵。
23.姨妹子
宝玉心血来潮,正月里到城外去看回家吃年茶的袭人,竟喜欢上了那个 “穿红”的姨妹子。宝玉可真是多情呢。
这可苦了曹雪芹。
秦氏出殡的半路上,宝玉已经喜欢过初次相遇的二丫头。
这一回又是如此,宝玉简直就像是一只见到了花的蜜蜂。
但曹雪芹的叙事却不能老调重弹,他不能让那只振翅的蜜蜂发出同样的嘤嘤声。
这一回,曹雪芹故意不让宝玉现场表现出他的多情,而是采用了事后补叙的策略。也就是说,等袭人回到荣府,宝玉趁众人不在房中之时,才觍着脸问袭人:
“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
是呀,是呵,这样写才叫好呢。
24.嗤的一声
置身荣府的黛玉,多少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宝黛钗之间的情感又那么纠结拉锯,再加上身体的孱弱,黛玉一直显得伤感与凄冷,甚至常常有些怪僻与忧郁。但其实她不仅爱哭,也很爱笑。某种意义上,黛玉的爱笑,也是对其人设 (还泪)的解构与超越。
一部 《红楼》,曹雪芹多次叙述了黛玉的笑 (第十七回、第十九回等)。
几乎每一次都是用 “嗤的一声”来描述。
虽然 “嗤”这个拟声字并不独属或专属于黛玉,我记得凤姐与宝钗偶尔也这样笑,但无疑,用在黛玉身上效果最好,也最是传神贴切,所以用得最多最频。我们想象一下黛玉的纤敏个性与忧郁气质,想象一下她那柔弱的身板,想象一下她的樱桃小嘴,她一定不会像湘云那样哈哈大笑,而只会是只能是 “嗤的一声”!连牙齿都绝不会露出来那种,特别会心特别挚真那种。
同样是女孩的笑,第三十五回 “亲尝莲叶羹”,曹雪芹写丫鬟玉钏儿对宝玉的笑就换成了 “哧的一声”,就没有 “嗤的一声”来得巧笑倩兮。
“嗤的一声”,这才是古灵精怪纤敏内敛的黛玉的情感释放与爆破方式。
我们再来欣赏曹雪芹用的另一个拟声字“嗄”。
第二十二回猜灯谜,贾政为了取乐贾母,主动要求参与猜谜活动,他放下架子摆低姿态,尽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与众同欢,说话都是这样式的:
“这是炮竹嗄。”
“这是佛前海灯嗄。”
一个 “嗄”字,写绝了古板者故作亲切、正经人强装随和的那种尴尬、腻歪与荒唐。
是的,对一个叙述大师来说,一个简单的拟声字或语气助词,就是一道杀手锏,足以用来寸铁杀人。
25.镜子
贾府还沉浸在省亲与欢庆的余绪里,再说正月还没过完,所以,大家都在猜谜、斗牌(贾母与老管家嬷嬷斗牌解闷、李嬷嬷打牌输钱迁怒于袭人,晴雯等耍戏赌钱)、赶围棋作耍 (贾环在宝钗那儿输钱耍赖与莺儿吵架)。
宝玉独自回至房中,袭人因生病早已 “朦朦睡去”,晴雯、秋纹她们都寻鸳鸯、琥珀耍戏去了。 “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问她为什么不出去玩,麝月的一番话尽显她的贴心与周全,让宝玉觉得 “公然又是一个袭人”。
宝玉想起麝月早上说头痒,就提出给她篦头,免得干坐着。正梳篦着呢,被进来取零钱的晴雯撞个正着,见他两个的亲密样,便冷笑道:
“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宝玉笑道: “你来,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没那么大福。”说着,拿了钱,便摔帘子出去了。
晴雯虽然是开玩笑,但似乎也半真半假话中有话。从后面的诸多细节,都可以看出宝玉与麝月的关系果然并不一般,如第二十一回宝玉续 《庄子·胠箧》时,把 “钗、玉、花、麝”并举;在泣血般的晴雯祭文 《芙蓉诔》里,宝玉则用 “镜分鸾别,愁开麝月之奁”的句子缅怀了这次篦头经历与晴雯的讥笑。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那段关于镜子的叙事:
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镜,二人在镜内相视。宝玉便向镜内笑道: “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
二人在镜内相视,他们在看什么,他们看到了什么?此处其实大有况味,曹雪芹却未着一字,这样的关节,这一面镜子,正是值得我们细加琢磨的地方。
镜子首先是一个取景框,把两人摄入同一个虚幻空间,恰如上了同一条船,从而产生一种隐约的同盟关系,两人应该看到了这种微妙的同框感及其暧昧性。
镜子又是一种间离工具,它让对镜的两人出离现实,置身于戏剧化的虚拟状态,目光在虚实之间交接,他们一定会看到一种贴身的亲缘幻象,就像看到了一场风月小阳谋。
而宝玉 “向镜内笑”,麝月 “向镜中摆手”,镜子仿佛成了一种特殊的媒介与桥梁,借助它,两个人瞬间建立起一种生活中没有或不便表达的梯己、默契与会意。就像诗歌是整个思维以及对世界感受的加速器 (布罗茨基)一样,镜子差不多就是类似的情感加速器或推进器。
从曹雪芹的身世,我们知道他小时候一定见过很多进口的西洋镜子,他对揽镜弄影的感觉应该很熟稔,对镜子的妖魅般的迷幻性质,也一定有自己的体验与感悟。另外,曹雪芹一定看过 《西游补》里对万镜楼的谐趣叙事 “一窦开时迷万镜,物形现处我形亡”,董说撒欢般一口气虚拟的奇镜 (“天皇兽纽镜,白玉心境,自疑镜,花镜,凤镜,雌雄二镜,紫锦荷花镜,水镜,冰台镜,铁面芙蓉镜,我镜,人镜,月镜,海南镜,汉武悲夫人镜,青锁镜,静镜,无有镜,秦李斯铜篆镜,鹦鹉镜,不语镜,留容镜,轩辕正妃镜,一笑镜,枕镜,不留景镜,飞镜”),想必给曹雪芹留下过深刻印象,并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 “镜子叙事”。所以并非偶然地,一部 《红楼》频繁写到镜子,镜子成了重要的叙事道具。除了第十二回的风月宝鉴 (照见的是欲望与死亡),除了宝玉与麝月一起照的支于镜匣的这面镜子,还有第四十一回刘姥姥误入怡红院撞到的大镜子 (看到了我之非我的幻象),第五十六回宝玉所照的应该也是这面镜子 (让他梦迷)。
人容易在镜子里迷失自我。我们都知道,《西游记》里有照妖镜:现实中的人,在镜中照出的却是妖。而 《西游补》里也有一面照见他者的兽纽方镜。
幻想文学代表人物博尔赫斯,对镜子的看法也是很有意思,他说: “镜子与交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使人口增殖。”这差不多是一种幽灵分身的惊惧感。
同样, 《红楼梦》里的镜子叙事,总体上呈现的无疑是妖魅的、欲望的、风月的影像。
难怪返回屋子的晴雯看到两人对镜心照不宣的样子,说了 “瞒神弄鬼”四个字。
也就是说,借助这次镜子叙事,在宝玉与麝月之间建立的是一种暧昧关系或风月征兆,而非精神的默契或心灵的感应,与此回稍后黛玉跟宝玉在又一次证情戏码中强调的 “我为的是我的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曹雪芹为我们勾勒的宝玉的爱情谱系或坐标中,既有心灵的情的区间,比如与黛玉与晴雯与二丫等 (一部《红楼》黛玉几乎虚弱到了没有身体性,就像那株绛珠仙草;而晴雯不肯跟宝玉一起洗澡,临死之前仍坚守着清白与贞洁);又有肉体的欲的区间,比如与袭人的初试云雨,宝钗与湘云的白膀子。宝玉与麝月的镜子叙事,显然也落在这个区间。
由于儒家伦理与风俗礼仪等文化影响,中国人的情与欲一直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西方人的情与欲则相对统一与融合)。我们看到第二十回刚刚叙述了宝黛的证情明心,第二十一回紧接着就是贾琏与多姑娘淫秽的欲望叙事。在一部 《红楼》中,宝玉的多情与贾琏贾珍贾赦等辈的淫欲始终构成了镜像反照。
一部 《红楼》,唯有宝玉一人,在情与欲之间,在精神与肉体之间,浑沌不分,天然相融,保持着一种理想化的平衡。宝玉不仅是《红楼梦》里的另类,他也是中国文化的异数。在这个空前的惟一的人物身上,当然也体现了《红楼梦》在爱情观方面的现代性。
26.瞪瞪的
第二十二回,宝钗生日,凤姐与贾琏商量礼物的时候,可见在钗、黛之间,凤姐的心理天平明显倾向于宝钗。
贾母要为宝钗庆生 “置酒戏”,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
宝钗深知贾母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
慧黠老成如宝钗者,她可真是比黛玉会来事多了。难怪长辈大多更喜欢宝钗而不是黛玉。
看完戏,贾母喜爱那小旦小丑,就叫人拿肉果和赏钱给他两个。
这个时候,旁边的凤姐忽然笑道:
“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
凤姐的话看似无心却似有意。这个地方,曹雪芹那无风起浪神鬼难测的叙事,已然探入人物的潜意识深处,凤姐对宝钗的偏爱,当然会反作用到黛玉身上,难免就会下意识地去触惹黛玉。敏感的黛玉听到凤姐的话,心里一定会 “咯噔”一声,她知道凤姐说的 “一个人”就是自己,好像怕什么就一定来什么!那一刻,她也许会本能地觉得,霉运就像一道落在自己头上的阴影,怎么也躲不过去。
接下来发生的戏剧性一幕,可比刚才看的舞台戏精彩多了。简直就是一出戏后戏。让人想起童年时乡村看戏之后的兴奋与吵闹。
大家都知道凤姐说的是谁,大家也都知道黛玉的脾气,所以宝钗 “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 “亦不敢说”,独大咧咧的湘云不知究里脱口而出: “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
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
宝玉万万没想到,自己使的这个眼色,竟然导致了一场灾难,就像蝴蝶翅膀的一扇,扇起的是一场风暴。
宝玉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既为湘云好,也为黛玉好,但结果却两头不讨好,糟得不能再糟。
先是湘云很生气,马上收拾衣包准备明天一早就走:“在这里作什么?——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宝玉过来劝湘云,表示自己使眼色的目的是不想让湘云得罪了黛玉,湘云听了越发生气,别人都可以说黛玉,独我湘云不能说? “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头,得罪了他,使不得!”宝玉急得赌咒发誓:“我要有外心,立刻化成灰,叫万人践踹!”湘云毫不领情,怒怼道:
“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恶誓、散话、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的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啐你。”
“啐”字一出口,宝玉知道自己只能离开了。
宝玉没趣,只得又来寻黛玉。黛玉也正生气呢,当然没给宝玉好脸色,而是让宝玉又碰了一鼻子更大的灰!宝玉问黛玉为什么恼,黛玉觉得宝玉明知故问, “拿我比戏子取笑”岂能不恼?宝玉道: “我并没有比你,我并没有笑,为什么恼我?”
对黛玉而言,宝玉 “没有比” “没有笑”当然远远不够。以黛玉的纤敏多疑,她一定感觉到了来自凤姐等人的偏向与疏离,甚至感觉到了那丝轻微却不可忽视的 “歹意”,所以,她就更需要确认并证明她与宝玉之间的那份情与爱。也就是说,她接下来的心理与话语已然涉入证情戏码,因而听上去就完全不讲理了(湘云虽然也耍性子,但毕竟事出有因):
“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
当然,黛玉气恼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听到宝玉巴巴的去劝湘云,听到湘云说她是 “小性儿” “行动爱恼的人”。所以,黛玉的生气实际上是双重的,也是双倍的,她那一刻心理之复杂之微妙,宝玉根本无从理解与体会。也因此,黛玉最后说出来的是气死人不偿命的狠话:
“我恼她,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宝玉无语凝噎,回房躺在床上:
“只是瞪瞪的”。
“瞪瞪的”准确之极!是呵,情难证,证情难,证情差不多就是自寻烦恼,就是自找气受 (就是宝玉后面在偈里说的 “无可云证”)!一边是湘云耍性,一边是黛玉证情,宝玉夹在中间,结果当然只能是 “瞪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