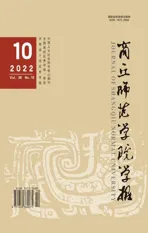徽州传统族规家训对当代乡风文明建设的启示
2022-12-30刘巍
刘 巍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近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留守农村的群体以老人和儿童为主,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治理难题先后出现。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目前所见,许多农村地区存在着一些不良社会风气,严重地影响到了乡村秩序的稳定,亟须得到重视和解决。回顾历史,徽州被誉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标本。当地人民聚族而居,形成了具有深厚内涵的宗族文化。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徽州宗族逐渐形成和发展了一套迎合本族现实需要的族规家训,在修身、治家、事亲、睦邻等方面对宗族成员进行教化与约束,有助于徽州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民风。有鉴于此,本文以徽州传统社会的族规家训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针对乡村社会失序、乡村共同体认同感缺乏等现实问题,将族规家训的道德教化作用与现代乡村治理有效结合,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提供启示。
一、当前乡村民风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不孝之风蔓延
进入21世纪以后,人口老龄化给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农村地区的老人赡养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所滞后,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主要依靠子女的供养为生。但是,由于不少年轻子女都进城求学或务工,留守在农村的老人难以得到晚辈的有效照顾,不孝之风逐步蔓延。根据当代学者的相关调查,目前农村不孝之风主要体现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1]。一些老人不仅在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方面得不到满足,还往往因为“天价彩礼”等原因被子女“啃老”。同时,子女由于身处异地或工作繁忙等原因,无法常伴身边,难以及时关心和问候老人,造成了双方关系的冷漠甚至仇视,引发了各种家庭纠纷。如此一来,农村老人就面临着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空虚和折磨。一些老人因为子女不孝被迫诉诸公堂,不得不将家丑外扬,类似的案例在各地均有发生。
(二)邻里矛盾增多
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村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为主,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在当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伴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来自经济层面的不和谐音符日益增多。由山林土地流转、征地拆迁、旧村改造、房屋交易等事件引发的纠纷不仅造成了邻里关系的紧张,还容易影响基层社会安定。根据相关报道,一些农户因为在宅基地建造房屋影响了邻居的采光,从而造成冲突,还有因为宅基地越界问题而使和谐相处几代的邻里走向反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发展,经济收入来源愈加拓宽,传统的收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家各户之间的经济水平也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影响了邻里和谐,甚至引发了家庭内部矛盾。
(三)铺张浪费严重
在传统时代,铺张浪费就是乡村社会的陈规陋习,民众崇尚勤俭持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地提升,由此也伴随着愈加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根据相关报道,一些地区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过分讲究排场以外,诸如生日、升学、乔迁之类的活动也开始大操大办。这样的支出规模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很多农户的实际负担能力,给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囿于人情、面子等因素,很多农民又难以真正摆脱铺张浪费的做法,使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对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进行大力整治[2]。中央部门的发声和表态,足以体现出农村地区铺张浪费问题的严重性。
(四)教育理念滞后
近年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离开故土前往城市谋生,多将年幼的孩子留置于村庄。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疏离程度明显增加,留守儿童多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老人受制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和传统观念,造成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更为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多农村的家长在经历了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之后,更为在乎眼前的经济利益。在他们看来,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之后,子女就应当外出务工积累收入。特别是在目前许多农村地区彩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继续求学不仅需要投入精力和财力,还会造成就业的延迟,养家糊口的目标都变得困难重重,娶妻生子更加遥遥无期。目前,随着高校不断扩张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报道屡屡见诸媒体,这种情况让很多农村家长更加不愿意让子女继续上学深造。不难发现,上述论调带有反智主义色彩。这种现象蔓延之后,不仅制约了子女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会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储备。
(五)精神生活匮乏
近年来,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硬件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乡村文化设施和活动场所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令人赞叹。但是,本来能够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的设施却陷入了有效利用不足的困境,往往带有形式主义的色彩。相关报道显示,一些农村地区的农家书屋长期无人光顾,农村大舞台沦为了仓库基地,妇女儿童之家则布满了灰尘。目前,留守在农村的一些中老年群众仍然以聊天、打牌、打麻将和看电视为主要娱乐方式。在手机日益普及的当下,还有不少群众通过手机玩游戏、刷视频消遣时光。相反,真正具有积极向上意义的精神文化活动却明显不足,一方面是难以吸引广大群众的关注和热情,另一方面是覆盖面明显较窄,特别是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群众吸引力较低。在这种情况下,留守农村的很多老年群众陷入了精神空虚之中,缺乏合理的价值追求,以至于部分地区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了阻碍。
二、徽州传统族规家训的社会功能及其对现代乡村治理的启示
从概念上看,族规家训也称作族规家法,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用于约束宗族成员言行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通常刻录于家典、宗谱等文本之中,以供时人和后世遵行。族规家训以儒家理念为精神内核,不仅承载了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诲,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风貌。根据赵华富的研究,宋元时代的徽州谱牒并未收录族规家法,直至明代中叶,在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的背景下,徽州社会出现了“风俗浇漓”的现象,对既存的宗族制度形成冲击,促使族规家法大量涌现[3]332。徽州宗族通过制定族规家训对现实危机予以回应,冀望于齐家收族,实现宗族的安定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徽州传统族规家训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族内部,在现实层面往往向乡村社会外溢和拓展,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徽州传统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和文化共识。卞利研究发现,“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和村庄呈现出重叠的特征,宗族的族规家法往往与村庄的村规民约相重叠”[4]340。在这种情况下,徽州传统族规家训就成了人人都须知晓和遵守的日常生活行为指南,即使是族长也概莫能外。清光绪歙县新州叶氏宗族家规就明确规定:“族长不守家规,为子弟者,反复委曲开论。及终不能听,然后会族告于祠堂,以彰其过,更立以次贤者主执家法。”[5]161如此一来,徽州传统族规家训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法律文化价值,不仅为维护乡村秩序作出了积极贡献,更成为徽州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徽州传统族规家训内容丰富,基本覆盖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其中固然包括不少陈旧、腐朽和落后的观点,但也有一些主张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值得重视和借鉴。
(一)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血缘共同体内部的长幼尊卑秩序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徽州社会崇尚儒家文化,孝敬父母几乎成为所有族规家训的核心内容。清嘉庆绩溪县旺川曹氏宗族家训就从父母爱幼的角度论述了子女敬老的合理性:“方其未离怀抱,饥寒、衣食、疾痛、啼嘻,无不关父母心”,父母含辛茹苦将子女养育成人,并为他们寻求谋生之道,因此,“父母之德,实同昊天罔极”[5]31。清雍正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宗族家训更是对老年人心态进行了生动解读:“当体老亲性情,大约记远而忘近,易怒而难喜。且涕唾痰涎虽污秽不免,而偏畏人憎嫌,议论筹画皆迂远难行,而偏喜人商量。”由于长辈的生命岁月逐渐减少,特别容易伤感动情,一方面担心被人疏远,另一方面则为子孙后代心心挂念。因此,“为人子者,须体此意,当时刻不离亲侧,于服劳奉养之余,为之譬喻宽解,以博亲之欢心”[5]14。值得注意的是,子女对于父母的孝敬并非无条件的单向约束,孝子是以慈父为前提的。清光绪绩溪县南关许氏宗族慠叙堂家训就用近似于白话的口吻明确要求:“父亲要做慈父,不要做狠父;儿子、媳妇要做孝子、孝妇,不要做逆子、逆妇。”[5]36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不妨对徽州宗族的经验进行借鉴。地方政府可以发布明文通告,列举不孝忤逆的具体表现,进行公开曝光和集中整治,助力农村精神脱贫。同时,可以由政法机构牵头成立相应的工作组,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在情节严重时可以诉诸法律,对于虐待老人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勤俭持家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懒惰和奢靡之风也在徽州社会有所蔓延。针对这种不良现象,徽州宗族在族规家训中提倡勤俭,希望规范族内子弟的行为。明嘉靖绩溪县积庆坊葛氏宗族家训明确指出,勤俭是生存的重要准则,二者相辅相成,“盖勤以开财之源,俭以节财之流,此生财大道也”,如果放任无忌地吃喝玩乐,必然导致家财耗尽[5]4—5。明崇祯休宁县叶氏宗族家规进一步对勤俭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士农工商四种行业虽然差异很大,但共通之处在于,“惰则职业隳,勤则职业修”。在日常生活中,“然勤、俭原相表里,勤而不俭,奢靡浪费,勤亦无用”。勤劳未必能实现大福大贵,但起码可以免于饥寒之苦,一旦奢侈,则会前功尽弃,因此,“勤而能俭,家道成矣”[5]129。清宣统绩溪县上庄明经胡氏宗族规训指出,节俭的本质是节以制用和量入为出,节俭的对立面是奢侈,“祖基虽厚,一再传而子孙贫不能守者,奢失之也,奢岂可训哉!”[5]111清宣统绩溪县华阳邵氏宗族家规更是明确反对族人在食衣玩乐方面奢侈无度,认为财富具有“难聚而易散”的特点,上百年积累的财富可能会在朝夕之间毁于一旦,“有口之积难应无穷之费也”。至于赌博、嫖娼等挥金如土的做法更容易将财富挥霍一空。因此,“吾宗子弟,当崇俭”[5]164。在徽州的族规家训中,勤俭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应该推崇勤俭,针对铺张浪费严重的现象,可以由乡镇党委政府制订方案,弘扬文明新风,提高群众的节俭意识。同时,成立督查小组,对于违反规定的奢侈浪费行为,坚决予以严肃处理,并形成长效机制。
(三)扶危助困
徽州社会聚族而居,繁衍生息长达数百年。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温情脉脉的亲缘关系。因此,扶危助困也就成了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清光绪绩溪县梁安高氏宗族祖训明确规定,如果家庭经济状况宽裕,可以做一些修桥铺路、赈济灾民、抚恤孤寡等功德之举。对于家境贫寒者而言,也应当“终身存好心,量力做好事”[5]71。民国初年祁门县河间凌氏宗族家训也要求在衣食住行方面对孤寡、残疾的族人进行照料,扶危助困的行为一直持续到养老送终。上述规定的承担者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依次演进,如果全家俱身处困境,帮扶工作则交由宗族承担。宗族内部的扶危助困活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对于漠视族规的行为要进行处罚[5]4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徽州社会扶危助困的行为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宗族内部,清雍正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宗族家训不仅要求对族内“鳏寡孤独及老幼无能者”和“贫病之家”进行关照,还将扶助对象扩大到素昧平生的行路之人:“村前村后桥圮路侧,急当倡众捐修,以便行旅。凡遇盛暑,宜煮汤茗,以济渴者。”[5]17-18这种公益行为不仅体现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和谐与温情,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文明中的公共服务精神。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徽州传统社会的扶危助困精神应当予以继承和发扬。政府部门不仅应该建设常态化救助体系,也应当积极动员民间力量参与生产和生活互助,树立邻里互助的文明新风。
(四)读书向学
在传统时代,读书不仅可以提升个人修养,也可以提升宗族子弟谋生的能力。清光绪绩溪县荆州明经胡氏宗族祖训要求,子弟幼年时期就要接受蒙学教育,如果学习资质尚可,则宗族应当鞭策鼓励其继续求学;即使才智平庸,也应当具备基本的识字水平,习得从商或务农的本领,不能将精力花费在喝酒、赌博、买春等歪门邪道之上[5]72。清宣统绩溪县仙石周氏宗族祖训也明确指出,“一族子弟,无论将来读书成名,即农工商贾,亦须稍读书本,略知礼义”。在此基础上,又对读书人的品格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延聘的老师必须要品行端正、礼貌周到,学生也要牢记师恩,不可以恃才傲物,也不应凭借着读书人身份结交官府,“如果品学都好,就不发达,一样有光门户”[5]77。难能可贵的是,清末科举废除之后,徽州宗族没有因袭守旧,反而紧跟时代,倡导族人接受新式教育。民国初年绩溪县鱼川耿氏宗族祖训特别指出,本族子弟无论智商高低,都应当接受中学以下的国民教育,然后学习一门可供安家立业的职业技能。即使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上中学和高等小学,也起码要在国民学校接受最基础的教育,“否则,不惟不知书,且不知做人道理,安望有谋生技能、自立于天演竞争之世乎”[5]90。在当今社会读书上学仍然是乡村农民家庭摆脱贫困、获得晋升的主要渠道,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应当继承发扬徽州族规家训中的“重学”思想,积极鼓励农村青年积极向学,牢固树立“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动员他们在学有所成之后,用知识回报社会和回馈家乡。同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出台支持政策,为农村学子保驾护航,坚决防止贫困子女因为经济困难失去求学的机会。
(五)和睦乡里
在传统时代,中国人讲究安土重迁,乡村社会的各家各户,往往形成长期共存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双方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明万历歙县黄山谢氏宗族家规提出,邻里乡亲之间应当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如有困难时应当互相帮助。即使偶尔遭遇冲突,也应当及时消解矛盾、重归于好,万万不能留下积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虽百世可同居矣”[5]125。清光绪绩溪县荆州明经胡氏宗族祖训也要求,邻里之间相处不要嫌贫爱富,而应该互相帮忙与扶持,相互之间经常来往,“若矜富欺贫,譬仇诘告,岂有极乎?凡我子孙,不可不知”[5]73。清宣统休宁县富溪程氏宗族祖训家规更是从现实利害关系的角度,认为邻里之间无论是居所还是田地都近在咫尺,双方应当结成融洽的关系,以便在婚丧嫁娶、疾病灾难时伸出援助之手予以救济。邻里之间虽然不是一家,但远亲不如近邻,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双方之间自然应该不生嫌隙。“若不相和睦,则尔为尔,我为我,孤立无助,嫌疑互生,作事难成,岂能长久相处?化民和好,莫切于此。”[5]168乡邻和睦,不仅有助于乡村治理,而且也是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的应有之义。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有关部门要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和热心村民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邻里纠纷的调解工作,避免矛盾激化。也应当加大对传统乡邻和睦思想的宣传力度,号召邻里和睦相处,助力和谐乡村建设。
(六)遵纪守法
在传统时代,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采取乡绅自治的模式,国家与百姓之间的直接联系相对较少,最为关键的互动媒介就是税收。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交粮纳税就成为乡民们遵纪守法的主要内容。清光绪绩溪县荆州明经胡氏宗族祖训明确告诫族人,应当向国家按期缴纳税粮,不要拖欠,以免遭到国家权力的惩处[5]72。民国初年歙县吴越钱氏宗族家训也要求:“朝廷有赋税,及时输将,无敢逾期,此即纳供之忠也。自古治乱不一,幸生盛世,得以优游。休养生息,一饮一食,莫非君上之所赐。凡践上之土而食其毛者,宜何如?报效也。而区区维正之供,所取于我者几何?而抗不输将,岂情也哉?且任土作贡,岁有常额,朝廷责之州邑有司而峻其考成,州邑有司督之图里之胥吏而严其责比。夫图里胥吏于我皆乡邻也,以吾赋之不时而累其受责比,于心何忍乎?州邑于我固父母也,以吾赋之未输而累其缓考成,于心奚安乎?况抗违法重,又不仅累及有司、胥吏已也。凡有田者,即当兢剋自爱,隔岁营办,输纳应期,慎勿偷延时日,以身试法。”[5]44在徽州族规家训中有很多要求乡民遵纪守法的内容,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应当深化乡村法治建设,加强普法宣传,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不仅要让他们遵纪守法,也要让他们懂得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实现乡村地区的长治久安提供法治条件。
三、结论
客观地看,当前农村社会的各种不良习气并非一日形成,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因此,乡风文明建设也不可能另起炉灶,完全和历史绝缘。从历史的维度看,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社会也面临着道德滑坡的困境,但是徽州宗族成功地利用族规家训维护了持续五百年的乡村社会秩序。可见,徽州传统族规家训是净化社会风气和提升村民道德的重要因素,积淀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可以为当代乡村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乡村社会的面貌与历史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科技进步、人员流动、观念变迁和国家权力的下移等因素的存在,传统时代的治理经验不能原封不动地平移和照搬。同样,徽州传统族规家训的基本内容和推行方式也必须进行针对性改造,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其一,就基本内容而言,徽州传统族规家训生成于儒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诸如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陈旧思想,应当予以摒弃。对于诸如子女尽孝、读书向学等方面的细节性规定,也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适当地调整。在工作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指望子女全天候在身边服侍,确实存在难度。同样,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时代,读书向学也不能和接受学历教育完全画等号,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同样可以给年轻人提供未来的生存之道。
其二,就推行方式而言,徽州传统族规家训是在父权家长制的权力笼罩下得以推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包括体罚在内的一系列落后做法。国家基于乡村自治的立场,往往对此不予干涉。从现代文明的视角看,这些做法当然也是应该废除的。当代的乡村文明建设以法治化为主色调,绝不允许私设公堂之类的现象出现。不过,在追求法理的同时,也应注重情理的运用,尤其是要将德治与法治相融合,通过启发、教育和感染等方式,在村民心中树立正确的观念,助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