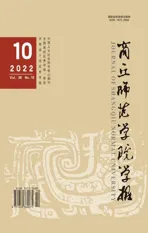解脱生死大宗师
——方以智《药地炮庄·大宗师》释义
2022-12-30韩焕忠
韩 焕 忠
(苏州大学 宗教研究所,江苏 苏州 215123)
在药地愚者方以智看来,《大宗师》其实就是庄子为那些身为真人、具有真知、勤于真学、堪为大宗师的人们所谱写的一曲赞歌,他们解脱了生死,超越了好恶、是非等的两端对立,活得很真诚,活成了真正的自己。
一、旨趣
方以智撰写《药地炮庄·大宗师》的旨趣,即抉择出庄子所说的真人、真知、真学、真正的大宗师具有儒家的血脉和渊源,主要体现在《药地炮庄总论·大宗师总炮》及《药地炮庄·大宗师》的解题之中。
在《药地炮庄总论·大宗师总炮》中,方以智将一切相互敌对的现象都视为生死,并对人类处置生死问题的态度和方式作出了总结。他说:“天以生死炼人乎?人以生死自炼其天乎?往来、动静、好恶、得失,凡相敌者,皆生死也。要且以魂魄之生死,缘督而条理之,由畏而尽心焉,由知而定志焉。屋漏之衮钺,邦家之应违,阳有刑赏,阴有鬼神,此四惧也。存亦乐,亡亦乐,以放而委生死也。聚则有,散则无,以气而凭生死也。立而不朽,没则愈光,以名而轻生死也。安时俟命,力不可为,以数而任生死也。此四胜也。”[1]97方以智将世界上一切相互对立的事物,如往来、动静、好恶、得失等,都视为生死。在他看来,生死是很能磨炼人的意志的,因此人们可以利用生死来磨炼自己,即根据自己精神状况,顺应变化,规划好目标并为得到实现而努力。由于对生死充满敬畏,故而会尽心做好义务;由于知道生之必死,所以会为实现志向而不懈努力。不需要外在的监督和鼓励,对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保持高度的警惕,人所共知的地方有刑罚和赏赐,人所不知处有鬼神的降殃和佑福。这四者使人心生畏惧。有的人活着很快乐,面对死亡也很快乐,将生死委诸放达;有的人认为气聚则有生,气散则归于死,以生死随诸气化;有的人认为生而立德立功立言,死而受到怀念,故而重令名而轻生死;有的人安于所遇,顺从命运,不愿进行主观努力,主张生死由命。方以智认为,这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处置生死的四种殊胜方式。
方以智将“明伦从类,各正性命”视为对生死的解脱。他所深思的是,人们面对白刃交前,也许会无所惧怕。但面对富贵贫贱关、憎爱关,就未必过得去,这能算知生死吗?有些人枯槁自处,对待至亲,如同陌路,能算无生死吗?有些人恣肆妄为,不将生死置怀,能算从生死中超越生死吗?那些所谓的舍弃生死、看空生死,在方以智看来,不免将人诱上悬崖,变为无用之物。无论是因畏死而养生,还是将生命置之度外而达观人生,方以智认为这都不是对生死的解脱,他也不同意一切听天:“天何言哉?天从何来,以何为天,知我其天乎,无可奈何而相与天之我之耳矣。大人曰:天无先后,时其时,当其当。明伦从类,各正性命,贞夫生死好恶之一矣。元会朝夕,薪火并传,虫鼠牛马,自古以固存。裁成尽职,戮无所避。旦宅所共,固如是也。”[1]97其言下之意,所谓天,不过是人们对自己的无可奈何所做的称呼而已。他很认可父亲方孔炤之说,认为天无先后,应当把握时势,做出适当安排,按照身份地位,尽到本性和天赋,生死如此,好恶亦然,时刻坚持这一原则。方以智还推而广之,谓时有久暂,事有对反,自古如此,人们必须尽到裁成万物、辅相天地之职,不能回避必然到来的杀戮即死亡。换言之,安于命运,尽到天职,就是解脱生死。因此他诠释《大宗师》的原则就是:“慎独未发,以炮其实;格物中节,以炮其虚。秩序即变化,变化即秩序,所以炮无实无虚之莽脱也。安用逞诶诒之肆,以坏人耳之耕耘乎?未知生,焉知死,正用以炼天下之生死,藏天下于天下,好不好也一矣。”[1]98即运用《中庸》《论语》,消除《大宗师》中的执着、虚妄、鲁莽、轻浮、恣肆,引导人们由“知生”而解脱生死。
在《药地炮庄·大宗师》解题部分,方以智广引阳明学派之言,具有以良知理解真知的意味。如其引阳明曰:“知来本无知,觉来本无觉。然不知不觉,则遂沦埋。”[1]196意在强调良知的自然品格,非有意而为之。其引罗近溪曰:“《论语》知之次也,是知也,两则正对照。从闻见起知,不是真知。直下了了,方是真知。”[1]196意在强调真知的超验色彩,对当下言行具有管领作用。其引王龙溪曰:“见在可知者,还其知之,不可模糊。其不可知之,涤玄去智,还其不知,不可兜揽。良知非闻见知识,而闻见知识,莫非良知之用。文辞,道之华;才能,道之干;虚寂,道之原。无思无为,良知未尝无虚寂也。沉守虚寂,则异端矣。有物有则,良知未尝无典要也,循执典常,犹拘方耳。”[1]196这段话既论述了良知与闻见知识的关系,又阐明了良知具有超验性(无思无为)和规范性(有物无则)。以下还有钱绪山、罗念庵、方大镇、张鄮西、李湘洲等,并为阳明后学。复引其出家师觉浪道盛之言:“惟非天非人,乃能天能人。于此知得,岂特为天人之宗师?”[1]196具真知即得大自在,其对真知之推崇,甚至远逾于庄子。方以智证成真知即良知后明确表示,彰显真知,就是他诠释《大宗师》的目标:“剑去久矣,乃彩画其舟痕。鹞过新罗,更自夸其好手。不立鹄的,而曰射无不中,是谁不被祸乱?非真知者,岂知此心之有大宗师乎?果然真知,大宗师犹是秕糠。”[1]197如果不具有真知,也就理解不了大宗师;而一旦具有真知,大宗师亦是多余。由此我们可知,真知在方以智诠释《大宗师》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方以智在阐明诠释目标之后,即按照他对《大宗师》的理解,广引诸家之说,对《大宗师》有关真人、真知、真学、真师的论述展开解说,以彰显其中流淌的儒家血脉,将庄子扶上尧孔真孤、儒宗别传的宝座。
二、真人
真人具有真知,故而堪为大宗师。但真知之所以为真知,亦因其为真人所掌握,是以庄子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2]226《大宗师》开篇先说真人,原因当在于此。方以智对于真知之由来、真人之处世、真人之表现等,显示出极大的兴趣。
方以智认为,真人之有真知,无不来自艰难困苦中的真参力究。在他看来,自以为得计的小聪明、小智慧是无须学习的,自然就会,但是真正的大智慧却无法运用出来。如郭象曾说,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仁义礼智信等五种永恒的法则就具足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人们对这种说法多不相信,即便是相信,也无法显示出来。如闻人说,心不是心、物不是物、天不是天,便像掉到胶盆中一般,无法挣脱,那么无论其出其入,都不免要坠落陷阱。“此处未定,则二十篇尾之三知、两端叩竭之无知,皆受用不着矣。生死鬼神,镂空吹影。旋毛星点,交网旁罗。随分举起,触处云雾。知天知人,质俟谓何?又况牛尾巴、干屎橛、花药栏、盌脱丘,甘为所漫,好不自在。惟有偷心死尽,自享万法森罗。不妨雷雨撄宁,庆快青天红日。已而笑曰:庸讵知?”[1]198《论语·尧曰》末尾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矣;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3]285《论语·子罕》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3]159在方以智看来,孔子“空空如也”之“无知”,恰成就其“知命、知礼、知言”之真知;世人因有黠智,故而无法获得如此之真知。对于《周易》所说生死鬼神之事,既已像雕镂虚空、吹动阴影般的难以理解,对于《华严经》所说毛纳尘刹、交光相网境界,便如堕在五里雾中,至于知天知人,质诸天而俟诸人的自信,也是无从谈起。那么就更不要说禅宗语录中常说的那些牛尾巴、干屎橛、花药栏、盌脱丘之类的话头了。而所有这些知识和智慧上的缺陷,均来自对郭象所说“人生七尺而五常必具”缺乏真诚信解和体会。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以养字、患字、当字、定字,剥出真字。文王于《剥》《复》后,不标真卦,而曰无妄。孔子曰:无妄,灾也;大畜,时也。语甚可疑。将谓无妄而行有眚,必赖学问以畜之耶?曾疑此真知而定当否?若有一丝疑,是真善知识。”[1]199其意谓真知须在患难中培养,经过灾难的磨炼。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方以智所认可的真知,是以人类的道德实践为基础并与之密切相关的,此论就等于给《大宗师》中的真人确定了儒家的基因。
方以智同意庄子关于真人处世自适其适的说法,但在对狐不偕等人的评价上却与庄子差别甚大。庄子说:“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也。”[2]232方以智引其师觉浪道盛之言曰:“亡身必真,方是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若狐不偕诸子,个个是菩萨,于大千世界无处不是他舍身命度生处。知此正是自适其适,能役人而非役于人者也。生杀在手,不随人脚根转,真用剑刃上事。”[1]202庄子所看重的是生命,而方以智师徒认为,狐不偕等人为了实践自己的信念宁愿献出宝贵的生命,正是真人自适其适的体现,甚至赞扬他们是能舍身命普度众生的大菩萨。方以智在理解这一问题时,更是加上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他说:“《渔父》篇中,所言圣人与物推移,即屈平之言也。知之而致命于其时位,又何尝不自适耶?庄生战国发叹,宜其翛然也。身遭昏乱,历尽坎坷,忽诵庞公鸡豕之叹,果然先几。不当以食事人,饥而噫矣。木榻北窗,翛然何有?鸿渐鹏怒,不妨支离。”[1]202屈原遭谗被逐,遂自沉汨罗江中。在方以智看来,虽然深明圣人应与时推移的道理,但因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仍然愿意付出生命,就是自适其适。庄子生当战国之世,对此感叹不已,所以他过得非常自在。不过方以智却是身遭政治极度昏乱的时代,经历了诸多的坎坷,多次都是求死而未能。如今虽安坐在北窗之下,木榻之上,但却谈不上什么安闲自在,只不过如《周易》渐卦所说鸿渐、《逍遥游》所说鹏怒一样,将自己的人生变得支离破碎罢了。他甚至认为,“庄子亦化一渔父身,画出精诚之至,即是素逝息影。有见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者耶?杖人以孟子、庄子、屈子,供养一堂,其适人自适处,谁知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耶?愚尝摹《曹娥碑》似屈子,草《藏真》《酒狂》书似庄子,临《座位贴》似孟子,亦足自适,又谁知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耶?”[1]203真人的自适其适的方式多种多样,大可不必拘执于一种,其要唯在于真诚而已。
在方以智看来,真人的表现其实很普通,也很有多样性,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一定的模式。方以智非常欣赏用“义而不朋”[2]234来描述真人的气象,他说:“此形容真人之全机大用也。其状义而不朋,纯用乾元,何处着肝胆血性等字?妙在说真人,似说庸陋人处。入泥入水,秘实显权,正于似处描画。”[1]204其言下之意,是说“义而不朋”(或“峨而不崩”)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真人具有的全部根机和巨大作用,真人虽然表现得非常伟岸,但却天然地保持着一种和气,没有那种让人受不了的严肃。这里把真人描述得非常阳刚,但没有使用任何血性之类的字眼。最奇妙的是,明明是在说真人,但却好像在说庸俗之人一般,这里的描绘只是在与真人相似的地方展开,而隐藏了真人的真实面目,展现的只是其方便善权的一面。庄子谓真人“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2]234,方以智认为这种表述将真人的一(真诚)与不一(因时、地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说:“一与不一,原自妙叶。特地离之,使人夺胜耶?桂丁枯树,甘草复活,一任花开花落,栽树却忌东风。”[1]204在方以智看来,真人的内在之真诚与外在之表现具有一定的紧张性,庄子特地将其揭櫫出来,正是在强调真人的生命力所在。
方以智总结庄子对真人的描述:“四番开演,谓之真人,然则天人师在何等耶?已乃专示人了生死,将谓有生死可了,与无生死可说者,谁堪作宗师耶?苍公曰:既不能横趋而去,又不能画地为牢,只得放开眼孔,看这伙铜头铁额互相推排,鼓粥饭气,撑撑拄拄,依旧可怜生也。一种时命大谬,蹲坐草里。畸才不可忍,中庸不可能,且推敲子桑之户,与他大叫一声。”[1]204—205就是说,在方以智看来,庄子所描述的真人,无不堪作大宗师。方以智生活在遍地干戈、死生为邻的动荡社会中,无法正常实践其自身本具的五常之性,不得已采取一种曲折的形式,如倪嘉庆、方以智之出家为笑峰大然、药地大智等,所谓化身支离,生死以之,即此之谓也。下文中将要提到的子桑户等,就是这样的真人。
三、真知
庄子在《大宗师》中叙过真人种种情状之后,又说道:“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也”[2]241;“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2]242;“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2]246。从逻辑上讲,此皆作为大宗师的真人所有之真知,概而言之,即死生两忘,安于一化,领悟大道。方以智从刀丛中转身而来,对此自有一番真切而深刻的体会。
方以智认为,寻常所谓生死两忘,须在事上磨炼体验,方得真实。他引其祖父方大镇《野同录》之言曰:“人以五行生,即以五行死。道以六根贼,亦以六根用。闭距不得,恃纵不得。中和中节,本自两忘。生死旦夜,平常极矣。至诚无息,即逍遥游。”[1]205意谓人之有生死,不过是水火木金土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罢了;大道因眼耳鼻舌身意的向外驰逐,贪图色声香味触法,而受到伤害,同时也从眼耳鼻舌身意的活动中得到显示和运用。人们既能保持内心境界的中和,又能把事情做得非常合适,就不会忧虑生死的降临,因为这本来就像昼夜交替一样,是最为平常的事情。只要时刻使自己的伦常实践保持在至诚不息的状态之中,便是实现了庄子所说的逍遥游。换言之,方以智世代祖辈都认为真实不虚的伦理实践是生命价值最为重要的体现,而对于死生存亡则视为平常,未尝予以较多的关注。而且方以智还特别强调,此事不只是口头所谓的知道,而是必须要经过世事的历练。他说:“《大学》以听讼结知本,《智证传》引《易》利用狱,正谓贪生无事甲里,自谓委化,忽经毫发许事,两忘在何处耶?睦州云:现成公案,放汝三十棒。你道庄子撄宁,还得已么?”[1]206《大学》在解释“知本”时说:“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3]10强调的是君子必须全副身心地投入到案情中,才能体察其中的真实情况。宋僧石门慧洪觉范著《智证传》,其中引《易》噬嗑卦曰“利用狱”,讲到黄龙慧南因寺庙失火而入狱,看到狱吏为了获得案情的真实,不惜用尽一切办法,由此发明“黄龙三关”之句,勘验天下曈曈往来的衲子,以探明其是否具有真实的悟境[4]189。方以智认为,平日无事之时,许多人自谓能够生死两忘、任运随化,而一旦经历很小的事件,他所谓的两忘、顺化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由此他认识到,庄子所说的撄宁,即在诸多不得已的事情上磨炼出来的智慧和境界,才是最可靠的。我们从方以智的这一诠释中,可以看出其间具有强烈的阳明学意味。
方以智从庄子藏天下于天下之说中得到启发,认为藏身于生死之中就是逃避生死的最好方式。他说:“曾知吾身之遁于地水火风乎?曾知苍天之遁于瓦砾矢溺乎?曾知太极之遁于马毛龟甲乎?此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也。且道四善一化,如何分别?”[1]207地水火风构成人身,人身就藏在地水火风中;瓦砾矢溺本是天然之物,苍天就藏在瓦砾矢溺之中;马毛龟甲从河洛中带来太极,太极就藏在马毛龟甲之中。这些事物皆因无所躲藏而保存下来,是真正的善夭、善老、善始、善终,能安心于造化的运行。佛教厌恶生死,欣求涅槃,但在方以智看来,这些都不过是生死的根本而已。他说:“生死是生死本,求大涅槃,亦生死本。然则,如何得出生死?曰:望梅止渴,击瓢缓筋。”[1]208说生死是造成生死的根本原因,这不难理解;说追求大涅槃,希望从生死中解脱出来也是生死的根本原因,则需费一番思量。盖生死为此岸,大涅槃为彼岸,涅槃生死既然是彼此相对,那么便属敌对的双方,即方以智所谓的生死,是以求大涅槃仍在生死之中,绝不是真正的解脱生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方以智否定了追求出离生死的真实性,认为所谓的出离生死不过如望梅止渴、击瓢缓筋一样,虽然在修行中具有相当大的鼓励作用,但终究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么问题也就来了,既然无法出离生死,那么如何成就大宗师呢?方以智对此早有思考,他自设宾主:“或问:罗汉以入生死为破戒,菩萨以不入生死为破戒,毕竟如何成得师耶?曰: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208所谓出离生死既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在生死中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做自己认准的事情,反而是逃避生死的最好、也是最真诚的方式。其言下之意,大宗师就是这样形成的。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体会到方以智具有生死涅槃等空花的般若学思想,还可以感受到佛教与《庄子》之间的融会与贯通。
对于庄子认为大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2]247的说法,理学家们提出了诸多的批评。如程迥说:“庄子谓道在太极之先者,非也。太极与道不可差殊。超乎象数,则为太极;行乎象数,则为乾坤。太极,大中也,无方无体,因阴阳倚而中乃见也。”[1]209在程迥看来,太极即道,道即太极。就其超越具体事物而言,谓之太极;就其通过具体事物得以体现而言,谓之乾坤。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没有具体的方所和形象,通过阴阳运转的相互依赖而表现出来。张载说:“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谓虚生气,则入老、庄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谓物与太极不相资,形性天人,偏见生病,岂悟范围天地,通乎昼夜,三极大中之矩?”[1]209张载认为,虚空是由气构成的,由此可以理解事物的有无、隐显、神化、性命等都是一气变化的状态。如果认为虚空生气,便会堕入老子和庄子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自然论之中,无法理解有与无的统一性,从而否认事物与太极具有相资相用的关系,对于形体、德性、天道、人为的理解也会产生诸多的偏见,无法领悟最普遍、最永恒、最根本的宇宙真理。对此方以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火弥两间,体物乃见。惟心亦然,体物而节度见焉,道器不可须臾离也。庄子正以虚无为对反之药,而归实于极物耳。太极亦是孔子创说,而随即泯之于阴阳中,表道、善、性,以贯仁智百姓之用,尚不执一,岂执三乎?羲图秩序,物物具此则也。知极知节,变化在中。圣人生而知好学,俯仰远近,格致会通,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故时出而用其极焉。学者定志一心,乃能复见。精入研极,乃通参两贞一之故,不受惑乱。”[1]209—210方以智非常重视庄子“以虚无为对反之药”,即破除执着的价值,同时突显孔子以太极表达秩序的意义,话语中蕴含着遵循秩序即解脱生死的意味。
方以智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曾遭遇农民军的俘虏和拷打、阉党余孽的迫害和追杀,还参与过桂王政权的拥立和策划,且具名阁学,又受到清军的俘虏和胁迫,可谓刀丛寄身、艰难备尝,故而对庄子以生死为夜旦之常的论调产生强烈的认同;身为遗民,寄迹僧寺,恪尽忠孝,终身以之,因此对遵循秩序即解脱生死具有独特真切的体验。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方以智关于真知的疏解其实也是他的真知的反映,都是从生死中得来的人生体验,因此具有其他注疏无法比拟的沉痛感和警觉性。另外还须提出的是,方以智在注疏真人真知时,大量引用了佛教经典和禅宗语录,如《首楞严》《华严经》《信心铭》《宗镜录》《德山麈谈》《大慧语录》等,对此我们虽然无法一一详为解析,但从其中充满佛教般若学破除执着的中道思维可以断定,方以智对《庄子》与佛学的融会贯通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
四、真学
方以智在颜回谈坐忘一段下有一句按语云:“或曰:‘意而子问’与‘坐忘’一段,当置在‘南伯子葵’前后。”[1]223此说可从。因为从行文上讲,在讲过真人、真知之后,应该有真学,而意而子和许由、颜回和孔子所谈论的,与女偊和南伯子葵讨论卜梁倚的学修一样,都是学道的体验,而且意而子和许由的谈话,似乎正是从有关大道的讨论而来。我们这里将方以智注解这三段的文字放在一起,由此可以考察他对真人大宗师如何真诚学问的相关思考。
方以智撰写《药地炮庄》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其师觉浪道盛的嘱托,证成庄子为“尧孔真孤”,因此他们师徒对于作为尧的对立面的许由十分不喜。如觉浪道盛评价许由时说:“《逍遥游》中,以许由寄尧之外臣,见尧能外天下。《大宗师》中,以许由寄尧之外道,见尧之能忘仁义。须知意而子与许由正互相齑。”[1]223《逍遥游》中,尧让天下于许由,觉浪道盛认为这是尧能外天下的证明;许由不受,则显示出许由根本就没有治天下的能耐;《大宗师》中,尧不畏别人攻讦他以仁义是非为黥劓,觉浪道盛认为这是尧能忘仁义是非的证明,而许由谓尧黥人以仁义劓人以是非,则恰恰说明他未能忘记仁义是非。这种理解很有一些天台宗谓诸佛不断性恶而于恶自在的意味。与讥讽许由不同,觉浪道盛对意而子倒是颇为欣赏,他说:“意而子亦是可人。一敲一唱,尽有钩锥。大梅由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将谓用处不换机耶?大小许由,今日被意而子堪破。”[1]223这里一方面用大梅法常的典故[5]174—175肯定意而子的自信,又表彰他以“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2]279一语堪破许由境界的高下,显然是极为赞许的。其俗家弟子薛更生所持论调与师相同:“许由一生败缺,不与覆盖。特识得师之一字,故借以点出。”[1]223他认为,许由一生无足称道者,只是由于还能认识到“师”的伟大,故而庄子在这里提到他,不过是为了陪衬意而子的真诚向学而已。对于师门的这些说法,方以智自然很是认可的。他也很是称许意而子:“既不受方内之黥劓,又岂受方外之黥劓乎?法眼喜渊明,攒眉便归去。何如范武子,不赴远公招?”[1]223意谓意而子自信其心的立场极为坚定,既不会受到方内的蛊惑,更不会受到方外的迷惑。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庄子在此处提到许由,实是大揭其短:“庄生无端椎发许由之塚,挂在了生死铺面行中。许由若知,必若歌若哭曰:我何为被汝黥劓一上?”[1]223我们说,这一段文字历来都被认为是对尧的讥讽,经过方以智师徒创造性的诠释,于是转化成了对尧崇高境界的赞颂。
方以智师徒对女偊向南伯子葵叙述的卜梁倚学道之次第很感兴趣。觉浪道盛首先运用这个次第会通禅教:“此中原无次第。而人于此中,又自有次第之累。于此次第指点之,正不妨与教义相参。直下堪破,又不妨如宗门顿悟。庄生于此,又露出内秘外现之手眼耳。撄宁疑始,安名最奇,此中便有亭毒含灵之妙。”[1]213究明大道,应当顿悟,故说原无次第;但具体学习,还需按部就班,故说自有次第之累。其次第可与佛教义理相互比较,其直下堪破则与禅宗顿悟相当。在觉浪道盛看来,庄子在此隐藏起禅师的本质,示现为传道的女偊,并展现出卓越的命名艺术,如撄宁、疑始等,单凭名字,就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养育、成就灵性的意思。觉浪道盛接着又以这个次第会通《庄子》内七篇:“妙在撄而后成,只此可会通内七篇旨趣。外天下,可通《逍遥游》之尧让许由。外物、外生,可通《齐物》之丧我。朝彻、见独,可通《养生》之薪尽火传。无古今而后入不死不生,可通《人间世》之无用为用。杀生不死,生生不生,可通《大宗师》之天人不相胜。无不将、无不迎、无不毁、无不成,可通《应帝王》之虚与委蛇而未始出吾宗。宜其为大宗师也。”[1]213女偊宜为大宗师,恰可证明其弟子卜梁倚之为真学。方以智对女偊的“撄宁”之说也是非常有感触,他说:“撄宁即动定。文王八卦,艮、震环冬春。而《序卦》为震艮,《大学》震艮,《中庸》震艮,此动静生死之几。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曾格致否?疑始无始,过反复关,乃能不惑,而享其本无动静生死之天。”[1]213其言下之意,那些从动心忍性中获得的认识和体会才是最深刻的,才能成为自己慧命中最为坚固的思想底蕴。但方以智毕竟是禅师,他在肯定女偊论道的同时,更加强调学者的自信自肯,是以又说:“吾闻道矣,看女偊面皮厚多少?好肉剜疮,徙痈高价耶?即令七层九转,一总抹杀,犹是半边。我作子葵,只与一蹋蹋倒。”[1]213—214从而展现出既虚心接纳他人指导、又重视自己心性体会的真正学者风范。
方以智将颜回的“坐忘”视为其真心精进修学的起点。他说:“颜子心斋、坐忘,乃自通一消息。夫子曰果其贤乎,犹恐坐在无事甲里,拈一同字,不落边际,何处着个好字?所谓一化之所待,安得有常?即是无住生心,正与他枯木上生花。夏时、殷辂、周冕、韶舞。此时即已密付。请从而后,犹云末后句也。异日,子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可见坐忘后,忒杀精进在。”[1]223—224孔子教颜回心斋,颜回向孔子说坐忘,注庄者每以此为庄子学行之极致,特别是在颜回向孔子叙述过自己坐忘的体验之后,孔子说:“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2]285很多人认为这是孔子对颜回的印证。但在方以智看来,孔子谓颜回“果其贤乎”是担心他以此为究竟,“同则无好”是肯定他不再有所执着,“化则无常”是表彰他认识到事物变化的必然性,“请从而后”则表明此后还大有事在。意谓孔子看到颜回已心无所住,认为他堪受咐嘱,于是将其平生本怀,即“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3]238,悉数付与。颜回去世,孔子不无遗憾地说:“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3]164方以智认为,这是孔子对颜回坐忘之后开始勇猛精进真正学习的赞叹。当时有人主张这一段应删除,方以智不赞成,他说:“此是火炉旁边大口,到此不觉真情迸出,无所回护,痛呼一声。将谓白马昙照叫苦苦,非大宗师耶?不然,纵说玄妙,与真天地,犹隔一膜。不见道止有一月,无第二月。”[1]224在方以智看来,颜回固然是知道真学的好学生,孔子更是善于锻炼学生的好老师,他们师徒二人关于坐忘的这番对话,也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就像白马昙照临终叫苦[5]247,并不影响其为大宗师一样,这些话也都是他们真实精神境界的反映。
中国禅宗历来都非常重视师资传承,但要找到真才实学的学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觉浪道盛与方以智师徒二人看来,《大宗师》中的意而子、卜梁倚、颜回等,能超脱仁义、礼乐、形骸、肢体乃至生死的束缚,能入于不生不死之域,同于大通之境,逍遥游于摇荡恣肆转徙之途,可谓都是能够真学的好学生。而方以智从觉浪道盛受大法戒,得与曹洞法脉,除感念其收留之恩外,对于其卓越胆识、艰苦修行、丰富学养、灵活教化等都极为钦佩,认为是稀世难逢的大善知识,因而也是真正大宗师。我们说,方以智接受觉浪道盛付托,努力著成《药地炮庄》一书,就是他真心向觉浪道盛学习的集中体现。
五、真师
在《大宗师》中,像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和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孟孙才等人,都是已经勘破生死、从生死之中解脱出来的真人,当然也是真正的大宗师。在方以智的诠释中,他们在生死之际,都忠实地践行了孔子关于生死的思想观念。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为友。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子来将死,子犁往问之。子舆、子来当此生死离别之际,对故人表达了安时处顺、唯命所适的人生感悟,显示出解脱生死的豁达与超然。方以智出家师觉浪道盛于此看到庄子与儒家的一致:“儒者以修身为本,至能易箦启手足,为全而归之。若庄子则以外生为宗,即天地覆坠,不与之变,撄而常宁,疑而无始。佛法未来,乃有创见,安得不谓之儒宗别传乎?”[1]215在觉浪道盛看来,曾子在易箦之际启其手足,是曾子视死如归、超越生死的证明。庄子《大宗师》以“外生”即解脱生死为宗旨,故而在天地翻覆的大变动中,也保持着内心的安定与宁静。庄子生活在佛教尚未传入中土的时代,这表明庄子对生死的超越无法得自佛教,而只能来自儒家的传承。方以智更是为庄子的豁达和超然从孔子那里找到了依据,并对子舆和子来的临终说法进行了佛学化解读:“子之所慎:斋、战、疾。盖门人摹写夫子之空空心法也。常时戏怠,斋时则诚,然犹有懈。战则轮刀拼命,何有他心?然犹有托者。疾则万念皆休,一切无所用矣。维摩室中一榻,以病而卧,为人解拈释缚,胜似诵千卷经。杖人曾曰:贫病死,是三大恩人。不见曾子发喊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药地肱已三折,确然感恩刀头,要须寂灭冷浇,始博闲中一笑。且如《德充符》扮出罪废残丑,《大宗师》扮出贪病死丧。看此者,闲而无事么?正恐闹在。”[1]215—216孔子以“空空如也”之心处疾病,示一切无所用,正是其解脱生死的表现。子舆、子来临终说法,与维摩诘卧疾一样,具有为人解除生死恐怖和畏惧的作用。觉浪道盛以贫穷、疾病和死亡为“三大恩人”,曾子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都是解脱生死的证明。而方以智本人也是迭经生死,故而非常感激死亡降临,期盼寂灭的实现,所以才会在人间世扮演《德充符》《大宗师》的角色。很显然,方以智这段话中包含着他自己对生死解脱的独特体验。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为友。子桑户死,孔子遣子贡前往助丧,见孟子反、子琴张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遂责以无礼,不想反被嘲笑:“是恶知礼意!”[2]267子贡还报孔子,孔子谓彼游方之外,自己则愿意与子贡相忘于道术。方以智师徒在解释这一段时对“礼意”予以较多的关注。方以智说:“《孔子家语》曰:曾皙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可悟浴沂风雩,是礼意也。而狂者专袭其倚门而歌乎!”[1]218曾皙曾经想恢复礼教,并受到孔子的称赞。曾皙在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一起侍坐孔子时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3]188—189方以智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曾皙所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就是“礼意”,与传统以曾皙是鲁之狂士颇为不同。方以智还广引众言以释“礼意”:“主静或挠于势,主敬或泥于貌,惟至诚无成位、无定时、无繁简、无拘放。《中庸》所谓致曲,与从容一也。登天游雾,正是颠实扬休。养生送死,莫安于礼,其意在此。”[1]218意谓礼是内心情感的流露,只要内心情感真诚,那么在外在表现上采取的方式就是合适的。孔子从生死一气的角度,对孟子反、子琴张的编曲鼓琴、临尸而歌给予肯定。觉浪道盛认为:“此夫子解其礼意也。原始反终,故通昼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说。朝闻夕可,犹有疑耶?”[1]219生死既然为一气之所化,就是必不可免的事情,只能是坦然接受而已,因此也就无须悲伤,更不必采取那些非常复杂、烦琐,但明显没有实际的思想情感作为基础,因而显得非常虚伪的所谓治丧礼仪。在方以智师徒看来,这自然是孔子与孟子反、子琴张一样已经解脱生死的证明。对于孟孙才在母亲去世后,虽然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但却以善居丧闻名于鲁国。方以智也是这样理解的,将其视为孔子已经解脱生死、堪为大宗师的体现。
在《大宗师》之末,庄子说到霖雨十日,子舆裹饭往食子桑,闻其若歌若哭,问之。子桑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2]286方以智引其业师虚舟子王宣之言曰:“各理掀尽,止此一实一真。曰命也夫,表其穷尽而至命也。天乎人乎,非衰飒语。求其至此极者不得,痴儿饭袋破矣,不生不死之法身亦推倒矣。若歌若哭,寄其自得。”[1]225人间世的一切既然都是由命决定,生死、寿夭、贫富、穷通便属于无可奈何之事,那么人生在世自当安时处顺,乐天知命,这也是解脱生死的体现。方以智还曾引王阳明之语,证明致良知即圣人安命之极则:“道家说虚,从养生来。佛说无,从出离生死来。圣人只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这些子意。”[1]215阳明意在突显致良知作为解脱生死之方相对于佛道两家的优越性。方以智对于致良知可以解脱生死虽然无异词,但他同时又指出庄子与佛教其实并不执着于养生与出离,从而显示出更为宽广、更为宏阔的思想视野。他说:“曾知庄生自破,佛亦呵无乎?生死昼夜,本自安顺。素位时措,学诲弦歌,正是行起解灭,何用帖一命字,作弄放憨耶?”[1]215实则在方以智的朋友中,如笑峰大然倪嘉庆、涉江子陈丹衷等,都能弦歌以终老,表现出解脱生死的超越与坦然。三教圣人,就是教人破除执着以各安性命的,其中儒家固然属于正道,而佛道两家虽为别路,但在天崩地裂的特殊时期却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用方以智的话说就是:“中和虽腐,随顺觉性,有谁不被薰耶?医理本明,历症辨药。无病各安茶饭,须申盥洗家常。然则别路弦歌,聊当奏乐以消食也得乎?”[1]227在方以智看来,生死本属平常之事,因此真正的解脱生死,就是在生死到来之际,能够以平常心处之,安之若命。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与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孟孙才这些人,无论是面对自己的死亡,还是面临好友或至亲的去世,都能坦然接受,安之若素,并以自己愿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临终送别之意,因此庄子认为他们是真人,是大宗师,对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欣赏之意和赞颂之情。庄子在妻子死后的鼓盆而歌,其实就是现实版的孟子反、子琴张编曲鼓琴相和而歌,是对他所理解的“礼意”的真诚表达。而方以智更是从《大宗师》中看到庄子在观念和实践上与孔子思想的一致性,并将其置入儒道佛三教相互融会和贯通中进行理解、诠释和接受,从而形成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力量和心灵寄托。
六、结语
方以智对《大宗师》的诠释,确实消除了原本具有的那种因旷达而产生的恣肆,因超脱而显现的消沉,因愤恨世俗礼仪对人性扭曲而导致的偏激,无论是真人、真知,还是真学和真正的大宗师,都不再具有原来的那种神秘感觉,其情感的真诚和真实,思想实践的直率和自然,学习进程的坚持和虔敬,乃至面对生死的那种超脱和淡定,得到充分的彰显,从而体现出人性美的熠熠光辉。可以说,方以智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使他对觉浪道盛提出的庄子为尧孔真孤、儒宗别传的说法形成了强烈的心理认同,因而将庄子视为自己在战国时代的同心和知己。明乎此,则不难理解,方以智对《大宗师》的诠释,其实带有强烈的孤独、苦闷和愤激的思想倾诉和心理释放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