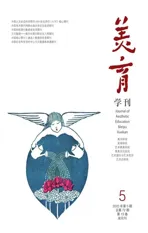试探16至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艺术趣味的接受
2022-11-11白薇臻
白薇臻
(南京工业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长久以来,中西方文化间的彼此影响已被视作“世界历史上自文艺复兴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具体到艺术领域,“东西方的交流,极大地开阔了艺术家的视野,有时也开阔了其作品受众的眼界”。但诚如迈克尔·列维所言:“艺术绝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同样,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和理解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西方艺术理念的时代变迁、中西方历史文化语境的巨变、西方视野下中国形象的“摆动”等发生鲜明的阶段性嬗变。目前,学界关于中西艺术的交流互动、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等论题均已有所探讨,但对中国艺术趣味如何在西方发展演变尚未做出系统梳理,对造成这种阶段性嬗变的深层文化逻辑也语焉不详。因此,本文通过梳理16至20世纪初中国艺术趣味在西方的发展和嬗变的基本历程,探讨产生嬗变的原因,由此呈现中国审美趣味在数个世纪中对西方艺术的发展起到的助推作用和影响价值,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之于西方的积极影响。
一、16世纪中西艺术的初遇
关于早期中西艺术的交流互动,英国著名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苏立文曾在其专著《东西方艺术的交会》(,1989)的引言中写道:“西方美术和远东美术之间的积极对话开始于16世纪。”大概是从159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时才真正拉开序幕。但西方对中国艺术品的接触和感知要远早于这个时期。从13世纪开始,西方有关中国的游记便层出不穷。中国在其中被描述为一个地域广袤、繁华美丽、物产丰饶且盛产神奇的丝绸、瓷器、茶叶的东方国度,充分体现出西方社会在转型期对世俗乌托邦国家的向往。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审美艺术的载体例如精美的丝绸、瓷器、漆器等,早已通过贸易传入西方并很快成为上流社会热衷和追逐的对象。这些在质地、纹饰和工艺上都迥异于西方审美的中国商品,让西方社会朦胧地感受到中国在装饰艺术方面的高超。随着中西方交流互动的日益深入,自16世纪开始,大批西方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其中,耶稣会传教士在将西方的绘画作品、创作技法、艺术理论等引入中国的同时,也向欧洲社会介绍中国艺术的基本情况,成为沟通中西艺术的关键桥梁。凡此种种,为中国艺术美学在西方的最初接受提供了基本前提。
因此,西方对中国艺术趣味的感知和赏析最初得益于某些中国艺术品的输入,铜版画、屏风画、墙纸画等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在1667—1669年间的收藏品清单中就包括中国的镶板屏风,上面绘制了风景、人物、花鸟等中国式图画。中国的手工制墙纸也成为欧洲家庭钟爱的装饰物。基于此,西方社会在初期对中国艺术的接受仍处于器物层面和装饰艺术,并未深入对中国审美理念的阐释。所以,与其说这一时期他们接触到的是真正的中国绘画,不如说是各类艺术品的装饰画。因此,西方在初期几乎未对中国美学理念进行详细阐发,即便有所介绍,也多通过对比中西绘画来批判中国的传统绘画技法,这在最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群体中颇为常见。
总体来说,传教士在赞美中国器物的精美和奇特之余,对中国绘画却较少肯定,尤其批评其缺乏西方绘画的透视知识、明暗对比、写实倾向和特征。比如利玛窦就认为:“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在工艺品上;但是在制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法国耶稣会士李明也指出:“除了漆器及瓷器以外,中国人也用绘画装饰他们的房间。尽管他们也勤于学习绘画,但他们并不擅长这种艺术,因为他们不讲究透视法。”相较之下,西方的绘画知识和技法反倒很快被中国画家自觉吸收和运用,一些传统的中国画中也出现了西方绘画的特征。
随着中国丝绸、瓷器、漆器、屏风等在西方的畅销,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中国器物,以及上面绘制的独特花纹很快便被西方人接受,以此延伸出来的新的绘画主题和西方人的改造或仿作也随之出现。首先,中国式主题开始出现在西方绘画作品中,其主要特征为描画中国人形象、中国器物和其他中国式花纹。毫无疑问,彼时中国瓷器是整个西方的宠儿,而垂柳青花图案的瓷器更成了中国艺术品的代名词。因此,“自16世纪开始,中东或欧洲人绘制的水彩画或油画,便屡屡出现景德镇的青花瓷”;德国画家丢勒在1515年创作的素描作品中也有两件中国瓷瓶;“到了17世纪30年代,中国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大量出现在了荷兰的静物画中”。其次,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捧也引发了西方仿造或改造中国艺术品的热潮。其中,对陶瓷的仿制一直延续到之后的“中国热”时期,例如荷兰的代尔夫特(Delft)和法国的纳韦尔(Nevers)在17世纪成功仿制大量中国陶瓷,并在西方广泛交易和传播。直至18世纪初,德国梅森瓷器的诞生才翻开了欧洲制瓷历史的新篇章。当然,西方在此“‘挪用’了中国丰富的青花陶瓷及其他陶瓷艺术,只不过在此过程中‘清除’掉了中国的指涉痕迹,然后借来丰富它自己的瓷器艺术”。除此之外,这些早期抵达西方的瓷器也免不了被欧洲人改造的命运。欧洲人总会依据自身的习惯和喜好,给它们安装上华丽的、镀金或银质的金属配件,甚至在器物上镌刻铭文和家族徽章。传统的中国器物也因此既显得中西合璧又变得不伦不类。
综上,中国艺术趣味在西方的最初接受只停留在中国装饰艺术上,未及深入高雅艺术的核心。其具体表现有二:一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拼贴和改造中国艺术元素,这些改造后的创作虽然也有中国要素的植入,但更多是以此来迎合西方对中国情调的想象;二是在论及中国绘画时,不论耶稣会传教士、画家,还是艺术鉴赏家、评论家,总现出傲慢的姿态,指责中国绘画缺乏基本的透视观、明暗法,因此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德国艺术史学家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于1675年出版的《德意志学院》()堪称“西方第一部评价中国绘画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即评价中国艺术缺乏影子的轮廓、空间的深度、浮雕的效果、再现的真实以及对自然的效仿,因而是与西方绘画迥然相异的艺术。桑德拉特对中国艺术的这番评价应该可以代表当时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普遍态度。
二、欧洲“中国热”时期的中国艺术趣味
17、18世纪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第一个高潮,兴起于17世纪中叶的“中国热”令欧洲对中国的美化达到了顶点,中国艺术趣味也在西方广泛传播。这场从法国、荷兰兴起并最终波及整个欧洲的浪潮,推动了极具异域风情的“中国风尚”或“中国趣味”,装饰着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正如苏立文所言:“这股席卷欧洲的中国风尚,或拟中国风尚,只限发生在次要的、装饰性的艺术范围内,或者是在像于埃和皮耶芒的阿拉伯式图案及拙劣的仿制品上,还有主要采用洛可可风格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家具、纺织品和墙纸上。”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美学艺术在西方的发展仍限于表层的繁荣,对西方主流艺术的影响仍十分有限。比如,出口到西方各国的中国瓷器无论在风格、色彩和样式上都与中国本土的传统瓷器相差甚远,大多是为了迎合西方审美趣味而特制的出口商品。欧洲人由于不了解中国艺术的核心,所以认为器物上“异国情调的、精雕细画、繁复华丽,甚至怪诞离奇的风格,都可能是中国风格”。由此可见,“中国热”在欧洲兴起离不开其出于自身需求对中国艺术的想象,以至于被西方人接受、喜爱和阐释的中国艺术风格,于中国人自己都显得十分陌生了。
当然,中国艺术元素仍直接或间接地渗入了欧洲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中,并在园林艺术设计方面独树一帜。因此,苏立文评价道:“虽然中国对18世纪的欧洲艺术影响甚微,然而还是有理由相信,中国美学思想最终以间接和微妙的方式对欧洲风景画产生了影响。不过在园林设计方面,其影响是立竿见影且具有革命性的。”可见中国园林艺术在17、18世纪首先引发了欧洲园林艺术的改革。在英国,中国园林那讲求顺应自然、错落有致、移步换景的美学思想和设计风格,经由英国园林专家威廉·钱伯斯和威廉·坦普尔爵士等的推介和实践,成为英国反拨欧洲传统园林过分强调对称规整、几何比例、人工雕琢的重要借力。因此,中西合璧的“英中式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首先出现在了英国,直到现在还作为中国艺术之于西方建筑的影响范例而存在。此外,中国园林艺术也间接影响了西方的风景画创作。苏立文在论著中对中西方的园林艺术和风景画技巧做出了精辟的对比:
中国园林的概念与西方园林对于风景绘画美的追求可以相互媲美,而二者又有微妙的差异。中国园林是微观式的,它在时间中展开,就像中国山水画卷一样,观赏者一边舒缓开卷,一边想象自身在山峦湖水中的游历;欧洲园林风景画的理想概念,体现为像观看一幅风景画似的对于美景的一览无余,正如这个词义所指,是一系列从选定角度观览到的经过认真构思的图画:这里是普桑,那里是洛林,下一个是萨尔瓦多·罗萨。中国人的概念是接近自然的,或至少看起来自然的;欧洲人则是静态的,赞赏人造加工。西方风景画似的园林从一个画面轻易地转移到另一个画面,具有连续性,其感觉仍然是从外部观看一个接一个的由框架割断了的景观——这在中国山水画的美学观念中属于最低的范畴;中国园林则是进入一个身临其境亲自感受的自然世界。
可见,中国园林移步换景的特色与山水画散点透视的技法,让绘画变得灵动自然、绵延悠长,充满无尽想象和无穷韵味,而这正是西方风景画所缺失的特质。因此,尽管此时欧洲艺术家仍不愿意以“理解和接受的眼光看过一幅中国山水画”,但在布歇、华多等洛可可时期有影响力的画家创作的风景画中,大量的中国主题已经逐渐显现。他们对线条、构图、比例等艺术技法的运用,亦显示出中国山水画的影子。
除此之外,作为与西方古典主义相对立的他者,新奇、混杂、怪异的“中国风尚”对西方艺术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助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在欧洲的兴起和发展。诚然,洛可可风格是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变奏,但其发展更离不开中国艺术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将“中国风尚”之于欧洲艺术的影响概括为“洛可可之风”。对此利奇温在其著作《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细致阐述了“中国风尚”与洛可可风格在瓷器、漆器、刺绣品、壁纸、绘画、建筑、戏剧及文学等诸多方面的相互融合与影响,从而指出:“罗柯柯艺术风格和古代中国文化的契合,其秘密即在于这种纤细入微的情调。罗柯柯时代对于中国的概念,主要不是通过文字而来的。以淡色的瓷器,色彩飘逸的闪光丝绸的美化的表现形式,在温文尔雅的十八世纪欧洲社会之前,揭露了一个他们乐观地早已在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中国审美对洛可可艺术的影响表明,中国艺术趣味在“中国热”时期成了欧洲摆脱以智性、整饬、拘谨为特征的古典主义艺术,寻求艺术新风的重要异域资源。
由此来看,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较之初期有了较深入的发展,但中国的高雅艺术及其美学理念仍被西方忽视。因此,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写道:“他们对于中国艺术天才所擅长的宏伟和庄严,无动于衷,他们仅只寻求他那离奇和典雅的风格的精华。他们创造了一个自己幻想中的中国,一个全属臆造的出产丝、瓷和漆的仙境,既精致而又虚无缥缈,赋给中国艺术的主题以一种新颖的幻想的价值,这正是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同样,汉学家劳伦斯·宾扬在1927年出版的著作《欧洲收藏的中国绘画》()中才会发问:“当瓷器、漆器、纺织品和中国风中的所有其他东西在欧洲长期受到如此狂热的青睐时,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却没有欧洲人有好奇心去研究一下,除了所有这些精美的装饰品之外,中国是否存在堪与欧洲的伟大流派相媲美的创造性艺术。”
三、19世纪中国艺术影响的回落
随着“中国热”在欧洲范围内的落潮,19世纪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接受热情也逐渐冷却下来,“中国艺术在欧洲的影响成为一股潮流,骤然涌来,又骤然退去,洪流所至足以使洛可可风格这艘狂幻的巨船直入欧洲情趣内港”。到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对中国艺术品的热情被新兴的严谨的古典主义浪潮吞没,欧洲与东方的短暂恋情到此结束”。
中国艺术在西方的回落,一方面与欧洲艺术旨趣和审美理念的转变相关。因为“新古典主义的品味与中国趣味的‘迷人’特点显然不大相容,新古典主义的装饰艺术中着力表现希腊和罗马精神的冷淡的优雅与坚硬,这与罗可可时代受人钟爱的异国情调相去甚远”。另一方面则与中国形象在西方的跌落以及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利用策略的改变有关。随着西方价值观、进步观、自信心的确立,一个在他们眼中正在走向衰败和沉沦的中国必定无法给予西方任何启迪。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学者受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的影响,对中国艺术的评价多为负面,且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1804年,马嘎尔尼爵士使团的审计官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在其出版的《中国旅行记》()中抱怨中国绘画不能准确运用光线,缺乏焦点与明暗对照。他写道:“说到绘画,只能将之视作可怜的涂鸦,它们无法画出许多物体正确的轮廓,无法运用恰当的光影给出形体的框架,也无法涂上漂亮的色调,以便使其与自然的色彩更加相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和设计师欧文·琼斯(Owen Jones,1809—1874)对中国艺术的评论则更具代表性。罗斯金不但猛烈批判了中国的偶像崇拜,还以帝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否定中国出现过伟大的艺术。因此,萨义德指出:“罗斯金的劝告性的语调中令人信服的是,他不仅强烈地相信他的主张,而且把他关于英国统治世界的政治思想和他的美学与道德哲学联系在一起……政治与帝国的一方面包含着并在某种意义上保持着美学和道德的那一面……在罗斯金看来,她的艺术与文化将依赖于一个强化了的帝国主义。”参与1851年世界工业博览会的英国设计师欧文·琼斯在其1856年出版的著作《世界装饰经典图鉴》中批评中国装饰艺术时说:“尽管中华民族拥有灿烂悠久的文明,并远远早于我们达到了实用技术的巅峰,然而在工艺美术上他们似乎并没取得多大的成就。……从进口到英国的大量用途广泛的物品中,我们已经熟知了这个民族的装饰艺术,它似乎还未能超越早期人类文明的阶段:他们的艺术是停滞的,既无发展亦无倒退。从纯粹造型上来说,他们甚至落后于新西兰人;不过,与所有的东方民族一样,他们拥有一种调配色彩的天赋。可是,这只能称为天赋而已,而不能算是成就,它与纯粹造型形式的获得不一样,纯粹造型形式的获得必须经过一个更为细腻的过程,必须具备更高的天赋,那些艺术粗胚必须经过几代艺术家们持之不懈地捶打。”毋庸置疑,琼斯的这番评价受到19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化普遍贬低的时代氛围的影响,不但透过西方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有色滤镜看待中国艺术,而且将艺术完全政治化,通过歪曲中国的装饰艺术来抨击中国的民族性。即便他也赞同中国人对色彩的出色运用,但他仍认为:“中国的装饰艺术忠实地反映出了这个民族的独特之处,它的总体特征便是怪异——我们不能称之为多变,因为多变也是想象力丰富的一种谑称。可中国人却是非常缺乏想象力的,与此相符,他们的作品也缺少艺术的最高准则——理想化。”这是19世纪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抨击中国艺术的典型论调,其深层的文化逻辑与19世纪末甚嚣尘上的“黄祸论”和20世纪初“傅满洲”系列小说的创作动机类似,显示出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盲目排斥和扭曲。
四、20世纪初中国艺术的“复兴”
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再次碰撞的历史性时期。在艺术领域,“此时的艺术家不仅相互借鉴对方的装饰性的题材内容,他们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对方的艺术主旨和艺术理想”。西方的艺术家、艺术批评家们惊讶地发觉,中国艺术中竟然蕴藏着长期被忽略的珍贵宝藏,而且恰好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理念高度契合。因此,以绘画、书法、雕塑、壁画、青铜器等为载体的中国高雅艺术形式,又一次以强劲的姿态回归西方人的视野,并与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一道成为对抗旧有美学理念的重要合力。中国艺术在19至20世纪之交的西方受到如此热爱和推崇,以至于诗人庞德、艺术批评家刘易斯·恩斯坦(Lewis Einstein)和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等西方知识精英视中国为新的希腊,将中国艺术之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等同于希腊文化之于文艺复兴的深刻启迪,以此猜想中国艺术将会成为西方现代艺术一次新的复兴的模式。
中国艺术趣味在西方的再一次勃兴有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首先,帝国主义在19至20世纪之交,通过多次侵略、探险、考古等活动发掘了大量的中国早期艺术品。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造成难以胜数的中国青铜器、唐宋瓷器、佛教艺术、卷轴画等的外流,并在西方引发拍卖、收藏、展览中国艺术品的热潮,从而“打破了古代中国收藏传统的狭窄视野,造成了中国收藏于全球范围内的现代性转变”。其次,思想上则受到了20世纪初西方兴起的反思启蒙现代性浪潮的影响。当以工具理性和进步时间观为宗旨的启蒙现代性遭受质疑时,西方的有志之士怀着对西方文明的忧虑,重新将目光投向东方,希冀从中获得自救良方。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艺术审美理念也因此进入了西方学术研究的视野中。尤其是西方艺术美学在朝着形式主义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始终将中国艺术作为自身参照和学习的对象,其对中国艺术元素的汲取和运用较之以往也更为自觉、成熟和深刻。
随着中国艺术美学在西方的传播,阐释和研究中国古典艺术观念的论著不断涌现,积极推动着西方的中国艺术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1905年,赫伯特·翟理斯出版的《中国图像艺术史导论》是欧洲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12年,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出版《中日艺术的纪元》,他的论著《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在1918年经埃兹拉·庞德编辑后出版,于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著名英国汉学家劳伦斯·宾扬先后出版《远东绘画》(1908)、《飞龙在天》(1914)、《敦煌绘画及其在佛教艺术中的地位》(1921)、《英国收藏中的中国绘画》(1927)等著作,并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公元四世纪的一幅中国画作》《大英博物馆白翼展览馆的中国画作》等一系列论文。宾扬的亲密好友、汉学家阿瑟·韦利也相继出版《禅宗及其与艺术之关联》(1922)、《中国绘画研究概论》(1923)等论著,系统介绍了中国艺术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特征,成为现代主义者接触、理解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媒介。这些论著的出版为西方了解中国高级艺术开了一扇明窗,同时也有助于西方学者匡正以往对中国艺术的偏见。著名汉学家费诺洛萨就认为西方艺术过于狭隘,而远东拥有高级的文化。尤其到了宋代,完全可以和古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顶峰时期媲美,因为儒释道的文化传统在此时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当时欧洲卓越的艺术收藏家、鉴赏家如拉斐尔·佩楚西、宾扬等,亦从中国宋元明的画作中发现了个性的表达、悠远的意境和抽象观念的呈现,认为中国画唤起了观者的情感共鸣,将外部自然上升到人类思想的高度,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中国人将空间视为‘平面’,让观赏者去找寻自己恰当的视角,像极了现代的‘平面’绘画”。
20世纪初中国艺术真正进入西方主流艺术视野并直接助推了现代主义的发展,对西方美学理念产生了直接且重要的影响,这是前期未曾出现的崭新局面。1903年在伦敦创刊的《伯灵顿杂志》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阵地,但它同时也是20世纪西方刊发中国艺术研究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截至1934年9月,《伯灵顿杂志》共刊登了250余篇有关中国艺术的论文,广泛介绍西方在中亚的考古发现,阐释中国艺术哲学和品评中国艺术作品。例如在1913—1914年的《伯灵顿杂志》中,宾扬便刊文评价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的发现:“大多数人都几乎没有意识到有多少有关古代艺术的第一手资料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的曾祖父甚至是我们的祖父都一无所知的……它揭示了其存在被忽略的文明古迹,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印度艺术,以及世界上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的艺术——中国的唐朝。”弗莱也在1912年发表的《中国沙漠中的遗址》中认为斯坦因的探险一方面揭橥了东西方在早期的充分融合,且西方艺术很可能源于这些影响的潜流;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艺术与中亚文化间的相互渗透、融合、影响等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关注。1917年,韦利在《伯灵顿杂志》上公开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一幅中国画》,评论了由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摹本。1920年至1921年,韦利又陆续推出“中国艺术哲学”系列文章,包括了谢赫、王维、张彦远、郭熙、董其昌等艺术家、艺术理论家的观点和成就,细致梳理并介绍了重要的中国艺术理论。
《伯灵顿杂志》不但以宽广包容的视野积极推介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非欧洲艺术,还成为现代主义艺术汲取异域养分的重要园地。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等诸多现代主义者都曾是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中国艺术的自觉接受、汲取和借鉴,直接影响了其现代主义美学的生成和发展。作为20世纪初最重要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家之一,弗莱曾担任《伯灵顿杂志》的编辑,并发表多篇有关中国艺术的文章。1910年,弗莱撰文《东方艺术》表达对中国艺术的关注,同年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慕尼黑的伊斯兰艺术展览》一文,追溯了早期中国艺术与伊斯兰艺术之间的关联。1925年,他又发表论文《中国艺术》,该文之后经过修改又被收入由宾扬组织编写的著作《中国艺术导读手册》中,并“成为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有关中国艺术的论著之一”。在《变形》《最后的演讲》等论著中,弗莱也详细梳理和介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与特征,尤其推崇中国的青铜艺术、宋代绘画、佛教艺术。
在阐释中国艺术的同时,弗莱敏锐地捕捉到中国艺术和其形式主义美学之间的契合,因此自觉将二者融合,用中国艺术的相关概念来捍卫西方现代艺术,由此形成了新的艺术修辞。首先,弗莱从中西方艺术间的相似性、互通性入手,指出艺术形式的纯粹美感是中国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可以交融互补的基础,亦是艺术得以长存并获得普遍认同的关键。其次,他借鉴了中国源远流长的“线性艺术”传统,汲取了其中对线条、轮廓、笔触等艺术元素的独特运用,并将“线性韵律”(linearrhythm)的概念与西方现代主义审美理念紧密相融。1918年,弗莱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文章《线条之为现代艺术中的表现手段》。在这篇文章中,弗莱明显借鉴了中国的书法艺术,集中阐释了现代艺术中的线条特征及其无可替代的表现力。再次,他还表达了对中国艺术的二维平面风格的推崇,使之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主义对立体空间感、自然真实的看法和表现,并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对抗写实主义传统的重要参考。在弗莱、贝尔等现代主义者的积极推介下,现代主义美学借鉴和融合了中国古代哲学,“线性韵律”“留白”等术语亦进入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批评视野,成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除旧布新的重要借力。在弗莱的影响下,20世纪初的美国作家、艺术收藏家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在评价毕加索时格外关注其绘画中的书法式线条,其形式主义艺术观念与弗莱趋同。斯坦因家族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但和毕加索、塞尚、马蒂斯等现代主义艺术家有密切交往,而且广泛购买和收藏中国艺术品,是20世纪著名的中国艺术收藏家。值得注意的是,毕加索、马蒂斯均在斯坦因家中观赏过中国艺术品,我们或可推测他们作品中的东方装饰元素也许与此有关。由此而言,斯坦因用中国艺术之眼来欣赏毕加索的作品,一方面敏锐地捕捉到了其艺术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另一方面也反向印证了中国古典艺术中存在着鲜明的“现代性”。因此苏立文说道:“如果说,东方艺术对印象主义画派所起的决定性的影响,仅是在解决绘画中纯形式和视觉问题这个有限的范围内,那么,西方当代美术运动不仅某些形式,甚至哲学基础看起来也非常彻底地东方化了,对此我们可以探讨,东方影响对西方当代美术运动是怎样更加深刻地起作用的。”
通过梳理16至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艺术认识和阐释的历史嬗变,我们得以清楚窥见中国艺术趣味在西方的发展。在20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美术的兴趣基本上只限于工艺品和装饰性绘画”,而对中国的高雅艺术视而不见甚至普遍贬低。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古代艺术才真正为西方学术主流所关注,并成为助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借力。正如钱兆明所言:“现代主义是国际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和现象,东方在其中的影响力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作为西方反省自身的一面明镜,中国艺术在西方的接受和演变受到中西历史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不仅反映了中国艺术西传的历史变迁,也折射出西方艺术美学自身发展的轨迹。中西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而绝非由西向东的单向输入。了解中国艺术趣味在西方的发展,厘清中国艺术进入西方的路径、方式、背景和影响,可以揭示中国文化在西方构建审美现代性历程中的参照价值。这无疑对重新审视“中学西渐”的动态历程、确证中国文化之于西方的积极影响,以及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