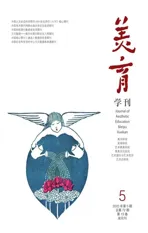艺术人文教育与人的“全面觉醒”
——玛克辛·格林美育思想的启示
2022-11-11刘琴
刘 琴
(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何为艺术人文教育?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人文”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名词,概指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包括符号、规范、价值观念等;二是作为形容词,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关心人。相应地,艺术人文教育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艺术教育要把握艺术与文化的关联,通过艺术提升人文素养、涵养人文精神,也即“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二是强调艺术最终是为了人,艺术教育是一种为人生的教育,如杜卫所说,艺术“所创造出的艺术人生,使人达到诗意的‘天地境界’”。这既是对艺术人文价值的阐释,也是对艺术人文教育目标的指引。拉尔夫·史密斯曾总结美育对人的三大裨益:“感知的精细化、想象力的激发和人类可能性理想的呈现。”“艺术人生”和“天地境界”可以说就是艺术—审美教育所追求的一种“人类可能性的理想”。如何达到这种人生境界或“人类可能性的理想”状态?通过艺术对人的“唤醒”进而激发人的“全面觉醒”,或许是艺术教育提振人文精神、摆脱工具化的一个观念进路。
一、艺术的教育维度:让人成为人
关于艺术与教育的关系,英国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在《通过艺术的教育》中阐述了“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这一宗旨。里德的这一论断基于他从人类发展的角度对艺术和教育这两大概念的审视,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育个体的成长,这里“成长”不只是身体的扩大以及思想和理解的发展,更包括“主观的情绪和情感对客观世界一种非常复杂的适应”,这些个人的成长最终通过一些表达来实现——声音、心象、动作、器物等。因此,里德提出他理想的艺术教育形态就是美育,也就是“人类个体的意识以至于终为智慧与判断所依据的那些感官的教育”。通过艺术所培育的感官的、感性的能力,是思想、逻辑、记忆、智能等“人类个体的意识”最终所依据的基础和条件。从促进人的成长角度来看,艺术的历程就是教育的历程,所以他干脆说,“教育的目的就是创造艺术家——善于各种表现式样的人”。
里德把艺术中的感知觉的培育视为个体意识成长的基础,当代美国教育学者玛克辛·格林则将其与人的意义世界的建构联系起来。格林说,“教育意味着开启视觉、听觉、感觉和运动的新方式,培育一种特别的反思和表达方式,以及对意义的寻求和学会学习”,教育是一个“让人变得不同、让人进入意义的多重领域的过程”。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探寻世界对我们的意义”,艺术更是以其非实用性而“更多地现实了‘意义’”,因此,教育和艺术在意义的层面上再一次汇集。
里德和格林通过重返“教育”和“艺术”的概念打开了我们重新审视艺术教育的视角——艺术如何育人,或者说艺术如何让人成为人。因此,艺术教育应该始终围绕着“人”——人的成长和意义世界的建构,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阶段的艺术教育都应包含人文精神。这一看似基础性的认知却并非自明的,甚至随着艺术教育门类与层次的日益发展和细化分殊,艺术教育的这一“初心”在很多时候却被种种的方法规范、复杂的技术指标遮蔽,以至于舍本逐末,得筌忘鱼。因此我们需要经常重返艺术教育的价值场域进行追问:艺术教育对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艺术教育人文性缺失与“麻木”的人
今天的艺术教育面临着很多外部的困境和自身的问题。在外部环境方面,艺术教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一种无处不在的功利化导向。这种功利化是一种“教育为经济增长服务”理念的表现,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功利教育批判》()中痛陈这种蔓延至世界各国的功利主义教育趋势:以经济效益为导向,推崇技术至上,人文和艺术教育课程被削减,等等。外部的功利主义追求和内在的工具理性产生合力,具体在艺术教育的实践中则表现为艺术教育的量化、标准化、知识技能化而忽视了艺术教育的人文属性和人的心灵的复杂多义性,如努斯鲍姆所说:“我们似乎忘记了应将他看做有灵魂的人,而不应仅仅看做有用的工具。”
艺术教育的知识技能化倾向可以概括为将艺术学习视为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用前人总结的艺术规律和艺术知识来拆解艺术经验和感受的完整性。比如,老师带领孩子学习一首曲子,先去分析节奏、节拍和曲式,学习一首诗歌,先找生词和划分段落。这种肢解式的教学方法和对艺术的工具性使用容易把活的艺术变成知识概念,使感受被认知掩盖或代替,导致学生得到的不是艺术形象带给人的心灵触动而是无生命的知识碎片和“炫技”式的技术技巧。在高等学校,审美教育的知识化常常表现为以美学或者艺术的知识传授代替美育。用玛克辛·格林的话说就是,艺术教育不是给艺术贴标签,不是“把一件艺术作品当作某个就在那儿的东西,由专家定义的以他人决定的方式被理解、阅读或聆听的东西”。前述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多,比如教育行政管理对可控性、可测量性的需求,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落后,等等。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对艺术、对艺术—审美教育的特殊性缺乏认知或者流于麻木。
在专业艺术教育领域存在的误区则是过分注重艺术技能的训练和技巧的学习,把艺术教育理解为艺术技能的教育。然而,单纯的技术训练容易形成一种“惯习”,玛克辛·格林称之为“经验中的麻痹状态”,也就是需要与艺术的真正相遇去唤醒的状态。技术化倾向对艺术人文性的挤压还导致一种所谓的“精致的平庸”。可以说,艺术教育中感官的工具性使用和技术技巧的娴熟所导致的“麻木”,制造出来的是一些没有生命的“标准件”甚至是不合格件。
关于艺术的技术性与人文性这一矛盾,丰子恺曾从“善”与“巧”的角度说道:“艺术偏废巧,仍不失为善良之事,犹可取也。若偏废善,则流于雕虫小技,而玩物丧志。是为匠化。或流于机变之巧,而作恶为非。是为助桀。”丰子恺对艺术一味追求技术或者流于工巧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这对今天的艺术教育仍有警醒:艺术的人文内涵不能因强调技术而被忽略,更不应被技巧的训练而取代。如果艺术教育工作者不能把握艺术教育潜移默化之教育功效,则“虽设图画音乐数十小时,亦不过制造画匠与乐工,无所补于教育也”。可以说,艺术的教与学,如果没有产生情感的触动和身心的改变,这样的“艺术教育”就不是美育,也谈不上人文素养的提高,更谈不上人生境界的跃升。艺术如果不能把人从无处不在的工具化的境地中解放出来,那么这种技术训练就是强化了人的工具性。因此,艺术教育要让人和艺术真正地“相遇”,才能使艺术具有唤醒的价值和解放的意义。
三、与艺术“相遇”,唤起人的“全面觉醒”
李斯托威尔曾说,美的反面不是丑,而是麻木、冷淡和单调。功利主义的、技术至上的艺术教育往往带来陈腐和重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感”、平庸和麻木。如何把人从“天真”或者麻木的状态中唤醒?如何使艺术与人的生命经验发生连接?玛克辛·格林在《蓝色吉他变奏曲:美的教育》这本汇集了她在林肯艺术中心多年工作演讲的书中反复阐述的就是艺术的品质何以“唤醒”人,在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格林对艺术如何关注个体生命、如何渗透人文关怀的关切。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艺术所带来的层层递进的觉醒历程。
第一,艺术通过一种特殊的感知觉方式的训练打开人的审美意识,使人摆脱惯例化的、庸常的日常生活世界,发现事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格林表述为“打破日常生活的无力感、被动性和百无聊赖”,“打破事物的平庸性”。她举了剧场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注意方式如何将一个礼堂感知为一个审美的空间:通过一种“刻意”的注意,可以将门、座椅、灯等日常事物的形状、质感、光及所有的一切从通常的、实用的视角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文学理论话语中所说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过程。格林用了很多具有表达力的语言和大量的诗歌、绘画、舞蹈的具体例子来阐述这个过程,“艺术中的语言、图像和声音使得日常生活中无法或未曾被感知、被诉说和被聆听的事物变得可感、可视和可闻”。概而言之,艺术使不可见的东西可见,使可见的东西向人们呈现出不同的面,在对事物多样性的体认中探索和发现世界的更多可能性。
第二,艺术使人发现自我,与自我相遇。艺术教育通过训练独特的感知方式,使人走出那种对艺术无感的“天真”的状态,具有了一种敏锐的感受性,能够体验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投入的力量,从而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相连接。“通过由审美教育(或者由以此为目的的真实教学)引发的全面觉醒,我们的学生将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地发现自己的声音。”格林还使用了“将光亮带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触摸到自己”,“找到自己存在于世界的新意义”等诗性语言来描述这种在艺术中发现自我的历程。回到前述艺术教育中的知识技能问题上,可以说无论是艺术的知识还是技能,都是为了更好地使自我和艺术相遇。也就是通过一种知觉方式的训练触发和培育情感,使艺术与个体的生命经验相连接。这也正是杜威所说的“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只有这样,艺术教育才可以说是活的、有灵魂的、具有人文性的教育。
第三,艺术使个体与人类共同的精神生活相遇。艺术特别是经典艺术中,凝聚着群体和族类的审美心理,因此,“艺术欣赏和创作过程也就意味着个性与社会、文化、历史的某种交融,是历史文化要素向个体内心的渗透”。这个过程也正是广义的教育的过程,赫伯特·里德用“统整”这一概念来描述:“教育不仅是一种完成个人化的历程,而且是一种统整的历程。统整就是个人的独特性与社会的统一性协调。”孔子所说的“诗可以群”,正是对艺术的凝聚、联结功能的最言简意赅的概括,艺术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群”的功能,就在于艺术表达了那种“将无数颗孤独的心编织在一起的微妙但又无可匹敌的坚定信念”。具有这种丰厚的人文品质的艺术教育让人可以在艺术所敞开的层层的“褶皱”中安顿身心,在人类共同的情感形式中找到共鸣。
三个层次概而言之,即艺术教育通过训练特殊的感知方式,使人发现和探索艺术中的世界,进而审视和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拥有了这种对情感形式的敏感性,也使他更易于发现别人的情感,进而产生与他人、与世界的连接,发现自我和世界的多种可能性,达到一种“全面觉醒”。玛克辛·格林用“唤醒”“觉醒”等词所描述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国传统话语中“以文化人”中“化”的过程,亦即艺术“陶冶”人的过程。丰子恺概括为“活用作画之真美心于生活”。他解释学习美术为何要画花果风景,是“借此训练心眼,使正确而敏感真而美。然后应用此真美之心眼于生活”。这里的“心眼”,就是格林所说的一种特殊的知觉结构,也是一种艺术的观看之道,进而成为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用艺术的“看”摆脱日常生活的平庸,用“唤醒”的艺术教育方式对治技术理性和麻木,这就是格林开出的美育“药方”。在这个从“唤醒”到“觉醒”的过程中,美育提升了个人审美意识成长的内在价值,促进想象力、创造力、团结力等能力的外在价值得到统一。概言之,艺术通过丰富审美体验、培养审美意识进而促进理想人格的塑造和人生境界的提升,通过想象力、共情能力的激发和涵养,使人具有探索各种可能性和参与公共生活的素质与能力,这就是艺术人文教育之价值的具体体现。用格林所引述的马尔库塞的话来说:“艺术不会改变世界,但是艺术可以改变能够改变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