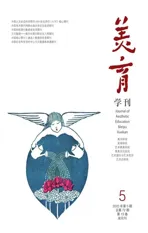数字时代的审美价值领导权与艺术人文教育
2022-11-11冯雪峰
冯雪峰
(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数字时代的艺术和文化景观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数字技术不仅广泛地被应用于各种大型庆典活动,更主要的是它早就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审美实践之中。人们驻足街头欣赏大型裸眼3D屏幕,足不出户参观云上博物馆,或者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获得沉浸式参与体验。数字技术深刻地参与到了当代审美创造和接受之中,这要求我们必须审视艺术教育该如何来面对数字时代的种种新变,从而更好地从事艺术素养的培养和审美价值的引导。
一、数字时代的艺术状况
随着数字媒介、数字经济以及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生活中的普及,数字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文化艺术领域,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尤其明显,各个门类的艺术创作均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前沿科技成果:影视艺术中的虚拟现实技术,表演艺术和公共艺术中出现的交互技术,等等。这些不同的数字技术促进了当代艺术创作在观念呈现和艺术表现力等方面的水平提升,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欣赏者的审美和感官体验。例如第24届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仪式以“数字科技+美学创新”为视觉标签,融合了大量高科技元素,证明了数字技术在当代艺术文化舞台上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开幕式美术总监陈岩直言,舞美设计团队“扔掉了传统的笔,但把技术作为我们的神笔”,勾画出了富有生命力度和灵性的自然图景。
当然,就社会大众层面而言,数字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艺术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层面。借助于互联网、电脑、手机和其他交互技术设备,艺术爱好者和学习者获得了更多的途径去接近和欣赏艺术作品。像英国国家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和美国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等世界知名美术馆和博物馆推出的网络虚拟观展服务就受惠于数字可视化技术的支持。虚拟展厅不仅可以为参观者提供更加完备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带给“游览者”更为丰富的感官体验和遐想空间。美国美学家托马斯·门罗曾在80年前感叹道:“一战以来的历史见证了美国艺术博物馆数量的惊人增长,这一增长并不仅仅只是体现于博物馆藏品的质量和范围,同时也是作为教育机构的博物馆的增长。”这些机构与各级学校展开合作,从而构成了门罗所倡导的博雅教育的重要一环。今天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显然可以帮助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在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数字技术和所有的技术一样,是一把双刃剑。随着使用成本的降低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对数字技术的“滥用”情况也随之大量出现。在现实和网络的双重空间中均充斥着通过数字技术制造出来的低俗审美趣味、扭曲的内容和价值。数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种低准入门槛的艺术状况,门外汉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戏仿经典艺术或快速制造艺术品。这种低门槛的艺术(创作、流通和评论)状况加上眼球经济和资本的介入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加剧了后现代以来艺术的虚无化、狂欢化和媚俗的趋势。社交媒介中屡屡上演的事关艺术和审美的争论以及争议所反映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数字时代审美价值领导权的危机问题。
二、艺术人文教育与审美价值领导权
“审美价值领导权”这个概念参考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著名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葛兰西所构想的“文化领导权”指的是通过文化和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方式在人民和社会中形成自愿的共识和常识,而非通过暴力和压迫等“强制”手段进行统治。这种共识就表现为具体社会的文化规范、世界观和价值观等。统治阶级或主导阶层一般是通过文化和教育机构来实行文化领导权的。艺术审美领域无疑与文化领导权密切相关,但是与诸如文化习俗和伦理道德领域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审美价值领导权作为文化领导权中的一个构成面更加符合讨论文艺作品的需求。同时审美价值领导权并非审美领导权,其目的并非为审美活动和现象制定一个统一的共识和规范,这在当下多元化的社会中显然是行不通的。审美价值领导权意味着在对“美”多元化和分层化的理解中需要形成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上的共识。正是这种审美价值的共识可以帮助我们在保持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前提下做到去芜存菁,以一种柔性的方式推动艺术作品在审美品质和价值观念上的进步,最终能够对艺术爱好者和接受者的审美感受和价值体认形成积极的引导。而当下社交媒体中随处可见的有关艺术和影视作品中审美和趣味问题的争议体现出的正是审美价值领导权和共识的缺失。
如果说审美价值标准的缺位在艺术创作上导致了低俗、庸俗和媚俗等问题,那么在艺术欣赏和接受方面则会产生出一种技术导向的消费型艺术欣赏方式。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在美术馆和艺术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参观者在面对艺术作品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简单看一下作品的文字简介,用手机进行拍摄,移步下一个展品。数字技术改变了欣赏者对艺术的感知、欣赏和理解方式,将主体的注意力模式导向了一种依赖于技术中介、不稳定和持续性短的状态。这种技术导向的消费型欣赏方式实际上取消了艺术欣赏者与艺术作品在审美和意义层面任何真正交流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缺少了审美价值领导权在审美和意义两个层面上的柔性引导,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接受环节都面临着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威胁。就如同文化领导权与教育息息相关一样,培养审美价值共识和领导权的最好方式就是艺术教育。不过这种艺术教育不能够仅仅只是关于艺术技巧的教育,而必须具有对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换言之,必须是一种艺术人文教育。杜卫在其近作中阐发了对艺术人文价值的思考,他指出,如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艺术的“主要特点是探寻世界对我们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在人和世界的多种关系中揭示出艺术的独特意义”,从而使得“艺术成为人生存发展的一个新维度”。正是在这种艺术人生的愿景中,艺术人文教育的理念彰显出了它对于当下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正因此,对艺术人文教育的倡导与当下党和国家对美育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的热切期盼正说明了艺术审美素养的养成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的。
艺术人文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两个关键方面。审美素养包括了“对高雅艺术的兴趣、欣赏和理解经典艺术品的审美能力以及较高水平的审美趣味,而审美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人文素养指的是“对艺术有一定的文化理解能力,具备高雅的生活情趣、超越私欲的宽阔胸怀和超越世俗的精神气质”。不难看出,艺术人文教育的指向不是培养专业艺术家,而是通过对审美价值共识的塑造和传播,培养出具有“丰厚的感性”、充盈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以及艺术人生态度的艺术爱好者。只有以更广大的艺术公众为目标,艺术人文教育才能够真正成为建立社会审美价值共识的最有力手段。
三、生存论美学和美的伦理
那么在数字时代艺术人文教育致力于建构的审美价值领导权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呢?结合肖恩·库比特和杜卫等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数字时代的审美价值共识应该是一种美学—伦理的构造,或者说是生存论美学和美的伦理的结合。
在资本的介入下,数字技术很容易形成一种“协作管理”的公司化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使用大数据和算法制造出高度同质化的审美需求,最终服务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当下的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介上,我们不难发现“协作管理”模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感受模式和生存伦理,从而严重地威胁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库比特在《数字美学》一书中认为创造一种数字美学实际上也是创造一种新的伦理,“这种伦理可以理解为一种美,……美学所追求的是生存的伦理模式,不管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在中国人文艺术的脉络中,这种美学—伦理的构造就是一种“艺术人生”的境界,“是一种有品位的人生,是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生”。
艺术人文教育所倡导的两个核心能力正好对应着美学—伦理构造中的两个维度:审美素养作为一种生存论美学的基础,而对人文价值的追求即对美的伦理的追求。审美教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它是通过“丰厚的感性”、想象力和创造力来掌握世界,同时改造主体和世界的关系,最终的结果不是生产知识体系或者树立道德原则,而是创造出“审美的人”。这种“审美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存在论深度的美学状态。而对人文价值的强调指的就是在艺术中始终带有对意义和价值的关怀,并引导这种关怀反哺到对人生境界和生命意识的塑造。这种人生理想和生命意识经过艺术的中介最终形成一种艺术人生的境界,或者说是美的伦理所支撑的人生。
在数字化的社会中,塑造一种以美学—伦理为基础,以艺术人生为目标的审美价值领导权势必要求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造的诸多正面优势,例如便捷的技术平台和传播效率等,去重新建立人和艺术交流的可能性。对于库比特而言,美学—伦理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艺术回答如下问题:“我们是否还会发言,我们是否还要倾听?我们是否还需要爱?我们是要梦想还是接受现存对一切的主宰?”在艺术中蕴含着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进行交流的契机——一种更全面的生活的可能性。这种艺术人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它不同于白日梦,“从不在空无的可能性中戏耍”,而是督促我们在艺术中去寻找“可预见却还尚未到来的存在”以及“另一种为人之道”。
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发挥艺术的力量和形式去积极地利用这种技术变革。当数字技术轻易地把年轻一代从文学和艺术领域“掠夺”到游戏和娱乐中去时,我们的艺术和艺术教育却还没能够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和方法去重新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审美价值领导权。艺术人文教育之所以在当下成为一个迫切的诉求,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它可以充当数字技术和艺术辩证发展关系的重要中介:通过对审美体验和人文价值的双重坚持,它可以在艺术共同体中创造出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乐于认同的审美价值新共识。
我们可以说在数字时代思考艺术人文教育,就是去创造和追求一种具备数字素养的艺术人文的形式和内容,提升艺术教育与其他大众文化产品的竞争力,通过将生存论美学和美的伦理与数字化社会结合起来,也许我们能够从中创造出“另一种为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