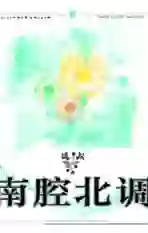中国生态电影中的非人类研究
2022-06-27武辰囿
武辰囿

摘要:本文旨在以非人类转向这一研究视角,对中国生态电影进行分析与考察,关注中国生态电影中的非人类研究。非人类转向的核心,在于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这一长期占据人类思想史的观念,强调转向对于非人类的关注。非人类大致可被分为四类:自然之物、超自然之物、人造物和人造人。而中国生态电影中的生态意识便体现在对非人类的关注,和表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因此,笔者以非人类转向这一理论背景,对中国生态电影进行考察与研究,集中分析其中存在的非人类的特点,和导演通过对非人类的关注与塑造来表达和传递的生态意识。
关键词:非人类转向 中国生态电影 非人类
人類一直所持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使得人类一直试图成为自然、生态和地球的主宰。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已然成为改造自然、改造地球的主导性力量,基于此,人类逐渐进入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创造了众多科学奇迹与新兴技术。然而,地球在极度发达的背后,却是生态环境不断地被破坏,工业污水被肆意排放,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等众多环境问题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人类开始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提出了后人类主义,而在近年来,随着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兴起,学界又提出了非人类转向。非人类转向旨在强调人类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倡对非人类的关注,非人类与人类共同发展,要与其和谐共处。哲学、生态学和文学界,都展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同样,电影创作者也有意识地在影片中表现生态意识,用影像的方式呈现人类对动物的屠杀和对自然的破坏,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
西方生态电影作品众多,其内容不仅呈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对动物的残忍屠杀,还有对于一切生物的关怀和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比如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体现着明显的生态意识,即对于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正如导演在《雕刻时光》中所述:“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在寻求物质财富与精神完善这两方面发展并不协调,导致我们似乎注定不能将物质所得造福于自身。我们建立了文明,可这种文明却威胁人类走向毁灭。”[1]由此可见,生态电影中的生态意识,并不是只体现人类对于自然的摧毁这样较为简单的议题,事实上,随着生态电影的不断发展和生态电影研究的不断发展,生态电影的定义逐渐被拓宽和丰富。其中,关于中国生态电影的研究,以华人学者鲁晓鹏教授为代表,鲁晓鹏教授指出:“生态电影就是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电影,它探讨人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土地、自然和动物,是以一种非人类中心的观点来看待世界,而对于中国生态电影,应该放在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去理解。”[2]可见,理解生态电影最重要的关键,便在于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摒弃,对非人类中心观点的强调。因此,笔者将以非人类转向这一研究视角,对中国生态电影进行研究,对中国生态电影中出现的非人类进行分析与考察,努力对非人类进行类型归纳,并对电影创作者表现的人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和相处方式进行论述。
尚必武教授在其文章《非人类叙事:概念、类型与功能》中提出非人类叙事这一概念,对文学作品中的非人类叙事的类型与功能进行论述。他指出,非人类叙事“即由‘非人类实体’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在具体叙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主要存在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在故事层面上,他们以人物的身份出现;在话语层面上,他们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3]。依照此定义,尚必武教授又将非人类叙事归纳与分类:“其一,自然之物的叙事,主要包括以动物、植物、石头、水等各类自然界的存在物为核心对象的叙事;其二,超自然之物的叙事,譬如以神话、传说、史诗中的鬼神、怪兽,和科幻文学中的外星人为主体的叙事等;其三,人造物的叙事,主要包括以诸如钱币、玩具、布匹、线块等人类创造出来的无生命物体为主体的叙事;其四,人造人的叙事,主要包括机器人、克隆人为主体的叙事,这在科幻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4]以上对于非人类的归纳与分类十分全面且准确,笔者将沿用此分类方式,对中国生态电影中的非人类进行分析与阐述。
一、自然之物:被人类主宰的自然
中国的传统观念,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这种对自然敬畏和保护自然的观念逐渐淡漠,转而被人类中心化思想所替代,自然也成为我们谋求利益,寻求发展的重要工具。人类逐渐成为自然的主宰,稀有动物惨遭屠杀的现象触目惊心,众多环境问题逐渐显现。于是,艺术家与电影创作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人对自然之物的破坏与摧毁。笔者将中国生态电影中的自然之物分为:被屠杀的动物和被污染的河流这两个部分,并从这两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 被屠杀的动物
2004年上映的《可可西里》被认为是最先突出表现生态意识的中国电影,该片将视角关注于藏羚羊这一非人类,片中的非人类——藏羚羊处于被人类屠杀的艰难处境之中。陆川导演在该片中以纪实的影像风格,呈现了凶残的盗猎者屠杀藏羚羊的残忍图景和盗猎分子为了利益将保护藏羚羊的许多巡山队员残忍杀害的场面。影片已经清楚地说明:自由生长在人迹罕至处的藏羚羊不幸成为盗猎分子猎枪的目标的原因,在于欧美藏羚羊绒市场需求量大,羊绒价格持续上涨,使得唯利是图的盗猎分子将鲜活的藏羚羊视为牟利的对象,大肆捕杀藏羚羊并残忍剥皮以换取高昂的利益。他们并没有将藏羚羊视为鲜活的生命,是同人类一样平等的生命,而是将众多的藏羚羊视为可以轻松换取大量金钱的工具,全然不顾大量屠杀藏羚羊带来的是藏羚羊物种的灭绝,这种短视且残忍的屠杀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远不及眼前的大量钱财重要。正是由于对不义之财的贪婪索取,造成了藏羚羊乃至其他动物被屠杀,并使它们成为牟利的工具。
《可可西里》中的藏羚羊是故事层面的非人类形象,也是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影像呈现了藏羚羊被盗猎分子残忍屠杀剥皮的艰难处境。在片中,惨遭剥皮只剩骨架的藏羚羊被一一排列放置在荒凉的大地上,导演将这样极其震撼的一幕直接呈现给观众,以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控诉了盗猎分子手段之残忍和人性之贪婪。影片开始的镜头,就简单而直接地呈现了盗猎分子屠杀藏羚羊的场景和藏羚羊濒临灭绝的处境。片中,盗猎分子挟持保护藏羚羊的巡山队员,用现代化的工具——汽车与猎枪结束了生活在偏远寂静之地的藏羚羊的生命,甚至将巡山队员挟持在车上,逼迫队员亲眼目睹藏羚羊被屠杀却无力阻止。夜幕降临,盗猎分子确认被挟持者是巡山队员之后将其残忍杀害,如同众多被残忍杀害的藏羚羊一般倒在荒无人烟之地。
《可可西里》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展现了藏羚羊被屠杀,呼吁各界对于藏羚羊和稀有动物的保护,而且,最重要的在于,他揭示了动物成为商品和人类屠杀生命获取金钱的背后原因,即残忍贪婪的盗猎分子长期持有的人类中心化思想根深蒂固,由此,盗猎分子将藏羚羊视为可供人类任意屠杀牟利的工具,而非鲜活的生命。电影将保护藏羚羊的复杂性和亟待解决问题的紧迫性都呈现出来,正如电影中马占林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他一面辩解自己朴实穷苦,成为盗猎分子的帮凶是因为家徒四壁无法谋生;另一面又将巡山队员的踪迹告诉盗猎人员,成为害死巡山队员的帮凶,在看到巡山队队长日泰被盗猎分子杀死以后,他又告知随行记者出山的路线。这样前后矛盾的行为,恰恰体现了这一人物的复杂性,同样也体现了保护藏羚羊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导演并未以戏剧性的或是好莱坞式的创作风格煽动观众情绪,刺激观众去保护动物,因为,夸张的方式挑动观众的情绪可能会引起观众的无力感,效果适得其反,造成观众的漠不关心。正如作者于晓凤认为的:“受众对生态电影内容的理解,就意味着认同了电影所传达的生态主义观点。这种理解本身建构起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并以此升华为受众个体的生态体验。在观看过程中,电影的文化内涵投射于受众内心并与之产生共鸣,发酵其潜意识层面的生态主义情感。一旦现实生活经验呼应了电影中再现的场景,受众的回忆就会被瞬间唤醒,从而接受生态电影的立场和主张。”[5]正是这样克制且冷静的呈现方式,让观众更深刻地反思人类对于非人类的侵扰甚至屠杀行为,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对非人类予以平等的关照与关怀。
2. 被污染的河流
1964年,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执导的《红色沙漠》,用不同的颜色反映工业社会对于人的异化和环境破坏的主题。该片呈现了被工业废水污染的河流和被废气污染的天空,还有生活在如此环境中内心孤寂精神落寞的人。在中国,也有表达相似内容的影片,其中,2000年娄烨执导的影片《苏州河》在一开始便呈现了上海周边肮脏且被污染的苏州河。影片一开始,伴有旁白的空镜头表现了苏州河、苏州河岸边正在修建的高楼和苏州河上的渔船。河水中布满生活垃圾,渔船上还运输着煤炭,如旁白所述,这条河承载了所有的垃圾,许多人靠苏州河生活,苏州河也叙述着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故事。晃动着的、昏暗且粗糙的镜头讲述着苏州河的故事,河上漂浮的垃圾、脏污的河水如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苏州河成为现代人内心世界的具象化表达,此时,非人类的河水被导演呈现在影片之中并被赋予深刻内涵。
1997年蔡明亮导演的影片《河流》也有类似的表达,在影片中,脏污的河水直接导致了男主人公小康突然患上歪脖子的怪病。小康偶然被一个电影剧组邀请出演河里的死尸,由于无法拒绝导演的盛情邀请只好答应帮忙,长时间被浸在脏污河水中的小康在影片结束拍摄之后,脖子就莫名其妙地无法维持正常状态,父母带着小康四处看病都无法治好小康的病。事实上,该片并未使用大量镜头呈现河流,但是河流却在承担着重要的叙事作用。人类对河水的污染,使得原本干净流淌的河水成为“有毒”的污水,这污水最终影响了了小康的健康问题,甚至精神问题。电影更深刻的含义在于:现代社会之中,人类秉持的人类中心化观念对非人类肆意侵扰与破坏,最终影响到的并非只有非人类,同样也会影响到身处在此环境之中的人类。导演将河流作为影片开端和重要意象,体现着非人类在中国影片中的重要性和导演对于非人类的关注。
二、超自然之物:作为指引者的美人鱼
由周星驰执导的电影《美人鱼》于2018年上映,该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导演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于保护环境、保护鱼类动物和人与海洋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表达。导演用浪漫的人鱼之恋和独特的喜剧风格,讲述了美人鱼作为非人类在这个以利益和金钱为导向的社会中被人类驱逐甚至牺牲的处境,并且,影片借由美人鱼这一非人类之口,传递了导演对于地球生态危机的反思。美人鱼作为超自然的存在,在影片中是真实存在的,而他们被人类发现以后,成为满足人类好奇的对象后,便迅速被驱逐甚至被屠杀。在本片中,美人鱼因为妨碍了唯利是图的商人获取高昂利益,便被视为异类遭到傲慢的商人大肆屠杀,导演对于这些商人的塑造,体现了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对傲慢的人类主导自然的行为的反思,由此,本片转向对长期处于被压制和被忽略的非人类的关注,将非人类应有的主体身份重新交还,为非人类诉说自己处境和引导人类反思自身的傲慢与自大,提供了影像表达这一途径。
《美人鱼》中的非人类是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影片中的,承担着诉说非人类处境、确认其非人類主体性地位和指引人类放下傲慢与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观念的这一重要任务。珊珊这一非人类形象的原始与纯真美好,恰恰反衬了人类的贪婪和拜金的虚伪本性,珊珊与她的族群生存的海洋不断地被人类破坏,甚至,他们常常被残忍屠杀,这些都体现了人类不顾生态平衡和环境危机,贪婪而无止境地追求金钱利益与地位。珊珊作为海洋的代言人,诉说了环境对于人类生存之重要性,指引原本唯利是图的商人刘轩的思想观念转变,刘轩从破坏海洋生态的刽子手,转变成为一个自觉保护海洋生态的环保人士。刘轩在美丽的美人鱼珊珊的指引下,并且在亲身经历了人类所制造的声呐技术带来的痛苦后,开始关注非人类的生存境况,并且自觉保护非人类不受人类的伤害,刘轩态度的重要转变是在珊珊的指引下完成的。
《美人鱼》中的非人类在影片中不仅是被屠杀被伤害的存在,更多的是作为指引者、教导者存在的。导演将非人类作为教导者,首先,这反映了导演对于非人类的关注;其次,导演让非人类诉说自己的生存状况,意在为一直遭受人类破坏的自然生物寻求生态表达的权利,美人鱼在影片中作为海洋深处的一员,他们亲自诉说自己族群的历史与处境,确认其主体性,这一改从前需要借由人类之口来言说的客体地位,并且,以其蕴含的大自然的深厚底蕴与神秘壮阔,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反思了长久以来的人类中心化的观念。
三、人造物:家园迷失的见证
存在于生态电影中的人造物这一非人类形象,如同自然之物和超自然之物一样,对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人造物这一类非人类形象包含对象甚广,使得难以有针对性地论述,而观众往往也会忽略人造物的存在。非人类转向这一理论背景,使得人造物变得可见,也使得生态电影中人造物的文化表征得以被关注和解读。
中国生态电影中的人造物,首先成为人类破坏自然行为的承担者。人造物被人类无止境和无底线地制造出来以供人类使用,短暂地为人类现代生活提供便利之后便迅速成为垃圾,这些垃圾难以进入生态自然循环之中,反而成为环境的负担——本该是宁静平和的田野,却飘满了塑料袋;本该是种植农作物的丰饶的土壤,却被塑料袋深深嵌入。如此,如塑料制品一般的人造物,成为人类破坏自然、破坏环境最细微的见证。同时,塑料制品成为破坏环境的责任承担者,成为制造塑料制品的人类的替罪羊,人类对自然和环境的破坏行为再一次被掩盖。
冯小宁导演的《大气层消失》便将人造物形态的文化内涵,融入影片叙事之中。片中,氯化烃的泄露使得臭氧层被破坏由此引发生态危机,这一重要情节,传递了导演呼吁人类保护环境并停止伤害动物的环保理念。但是,电影中引发地球危机的氯化烃,却替代人类成为在发展经济的口号下对自然肆无忌惮地破坏而造成的生态危机的责任承担者。
更重要的是,彰显着人类奇迹般的创造力和空前智慧的人造物,也会反噬人类。这些人造物,由于创建美好家园之期盼产生,被人类以科技和发展之名创造,然而却成为家园消失覆灭的见证,自诩为万物之主的人类努力建设的家园,却被人类自身制造出的人造物所吞噬。家园意识是生态电影中所彰显的生态意识之一,家园除却指故乡或居处这一物理层面的意义之外,更有精神和心灵回归之意义。在我国的生态电影中,家园常常成为主人公难以回归之处,由此造成精神与心灵深处的孤寂与落寞,因此,电影反思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行为,最终造成了家园难归的现实境况。“‘家园意识’就与自然生态有了天然的联系。人生存在自然之中,自然是人类的家园。保护自然,维持生态平衡发展,就是保护人的家园,就是指引无家可归人的返乡之路。至此,‘家园意识’既有维护人类生存家园,保护环境之意,又有人的本真存在的回归之思。”[6]生态电影中呈现家园难归、家园覆灭境况的方式众多,其中之一便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的人造物这一非人类形态最终吞噬乃至替代人类试图追寻的精神家园,此种方式更为深刻地反思了长期占据人类思想与文化建构的人类中心论,也更为深刻地警示了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乃至人类精神生态问题中的危机。
2015年,李睿珺导演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表现了草场退化引起的沙化与水源枯竭这一生态危机,不仅体现了导演的生态意识,而且蕴含了导演对草原文化的关注。有别于简单陈述事实以呼吁观众保护环境的口号宣传类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深化了其主题内涵,并追求一种诗意的审美意蕴。该片聚焦于两个男孩的寻家之旅:父亲告诉两个男孩家在远处,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父母曾在那里放牧……在归家之旅中,两个男孩修复了亲情,但本应是水草丰茂的地方,却变成冒着浓烟的工厂和布满石块的贫瘠大地,两个男孩见到的也并不是在放牧的父亲,而是加入淘金的父亲。两个男孩向往的水草丰茂的家园,已被人类制造出来的烟囱和工厂所替代,追求和向往的家园,只停留在两个男孩的回忆中。除了表现儿童的成长,影片呈现了丰茂水草逐渐沙化和干涸的生态危机,对悠久的草原文化的衰落也有着深深地感慨。不仅如此,导演意在表现现代化的工厂和现代性的观念对草原和家园的冲击,家园已经改天换地,被工厂与浓烟占据,水草丰茂成为回忆。在这部影片中,人造物最终替代了家园。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价值理性逐渐让位于工具理性,效益与利益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自诩为宇宙中心的人类制造出大量的人造物,试图拥有便捷与高效的生活。只是,表象背后却是过剩的人造物造成的环境负担与生态问题。人类为了构建美好家园而制造出的人造物,成为家园的替代品和吞噬物,然而,这一切的源头却是人类自身。因此,在非人类转向这一理论背景下,研究生态电影中人造物这一非人类形态,应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检视,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义为和谐共生理念的再度彰显,更是将人类中心主义转为生态中心主义的开放包容的价值观与生态观的影像化呈现。
四、人造人:尚在发展阶段的仿生人
被人类制造出来的机器人或克隆人可以被统称为人造人,这一非人类多出现在科幻文学、科幻电影之中,他们在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与特征是不断变化的。最初,这类人造人多承载着人类对于技术文明的反思或恐惧,逐渐地转变为思考人与人造人之间区别的切入点,在情感模式上,由敌视警惕的忧虑转变为人与人造人和谐相处,协同进步的观念。这样的转变,在西方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中均被体现,优秀且经典的科幻电影,对于人造人这一非人类形象的思考上升到哲学高度。虽然,中国的科幻电影仍处于探索与萌芽时期,但是,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中出现的莫斯这一人造人形象,仍然因为其艺术内涵引起人们关注。
在电影《流浪地球》中,莫斯的最初职能在于辅助人类工作,根据航天员们的安排与指令完成工作。但是,在刘培强为救儿子拒绝执行休眠任务之后,莫斯却反抗刘培强的指令,甚至杀死了与刘培强同行的航天员。其原因在于,地球上人类的生命已经被放弃,而莫斯需要执行的指令便是保证太空中的人类的安全。
事实上,《流浪地球》致敬了许多国外经典的科幻电影,人工智能莫斯杀人这一情节来自库布里克执导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只是两者的表意有所不同,《2001:太空漫游》旨在表达对于技術文明的忧思、对于人与非人类差异的哲学思考,而《流浪地球》反思了冰冷严谨的执行命令所代表的机器特性,恰如莫斯这一非人类形象的边缘性与局限性。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生态电影中的非人类类型仍处于发展与探索阶段,尚未出现创作者真正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来表现非人类形象的电影作品。
结 语
在当下环境危机愈发严重的背景下,人类急需拯救被破坏已久的生态环境。而在此过程中,人类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将关注视角转向非人类,在关注非人类的生存的同时,秉持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保护环境和动物等一切非人类。这种生态意识与生态观念的表达与传播,可以依托生态电影完成,经由电影关注人与生态、人与非人类的关系,通过电影来传达对非人类的关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意识。
参考文献:
[1][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M].张晓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48.
[2]鲁晓鹏,陈旭光,陈阳.“华语生态电影”:概念、美学、实践[J].创作与评论,2016(24).
[3][4]尚必武.非人类叙事:概念、类型与功能[J].中国文学批评,2021(04).
[5]于晓风.生态电影:当代中国生态批评对象的延伸与拓展[J].电影艺术,2016(02).
[6]张玮艳.《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的精神家园审视与生态审美之思[J].电影评介,2021(11).
基金项目:山西师范大学科技创新项目课题:人类世时代下中国科幻电影研究(项目号:2021XSY012)。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