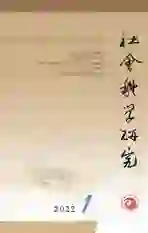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
2022-03-22班涛
〔摘要〕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 城市化;农民家庭转型;市场区位;家庭能力;城乡三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1-0120-09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研究”(2019M660995)
〔作者简介〕班涛,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講师,安徽 合肥 230601。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超过9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3.89%。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21%,预计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5%至80%,新增近4亿城镇居民。城市化作为由人、资源与生活方式等要素构成的系统,城市化的发展会对深嵌于这一进程中的农民家庭产生重要影响。在城市化发展中乡村单身群体呈增加趋势,以及年轻人的婚姻解体占到离婚人群的多数,其婚姻面临不稳定,这些趋势是意味着中国农民家庭转型与西方家庭现代化转型趋近,还是有着特有的内涵,对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作为现代化进程重要衡量指标的城市化会推动农民家庭如何转型、向什么方向转型以及农民家庭的应对策略,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中国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机制与逻辑,构成本文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农民家庭并非是单方面地被动为城市化所形塑,二者是互为能动的生成,即微观的农民家庭的实践也会反塑城市化道路、城乡关系及其社会结构,因此通过考察农民家庭转型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认识。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民家庭也在经历转型,其不是遵从西方家庭现代化的简单线性进化而是颇为复杂。在家庭结构上不同于西方的核心家庭化与小型化,相反呈现出扩大化,联合家庭与直系组家庭占到相当比例,代际关系不是走向松散而是趋向团结。[齐燕:《新联合家庭: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杜鹏、李永萍:《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王跃生:《直系组家庭:当代家庭形态和代际关系分析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在家庭关系上横向的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增加,女性的自主性提升,其对于婚姻的话语权增强,年轻人离婚的提出主体多是女性,这表明个体化趋势增强,然而有研究者指出这一个体化与西方个体本位的个体化不同而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个体化。[李永萍、杜鹏:《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J村离婚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5期;郑丹丹:《个体化与一体化:三代视域下的代际关系》,《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在家庭分工模式上并非是夫妻独立自主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共同养育下一代,而是年轻女性选择退出就业市场并承担照料劳动职责,夫妻间形成内外分工。[朱战辉:《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教育转型与农民家庭策略——基于已婚青年妇女陪读现象的经验考察》,《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1期;苏运勋:《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农村陪读:以豫南S村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在家庭伦理上则趋向于恩往下流的下行式家庭主义,传统的反哺模式受到挑战但又没有形成西方的接力模式。[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康岚:《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青年研究》2012年第3期。]在家庭权力上,并不意味父系权威一定衰落,相反在城郊与东部沿海资源密集型地区出现了亲权的回归,父代对子代的生活与婚姻进行干预。[黄佳琦:《代际交换下家庭权力关系重构——基于苏南农村并家婚姻模式的田野调查》,《天府新论》2021年第2期;纪芳:《并家模式下的家庭权力重构及其实践逻辑——基于苏南农村的并家经验考察》,《天府新论》2020年第1期。]
家庭转型不仅体现在家庭结构、关系、伦理、权力各个维度的变动上,还会对个体处境产生影响。基于农民家庭形成了接力式进城模式,代际关系特别是父代对子代的支持为研究者所重视。然而研究者对此的认识有差异,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正向的,代际间实现了紧密团结与情感流动[张建雷:《接力式进城:代际支持与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分担机制研究——基于皖东溪水镇的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王德福:《弹性城市化与接力式进城——理解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及其社会机制的一个视角》,《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却也有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子代对父代的剥削,子代的啃老是非正义的,父代不得不做出牺牲,极端的表现即是老年人为了不拖累子女,给子女减轻负担,在生活不能自理时选择自杀,这种悲壮的利他式自杀让人颇为唏嘘。[陈锋:《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杨华、欧阳静:《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近年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5期。]除了对代际维度的关注之外,研究者关注得较多的还包括女性,随着农民家庭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年轻女性选择陪读的增多,由此引发了对母职问题的探讨,由于一些女性在陪读的同时还会打零工,从而形成了陪读工与半工半陪的现象。[吴惠芳、吴云蕊、陈健:《陪读妈妈: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基于陕西省Y县和河南省G县的调查》,《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4期;蒋宇阳:《从“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读”——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新特征》,《城市规划》2020年第1期。]对女性处境问题的解释视角主要是性别主义,研究者持女性承担母职的照料劳动是不利的观点,女性在此过程中遭遇母职惩罚,因此需要打破这一分工。中国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不仅与西方不同而具有本土性特征,而且不同地方也有差异,因此虽不能直接套用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现象进行解释,但西方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国家庭转型也有启发。
西方家庭从传统的大家庭与家族网络转向核心家庭,以及对核心家庭内部亲密关系的追求,核心家庭作为情感共同体对个体提供支持,在婚姻选择上个体独立自主,既可以不婚也可以选择结束婚姻。西方家庭转型的发生建立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相适应的社会基础上,其中两次工业革命推动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城市化的发展有着工业化做支撑,工业化为个体独立参与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可能,从而增强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意识,并且工业化的发展保障了家庭具备城市化的能力。[威廉·古德:《家庭》,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45页;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李茹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23页;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页。]此外,从地区空间分布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格局相对均衡,各个地区更多是产业格局的差异,如重工业城市带与轻工业城市带之分。中国农民家庭转型之所以呈现出上述复杂面向,一方面在于中国工业化分布在区域间的不均衡,即存在东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工业欠发达地区之别,另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不均衡的基础上,不少中西部地方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适应,存在城市化快于工业化的情况,这两个特征对农民家庭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分析西方家庭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基础,本文将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问题置于市场区位的框架下进行解读。不同于学界对市场区位界定的单一维度[齐燕:《我国不同地区农民城镇化路径差异研究——基于农民与市场关系的角度》,《城市问题》2020年第3期;李永萍:《农民城市化的区域差异研究——市场区位条件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1期。],本研究所指涉的市场区位包含婚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在务工经济带动的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此外,还有次级本地婚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之间存在正相关,即在劳动力市场区位中占据优势,相应的在婚姻市场中也处于高地。所谓市场区位即是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位置。婚姻市场区位影响的是农民家庭城市化的推力,进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启动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当其在婚姻市场区位中处于劣势,意味着来自婚姻压力而进城倾向愈益凸显,相反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优势,其城市化的自主性就愈明显。劳动力市场区位形塑的是农民家庭城市化的能力,当其越靠近工业发达地区,其家庭能力就越强,相反距离工业地区区位越远,家庭能力则越弱。当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区位中都占据优势地位时,意味着其家庭能力与城市化要求相匹配,從而家庭转型得以顺利开展,然而当其在两个市场区位中都处于劣势时,意味着家庭能力与城市化要求不易相匹配,相应的农民家庭转型就会面临不小的困难。以此为划分标准,前者对应的是东部工业发达地区,后者则对应的是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据此,基于本地婚姻市场在全国婚姻市场中的位置、本地婚姻资源的流动方向与婚姻资源稀缺度,以及基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家庭劳动力就业充分程度、劳动力就业空间场域等衡量婚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区位的指标,可以划分为处于市场区位优势的东部工业发达地区与市场区位处于劣势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前者是少数,其家庭转型中的张力不大,而后者占到农民家庭的多数,其代表了多数农民家庭转型的处境,同时其转型面临的压力更大,因此后者很值得深入探讨,由此本文所探讨的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在空间上指涉的即是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笔者从2014年以来对山东菏泽、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湖北黄冈、安徽淮南、江西井冈山、湖北孝感与湖南常德等多点开展了田野调查,从经济发展程度与所处区位看这些地方都属于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此外,由于年轻男性在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有着强烈感受,家庭转型对其处境影响很大,因而本文选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点来理解广大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问题。
二、成家不易:城市化下的婚姻成本与农民家庭应对
成家,即年轻人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不仅是社会继替的需要,也是小家庭进行家庭再生产的第一步,先成家再步入到繁衍生育与抚育的新阶段。成家的条件是男方及其家庭需要承担一定的婚姻成本,其需要男方及其家庭的婚姻偿付能力与女性的婚姻要价相匹配。城市化进程中普通农业型地区婚姻市场区位的劣势带来婚姻成本快速增长,这意味着男性成家不易。
1.婚姻市场区位与女性婚姻要价
婚姻市场区位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本地在全国婚姻市场中的位置,是处于优势地位的高地还是位于劣势的低洼地带,以此衡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处于优势,相反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处于劣势,女性婚姻资源的流向是从中西部流入东部沿海;二是在本地婚姻市场内部的城乡间的区位,其中总体趋势是从乡村向城市流入;三是本地乡村本身的男女性别比,即不考虑婚姻资源流动的情况下,本地乡村由生育观念决定的男女性别比进而影响了婚姻资源的存量。从上述三个层次来看,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婚姻市场区位陷入多重劣势境地,首先农村生育观念转变相较于城市比较滞后,传统生男偏好的生育观念导致男女性别比存在失衡,由此乡村男多女少增加了女性婚姻资源的稀缺性;其次婚姻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女性婚姻资源的紧张;最后在婚姻资源的全国流动中存在中西部女性婚姻资源向东部流入的趋向,三个层面的叠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年轻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意味着她们的婚姻要价权提高,由于她们拥有主导的话语权而在完成婚配中对男方要求的条件随之提高。[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年轻女性的婚姻要价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要在城里买房,在中西部调研时村民普遍提到近四五年,在城里买房已然成为结婚的必备条件。一些女性在相亲时向媒人明确提出,只有男方在城里买了房,才同意见面,否则连面也不会见。男方即使在农村建了新房子也不行,更不用提将农村的房子装修下用作婚房,城里没有房子,想结婚免谈。从在城里买房的层次看,镇上是不行的,至少要在县里买,有条件的能在地级市以上的城市购房那更好。年轻女性要求在城里买房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个是其生活面向已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其对城市生活向往;另一个是为了下一代教育考虑,她们希望下一代在城里接受教育,通过买房能够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其次男方要想完成婚配,还要支付一笔彩礼给女方,女方父母一般都不会自己要这个钱,多半是在结婚后让女儿带回来,带回来的彩礼存在女方自己名下,怎么支配由其决定。彩礼数额在不同地方不等,但总体趋势是一致的,都在趋于上涨,以安徽淮南为例,彩礼数额在20—30万,山东菏泽则在10来万。最后女性的婚姻要价还包括仪式性支出,主要是结婚典礼与三金首饰,拍婚纱照、请婚车以及买首饰,整个仪式流程走下来也要花上好几万,这还不算男方办酒的开支。除此之外,在一些地方女性要求男方买车趋于增多并正在成为结婚的标配,虽然对车的品牌没做要求,但其费用也在10万上下。
2.劳动力市场区位下的男方婚姻支付能力
女性的高婚姻要价意味着男方完成婚配的婚姻成本大大增加,这就对男方的婚姻支付能力构成了考验。男方的婚姻支付能力包含其个体与家庭两个层面,家庭即是代际支持,代际支持的动力在有些地方是责任与义务,为儿子完成婚配是父母应尽的职责,在有些地方虽然不是不能推脱的责任,父母更多是帮忙,但在儿子不多,不少家庭都只有一个儿子的情况下,父子一体的家庭伦理也使得父母会倾尽全力对子代提供支持,因此代际支持意愿不构成问题,关键是代际支持能力。无论是个体自身还是代际支持能力都与农民家庭在全国劳动力市场区位的位置紧密相关,对于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而言,本地工业经济欠发达,正式就业机会有限,特别是体面职业尤其稀缺,相对高收入的体面职业对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要求高,大部分年轻男性不具备这个条件。在属于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安徽淮南、山东菏泽与湖南常德调研发现本地年轻男性的学历多数仅是初中水平,这让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由于本地就业机会有限,年轻人为了获取更高收入,他们多半选择到东部沿海务工,即使如此,他们的职业选择也比较有限,要么是进工厂从事流水线工作要么是进工地,无论怎样,受教育程度低限制了年輕男性的职业向上晋升机会。在安徽淮南调研时一姚姓男青年就提到本来其可以从流水线提升到质检员,但因为是初中学历而失去机会。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年轻男性不仅在职业选择上受限,而且因为其务工模式属于离土又离乡型,这意味着要在务工地租房并生活,相应的生活支出就会增加,这些都对其进行积累不利。
从代际支持这一维度看,本地正式就业机会的有限意味着父代难以捕获这些机会从而其劳动力无法充分利用,由此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不像东部那样可以很好地优化与充分利用,东部地区形成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全家务工的生计模式,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普遍形成的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由此两个地区的家庭积累进而代际支持能力有明显不同。在中西部农村的父代所能捕获的本地非正式就业机会主要是建筑工与给农业大户做小工,但这些非正式就业机会不那么稳定,收入也不多。对于父代而言,农耕才是其主业,即其更多是依靠农业获取收入,农业收入虽然不多但比较稳定,通过不计劳动力投入的精耕细作使得一亩地能获得一千元上下的收入。父代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勤俭与通过自给自足有所节余,自给自足主要是自己种田、种菜与庭院经济,这些自给自足部分大大降低了父代的生活开支,从而使得父代能够形成一些积累。
一方面是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中的区位劣势使得其要偿付的婚姻成本愈益升高,另一方面是在劳动力市场区位劣势的情况下男方婚姻支付能力的受限。这意味着年轻男性成家不易,为了与之相匹配,年轻男性个体一方面要努力苦做,另一方面父代还要积极捕获非正式就业机会与勤俭节约给予代际支持,两方的紧密合力才有可能顺利成家。为此男方所形成的代际合力与团结明显,一些家庭为了增加积累,采取年轻男性在保留基本生活费之后将剩下的钱交给父母保管的“共财”策略,在一切为了成家这一共同目标下,年轻男性主动将其自主性进行适度压缩以实现成家目标。成家成本的增加意味着若男方的婚姻支付能力无法与女性的婚姻要价相匹配就无法顺利成家,因而这部分男性为婚姻市场所淘汰从而演变为失婚者,即村民口中的“光棍”。
三、做个“好丈夫”与“好爸爸”:城市化下的新生代农民家庭再生产
在成家后,新成立的小家庭即步入到生育与抚育下一代的家庭再生产阶段,对年轻男性而言,“守家”同样不容易,一方面要在夫妻关系中做个好丈夫,另一方面要在亲子关系中做个好爸爸,这对男性提出了高要求。倘若男性无法达到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即意味着守不住家,由此小家庭陷入解体的几率就会增加。
1.做个好丈夫
好丈夫的标准在城市化进程中水涨船高,首先由于农民家庭在城里买了房,大部分家庭是按揭的,这就要每个月偿还房贷,此外,由于下一代进城接受教育,加上女性选择陪读的增多,日常生活开支也随之增加,这些都对男性的经济收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家庭分工上,传统的代际分工由于导致孩子留守而愈益受到年轻人的否定,因而夫妻分工逐渐取代了代际分工,即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女性主要负责照料孩子,男性则在外务工,夫妻分工相较于代际分工在经济上没有对家庭劳动力进行最优配置,而在小家庭所需要经济资源增加的情况下,年轻男性身上的经济担子由此增加。此外,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父代虽有心对子代提供扶持但就业机会的稀缺让他们的剩余劳动力难以找到出路,因此父代在子代成家后的经济支持同样很有限,父代更多是给子代帮忙照料下孙辈以及提供些农副产品。城市化下家庭再生产成本增加,然而代际支持能力偏弱的情况下,使得年轻男性的经济担子更重,由于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苦做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与增加劳动强度来增加收入。在职业选择上他们更倾向于工资更高的工地与装修工,这些工种更辛苦而且风险更高,同时这些工作的稳定性不及工厂。在安徽淮南、湖北孝感与安徽芜湖等地,年轻男性多在工地上做钢筋工、做煤矿的下井工人与做装修工,一天收入三四百元。当他们的工作面临不确定性而陷入暂时失业状态时,男性的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在湖北黄冈,一位33岁的男性,其有两个女儿都在县城的私立学校读书,两个孩子的一年读书费用就在6—7万,其老婆专门在城里带孩子,家庭收入单纯依靠该男性。2020年因为突发疫情,导致其原本在武汉做钢筋工的工地无法开工,一下丧失了收入来源,那段时间他心理压力很大,每晚都是辗转反侧,早晨则早早醒来绞尽脑汁琢磨出路。
好丈夫除了要在经济上能承担重任之外,还要在日常生活中体贴女性,主动分担家务劳动以及懂得哄女性。虽然在夫妻分工上是男主外、女主内,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对家庭事务的不参与,他们不能再像传统男性那样在家里当个甩手掌柜,什么事情都不管。女性不再接受丧偶式育儿的模式,她们对男性在家庭内部事务中的参与提出了要求,对另一半的情感支持很看重,因此男性要既能外又能内。当男性回到家时,要主动做些家务,男性还要在一些节日特别是女性生日时准备个小礼物或给女性做餐饭来表示下浪漫,平时也给女性主动买些衣服,男性对这些生活琐事的参与在女性看来很重要,这被视为男性对女性的在意与爱,进而对增进夫妻关系很有意义。从年轻女性角度看,她们感受到并认同现代城市文化,追求核心家庭中的情感支持,同时她们所承担的照料劳动在科学育儿观念的影响下要投入很多从而比较辛苦,因而女性很看重婚姻中男性所提供的情感支持,这是她们衡量男性与婚姻质量的重要维度。农村年轻女性对夫妻间相处模式的要求趋近于城市中产家庭,但后者具有资本优势,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能够支撑起现代的情感导向的夫妻相处模式,然而农村家庭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尤其是对年轻男性的要求偏高,为此男性只得主动调适以适应女性的要求,否则其婚姻就不稳固。
2.做个好爸爸
成家后男性不仅要扮演丈夫的角色,在生育下一代后还要扮演父亲的角色,由此亲子关系中的父职问题凸显。在城市化进程中做个好爸爸的要求是首先要为下一代提供好的生活与教育条件,好的生活是给孩子买衣服、买玩具、买零食,即在物质条件上要提供得比较丰裕,还要带孩子到游乐场玩。除了生活条件之外,教育尤其重要,因而要给下一代提供好的受教育条件,由此推动了农民家庭的教育进城,在城里买房很大部分就是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随着孩子进城,妈妈随之跟着到城里陪读,这又增加了在城市生活的支出。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生活与教育条件要求男性的经济收入能支撑,这是好爸爸的经济基础。其次,在亲子关系互动中男性还要陪伴孩子,学会与孩子做朋友,传统的威权式的父亲角色受到否定,依靠棍棒的教养方式很难再奏效,现在对男性的要求是要能走进孩子的内心,为孩子所信任,这样孩子才愿意与其分享并听从其建议。然而经济与陪伴的要求之间存在张力,男性为了更多获取收入只得去外面务工,因而他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就很有限,他们更多是在务工间隙回来看看老婆孩子,给孩子带些礼物,平时更多与孩子通过手机视频进行交流,而不少男性为了节省开支,会尽量减少回家次数,因此男性不易达成二者的平衡。相较于传统男性,现在年轻男性在父职参与意识上要比之前积极,他们认同父亲角色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然而关键问题是其参与能力难与之相匹配,在外面务工与其陪伴并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之间存在张力,这又是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区位劣势紧密相关的,他们无法像东部地区那样形成本地务工模式。
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转型遭遇,无论是成家不易还是守家更难,都受到其市场区位条件的影响,城市化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对各地区农民家庭所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即为了更好地体验城市生活要进城买房,在夫妻关系中要注重情感的培养,在亲子关系中除了要对下一代教育与教养重视,还要多陪伴,这些现代化要求通过女性获得的优势地位而由其来推动。然而城市化进程中对家庭现代化的要求建立在家庭能力的基础之上,家庭能力与家庭所处的市场区位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区位条件紧密相关。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在工业化进程中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形成东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农业型欠发达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区位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在应对现代化的要求上颇为不易,一方面是夫妻分工下家庭劳动力利用的不充分与父代劳动力的闲置影响了家庭经济积累能力,另一方面男性外出务工,又影响了男性在分担照料与陪伴孩子方面的参与度从而影响其经营家庭关系能力的发展。
四、无根的个体化:城市化进程中转型失败的新生代农民家庭遭遇
家庭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个体化进程,这种个体化中个体是主动的,其个体本位是以自我为中心,个体是独立自主的。然而,城市化進程中转型失败的中国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家庭则陷入“无根的个体化”困境,即这种个体化是被动的,个体要么无法成家要么成家后却守不住家而被动成为孤立的个体,无根的个体化指涉的是因为无法嵌入家庭中,让个体无法找寻归属与意义,从而个体生命陷于悬浮与漂浮境地,个体由此陷入自我的放逐。
1.无根的被个体化
当年轻男性无法顺利成家即意味着成为“光棍”,那些未能守住家的男性因为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而很难再完成婚配,因此基本宣告男性“重返光棍”,无论是光棍还是重返光棍都意味着没有核心家庭做依靠。这些男性之所以没能顺利实现家庭的现代化转型,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年轻男性自身不愿苦做,在其看来做钢筋工以及做装修都很辛苦,这导致其经济收入能力在与其他男性比较中处于弱势,从而在婚姻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即使勉强成了家也无法支撑起家庭再生产而导致小家庭解体;二是其父代因病残而在对子代的支持程度上与其他父代相比处于劣势,这导致家庭的代际合力弱,因而这部分家庭能力与其他家庭相比处于弱势,这让其无法应对城市化进程中愈益增加的成家与家庭再生产成本而被甩出来。
之所以将在城市化进程中成为光棍与重返光棍而家庭转型失败所形成的状态称之为无根的个体化,在于中国家庭现代化的个体化与西方个体本位社会不同,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是在家庭中得以定位的,有研究者将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平衡称之为新家庭主义,即家构成了个体化的本体性的归属,当个体化没有家做依靠即处于无根状态,无论这种个体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家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特殊的价值意涵,中国人在家庭中获得本体性价值体验,有研究者将家称之为中国的宗教,这与西方个体直面超验上帝的宗教体验有很大不同。[桂华:《礼与生命价值——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宗教与法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8页。]虽然那些成为光棍与重返光棍的男性还有大家庭做支撑,但现代化下的家庭认同单位是核心家庭,即自己的小家庭才是个体意义归属的来源。
2.自我的放逐与躺平心态
没有“家”的年轻男性自然没有了城市化的动力,他们的生活场域回归乡村从而呈现出去城市化特征。当明晰进入家庭的希望已不大时,就失去了向上奋斗的动力,转而考虑的是底线的个体自我生命的维续。由于可以依靠农村的土地与宅基地而获得一定的生活资料,这让其对待务工的态度不再是辛勤劳动,而是转向量入为出。他们多半选择在工地上打零工,打一段时间工挣了点钱就会回到乡村生活,待挣的钱花得差不多时再出来打一段时间工,因而其打工呈现出消遣性,无论是对自我劳动力的利用还是劳动的辛苦程度都不充分。不像那些努力成家与守家的男性那样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与增加劳动强度获取更高收入,被个体化的男性打工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而是干少休多,当天气炎热时他们也会多休息一段,他们更不会主动去提高职业技能,而是停留在做最简单的可替代性强的工种。在他们的生活安排中,劳动更多是生活的点缀,他们既无辛勤劳作的压力也无动力,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闲暇活动上,他们属于农村的有闲群体,生活节奏要悠然很多。因为他们并不属于有钱群体相反在经济上处于较为困窘境地,因而在闲暇活动上更多选择低成本地打发时间,常见的活动是打牌、聊天、闲逛与钓鱼等。他们在村的生活节奏颇为舒缓,晚上玩手机到很晚,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其生活状态呈现出无压力的特征。
由于没有了家作为本体性的归属,这部分男性的自我停留在低层次的本我阶段,其价值追求是底线的自我生命的维续,维持基本生存的目标不难实现,由此带来其生活意义的无目的性与无着力点。这种生活状态持续到一定时间,他们会感觉没有价值的空虚与孤独,每天更多是周而复始无意义地打发时光,因此可将其心态称之为躺平心态。这一心态颇为消极,他们不再积极劳动,不再积极奋斗,对于生活是随波逐流,根本原因是他们已然被“家”甩出成为原子的个体。被动的个体化与西方主动的个体化有很大不同,后者即使不成家也能找寻个体的价值意义追求,如他们通过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与意义感,但前者还未发展到那么高层次的阶段。
3.逃离主流舆论与亚文化建构
由于那些无法成家与守不住家的年轻男性的生活场域呈现出去城市化即返回乡村的特征,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他们会面临村庄主流舆论的压力。在村庄社会评价中“光棍”一词本身就是负面标签,意味着他们为婚姻市场所淘汰而成为边缘群体。虽然村庄社会不再像以前对光棍那么强的排斥,但成为光棍或重返光棍仍然不光彩。这部分年轻男性成为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因而在村庄生活中他们在与他人互动交往中能够感受到来自主流舆论的压力。不仅如此,因为缺乏本体性价值的推动,那些被个体化的年轻男性走向消极的躺平,这种心态与村庄主流舆论不相符,被认为是懒、不务正业。在安徽淮南一个村庄的村支书就针对那些不愿外出务工的光棍,专门在村庄大喇叭中批评他们的行为,村支书的言语反映了村庄主流舆论的看法。
为应对来自村庄主流舆论的压力,这部分群体的策略是首先用不婚替代负面的光棍标签,他们会举例现在城里不少年轻人属于不婚族,以此混淆二者的实质差别,不婚是主动的行为,这与那些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而没有条件进行婚配根本不同。其次,他们还会通过减少与村民的交往以及与村民生活节奏错开等策略来逃离主流舆论。乡村拥有一定非正式的公共交往空间,这些公共空间扮演着公共舆论传播的功能,为了减少被大家谈论的压力,他们就会减少去公共空间的频率。同时他们还会尽量减少串门聊天频率以降低来自村庄舆论的压力,要么是在家待着看电视玩手机,要么会到外面转转。最后,他们还会通过建构亚文化与建构交往圈来弱化与消解主流舆论的压力。他们会与那些经历相似的进行交往互动,其更能玩到一起,这些关系可能是越出村庄的,他们会约在一起聊天打牌以及聚会吃饭,由此年轻人之间形成不同的圈子。通过建构属于这部分群体的自己人圈子,他们会形成一定的亚文化,这一亚文化认为是否结婚以及婚姻是否解体都是个体的私事,村庄进行干预是不义的,相反村庄应对其行为予以尊重,赋予个体自由选择权。这一亚文化还会通过将其无法成家与守不住家的责任向外转移,进而让外部因素对其形成的躺平心态负责,以此卸载其担负的心理压力。
五、城乡三元结构的生成与风险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状态不仅对个体、家庭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社会产生作用。以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形态的类型为标准可将城乡社会区分为三元结构,一是少数家庭通过考学而进入体面的体制岗位或者通过经商做生意而获取较高经济收入,这部分家庭实现了人的城市化,即完全城市化,他们可以在城市体面地生活与进行家庭再生产,既能成家又能守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家庭得以实现现代化转型。二是占到多数的通过苦做而勉力进城的农民家庭,这部分家庭未达到完全城市化层次而处于半城市化层次。买房只是进城的第一步,这部分家庭的收入距离在城市体面生活尚有不小的差距。半城市化不仅指涉的是其城市化层次不高,还包含这一层次的城市化并不稳定,其处于城乡间的摇摆状态。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生活面向已从乡村转向城市,他们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再加上对下一代教育的重视进一步增强了进城的动力,然而在城市开展现代生活与家庭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与其家庭能力不相匹配,因此其承担的压力大,处于成家不易与守家更难的焦灼境地,倘若成本再增加,就很有可能滑向更低的层次。三是占到一定比例的因成不了家或守不住家而被個体化的家庭,从城市化进程退出而呈现出去城市化特征,这种去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不同,后者是在郊区各种公共服务便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主动选择,而前者则是被动地没有了追求家庭现代转型的动力与压力,他们选择在乡村躺平,这导致其不仅心态消极,而且对自我劳动力的利用不充分,进而对宏观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供给产生不利影响。从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处境角度看,城乡形成了完全城市化、半城市化与去城市化的三元结构,这比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要更为复杂。
城乡三元结构中半城市化的农民家庭所占比重最大,其在城市化进程中压力也最大,受制于家庭能力,其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带有不确定性,很有可能从半城市化滑向被甩出城市化进程的被动的去城市化。半城市化的不稳定性要求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上要秉持稳健有序渐进的态度,然而不少中西部地方政府从短期的土地财政与政绩角度考虑采取的是激进主义,一方面通过控制农村宅基地兴建的审批以及鼓励农民退出农村宅基地来推动农民进城买房,另一方面通过将公共资源向城市倾斜特别是优势资源向城市的集中倒逼农民进城。地方政府的激进做法未能考虑到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区位劣势导致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家庭能力不足,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生活与开展再生产所需要的家庭资源积累之间不相匹配,因而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周期来增强与发展家庭能力,短时间的盲目进城只会增加家庭面临的压力,进而压力会向家庭内部成员传导,其中的弱势群体——老年人被牺牲的风险就会增加,同时小家庭的秩序也面临不稳定。
城乡三元结构中处于最低层次的去城市化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很大,由于这部分群体已被甩出来成为孤立的个体,他们进而追求的是本我的低水平满足,这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此外,他们所形成的躺平心态不仅导致心态趋于消极被动,同时由于他们作为重要的劳动力,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所需要的重要劳动力资源,但是他们在没有向上奋斗动力的情况下不愿积极劳动而让自己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这从宏观上会使得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需失衡,从而增加用工荒趋势。近年来新闻媒体报道的从老板挑工人到工人挑老板,老板举牌等着工人来选,工人的各方面待遇都有了不小的提高的情况下招工却变得越来越难,这不仅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还与存量劳动力的闲置有关。不仅如此,他们不愿辛苦的劳动态度,使得其即使在工作时也不会认真积极,而是比较消极懒散,这让管理难度增加,企业的生产效率无法得到保证。
在农民家庭的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完全城市化、半城市化与去城市化的城乡三元结构中,无论是半城市化还是去城市化都存在不小的风险,这需要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与方向上做出调适。首先,中西部地方政府应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从而拓展本地就业机会,一方面增加对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利用,从而增强家庭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让一部分男性可以在本地务工,从而形成离土不离乡的家计模式,这有助于男性对核心家庭内部事务的参与,进而推动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中西部通过承接产业结构的区域转移,能够对区域间工业布局的不均衡适当调整,进而让工业化惠及更多地方。其次,地方政府应从农民家庭能力角度思考城市化的推进,即城市化应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的城市化才是核心,而不应该是土地城市化,否则盲目推动农民进城就会导致城市内二元结构的生成,即那些进城家庭沦落为城市中的底層。以农民为主体的城市化应采取渐进稳健的路径,即基于农民家庭能力而自主选择,关键是对那些尚不具备进城能力的农民提供保障,一方面通过城乡公共资源的配置为农民家庭留有希望,特别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上要从之前对乡村的过度抽取转向城乡均衡发展,尤其是通过对乡村教育布局的优化整合,凸显乡镇学校的中间作用;另一方面要为农民家庭留有退路,因为占多数的农民家庭呈半城市化状态,很有可能面临城市化的失败而返乡,这时农村的耕地与宅基地就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对此地方政府不应用各种政策与制度“诱导”农民退出耕地与宅基地,其政策应与农民家庭城市化阶段及多数家庭所处状态相适应,即要尊重农民家庭的自主选择。
六、结语
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也在经历快速转型,其中关键变量即是城市化进程,作为现代化程度重要衡量指标的城市化对微观的农民家庭产生什么影响需要深入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家庭转型陷入多重“陷阱”与风险中,包含家庭层面的成家与守家不易、个体层面的被动的个体化与躺平心态、社会层面的城乡三元结构。农民家庭转型之所以遇到困境,在于占到多数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婚姻市场区位劣势大大推高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婚姻与家庭再生产成本,但由于劳动力市场区位劣势导致农民家庭能力难与之相匹配,少数家庭能力强的能够实现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他们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家庭能力次之的则陷入成家与守家不易的半城市化,家庭能力最差的则未能成家与守住家而选择返乡的去城市化,三类群体的生活场域呈现阶层化的区分。对此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地方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针对农民家庭转型的遭遇,需要在承接产业结构转移以提升农民家庭能力与为未能顺利完成城市化转型的农民家庭提供保障与退路两个方面使力。
城市化进程不仅对宏观制度层面产生重要影响,还会对微观层面的家庭领域产生重要作用,同时在理解微观家庭转型基础上有助于增进对城市化发展的认识,从而思考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诸问题都离不开对城市化这一核心变量的分析,通过考察城市化所启动的中国农民家庭转型经验有助于研究者提炼出家庭现代化转型的本土化理论,这要求研究者在与西方家庭现代化充分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概括,本文中的市场区位、家庭能力等尚不太成熟的概念即是对此所做的初步尝试。
(责任编辑:何 频)
sdjzdx202203231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