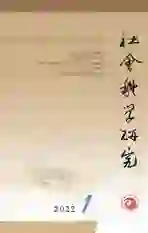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角色的构造
2022-03-22李扬
〔摘要〕 知识产权法政策学是研究知识产权法制度设计及其运行技法的学问。按照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知识产权是一种制约他人行动自由的特权,在其设计与运行过程中,立法、行政、司法、市场应当分担不同的作用。在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在适用法律处理个案过程中,无论面对立法、行政还是市场,都应当发挥能动性,立足于改善作为知识产权正当化根据的效率性和一般公众的行动自由,在个案中积极纠正立法、行政或者市场中不利于实现效率性或者过度妨碍一般公众行动自由的做法或者因素,促进创新和创造,以此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
〔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政策学;效率; 行动自由 ;司法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3.4;DF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1-007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知识产权反公地悲剧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研究”(18BFX163)
〔作者简介〕李扬,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100088。
①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第九点、《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第三点。
②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的统计,2020年,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525618件,审结524387件,比2019年分别上升9.1%和10.2%。最高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3470件,审结3260件,比2019年分别上升38.58%和64.98%。地方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43326件,审结442722件,比2019年分别上升11.1%和12.22%。地方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二审案件42975件,审结43511件,比2019年 分别下降13.54%和10.67%。最高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1909件,审结1735件,比2019年分别上升79.08%和96.27%。地方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18464件,比2019年上升14.44%,审结17942件,比2019年增加4件。地方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二审案件6092件,审结6183件,比2019年分别下降16.59%和上升4.06%。地方各级法院新收侵犯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5544件,审结5520件,比2019年分别上升5.76%和8.77%,新收涉知识产权刑事二审案件869件,审结854件,同比分别上升7.55%和5.85%。
引言
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5年12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①2017年11月20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不断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環境,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三个关于知识产权的纲领性文件,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创新的重大意义,为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些重大决策部署,近十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大力强化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②,中国法院日益成为国内外当事人信赖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优选地”。[许昊:《发挥司法在知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人民法院报》2018年4月9日,第2版。]
究竟如何理解上述三个纲领性文件中的“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理解为“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终局裁判作用”[吴汉东、锁福涛:《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理念与政策》,《当代法学》2013年第6期;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课题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研究——以湖北省司法与行政“双轨制”知识产权保护为研究对象》,《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也有观点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理解为“司法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唯一途径”。还有学者结合上述三个纲领性文件的规定认为,“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是专门针对行政保护知识产权的作用而言的,司法也只有在面对行政时,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对于立法和市场而言,司法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2019年6月17日,在西南政法大学笔者主讲的“中国知识产权名家讲坛第27讲”上,该校邓红光教授、黄汇教授、易健雄副教授、曹伟副教授持这种观点。]本文无意评述这些观点和探讨何为“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而意在另辟蹊径,引入知识产权法政策学的视点,从司法对立法、司法对行政、司法对市场三个关系面向,探讨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角色构筑,以期为上述三个纲领性文件确立的战略决策得以更好贯彻提供可能的理论支撑,并为理论界重新思考知识产权司法过程提供一个全新的视点。
一、知识产权法政策学的视点
日本著名知识产权法学者田村善之将日本民法学者平井宜雄构建的法政策学[按照平井宜雄先生的论述,法政策学是指从法律层面对决定理论进行重构,并结合日本现有实在法体系,设计法制度或者规则体系,以期就日本当前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控制或者提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向法律决定者提供建议,或者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和技法。要言之,法政策学,即关于法制度设计的理论以及技法。参见平井宜雄:《法政策学——法制度設の理论と技法》第2版,東京:有斐阁,1995年,第5页。]基本原理应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发展出知识产权法政策学的构想。
知识产权法政策学并非要从传统政策学的视角研究知识产权法,更不是将知识产权法当作国家政策或者其他政策的一部分,而是要从法的视角出发,利用社会行为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系统论、决策科学等,研究知识产权法制度的设计及其技法,属于以法学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独立学科。[平井宜雄:《法政策学——法制度設の理论と技法》第2版,第1—4页。]
按照知识产权法政策学的视点,要创设出一套合理且能够在实践中运行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制度,首先需要解决通过法律创设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依据。关于知识产权正当化的依据,理论上存在自然权利理论和激励理论之争。[对知识产权自然权利理论的详细介绍和评论,可以参见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pp.41-91.]自然权利理论认为,人对自己的创作物当然享有权利。激励理论主张,如果过度地允许免费使用创作物,后来的模仿者将处于过分有利的地位,从而可能导致对知识财产创作进行投资的先行者数量减少。为了防止这种现象,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禁止免费使用的行为。
自然权利理论又有洛克的财产劳动所有权理论和黑格尔的财产精神所有权理论之分。洛克的财产劳动所有權理论认为,由于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所以人对其身体劳动的产物也拥有所有权。但是田村善之教授认为,洛克的财产劳动所有权理论用于知识产权正当化论证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知识产权中,洛克财产劳动所有权理论的前提命题不成立。洛克的财产劳动所有权理论存在如下前提命题:上帝为了使人类利用自然,将自然这种共有物给了人类所共有,而且在其腐烂之前,人类通过劳动在自然物的基础上生产出与其相区别的物品。为了利用该物品而对其主张所有权,并不需要共有物其他相关者的同意。[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86-289.]知识财产不像有体物那样只能由一人独占,权利人即使不对他人利用行为行使排他权,自己亦可进行利用,并不会腐烂。换句话说,知识产权不像有体物那样,存在使用和消费上的排他性和消耗性,不存在腐烂和浪费现象。二是知识产权和财产劳动所有权的理论基础——自身所有的原理相矛盾。洛克财产劳动所有权理论认为,人类对其自身享有所有权,这是一种无需证明的自然权利。既然如此,人类对自己身体的劳动和自己的双手所从事的工作也享有所有权。所谓自身所有权,是指除了自己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对这个“自身”主张权利。[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pp.287-288.]而知识产权的情况与之不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直接或者间接制约他人身体活动自由的权利,显然与洛克财产劳动所有权理论所主张的“自身”所有权相矛盾。田村善之教授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财产劳动所有权理论当中为知识产权寻找正当化的积极根据是困难的。[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載《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第20号,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2008年3月,第1—2页。]
田村善之教授亦不赞成将自然权利理论的另一支,即黑格尔所主张的精神所有权理论作为论证知识产权正当化的依据。精神所有权理论主张,知识产权是创作者人格的表现物,因而应当受到保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人在自由意志的表现上应当拥有财产权。其理由是,在精神世界中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生活在外部世界的时候,必然会对外界做出某些决定,自由意志决定将外界作为自己的东西时,其最初的具体化的形象即是财产权。否定财产权,自由意志也就不可能存在。[G.W.F.Hegel,《法哲学講義》,長谷川宏訳,東京:作品社,2000年,第102—109页。]但是,由于外部世界同样存在作为他人自由意志表现的财产权,因此通过自由意志将外界作为自己财产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他人的自由意志,从而对自己财产的利用行为进行必要限制。田村善之教授认为,这一点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在物质性社会的外界中生活而言,拥有有形物质的财产权就足够了,知识产权并非必不可缺少。即使认为知识产权不可缺少,知识产权与他人自由意志表现的财产权的行使也会发生冲突。据此,田村善之教授认为,仅仅以自由意志的表现为依据,论证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进而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绝对化的权利,亦值得商榷。[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第2—3页。]
在田村善之教授看来,知识产权表面上是创造者对其创造的抽象物进行排他利用的权利,但实质是人为拟制出来的一种制约他人行为模式的权利,其正当化根据不能仅从洛克的财产权劳动理论或者黑格尔的财产权人格理论中去寻找。仅仅由于是人的劳动产物或者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就可以因此而享有权利,广泛制约自身以外的他人的行动自由,以此将知识产权正当化并不具有足够说服力。知识产权正当化的依据,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而必须将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人的行动自由的利益作为重要因素纳入考量中。换句话说,对某种程度上的搭便车行为,如果不加防止,致力于创新创造的人将因此而过度减少,一般公众将因此蒙受损失,这种有利于一般公众的福利性观点或者说效率性观点,才真正是制约他人行动自由的知识产权正当化的依据。从福利或者效率性的观点来看,人的创新创作,即劳动,最多不过是知识产权正当化的消极依据。这些看法是具有工具主义性质的激励理论所提倡的知识产权正当化的核心观点。[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第5版,東京:有斐閣,2010年,第7—9页。]
在解决了知识产权正当化、知识产权制度创设和运行的理论依据之后,田村善之教授所持的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进一步主张,尽管应当在社会整体福利或者效率性的改善上追求创设和运行知识产权制度正当化的根据,但特定知识产权制度的创设和运行到底是改善还是恶化了一般公众的福利或者效率性,如果改善了,则改善的程度如何,并不容易测定。这一点正像郑胜利教授指出的,要证明一种知识产权制度给社会带来多少好处很难,但要证明一种知识产权制度给社会带来多少坏处,则相对容易。[郑胜利:《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57页。]为此,田村善之教授指出,知识产权制度创设和运行的正当化积极根据,除了不应当聚焦于在现时点上的、短期的、静态的效率性的改善程度而应当致力于未来的、长期的、动态的效率性改善之外,还应当寻求创设和运行这一制度在民主决定程序上的正当性。在此情况下,知识产权制度正当化的根据,一部分就依赖于立法机关的政治责任。[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第5版,第11—12页。政治责任是指政治官员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并推动其实施的职责及没有履行好职责时所承担的谴责和制裁。政治责任不仅仅是对政治责任主体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即形式正义的评价,更是对其政治性决策及其后果是否合理正当即实质正义的考察。关于政治责任特点的论述,可以参见王美文:《当代中国政府公务员责任体系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第117—120页;刘俊生:《中国人事制度概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2—283页。]作为立法机关在民主立法程序基础上的一种法政策选择,结果无论是否增进了效率和兼顾了他人行动自由,都只能承认该种选择具有正当性。
虽然立法机关经过公开、透明的民主决定程序创设出来的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具有正当性,但现实可能发生偏离。其中原因,除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立法者理性认识能力受到限制等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根据集合行为理论,立法机关在进行民主决定过程中,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容易被组织化的利益,相比分散于汪洋大海中的多数人手中、不容易被组织化的利益,更容易因游说等制度被其充分利用而在立法上得到反映和确立,后者的利益则缺乏足够的保障。[マンサー·オルソン(Manson Olson)《集合行為論-公共財と集団理論》新装版,依田博、森脇俊雅訳,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年,第10—11·41—42·157—159·181—182·202—203頁。]由此从福利或者效率性的视点来看,依赖于公开、透明程序的立法机关所从事的民主决定,容易出现利益反映不均衡的现象。由于除了追求效率和福利之外,还有确保自由的必要,知识产权制度的创设和运行,仅仅在立法上寻求程序的正统性依然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出发,田村善之教授所持的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认为,围绕知识产权制度的创设和运行,市场、立法、行政、司法应当扮演不同的角色,分担不同的作用,对此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角度展开讨论也就成为了知识产权制度论的关键。[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第4—6页。]具体而言:
1.市场的活用。立足于知识产权正当化的激励理论而非自然权利理论,在具有创新诱因功能以及私人发现和扩散信息功能的市场本身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解决效率性的情况下,由市场决定知识财产的创出和分配即可,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威决定没有必要介入。认为在出现个别现行知识产权法尚未权利化的创新创造物时,就直接认定这是现行法保护上的缺陷,并主张有必要针对该对象进行知识产权配置,是学术界的短浅观点。即使没有法律介入,市场先行利益和评价也可以确保适度的成果被开发出来。在此情况下,人为创设制约他人行动自由的知识产权就丧失了根据。这种视点可称为市场指向型知识产权法的视点。[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第6、9—10页。]
2.法律介入和权威决定。未创设排他权的市场决定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效率性问题。即使已经创设了排除权,也不能低估赋予排他权给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知识利用行为带来的成本。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市场决定失灵。在市场决定失灵,无法解决知识产权创新创作激励机制,因而需要法律介入和权威决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才能登场。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可否创设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种类和保护范围应当由立法、司法、行政哪个机关作出判断和决定?具体规制方法是赋予权利人停止侵害请求权还是报酬请求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抑或是通过登记制度的介入使权利转让变得便利?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对权威机关和法律规制方法的选择,使法律制度具体化。这种视点可称为功能型的知识产权法视点。
细言之,在市场决定失灵,确实需要权威决定介入但所欲达成的效率性目标又不明确的情况下,由具有程序正统性的立法进行意思决定,成为承担政治责任的主体,更为合适。但在某些需要专门技术知识并紧急进行判断以迅速应对现实需要的事项方面,专责管理机关相比立法和司法而言,更为专业,更适合于对这些紧急事项作出权威决定。
然而,并不是依靠立法决定和行政决定,效率性和自由就可以完全得以实现或者保证。围绕立法决定过程中利益反映不均衡的现象,以及行政决定过程中严重阻碍效率性实现和行动自由的现象,在技术适格性已经逐渐消除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司法积极介入,以维护立法决定过程中未被顾及的利益,消除阻碍效率性实现和行动自由的体制、机制和做法。这种视点可以称为自由统御型的知识产权法视点。[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第5版,第11—26页。]
总结田村善之教授所提倡的知识产权法政策学,可以将其核心观点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知识产权是一种制约人的行动自由的权利,以劳动所有权理论、精神所有权理论等自然权利理论及其存在的意义正当化知识产权存在理论上的难题,知识产权正当化的积极根据不得不依靠以改善效率性为目标的激励理论。
2.效率性的判断标准存在争议,除了效率和自由之间的矛盾,效率性改善程度的检测也存在困难,所以知识产权的正当化也需要引入程序正义视点,即知识产权正当化离不开负有政治责任的民主决定的程序正当性。
3.在知识产权的民主决定过程中,易于组织化的大企业的利益容易得到反映,不易组织化的广大私人的利益难以被反映,因这种利益反映的结构性不均衡的作用,知识产权存在被过度强化的危险。
4.为了尽可能消除利益反映的不均衡现象,探索统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构造,同时确保他人的行动自由,应当运用司法的作用,保障程序的正当性。
5.从效率性的观点看,尽可能释明所希望的制度,将应该确保的自由领域明确化,缩小由程序决定的自由裁量的范围。[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第20—21页。]
田村善之所提倡的知识产权法政策学,尽管2010年就由笔者和现任暨南大学法学院讲师的许清博士一起翻译推介到国内[田村善之主编:《日本现代知识产权法理论》,李扬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38页。],但其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至今尚未被我国知识产权界充分认识。就笔者的解读和认知而言,建立于激励理论基础之上、依赖程序正义、兼顾效率和自由,意在为设计一套能够良好运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具体手法的知识产权法政策学所揭示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比如,其所提出的民主立法过程中存在的利益反映不均衡现象、具有技术优势的知识产权专责机关可能采取的阻碍效率性实现的现象等,决定了司法应当积极介入知识财产的创造、利用和分配过程,以确保利用者的行动自由,克服效率性实现障碍的观点,市场、立法、行政、司法在知识产权制度创设和运行过程中应当分担不同作用的观点,等等,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而言,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下文将紧密结合上文所介绍的田村善之教授所提倡的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从司法对立法、司法对行政、司法对市场等三个关系面向,详细探讨司法在保护知识产权过程中的角色构造。
二、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对立法关系面向的角色构造
如上所述,一方面,以效率性为目标由立法创设的知识产权制约了他人的行动自由,作为其正当化根据的效率性改善的程度不容易检验,所以不得不通过民主决定的方式以寻求该制度在程序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依赖程序正当性的民主决定形成过程中,易于组织化的大企业、大集团等主体的利益容易得到体现,而不易组织化、分散于汪洋大海的小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不容易得到体现,因而形成立法上利益反映不均衡的现象,对这种不均衡现象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和途径加以纠正。
基于上述视点,就司法对立法的关系面向而言,对于知识产权的创设和强化解释,司法首先应当尊重立法的意思决定,努力从法条构造中领会知识产权法的趣旨,并以此进行解释。尽管相对于立法而言,司法无需承担很重的政治责任,但也应当注意其就知识产权的创设和强化解释生成专业、综合的判断时,从技术适格性上看,受到立法构造的限制[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第11—12页。],因此原则上应当坚持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能随意无视和超越立法的意思决定,毫无克制进行造法活动。[对知识产权法官造法的批判,参见崔国斌:《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不过本文并不赞成崔教授在文中所列举的一系列“法官造法”现象及其对这些“法官造法”现象的批判。关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含义、理论基础及其适用,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兼与梁慧星、易继明教授商榷》,《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否则,司法真有可能变成法治主义最精致的破坏力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司法对于立法而言,坚持传统法治主义原则,坚持绝对权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忠实扮演法律适用者而非立法者的角色,就是应有之义。
在商标权领域,最近几年不断出现这样的判决,即利用商标的所谓品质保证机能,将改变商品包装、磨损商品序列号后进行销售但并不导致相关公众混淆商品来源因而并不损害商标来源识别机能的行为,认定为侵害注册商标权的行为。[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知初字第416号《民事判决书》。]然而,无论是1982年和1993年商标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2001年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还是2013年和2019年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均只保护注册商标的来源识别机能。[李扬:《商标法基本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225—226页。]司法通过扩大商标的独立机能从而扩张注册商标权保护范围,限制他人選择和使用商业标识自由的做法,显然超越了商标法立法意思决定的范围,严重背离了知识产权法定原则。
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判决,即将“容易导致混淆的”解释为既包括正向混淆(即相关公众误以为被告的商品来源于原告)也包括反向混淆(即相关公众误以为原告的商品来源于被告),从而将引发相关公众反向混淆但并不引发相关公众正向混淆的商标使用行为,认定为侵害注册商标权的行为。[我国法院引用反向混淆理论的典型案件有:“蓝色风暴”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民三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2000”案,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浙民三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卡斯特”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新百伦”案,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44号《民事判决书》。]然而,1982年、1993年、2001年、2013年、2019年的商标法所禁止的“混淆”,是否包括“反向混淆”文言上并不明确,这至少说明商标立法决定者在是否要禁止“反向混淆”行为的问题上,态度犹豫不决。司法是否可以通过扩张解释,如此果断地替立法者朝着强化注册商标权保护的方向作出具有立法性质的意思决定,不无疑问。[李扬:《商标法基本原理》,第227页。]
在著作权领域,日本出现了大量这样的判例,即利用日本最高裁判所在“猫眼俱乐部”案开创的有关著作权侵害主体论的“卡拉OK法理”,将提供诱发大量私人复制行为和非营利性使用作品行为的工具、手段、场所、服务的提供者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认定为著作权侵害行为的直接主体,并允许著作权人针对这些提供者主张停止侵害。[日本最判昭和63.3.15民集42巻3号199頁。对该案以及后续一系列案件的详细介绍及其评论,可参见李扬:《日本著作权间接侵害的典型案例、学说及其评析》,《法学家》2010年第6期。]“卡拉OK法理”仅仅为了解决原告主张停止侵害的请求权基础问题,就将为日本著作权法上规定的著作权限制与例外领域中的合法利用作品行为提供利用工具、手段、场所或者服务的行为,通过司法拟制为直接侵害著作权行为,完全超越了知识产权对直接利用人进行人的支配这一主要领域。[田村善之:《検索サイトをめぐる著作権法の諸問題―侵害、間接侵害、フェア.ユース、引用など》(1)(2)(3),載《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第16、17、18号,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2007年8月、11月、12月。]
商标的品质保证机能是否要独立于商标的来源识别机能受到商标法保护,反向混淆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商标权行为,诱发大量非营利性使用、私人复制系统的提供行为是否需要进行规制;若需要进行规制的话,是仅仅赋予原告损害赔偿请求权还是同时赋予原告停止侵害请求权,这些涉及产业发展和文化多样性(效率性)以及他人利用自由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争议巨大,司法在少数个案的短暂探索难以把握未来立法者可能会选择的方向,因此还是应当交由负有政治责任的立法进行决定。
然而,司法所面临的立法构造上的限制,并不意味着司法在立法意思决定面前就只能无所作为,更不意味着司法绝对不能沿着创设和强化知识产权(不管是绝对权还是非绝对权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的方向对已有的立法决定进行解释。在现有的立法决定已经阻碍作为知识产权正当化根据的效率性实现,同时并不存在技术适格性限制,也不过度限制他人行动自由的情况下,似乎没有理由绝对不允许司法积极介入。只不过司法进行介入时,应当遵循法条的构造、揣摩法制度的趣旨进行解释。[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第12页。]这种情况在知识产权领域,可以说大量存在。
在著作权领域,伴随着创作和传播技术进步而出现的网络游戏,虽然不存在电影作品或者类电作品一样的摄制过程,除挂机部分之外,其他部分的呈现需要借助游戏玩家的行为,与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借助机械设备自动播放的方式不同,但在上海飞狐网络科技公司诉霍尔果斯侠之谷信息公司、广州柏际网络科技公司侵害网络游戏《昆仑墟》前81级整体连续影像画面以及82幅美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以及上海恺英网络科技公司、浙江盛和网络科技公司与苏州仙峰网络科技公司侵害页游《蓝月传奇》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广州互联网法院和杭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并未拘泥于技术上的限制,而是抓住挂机网络游戏(广州互联网法院)或者非挂机网络游戏(杭州中级人民法院)的表达方式和电影作品、类电作品本质上相同,都不过是“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动态影像画面”,进而将其认定为类电作品进行了保护。[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18)粤0192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3728号《民事判决书》。]这种裁判手法可以确保游戏开发者投资风险巨大的网络游戏开发和运行的激励,增加越来越挑剔的游戏玩家们的整体福利,也并不妨碍他人创作和运行同类型的游戏,正好是著作权鼓励作品创作和传播立法趣旨的具体表现,这种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介入著作权法制度运行的司法裁判做法,可以说完全在立法决定的意思范围内。2020年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款将原著作权法的电影作品、类电作品改为“视听作品”,从而将网络游戏纳入视听作品保护范围,说明司法在某些个案中沿着强化著作权保护的方向解释法律,并不违反立法者的意思决定。
在专利法领域,虽然现行《专利法》第十一条并未将提供专门用于侵害他人专利权的材料、设备、零部件、中间物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侵害专利权行为,但如放纵这些行为,未经许可直接实施他人专利技术的行为必将因此而获得极大便利。虽可追究直接实施行为人侵害专利权的责任以保护专利权人,但这些专用材料、设备、零部件和中间物的存在对于专利权人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此等因素的联合发酵,专利法立法者所期待的通过授予和保护专利权从而促进技术公开和创新并使整个社会大众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的趣旨必将受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将“明知有关产品系专门用于实施专利的材料、设备、零部件、中间物等,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将该产品提供给他人实施了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和“明知有关产品、方法被授予专利权,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积极诱导他人实施了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分别解释为帮助侵害专利权行为和教唆侵害专利权行为,可谓准确揣摩专利法制度趣旨、踏寻专利法法条构造沿着强化专利权保护方向解释法律的典范。
对于无法或者尚未在《著作权法》或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单行知识产权法中被规制的欠缺独创性的数据库或者其他信息集合体、具有纯粹经济价值的某些客体(人物形象、虚拟角色名称等)[即被称为“商品化权”的保护客体。参见知的所有権実務編集会議編:《商品化権》,東京:三樹書房,1994年。]的利用行为,在原被告之间具有具体竞爭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兼具公私法混合性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或者通过《民法典》关于保护民事权益的一般条款进行规制,作为创设利益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的解释,尽管被很多学者批判为违反了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关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及其缓和,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兼与梁慧星、易继明教授商榷》;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缺陷及其克服——以侵权构成的限定性和非限定性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2期。],违背了立法决定的趣旨[王太平、杨峰:《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领域》,《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确实应当慎重,但也没有到完全堵塞不允许存在任何例外的地步。在效率性能够得到改善又不过度限制他人利用自由的限度内,允许司法以法律条文构造为基础,朝着进行创设利益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方向解释法律,可以说仍然在民主决定的框架之内。
具体而言,当原告付出了劳动和投资的某种知识成果已经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成了市场交易的对象,而允许被告免费搭便车使用将导致开发该知识成果的激励不足时,为了保证该知识成果的供应,即使尚未存在立法决定,从知识产权正当化积极根据的效率性视点出发,允许司法不再保持谦抑,朝着创设非绝对权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利益)方向进行解释,既有利于促进该成果的开发和供应,也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李扬:《法政策学视点下的知识产权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23—39页。]简言之,对于立法尚未作出决定且在《著作权法》等单行法上欠缺保护要件的某些知识成果,应当在激励理论指导下,进行是否应当保证该成果供应激励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是否允许司法朝着创设知识产权的方向解释法律的结论。说到底,这种解释虽然不符合著作权法等专门法立法者的意思决定,但仍然可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典》等立法者的意思决定范围之内。
从实务上看,已经出现不少这样的判决。比如,在金庸(CHA,Louis)诉江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典博维公司)、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购书中心)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虽不认为被告作品《此间的少年》利用原告诸多作品中的人物名称、人物性格、人物关系等抽象元素侵害原告著作权,但也明确认为“原告作品中的人物名称、人物关系等元素虽然不构成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不能作为著作权的客体进行保护,但并不意味着他人对上述元素可以自由、无偿、无限度地使用。本案中,原告作品及作品元素凝结了原告高度的智力劳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读者群体中这些元素与作品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具备了特定的指代和识别功能,具有较高的商业市场价值。原告作品元素在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情况下,在整体上仍可能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并据此认定被告不正当攫取了原告应当享有的利益,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68万元人民币。[参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2068号《民事判决书》。]日本也存在同样处理手法的判例。在日本《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2条第1款第3项新设立商品形态酷似性模仿规制之前,一直存在将酷似性模仿他人商品形态认定为不法行为[东京高判平成3.12.17知裁集23卷3号808页“木目化妆纸”事件。];将不具有独创性而不作为作品进行保护的网罗型数据库的利用行为,认定为不法行为,以保护开发者的利益[东京地判平成13.5.25判时1774号132页。];以及明确否定保护客体的著作物性但仍然肯定免费使用行为人应当承担不法行为责任的判例。[知财高判平成18.3.15平成17(ネ)10095“通勤大学法律课程”事件。]
要指出的是,虽然上述情况下允许司法积极介入以确保新成果开发的激励,但从规制手法上看,赋予原告金钱请求权即足以确保其开发这些成果的激励,赋予原告对他人使用这些成果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将过度强化权利人的排他性利益,不利于他人利用成果的行动自由,可以说已经超出立法决定的限制。[李扬:《法政策学视点下的知识产权法》,第30—39页。]
以上讲的是司法对知识产权法中的立法决定进行扩张解释的技法。与此不同,对知识产权法中的立法决定进行限制的解释,则应当围绕立法决定形成过程中利益反映的不均衡问题,依靠司法的判断在个案中加以调整,而不是期待需要更多时间成本的立法决定进行更正。此种解释的根据不在于改善不容易检测的效率性,而是为了及时在个案中确保使用者的自由。因不存在太多技术适格性限制,也不涉及立法决定的政治责任问题,在对知识产权的限制方面允许司法积极介入既有可行性,也有必要性。[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第13—14页。]
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限制,采取的是在《伯尔尼公约》规定的三步检验法之下的限制与例外模式,并不存在美国式样的限制著作权一般条款的合理使用。在此情况下,努力揣摩《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关于著作权限制规定的趣旨以及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并以该条规定的两个一般性要素,即“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和“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进行限定,以探寻《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特定情形之外的著作权限制情形,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事实上,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采取这种手法的值得肯定的判例。比如,在《受戒》案中,针对被告未经许可将原告拥有著作权的小说《受戒》拍摄成电影在学校内部播放以及参展法国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并入围法国克雷芒电影节以及在参展会上播放的行为,法院认定,虽然被告利用原告作品方式不属于1990年《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翻译或者少量复制行为”,但被告将原告拥有著作权的小说拍摄成电影在学校内部免费播放的行为,仍然属于1990年《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为了课堂教学的合法行为。[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5)一中知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在吴锐诉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7)海民初字第807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定,被告复制他人作品片段供公众搜索的行为,“主要目的是给读者介绍图书,使读者了解图书的主要内容,并根据极少量的正文阅览,了解作者的基本思路和表达方式”,属于2001年《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适当引用”行为。
在对专利权利要求进行解释时,虽然专利法未明确规定禁止反悔原则和捐献原则,但为了确保公众对自己可以实施的技术范围的可预见性,侵权诉讼过程中,法院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不允许权利人在专利授权确权过程中明确放弃保护的技术方案,在侵权诉讼过程中重新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而产生二次获利现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同样,按照《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据此,未能得到说明书支持的权利要求,不予保护自不待言。“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求中未记载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中将其纳入保护范围的”,也应当在捐献原则指导下,视为权利人对社会的奉献,不予保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书》。]
2019年《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在先使用抗辩,因规范目的在于克服商标权注册主义的不足,保护商业标记既有使用事实和商誉,加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像商标法第五十九条那样规定商业标识在先使用抗辩,因而该条中的“在先使用商标”,就应当理解为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的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最低限度知名度的发挥了识别商品来源的所有商业标记。[李扬:《商标在先使用抗辩研究》,《知识产权》2016年第10期。]
綜上所述,基于知识本身非有形财产客体的非物质性和利益平衡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知识产权立法[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兼与梁慧星、易继明教授商榷》。],由于过分坚持侵权构成的限定性从而可能导致随科技发展而新出现的知识性利益、被民主立法程序有意或者无意忽略的知识性利益或者他人的行动自由难以得到保护[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缺陷及其克服——以侵权构成的限定性和非限定性为中心》。],这就要求司法充分施展法律解释者的角色,树立专利法等狭义知识产权法、竞争法、民法、诉讼法、刑法等属于知识产权法的整体性知识产权法观念[李扬:《重塑以民法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产权法》,《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充分发挥体系性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社会学解释方法、比较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漏洞补充方法等法律解释方法的作用[李扬:《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I——基础理论》第7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24—230页。],尽可能从宪法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私法原则中发展出默示许可抗辩、权利懈怠抗辩等原则乃至规则[李扬:《商标侵权诉讼中的懈怠抗辩——美国法的评析及其启示》,《清华法学》2015年第2期。],以弥补立法者理性认识能力不足造成的效率性难以实现的缺陷,调整立法中由于利益集团游说等原因造成的利益反映不均衡的结构性现象,从而使知识产权制度的创设和运行既有利于实现效率性,又能够兼顾他人的行动自由。虽然由于宪法构造限制,司法不能够违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随意改变具有政治责任的立法决定,但从及时克服立法中不利于效率性和自由的障碍角度而言,司法从法条本身采用的文言出发,对知识产权适当作出扩张或者限缩解释,而不是等待立法者通过漫长的修法活动重新作出意思决定,并未背离法治主义的要求。僵硬地坚持在立法决定限制下,司法只能扮演判决输出机器者角色的观点,并不符合现实需要。
三、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对行政关系面向的角色构造
按照知识产权法政策学司法和行政在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成和运行过程中,应当分担不同角色的视点,从技术适格性角度看,需要对传统法治主义模型进行再认识。[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第14—15页。]
传统法治主义认为,对于特定时空的法律,首先无论司法还是行政都必须尊重立法决定的拘束力,其次行政仅仅是执行法律管理社会的手段,其合法性甚至合理性都必须服从司法的全面审查。[田村善之主编:《日本现代知识产权法理论》,李扬等译,第27页。]然而,商业标识领域,经济活动在不断变动,作为规制对象的商标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发生变化。技术领域中,何谓发明、实用新型、产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理论和实务界的理解也与往日不同,诸如计算机程序是否是发明、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是否是发明、生物工程技术是否是发明、图形用户界面是否属于产品外观设计,争论一直非常激烈。这些领域都需要行政根据效率性和自由的关系及时调整审查基准,采用统一且透明的程序对可以申请注册的商标范围和具体要件、可以申请专利的发明和产品设计以及可以申请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和植物新品种权的范围和具体要件进行适度变更,此种意思决定的方式,相比由司法在个案中进行具体判断,显然更加有利于实现效率性,并且兼顾他人的可预见性和行动自由。对于行政的这种裁量,司法应当给予足够尊重,而不能在全面司法审查中以违背法治主义为由随意加以推翻。
在专利权、商标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有关技术系列和标识系列的知识产权的要件和有效性方面,一直存在根深蒂固的“权利主义”主张,认为这些知识产权并非国家创设和授予,主管知识产权的专责机关的审查、核准和公示仅仅是对已经存在的自然权利意义上的“专利权、商标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权利的确认,有关这些權利的要件及其有效性的争议,仅是私人之间的纠纷,专责机关的自由裁量发挥不了作用,也不能发挥作用,有关这些事务的终局判断权力也应当按照传统法治主义的模型交给司法机关。[田村善之主编:《日本现代知识产权法理论》,李扬等译,第26页。]
然而,如上文所述,技术系列和标识系列的知识产权在产业政策上是以技术创新和普及利用以及产业发展为目的而由国家人为创设和授予的法定权利,而非自然权利。何种技术和标识应该被创设和授予权利、被创设出来的权利最终是否有效,由掌握纷繁复杂技术发展背景和脉络、拥有丰富数据库和强大检索手段的专责机关进行判断,客观而言,确实比司法更具有优势。以为技术调查官制度已经弥补知识产权法官技术知识不足的缺陷,司法已经完全具备判断各领域不同技术和标识是否应当授予权利的能力,进而认为应当将技术系列和标识系列知识产权授权要件和有效性判断的最终权力交由司法,从而加快审判效率、尽快确定权利的稳定性和交易秩序看上去虽然十分理想,但不得不说有些过于冒进和超前了。在法治主义模型下,专责机关对于这些技术系列和标识系列知识产权的授权要件和有效性的裁量受到立法意思决定的严格束缚虽属正常,但正如田村善之教授所言,“在法律的文句上存在解释空间时,基于与司法机关的关系而禁止行政机关进行任何裁量,这种想法却过头了。”[田村善之:《知的財産法政策学の試み》,第14页。]至少在计算机程序、生物工程技术、图形用户界面、人工智能等较为前沿的技术或者产品设计问题上,由专责机关根据实现效率性和确保自由的需要,在法律文句的限定范围内,发挥裁量空间,通过审查指南决定这些客体是否具有可专利性,是合适的。
事实上,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基准的调整[2010年和2014年的《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第2节第(1)项规定,“仅仅记录在载体上的计算机程序”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2017年2月28日发布、2017年4月1日施行的《专利审查指南》对此补充强调,“计算机程序本身”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除此之外,2017年《专利审查指南》删除了原第二部分第九章第3节第(3)项中的例9。在权利要求书的撰写上,2017年《专利审查指南》将原第二部分第九章第5.2节中的“即实现该方法的装置”修改为“例如实现该方法的装置”;将“并详细描述该计算机程序的各项功能是由哪些组成部分完成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功能”修改为“所述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包括硬件,还可以包括程序”;将“功能模块”修改为“程序模块”。]、对于图形用户界面由2006年版及2010年版的《专利审查指南》明确排除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到2014年修订版的《专利审查指南》将其纳入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的调整[2006年和2010年的《专利审查指南》规定,“产品通电后显示的图案”并非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的客体。但2014年3月12日公布、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版《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三章第4.3节第三段第(6)项之后新增第(7)项:“对于包括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必要时说明图形用户界面的用途、图形用户界面在产品中的区域、人机交互方式以及变化状态等。”不过这种修订是否受了司法的影响,也值得研究。在跨越2014年《专利审查指南》修订始末的苹果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权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中,苹果公司于2010年7月2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为“便携式显示设备(带图形用户界面)”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但2011年6月16日被审查部门驳回,理由是该申请视图表达的内容包含产品通电后显示的图案,属于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客体。2013年5月2日,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维持驳回裁定。2014年4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涉案申请虽包括了在产品通电状态下才能显示的图形用户界面,但其仍是对便携式显示设备在产品整体外观方面所进行的设计,也满足在工业应用和美感方面的要求,可以成为受外观设计保护的客体”为由,一审撤销复审委裁定。2014年12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每次都并不经过立法决定和司法审查。这种调整显然并不严格符合传统法治主义模型,但确实是符合产业政策发展变化作出的必要调整,司法和立法都应予以尊重。
话虽如此,由于部门立法体制[我国采取的是“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和第九十条以授权的方式确立了国务院及其部委具有行政立法权,能在其职权范围内有制定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条和八十一条则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部门规章的效力。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二条,省市级地方政府有权在其辖区内制定地方性政府规章。参见刘松山:《国家立法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李林:《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的理论与实践》,《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制[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我国采取的是“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并行的“双轨制”运作模式。国务院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唯一主体,有关行政部门具体履行保护职责,承担行政执法任务,执法形式多样,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多层级保护体系。但是,这种执法权分散的执法体制导致执法主体过多,没有形成行政保护合力,影响了执法效率。参见曲三强、张洪波:《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研究》,《政法论丛》2011年第3期。]等原因导致的利益部门化现象的存在,原本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行政部门,在执行立法决定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既妨碍效率性实现又过度限制他人行动自由的现象。比如,虽然由于技术适格性限制,专利权等技术系列的知识产权对世是否有效最好交由行政进行判断,但在法治主义模式下,行政判断需要接受司法的最终审查,而且由此引发的诉讼在我国属于行政诉讼,司法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拥有对具体行政行为实体上的变更权,由此导致的循环诉讼现象使得专利技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方面使权利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减少了对权利人进一步创新创造的激励,另一方面使对手方的行为长期得不到定性,因而在是否进一步进行市场扩张面前举棋不定、进退两难,这种体制既影响了效率又妨碍了他人的行动自由。又如,负有商标注册申请审查和核准职责的专责机关,或许出于全面提高全民商标意识等方面的需要,放宽了《商标法》第四条“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其商品或者服务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审查,导致了大量不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注册申请现象[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013年發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13年商标申请总量为1733316件,其中注册总量为909541件。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014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14年商标申请总量为2076469件,比2013年增加了19.8%,其中注册总量为1242840件,比2013年增加了36.6%。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015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15年商标申请总量为2658674件,比2014年增加了28%,其中注册总量为2077037件,比2014年增加了67.1%。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016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16年商标申请总量为3526827件,比2015年增加了32.7%,其中注册总量为2119032件,比2015年增加了2%。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017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17年商标申请总量为5538980件,比2016年增加了57.1%,其中注册总量为2656039件,比2016年增加了25.3%。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018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2018年商标申请总量为7127032件,比2017年增加了28.7%,其中注册总量为4796851件,比2017年增加了80.1%。],严重妨碍了他人选择和使用商标的行动自由,阻碍了产业发展,与商标法创设排他效力及于全国范围内的商标权的目的背道而驰。
针对行政上述不利于效率性和自由的种种意思决定,一方面,面对具有对世效果的专利和商标确权权力依旧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的状况,以及在一种创新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导致的不正常的大规模专利、商标注册申请及授权的现状,应当允许司法利用“行政行为无效法理”[“行政行为无效法理”是与“行政行为公定力原理”相对的一种法理。根据行政行为公定力原理,行政行为一旦作出,除了无效的情况外,行政行为即使违法,原则上应当被推定为合法,在有撤销权者撤销之前,任何人都必须服从该行为,不能否定其效力。参见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南博方:《行政法》第6版,杨建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0页;汪利红:《日本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436页。但根据行政行为无效法理,如果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那么该行政行为的效力从成立之时起便全然不发生。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98—200页;南博方:《行政法》第6版,杨建顺译,第53—54页。]在个案中发展出“权利当然无效抗辩的法理”,让侵权诉讼中的被告在个案中直接攻击专利权、商标权的有效性,从而避免被迫进入无效宣告程序导致的循环诉讼,实质加快案件审理效率[李扬:《日本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原则及其启示》,《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或者根据法律目的解释直接适用民事权利不得滥用的法理,在不触及技术系列知识产权对世效力的前提下,在民事侵权案件中驳回专利权、商标权空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拥有者即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从而确保专利、商标的申请与授权符合专利法、商标法立法者的意思决定。[李扬:《商标法基本原理》,第205—207页。]
另一方面,对于行政以职权主义为基础主动作为给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效率和成本方面的优势,建立于程序正义基础上在效率方面相比行政天生不具有优势的司法,应当充分体会我国当今采取的知识产权强保护国策[参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第十三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意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第二部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部分第三点。],坚持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所具有的排他性本质,并考虑我国侵权频发、反复和恶意侵权现象严重,因为财务制度不健全致权利人损失难以计算等国情,在经过听证后认定知识产权人具有胜诉可能性的情况下,及时采取知识产权行为保全措施,从而提高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效率。[李扬:《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产权行为保全规则》,《知识产权》2019年第5期。]知识产权行为保全的要件、审查期限、执行机制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司法面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最终由谁作出意思决定的理念问题。非常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2日发布、2019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利益平衡论为指导,严格设定了权利人申请行为保全的要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极大限缩了权利人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获得行为保全的可能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行为保全的条件是,“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并无其他特别要件。]显然,这种纯技术规则设计模糊了司法和行政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角色分工,并可能萎缩司法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意思决定功能,并不恰当。
以上是从解释论角度讨论在保护知识产权时,对行政关系的面向,司法应当具备的角色构造。就立法论而言,司法则应当坚守底线思维,上下齐心,尽力游说立法机关尽快将技术系列和标识系列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程序修改为准司法程序,视为行政或者民事一审,当事人不服的,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或者特别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庭起诉,并将确权程序作为当事人序列的民事案件处理,从而在程序上加快效率性,确保市场主体创新创造的激励机制不被扭曲。此外,行政执法中的行政罚款由于行政职权主义的原因,往往比侵权民事赔偿责任先行,在侵权行为人金钱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常常导致权利人丧失获得金钱赔偿的机会,并不利于创新创作的效率性,亦需要由立法重新进行意思决定。[李扬、施小雪:《知识产权金钱责任的冲突与协调》,《知识产权》2014年第2期。]
四、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对市场关系面向的角色构造
如上文所述,以激励理论为导向的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认为,在市场本身能够发挥创新创造激励功能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由立法作出创设排他性及于全国地域范围、严重妨碍他人行动自由的知识产权的意思决定。只有在市场失灵、搭便车现象过于严重、需要创设创新创造激励机制或者对市场本身拥有的激励机能进行增援的情况下,作为权威的立法、行政、司法才有介入的必要。这意味着,在市场本身发挥了激励功能的时候,司法也应当尊重市场对于效率性和自由的安排,并沿着这个方向解释法律和规则,尊重行业内通行的商业实践。
比如,互联网领域中掌握技术的经营者遭受其他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常常采取在互联网公共平台发布略带渲染性和夸张性甚至刻薄性的评论、帖子和文章以澄清相关事实,设置插标警告,屏蔽、删除在先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的产品或者服务,终止兼容合作等措施进行私力救济。互联网领域中
受害的经营者采取的此种私力救济行为,从奇虎诉百度不正当竞争行为案[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5724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中,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杀毒软件上线受到原告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的拦截、篡改,为了抵制奇虎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在其主办的“百度安全论坛” 上开展了名为“举报360恶意行为”在线活动;另外百度杀毒微博发布了名为“不骚扰、不胁迫、不窃取”的讨论话题,其中包括图文“成功的人做产品,失败的人耍流氓……比忽悠,我不行”,还将百度杀毒与360产品进行比对:百度杀毒“不骚扰、不胁迫、不窃取”,360产品则是“弹窗、恐吓、骚扰、篡改、偷窥”。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诋毁其公司商誉和产品声誉,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告的请求得到法院支持。]、金山诉合一不正当竞争行为案[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17359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原告金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金山公司”)开发经营的猎豹浏览器通过屏蔽广告技术屏蔽了被告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合一公司”)经营的优酷网的广告。因此合一公司拒绝向猎豹浏览器用户提供优酷网视频播放。另外,猎豹浏览器的用户如自行安装了广告屏蔽插件,将无法观看优酷网视频。但其他浏览器用户如果安装相同插件,在关闭屏蔽广告功能后还是能正常观看优酷网视频。据此,金山公司认为合一公司有歧视性对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合一公司辩称,金山公司多次利用猎豹浏览器,使用非法手段对优酷网站内容及网络服务器进行恶意篡改,过滤了优酷网的广告。而且,合一公司为了防御攻击,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回避并发出过警告函,金山公司仍变换手法进行升级对抗。因此,优酷网针对金山公司在先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采取了必要的技术救济手段。被告的行为被法院认定为歧视性对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360诉雅虎不正当竞争行为案[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字第46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民终字第13142号《民事判决书》。2007年,北京三际无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反诉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称其推出的“雅虎助手”软件对360软件进行了干扰和攻击。比如在用户安装360软件时,雅虎软件主动弹出诋毁360软件对话框、诱导用户删除该软件、删除用户本地电脑中的360软件、屏蔽360软件的正常运行等。原告据此认为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在本案中,阿里巴巴公司答辩称,三际无限公司经营的360软件将雅虎软件认定为恶意软件,并诱导用户删除,导致雅虎软件与360软件之间存在冲突,侵权故意十分明显。该案中被告的行为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决结果看,均被法院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这种认定可以说是并不尊重市场安排的结果。互联网领域中的竞争具有效率高、受众广、技术硬、淘汰快、影响深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互联网领域中的经营者不得不依靠自身的技术能力对其他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快速做出反应和处理,以最大限度降低遭受的损害,恢复公平的市场竞争。如受害经营者只能通过冗长的诉讼解决问题,等待受害经营者的只能是一份胜诉判决和一个早已失去的市场。对此,针对互联网领域中具有威胁性和紧迫性的在先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私力救济具有及时性、防御性和保守性等限制性条件下,承认受害经营者私力救济抗辩的权利,完全是尊重市场安排这种自发秩序的结果,具有合理性。[李扬、张旗:《私力救济抗辩初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又比如,对通讯领域在全球有着最广泛影响的标准化组织——欧洲电信标准化组织(ETSI)[该标准化组织1988年成立于法国南部尼斯。该组织否定了其1993年版本的知识产权政策,从而诞生了1994年11月版本的知识产权政策,该版本的重要内容至今有效。]知识产权政策的解读,尤其是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承诺含义的解读,司法除了应当结合其制定历史[比如,1994年版本的ETSI知识产权政策删除了1993年版知识产权政策中对许可人的如下限制:意图获得金钱对价许可;始终适用于所许可的知识产权整个生命周期的许可;最惠被许可人条款;对标准应用区域的限制;要求许可具有允许被许可人遵守标准的技术范围;许可人仅在发生违反许可协议的情况下终止许可;被许可人可随时终止许可;在无相关知识产权的国家里对活动的限制;关于版权、掩模作品和未注册设计的附加规定;许可的追溯效力;关于拒绝许可的详细规定,该种拒绝可在180天内作出;详细的互惠规定;详细的披露规定,包括禁止知识产权人在向ETSI提供知识产权通知之前就侵权行为寻求禁令救济;与采购合同有关的许可条件限制;关于谈判期间侵权行为的法律诉讼限制;禁令限制;关于合資企业、收购和剥离附属公司的限制;强制性仲裁。再比如按照ETSI知识产权政策4.1规定,成员虽应尽合理努力披露“可能必要的”知识产权,但完整或者接近完整的披露SEP并非标准制定前提。原因在于提交专利申请后一般18个月内专利局才会公开,披露人无法确定是否已经披露了所有的SEP,且申请可能发生变化,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亦可能发生变化。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消除,因此几乎不可能将ETSI成员的知识产权声明认定为“过度声明”并认为违反FRAND。]及现存一直适用的文本进行解释外,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在尊重长期行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解读。基于经济和商业上的理由,电信行业中就专利许可进行谈判的通行做法是,就专利组合的价值和重要性进行谈判而非就单个专利的价值和重要性进行谈判。在涉及大型专利组合许可协议的善意谈判中,当事人双方通常不会解决协议所覆盖的每项专利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是否侵权的问题。尽管如此,双方仍将协商出令双方满意的商业条款,即使双方对实施者实际使用的专利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有效的、哪些侵权,可能仍然存在分歧。基于上述原因,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达成的许可协议中包含标准必要专利和非标准必要专利通常也是合理的,并不违反FRAND承诺。相反,专利实施者坚持要求对拥有巨大专利组合的专利权人的每个专利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是否侵权进行谈判,违反了与专利权人进行善意谈判的义务。[Marvin Blecker, Tom Sanchez and Eric Stasik,“An Experience-Based Look at the Licensing Practices That Drive the Cellular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Whole Portfolio/Whole Device Licensing,”Les Nouvelles Journal of the Licensing Executives Society,vol.51, no.4, 2016, pp.221-233.]
在设备层级上进行许可和以整机净售价作为许可的计费单位,而不是以最小可销售的专利实施单元(SSPPU)作为许可计费单位,是否违反FRAND,司法同样应当尊重通信领域长期通行的许可实践。[ETSI 知识产权政策第6.1条-按FRAND条款授予许可的表述着重于制造“设备(EQUIPMENT)”而非部件(“components”),并且 ETSI 将“制造(MANUFACTURE)”定义为“设备生产(production of EQUIPMENT)”,将“设备”定义为“完全符合标准的任何系统或设备”。另外1994年版 ETSI 知识产权政策的某一版草案中将“GOODS”定义为“EQUIPMENT, parts thereof and METHODS”,这表明“EQUIPEMNT”本身不包含“parts thereof”。在制定、辩论、起草和通过ETSI知识产权政策时,起草者充分意识到完全符合标准的终端用户设备和该等终端用户设备的部件之间的差异,这使得在政策中选择使用的语言特别具有启示性。在设备定义中,通过使用术语“系统”“设备”和“完全符合”——意味着成品而不是单个部件,并通过将制造定义为此类设备的生产,起草者表示,根据当时的行业惯例,FRAND承诺扩展到终端用户设备,而不是该等终端设备的部件。]从历史形成看,这种许可和计费方式开始于1991年摩托罗拉和爱立信之间的授权许可,形成于1994年ETSI知识产权政策生效文本出台之前。摩托罗拉向手机制造商提供完整组合许可的做法被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高通和其他主要许可方效仿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事实上,阿尔卡特朗讯、爱立信、华为、摩托罗拉、北电网络、诺基亚、诺基亚西门子通信、高通和中兴通讯均已经公开宣布各自针对手机设备的如下专利使用费:
北电网络表示,“具有竞争力的手机设备专利费百分比约为1%。”
阿尔卡特朗讯表示,“我们将以不超过2%的折扣率授予LTE标准必要专利的使用权。”
爱立信表示,“我们针对手机设备的LTE专利使用费率将在1.5%。”
华为表示,“专利使用费率存在一定的变动性,但针对终端用户产品不会超过1.5%。”
摩托罗拉表示,“预计LTE系统和设备的必要专利使用费率约为2.25%。”
诺基亚表示,“使用LTE作为唯一一种无线通信标准的设备的专利使用费将在终端用户设备销售价格1.5%的范围内。”
高通表示,“预计将根据LTE标准必要专利组合对许可授权批发销售价格约3.25%的专利费。”
诺基亚西门子通信表示,“终端设备的LTE专利使用费将在其销售价格0.8%的范围内。”
中兴通讯表示,“将对移动通信终端许可LTE必要专利收取不超过终端设备销售价格1%的专利费。”[Eric Stasik, “Royalty Rates and Licensing Strategies For Essential Patents On LTE(4G)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s,”Les Nouvelles, vol.3, January 2010.]
美國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全称是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于2005年修改其知识产权政策以SSPPU为计费单位时,ETSI曾对此进行过充分讨论并最终不采纳类似要求,而是继续维持ETSI现有知识产权政策,也表明各方在完整、可操作的终端用户设备级别上获得许可,符合长期的行业实践,而且该等实践促进了移动通信行业的空前增长。其他标准化组织同样拒绝追随IEEE的做法。[M Lindsay and K Karachalios, “Updating a Patent Policy: The IEEE Experience,”Antitrust Chronicle, 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vol.3, no.2, 2015, pp.1-6.]
通信行业中在设备层级上进行专利许可并且以整机作为计费单位的上述做法表明,这种做法并不违反FRAND,更不构成违反反垄断法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司法对于长期存在于通信行业中的此种有利于效率和自由的安排应该予以充分尊重,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认定这种许可实践违反FRAND。
同样,司法尊重市场对于效率和自由的安排,并不是说司法在市场面前就只能俯首帖耳。即使立法完全履行政治职责,制定出了产权安排明确的知识产权法规则,弥补了市场激励功能的不足,乃至主动创设出了有利于效率性的激励机制,也并不意味着市场会自动沿着立法者预设的有利于效率和自由的轨道上行进。在市场没有发挥或者没有充分发挥调节效率和自由之间矛盾的功能时,司法应当凭借终局、稳定、公正的判决,正确引导知识产权市场,恢复市场在知识产权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司法而言,停止侵害、损害赔偿不应当仅仅成为行为人侵权后承担的民事责任,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应当仅仅成为原被告双方攻击和防御的简单工具,而应当充分发挥这三个工具在修复已经被扭曲的知识产权市场功能方面的作用。比如,面对立案登记制改革、批量诉讼带来的当事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协商谈判,即市场尚未失灵尚未发挥任何激励作用所带来的法院不堪案件重负的现状,以及新出现的商业模式和知识产权人之间的博弈时,法院就可以灵活运用停止侵害[李扬、许清:《知识产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法学家》2012年第6期。]、赔偿损失、举证责任分配[李扬:《日本解决IP侵权诉讼中权利人举证难的组合拳制度》,《电子知识产权》2017年第8期。]三种工具,从而促使当事人尽可能协商解决纠纷,恢复市场本身在激励创新创造、确保自由方面的作用。
举例而言,对于连续未使用不满三年的注册商标,权利人针对对方当事人行使商标权时,考虑到商标法创设商标权的目的,法院就可以只判对方当事人给予权利人一点权利金而不判决对方当事人停止侵害。面对各种大规模商业维权现象,法院则可以更加严格要求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其遭受的损害,在权利人不能举出清晰、完整、真实的证据链证明其权利人身份,或者权利因受侵害确实存在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则可判决驳回权利人起诉,或者判决零损害赔偿,或者至多判决被告给予权利人一点象征性的权利金,从而将此种过度限制他人行动自由但对真正的创新创造活动并未发挥多少激励作用的商业模式限缩在最小规模范围内,直至扼杀在摇篮中。
综上,司法面对市场,既要给予市场足够的尊重,发挥市场在创新创造激励和确保自由方面自发做出的符合商业和经济伦理的安排,又要善用立法决定中已经给出的司法工具,尽可能消除市场失灵对效率和自由造成的负面影响,引导市场真正朝着有利于效率性和自由的方向发展。
结语
本文在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选取知识产权制度和运行中的不同侧面,结合某些典型案例和事例,从司法对立法关系的面向、司法对行政关系的面向、司法对市场关系的面向,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创设和运行中司法的角色构造问题。通过这种探索可以发现,司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于在个案中改善作为和技术、经济、民生、国际关系等紧密关联的知识产权正当化根据的效率性和一般公众行动自由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的适用发现并修正或者完善立法、行政或者市场中不利于实现效率性或者过度妨碍公众行动自由的意思决定、做法或者因素,促进创新创造,以此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非常具有必要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传统法治主义的观念需要进行认真反思。
发现并在个案中修正或者完善立法、行政或者市场中不利于效率性和自由的意思决定、做法或者因素,有赖于具有占位高、理念先进、法理深厚、知识产权法知识扎实、司法艺术高超的知识产权精英法官队伍。当下,我国知识产权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虽然已经非常高,但与能够在个案中准确领会立法意思决定、发现行政决定和市场决定的优劣势、把握效率与自由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裁判的客观需要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精英化稍显不足。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司法与立法、行政、市场之间错综复杂复杂关系,尽快培养一大批知识产权精英法官,可能是司法内部最高决策者今后一段时间需要面对的重要任务之一。
(责任编辑:周中举)
sdjzdx20220323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