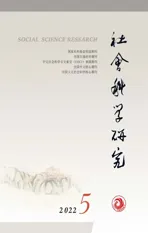再论治理的历史起源
——兼论中国政治科学应该回到哪里的历史
2022-03-18胡键
胡 键
关于治理的历史渊源,本人曾在《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一文中,对治理的一般性概念及其内容进行了探讨。(1)胡键:《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吉首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此文的目的在于表明,治理并非西方舶来之品,作为一种权力互动关系,中国历史传统中早已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关系,不是权力的单向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制度之下,权力互动关系的工具、形式会大相径庭。笔者在这里再来讨论治理的历史渊源,将围绕政府治理(国家治理)来讨论“治理”问题,本文将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治理并非现代政治语境下的范畴和实践,甚至它比“统治”这一概念出现得更早。如果从权力关系的内容和客观实际来看,“统治”作为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垂直规训关系,只有进入帝国时期才会产生“统治”这种规训关系,部落社会和王朝时代的权力关系主要还是一种互动关系,因而是一种扁平治理的权力关系,尽管权力客观上存在等级关系,但二者并不矛盾。
一、从“政治科学回到历史”谈起
近年来,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政治学(其实是指广义上的政治科学)要回到历史,并提出了“历史政治学”这个概念。(2)主要是杨光斌教授及其团队。近年来,杨教授团队以及他主编的《中国政治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历史政治学”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高度关注。那么,究竟是要回到哪个时期的历史?众所周知,政治科学是对现实政治进行阐释的学说。历史政治学究竟是用政治学说来阐释历史,还是用历史来解释政治?若是用政治学说来阐释历史,由于政治学是为阐释现实政治服务的,那么历史就很有可能被现实政治符号化,这样的历史就会成为被政治符号化的历史、“政治化了”的历史,也就是政治建构起来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政治的确在建构历史,但政治大多数是以其客观的政治进程来建构历史的,只有少数情况下是政治家或学者主动以政治权力来建构历史。因此,用政治学说来阐释历史,很有可能使历史缺乏真实性。如果用历史来解释现实政治,这就意味着政治被历史所束缚,不符合历史的政治现象就会被视为历史的“噪音”而无法“入史”,从而导致政治陷入历史机械主义的陷阱之中。
“政治科学回到历史”与“历史政治学”实际上是两回事。笔者非常赞同前者而不苟同于后者,这是因为一切科学知识都有历史渊源,政治科学的知识同样是从历史深处成长起来的。回到历史,就是梳理知识的来龙去脉,以便更好地为构建当代政治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服务。这就是平常所言,必须从历史传统挖掘相关智慧,从历史之中寻找学术的根源。当然,“回到历史”首先要确立历史的方位问题,或者说是回到某一段历史,还是回到我们已经有把握的历史?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涉及中国政治科学知识的起点。
一种观点是政治科学当追溯民国的历史。这非常必要,但这不是中国政治科学知识的起点。民国时期是中国政治学科的起点,但不是中国政治科学知识的起点。在民国时期,西方政治学科传到了中国,经过了包括严复、梁启超、钱穆等学者的构塑,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政治学科。严复撰写了中国第一本政治科学著作《政治讲义》,在这部著作中,他剖析了两种政体,即“一为无舆论机关之专制,一为有舆论机关之立宪”,而他更强调“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为变”,因此萧公权借此认为,严复的这种思想与康有为的虚君立宪之说如出一辙,实际上也是为清末立宪摇旗。(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19—820页。不管怎样,严复的《政治讲义》开启了中国政治科学规范性研究之先河。严复(实际上也包括谭嗣同)对梁启超的影响非常大,直到1895年,梁启超被康有为的思想支配着,但从1896年开始,梁启超受严复从西方介绍到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重要影响。(4)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7页。而梁启超正是在这一年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组文章(5)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106页。,围绕专制政治、国体政体、国会内阁、法理学发展史、中国历史研究法、政治思想史形成的论理撰述,而跻身于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列。(6)任峰:《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期。也正是在这一年,梁启超读到了严复翻译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当然此前的1895年,梁启超还读过严复关于改良主义的文章而逐渐成为严复思想上的重要追随者。此外,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还提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事实上他众多关于变法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文章,都是受李提摩太影响而成文的。这些情况表明,梁启超是借助于西方的政治学说尝试改造晚清中国,同时也在尝试以西方的政治学科来构建中国的政治科学知识体系。不过,梁启超的学说涉及的是制度建设,没有涉及政府治理的问题。梁启超之后在中国政治科学上有重要建树的当是钱穆,但在钱穆之前有一人很少被提及但他的一本著作却对中国政治科学的构建有重要影响,这就是从事经济科学研究的王亚南。他于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是研究中国官僚制度的政治学著作,该书“以历史叙述与逻辑推演相结合之手法,检讨中国官僚政治之一般与特殊,探索其演变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之联系……实为不可多得之划时期代表作”。(7)孙越生:《重读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王亚南虽然被称为经济学家,但此书却是一本对官僚制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政治学著作。在此书中,王亚南对钱穆关于中国历史上“政治不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8)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8—39页。而中国历史上“政治不专制”之说,正是奠定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对中国政治科学重要贡献的观点。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以史学不自觉地进入政治科学,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式民主”思想。(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37—38、43、79页。不过,对中国政治学科进行系统性梳理的民国时期政治学学者当属萧公权。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所选取的政治文献研究资料,上自晚周,下迄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做了极为系统的叙述和分析。(10)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页。民国时期的这些学者,在关于中国政治学科构建上,都是受“西学”影响后才开始探索。像严复留学英国,萧公权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长期在美国教学和研究,王亚南留学日本并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学说,梁启超虽然没有留学,但在严复的影响下接受进化史观,钱穆也没有西学背景,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借用了“西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政治现象。
另一种观点认为回到“大一统”的历史,并以此为起点来追溯中国政治发展史。诚然,“大一统”政治对中国政治学科的构建有重大影响,但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把“大一统”理解为“大统一”,因而就必然把“大一统”与秦国统一中国和推进新郡县制联系在一起。于是,所谓“政治科学回到历史”,大多数学者也主要是追溯秦统一中国的历史。因此,有学者把“大一统”体制、郡县制、科举考试等都囊括在“中华文明基体”之中,认为这些是构成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关键要素。(11)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基体”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提出来的概念,他所说的“中国基体”,就是指“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这体现于长期持续的种种现象在不同时代里的缓慢变化上”。(12)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1页。有学者借此认为,“郡县制是中国所独有的,具有‘超级现代性’。这一事实要求政治学重新思考何为优良甚至终极政制。”(13)姚中秋:《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这句话尤其是关于“超级现代性”之说,让读者感到其目的不是“何为”,而是明明确确地表明要关注“何为优良甚至终极政体”了。而事实上,“大一统”最初并非一种统治制度,而是一种权力合法性来源。《春秋公羊传》记载:“(隐公)‘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4)《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1,何休解诂,徐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12页。由此可见,明确把“大一统”当做诸侯国君获取“正统性”的思想与实践基础。(15)杨念群:《“大一统”与“中国”“天下”观比较论纲》,《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当然,郡、县的设置较早,在《逸周书汇校集注·作雒》中有记载:“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口鄙”。(1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作雒》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0页。但是,郡县制度则的确是秦统一后而建立起来的,是“大一统”的新内容。也就是说,“大一统”在先秦时期和秦统一后的内容是不同的。有学者把“先秦、秦汉至清、现代共和”看作是“大一统”的三大历史阶段。(17)任峰:《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人文杂志》2021年第8期。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自秦汉至清是否都是“大一统”是有待商榷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不仅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体系构成有重大变化,这一点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有阐述,特别是宰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其间还有相当长的历史是分裂的,作为君权支撑的思想意识形态也有重大变化,自黄老而至法家、儒家思想,后来又受来自周边民族即异域思想的冲击,佛家、道家思想也曾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排挤作用,最后经过中唐的安史之乱以后,儒家思想被士大夫重新塑造成为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支撑。这个过程实际上充满了血雨腥风。因此,简单地概括为“大一统”的三个历史阶段,这显然是把纷繁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科学若仅仅是回到自秦国统一后的历史,这依然是“断代”历史,不是已经形成共识的全部中国历史。
那么,已经形成共识的全部中国历史是什么?这无疑就是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如果把“大一统”理解为“大统一”,其历史也不过两千多年,另外还有两千多年则是分封意义上的、作为一种部落首领和国君“合法性”思想与实践基础的“大一统”,而恰恰这种意义上的“大一统”往往被以阐释郡县制“大一统”的研究所忽视。所谓分封之说,在殷商之前的确没有文字可考的史料,但依据后人的追溯性记载,“分封”在尧舜禹时期就已经成为当时的制度,并通过帝与诸侯之间的互动而构成当时华夏民族的政治运作机制。例如,《尚书·尧典》就记载了尧与四岳关于治理洪水的“协商”:“帝曰:‘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又能俾乂?’”而“四岳”就是“分掌四岳之诸侯”。(18)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尧典》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页。如果以此为据来推算“分封”的历史,也就是部落联盟的“分封”,这历史就更加久远和漫长了,“分封”的历史就不止两千多年。殷商实际上也是部落联盟的“分封”,中心为殷商部落,而其他部落则为方国。《史记·夏本纪》记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19)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8页。而司马迁在该部分做评论的时候也有一段关于夏朝“分封”的话:“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20)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卷2,第109页。而《尚书·禹贡》中明确了分封制度,“锡土姓”即“天子以地名赐之姓,以尊显之”,也可以理解为“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21)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禹贡》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尚书·禹贡》卷2,曾运乾注、黄曙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0页。《史记·殷本纪》也有这样的记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22)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卷3,第125页。以上材料说明两点:其一是商汤时确实获分封诸侯。这里所说的“诸侯”实际上都是指部落联盟中除中心部落之外的各部落。而商族的“皇亲贵族”实际上也都是有封国的,如微子、箕子等。(23)刘宝楠:《论语正义·微子》卷21,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11页。当然直到周灭殷商以后而所采取的政治运作使得分封正式成为一种政治权力制度。其二是分封的历史要远比郡县的历史长得多,即便是后来以郡县制为主的“大一统”时期,分封制也依然或多或少地保留在华夏帝国的政治框架之内。因此,当今中国政治学科回到历史就应当回到尧舜禹夏商周时期的历史。既然如此,下面我们来讨论古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问题。
二、古代中国政府治理的起源
此处论及的“国家”,不是现代政治语境下的现代国家,而是广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也包括部落联盟。因而,本文所用的国家治理也是广义上的国家治理,即在某种“政治共同体”名义下的权力互动关系,都可以视为国家治理的形式。当然,毋庸置疑,现代政治语境下的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诞生以后的现代政治行为。这里是以互动的权力关系来确定治理的内容,又是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因而这种行为就具有国家治理的意蕴。
国家治理首先是政府治理,也就是治国理政。上古时期,有两本书直接论及治国理政的内容,但基于现代政治治理逻辑的研究,一般都不注意这两本书的价值。一本书是《周易》,另一本书是《尚书》。《周易》中不同的卦所指的对象不同,内容也不一样,尤其是需要借助于卦象、爻辞、爻数来理解,其思想也是碎片化的,难以形成一致的逻辑。《尚书》里的文章涉及治国理政的内容具有整体性,也容易形成整体性的思想。下面试做具体分析:
关于《周易》与治国理政相关的内容,有学者专门对《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了分类,其中论述治国执政的有23卦,即巡(坤)、比、泰、否、同人、大有、谦、豫、临、噬嗑、剥、大畜、睽、解、萃、井、革、鼎、豊、涣、节、中孚、小过。(24)曹音:《周易释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导言”,第17页。这里不妨对这23卦的其中数卦作为典型例子以简单分析:例如巡(坤)卦,实际上就是巡视诸侯之意,但武王灭商,获得西南各部族如庸、蜀、羌、髳、微、纑、彭、濮等方国的支持,而东北各部族还对周怀有敌意或者还忠于殷商。(25)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卷4,第158页。因而,巡卦中的爻辞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也就是周天子要安抚西南各方国和防范东北各部族,这才是有利于周朝的国策。(26)曹音:《周易释疑》,第4页。又如比卦,本意是与人亲近和睦,派使者亲善边远方国,国家就不会有灾难,而与恶人亲近就有凶险。比卦实际上就是提醒在处理诸侯方国的关系时要慎重交朋友,特别是不要与恶人交朋友。这跟泰卦乃异曲同工。再如豫卦爻辞指出,适当逸乐有利于国家大事,而过度逸乐就必然有凶险。所以,豫卦提醒治理者不能荒淫奢靡,酒池肉林必然人亡政息。同人卦就更强调普天之下当和睦相处,若能“同人于野”,则可“利涉大川,利君子贞”。通俗而言,若能够与山野匹夫做朋友,那么任何困难都可以解决。同人卦的思想与《礼记》中的“大同”思想颇为接近。这些思想都是关于治国理政的思想。
《尚书》与治国理政的相关内容更具有系统性。其中今文《尚书》中的《皋陶谟》《禹贡》《洪范》和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最具有代表性。不管这些文章作于何时,但都反映了上古时期“治国理政”的思想内容。
《皋陶谟》的思想内容大致表现为六个方面,即继承治国的政治传统、修身、知人、安民、节制私欲、维护伦常关系和等级制度。所谓政治传统,就是指尧帝所倡导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27)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尧典》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页。这种境界是作为一种理想政治秩序来追求的。由于没有实际的文献,我们只能在《尧典》中追溯到这种理想政治秩序的蛛丝马迹。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理想政治秩序?《皋陶谟》中指出:关键在于“知人,安民”。“知人”才能“官人”即用人得当;“安民”则在于惠民。(28)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皋陶谟》卷4,第145页。为此,作为国家治理者而言,要达到这个目标,自己必须要修身,即“慎厥身,修思永”,也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有“九德”(29)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皋陶谟》卷4,第147页。,即宽宏大量同时严肃恭谨;性情温和且能坚定自信;小心谨慎却能有坚守;善于听取意见但又果断刚毅;性情直爽但态度温和;性格豪迈却又清正廉洁;刚正而不鲁莽;强勇而守道义。除此“九德”之外,理想政治秩序需要“天序有礼”,也就是要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社会伦次,以及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政治等级。另外,《皋陶谟》中已经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30)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皋陶谟》卷4,第153页。,意思就是说,上天听取民众的意见并据此来表彰与惩罚,从而实行上天与下民的相互通达,由此才能够恭敬地处理政府和保护自己的国土。这种民本思想也体现在《大禹谟》之中。
关于《大禹谟》的思想内容,最重要的也是通过“养民”而达到“善政”,即“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31)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大禹谟》卷3,第123页。通俗地说,就是君知为君之难,臣知为臣之艰,则都能谨慎恪勤,各司其职。由此,政务就能够实现有效治理。“乂”就是治理的意思。而这种“善政”也需要广泛听取民众意见,政策不能有偏私之处。即所谓“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3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大禹谟》卷3,第123页。而“善政”就在于“养民”,而“养民”则需“正德、利用、厚生”(33)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大禹谟》卷3,第126页。,即端正的品性、发展生产和贸易、确保民众丰厚的生活资料。对上古先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生活资料,所以“乂”才有治理的意思。“乂”是一个表示动作的象形字,也就是收割的动作。有收割即有收获,有收获就意味着民众获得了生活资料,因此社会才能得到有效治理。(34)胡键:《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养民”还应该用宽大的法度来治理百姓,“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并且“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35)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大禹谟》卷4,第130页。这里特别强调在国家治理中要奖惩有度,执法错误要承担相关责任。这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的政治逻辑,同时也明确了制度的重要性。不过,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则详细地体现在《禹贡》之中。
总体而言,《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不过在文中也确立了相关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土地分封和赐姓制度,前文已有论及,不必赘述;领地和赋税制度,如“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36)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禹贡》卷6,第240—242页。;以及劳役制度、戍守制度、教化制度等。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依据,上古时期中国就已经有如此成熟的政治制度,仅此而言就显示出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确是早熟的文化。(3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实际上,梁漱溟只是论及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观念、价值,以及从制度上追溯到上古时期。若论及上古时期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中国文化就更显早熟。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洪范》之中。
《洪范》是关于古代治国理政最系统的著作。其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君权的来源。根据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内容,不仅人是上天创造的,即“惟天阴骘下民”,而且君权也来自上天,即“君权神授”。(38)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禹贡》卷6,第446—448页。这种思想在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的,均宣扬神权政治。二是天地伦次是社会秩序之源。不尊重自然的秩序就不会有人间的社会秩序,自然的秩序是上天按照五行的规律创造的,水、火、木、金、土“五行”,不仅“构造”了人间生活资料来源的载体,而且还指涉人们日常的“五事”,并划定了人们的貌当恭敬、言当顺从、视当明了、听当聪敏、思当通达。天地伦常除“五行”外还有“五纪”,即岁、月、日、星辰、历法,在遵从“五行”与“五纪”的前提下来安排人间世界的“八政”,即食、货、祭、司空、司寇、宾、师。这样就不至于使上天震怒,“不畀洪范九畴”,而至“彝伦攸斁”。三是以政治伦理来构建“五福”的理想政治秩序。其中包括:其一,以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聚敛“五福”;其二,臣民不结党营私,以最高政治原则为唯一准则;其三,臣民必须为天子虑,不得违逆天子之意;其四,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也不要对达官显贵有所偏私;其五,要知人善任,从而使臣民能归顺最高政治准则,天子则要像做臣民的父母一样为君主。四是构建神权政治的合法性。解决政治之惑在于卜筮,卜筮则通过相应的征兆来揭示吉祥祸福和阴晴圆缺,据此以彰显政治秩序的状态和未来趋势。(39)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洪范》卷11,第445—483页。因此,《洪范》是最全面、最系统、最珍贵的古代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和具体政策。
综合上述四篇文献,我们基本上可以梳理上古时代关于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一是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政治理想:“善政”。这是人类作为理性的政治动物必然要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但不同的民族在远古时代所追求“善政”的形式和内容是大相径庭的。不过有一点都相同,即远古时代人类政治生活都是神权政治生活,并以神权政治来构筑权力秩序。所以,卜筮在远古时代无论是在中国、印度、两河流域,还是古代希腊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古代人类社会政治治理的重要手段。二是要选贤任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才能实现当时社会的有效治理。三是要取中和之道,不可有偏私,中和之道,是上古时期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四是要慎位、敬民。慎位就是对权力要有敬畏感,当然这主要是针对为君王服务的官员;敬民就是对臣民当子民,为养民、保民、乂民,以从“好生之德”。这些都体现了朴素的民本主义政治逻辑和政策取向。但是,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秩序,只能说在当时的政治认知和客观条件下,这些政治思想的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政治合理性。鉴于此,中国政治科学回到历史,那就不应该只是回到秦国统一中国后的“大一统”的历史,而应该回到古代中国政治治理起源的历史,笔者甚至认为,这个历史所体现的“大一统”才是更具有当代意义的“大一统”。
三、“大一统”治理的变迁逻辑
有学者认为,从分封制的“大一统”走向郡县制的“大一统”即“大统一”,这是历史必然,代表了文明的演进,且使“统一的性质和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强化”。(40)任峰:《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这果真如此吗?从“大一统”演进的客观历史事实来看,“大一统”可能并非代表了文明的演进,而纯粹是为了统治者更方便对权力的运用而已。
第一,“大一统”究竟是何时出现的。有学者认为,孔子言及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时,“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41)刘宝楠:《论语正义·季氏》卷16,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1页。这种判断已经初步蕴含了“大一统”思想。(42)杨念群:《“大一统”与“中国”“天下”观比较论纲》。若“大一统”是这样一种思想,则主要是用于统合当时华夏各部落、各部族、各聚族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可能比这还要早。《尚书》中既有“大一统”的实践,也有“大一统”的思想。前者如《尧典》记载尧帝问“四岳”(即四方诸侯)谁能治理这滔滔洪水;后者如《尧典》中也有“协和万邦”的理想。(43)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尧典》卷2,第52、37页。《益稷》中也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为帝臣”之说(44)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益稷》卷5,第174页。,这也体现了“大一统”的思想。也就是说,“大一统”并非秦国统一中国以后才出现的思想和政治实践,早在尧舜禹时期“大一统”就有雏形,到春秋时期,这种思想随着“天下观”而得到发展和推进。因此,“政治科学回到历史”不能仅仅是回到秦朝建立郡县制的“大一统”历史,而应该回到更遥远的“大一统”发轫的历史。这样才能真正以历史主义的逻辑来剖析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仅仅从郡县制的历史来理解“大一统”思想和政治实践,显然是不全面的,也割断了中国悠久的政治发展史。
第二,从秦国血统的因素来看,秦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制具有必然性。周朝的分封制主要以血缘为纽带来进行政治分封,而且周朝尤其强调嫡长子继位制。这也是为了避免出现类似殷商诸子争权的现象,当然,周王还分封了舜帝的后裔于陈、殷商的微子于宋等。然而,嬴政在政治权力博弈中几乎剥夺了自己所有兄弟的生命,自己的亲兄弟嬴成蟜在公元前239年攻打赵国失败而投降赵国,最后面壁自杀。(45)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第291页。另外,公元前238年即秦始皇九年,太后与嫪毐所生的两个王子也因嫪毐之乱而被诛杀。(46)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卷25,第3049页。所以,嬴政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没有任何血缘兄弟,因而按照血缘分封的家族条件已经不存在。这就正如晋国在骊姬之乱后,不允许收留诸公子,“自是晋无公族”(晋国因诸公子都不在国内而废除了公族这一官职)。(47)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宣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725—726页。从这一点来看,秦始皇抛弃分封制也是一种无奈选择。当然,仅仅从血缘因素来考察还不充分,除血缘因素外,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是最重要的前提。
第三,从分封制的教训来看,分封制会导致权力离散的问题,以致天子大权旁落。在秦初定天下以后,朝廷上就有数次讨论。例如,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就说:“……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所以“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为一统……”。廷尉李斯进一步指出:“周文武所封子弟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48)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第304、307页。客观而言,秦国对周朝分封制教训的总结的确是到位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分封制引发的权力离散现象,唯一的方法的确只有推行郡县制为妥。然而,一个王朝仅仅从前朝的历史来总结教训,这种教训往往可能只是一种政治审美,而不是历史逻辑。因为,推翻前朝之后,政治审美的目的就必须把前朝的一切加以否定,即便前朝的诸多政治实践乃至政制设置有其合理之处,出于政治正确的逻辑,否定它就是必然的选择。这无论在哪个民族都被视为理所当然。除非前朝的政制设置完全有利于自己,此时这种政制设置就会以各种理由被强化。分封制是否如王绾、冯劫、李斯等所认为的一无是处?他们所总结的主要还只是面上的问题,对分封制本身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周文王、武王将始于尧舜禹时期、成熟于商朝的分封制进一步完善,并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权力制度,这绝非一种政治实践上的偶然,而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变迁而完善起来的。如果这种制度天然地导致权力离散、政令不通,以周王朝的开国先君的智慧绝对不会选择分封制来构建“天下”秩序。事实上,分封制在当时条件下是“天下”秩序和“大一统”思想的最佳选择。地域广阔却交通不便,天子的政令不可能及时传到四海九州,如何能够维护“大一统”?只有分封制可以使周天子为“天下”之君,也能够避免本不可能以统一的政令来维持“天下”秩序的麻烦,只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尊周天子之尊严即可。因而,分封制与“正统论”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缺一不可。只有分封而没有“正统论”,则周天子的权力必然离散,失去驾驭诸侯的权力。可见,在分封制下“正统论”是权力合法性之源。例如,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州吁与石厚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但无法稳定国家,石厚问其父石碏如何办,石碏说:“王觐为可。”(4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隐公》,第40页。即若能见到周天子并得到认可,就能取得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正统论”。又如,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主地位也是通过“正统论”“尊王攘夷”确立起来的。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的葵丘会盟确立的五条盟约:“诛不孝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尊贤育才,以彰有德”“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无曲防,无恶籴,无有封而不告”。(50)焦循:《孟子正义》卷24,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43页。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楚国大败后,晋文公“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结果周襄王则书面命令“赐之大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并说:“敬服王命,以绥四国”。(5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第508页。简言之,由于晋文公“尊王”,周襄王除了赏赐给晋文公一些重要礼品外,更重要的是周天子还要晋文公好好地安抚四方诸侯和惩戒那些邪恶的坏人。这也就以周天子的名义“授予”了晋文公霸主地位。若只有“正统论”却没有分封制,则必然“大统一”,这就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郡县制下的“大一统”。
第四,“大一统”完全被“大统一”所替代,根本的原因在于“大统一”更有利于统治者运用权力对社会进行控制,而不是有利于社会治理。有一种观点认为,“大一统国家体制变革的直接目标是维系和巩固皇权,其实质是维护社会稳定”。(52)赵德昊、周光辉:《体制变革: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笔者认为这是工具与目的的倒置,郡县制的“大一统”本质是为了巩固皇权,而维护社会稳定只是手段或名义。分封制下的“大一统”只是权力的合法性,当进入以无礼征伐来夺取天下的时代,也就是“道术为天下裂”以后,权力的合法性已经不再遵循周礼,而强调的是实力,因此在郡县制下的“大一统”就更加强调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握和便于运用,而不是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在任何时代,权力一旦被人掌握,权力的“恶”就会因人性的恶而体现出来,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权力就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比之下,在分封制下,周天子使用权力的确因“正统性”的逐渐崩溃而捉襟见肘;在郡县制下,掌握权力的帝王则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任性。由此可见,并非“大统一”的“大一统”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从权力运行来看这种体制使统治者更容易使用权力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自秦历经汉、唐、宋、明、清各朝,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过分封制,但这些分封制完全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分封制。汉代的“列土封疆”分为王、侯两级。对汉朝皇帝而言,“地方”首先是指这些王国、侯国。“七国之乱”平定后,经由汉景帝、汉武帝两代的制度变更,王国、侯国在行政级别上分别与郡、县等同,内政由中央派遣官吏管理,王、侯仅享受本国租税中的一部分。唐代爵位分为九等,分别是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品阶从正一品到从五品递减,封户数从一万到三百户递减。但封户数是虚封,受封者的实际收益取决于“食实封”的数量,朝廷按实封的户数给予相应的庸、调。虽然实土实民的分封制在汉朝已经终结,但享受食邑封户的封爵制则一直延续到清朝。汉唐以后,王侯不具有实际的统治权力,他们在政治场域中仅具有代表地方的礼仪性质。(53)刘雅君:《普遍政治秩序与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话语重构——以贡献制的体制功能为线索》,《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更热衷于郡县制下的“大一统”体制,因为只有这样的“大一统”才更有利于他们使用权力。
四、治理伦理的变奏
治理的伦理大致存在两种,“一种是以公共秩序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取向,另一种是以公共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取向。两种不同的伦理取向决定于权力主体在管理或治理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前者强调秩序,后者强调正义。”(54)胡键:《公共管理伦理变迁:从传统社会到大数据时代》,《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6期。如果两者能够兼顾,这种治理就可以走向善治,即理想的政治秩序。然而,从历史实践来看,虽然表现为两种治理伦理,但实质上是二者合二为一,只是先秦与秦以后,合二为一的内容有根本区别。
在先秦时期,秩序与正义的合二为一表现为:以礼乐为秩序之源,以道德为正义之本。因此,为了维护秩序和实现朴素的正义价值,统治者强调的是“一礼乐”。礼在夏、商时期便已产生,《尚书·君奭》中就有“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55)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君奭》卷16,2007年,第648页。之记载,而《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56)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政》卷2,高流水点校,第71页。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夏殷之礼尚未系统化,周公则将既有的礼进行系统化并加以创新,再将这些礼仪式化。因此,所谓“一礼乐”,就是指周公“制礼作乐”而构筑的“天下”统一的礼乐系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57)孙希旦:《礼记集解·乐记》卷37,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90页。上古之人之所以视礼乐为天地之作,是因为天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秩序源于天帝所作的天序伦常,存于经天纬地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并通过巫、觋等仪式将空间秩序内化为百姓的“天下观”“国家观”,从而构筑一个在“天”的神秘感之下的神权政治秩序。
不过,秩序建立起来以后,必须要人来维持这种秩序。谁堪担此重任?只有贤能之人才能够担此重任。以贤能为标准来践行权力秩序之下的正义,这始于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例如,尧在选择舜的之前,曾经是想要把大位禅让给许由的,但许由结志于“采山饮石”而无意于功名利禄。后经过多方考察而知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58)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卷1,第36页。的正义标准“乃命以位”。(59)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君奭》卷3,第72页。舜让位于禹,也是因为禹成功治理水患,“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60)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大禹谟》卷4,第133页。,最终禅位于禹。当然,在此之前,在大禹与皋陶之间也相互让贤,认为自己不如对方,尤其是大禹对舜帝说:“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念帝功。”(61)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大禹谟》卷4,第129页。这实际上是大禹在陈述皋陶的功德,并希望舜帝能够考虑禅让给皋陶。在商汤灭夏后,成汤因流放夏桀而害怕“来世”报应,仲虺对成汤说:“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6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仲虺之诰》卷2,第291页。也就是说,没有君主,世界就会大乱,但上天是派聪明人来治理的。这一方面是强调了君主对秩序的重要性,但谁为君主则体现了正义的伦理,而且正义恰恰是权力的又一重要合法性。不过,汤灭夏桀之时,也想让天下于务光,以免天下言己之贪。但务光宁愿投河自杀也不愿被权力所累。(63)实际上,尧、舜、禹都曾试图让位给别人,拟被禅让者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有的甚至还因此而自杀。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让王》,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45—867页。后来周灭商,也是以正义的名义发动战争的。“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因此,“商罪贯盈,天命诛之”。(64)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泰誓上》卷10,第402、405—406页。可见,武王伐殷是因为殷纣有罪行而奉“天命”的善举。这也就确立了伐纣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即便是在礼坏乐崩以后,大多数诸侯国依然是坚持政治的正义伦理的,主张有道之人才可以治理国家。例如,鲁僖公八年(公元前652年),宋桓公去世之前,兄弟都有“让国之美”,宋桓公立兹父为太子,但兹父却辞让说:“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兹父要把太子之位给庶兄目夷,目夷知道后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6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第353页。这就是说,能够把国家让给出来,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仁?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宋国这兄弟俩所彰显的正是政治的正义伦理,而周所确立的嫡长子继位制及其所体现的秩序伦理,也同样得到了彰显。事实上,正义伦理是优先于秩序伦理的,只有在正义伦理前提之下,秩序才能得到有力的保证。
秦统一中国以后,君权成为秩序之源,而贤能、仁义的正义伦理被以绝对服从为内容的秩序所遮掩,但当“一人之私为天下之公”的时候,公共利益实际上就是皇家利益,正义必然回到秩序的逻辑之中,并为秩序服务。于是,在一切为了秩序的前提下,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是:思想上“一思想”,体制上推行中央集权。所谓“一思想”,也就是加强思想控制,以皇家的思想为国家唯一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除此之外都是异端,必须禁止甚至要摧毁。国家统一后,为了“定于一尊”,大秦帝国朝廷认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皆烧之”。于是,“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66)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第325—326页。而作为思想生产者的儒生,凡与朝廷思想不一致的则以秩序为由即“欲以兴太平”而“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67)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第329页。汉随秦制,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一思想得到确立以后一直影响到东汉末年,直到黄、老、浮屠蔚然兴起。这期间“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68)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卷56,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的现象逐渐消失,“儒者之风益衰矣”。(69)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卷79,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47页。于是,皇帝开始“祠老子于龙濯宫”。(7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0页。黄老思想和从南亚经西域来的佛家思想从此进入中华帝国正统的思想世界,并且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以致在大唐帝国时期,老子、释迦牟尼的生日竟然作为华夏帝国的国定假日。(71)杨联陞:《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程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思想世界的这种情形直接构成了帝国的政权危机,所以在安史之乱以后,重建思想之需的呼声就迅速化成一股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韩愈为代表,矛头直指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目的是重建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思想之需。这实际上是士人主导下的“一思想”的文化运动,主要是想通过思想秩序的重建而使政治重新恢复权威与秩序。韩愈以后经王安石到朱熹及以降,在强调儒家正统上是一步步加强的,虽然王安石强调《周礼》也就强调“一君万民”,而朱熹重视《春秋》也即强调以君臣之间的名分为基础,倡导的是上下尊卑的身份性质的意识形态。(72)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龚颖、赵士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11页。不过,这都是在儒家思想之内的不同主张,都还是强调“一思想”。
关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之形成,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他认为一个原因是自然的力量所驱使的,即华夏民族是农耕民族,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而这里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患频出,所以中央集权才可以给民众以应有的安全。另一个原因还在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在寒冬岁月南下掳掠。(7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2—23、26页。这种说法似乎能够自圆其说。然而,即便有自然的力量和对北方少数民族防范的需要,但这也只是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外部因素,而不是根本性的内部因素。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君权之下的秩序。(7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9页。基于此,黄仁宇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一种抗击灾害的体制。这种判断有一定的道理,黄仁宇认为,《孟子》中提及治水十一次之多,然后推理孟子所说的“定于一”就是指一统而安定。(7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3页。不过,即便是抗击灾害的体制不会也不应该成为一种常规体制,如果一个民族始终处于一种应急体制下,这个民族的心理就成为一个大问题,无论如何,应急体制必须要回到常规体制之下。实际上,黄仁宇对孟子的“定于一”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孟子所说的“定于一”之“一”所指的是“仁”而非“一统”。《孟子正义》非常明确地指出:“孟子谓仁政为一也”。“疏”也说:“惟有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天下皆遵奉之而后定。孔子作春秋,书‘王正月’,公羊传云:‘大一统也。’孟子当亦谓此。”(76)焦循:《孟子正义》卷3,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页。因此,孟子之所谓“定于一”实乃定于仁,“仁”就是“一”。后来《吕氏春秋》中的“一则治,异则乱”和李斯所说的“定于一尊”是完全不同的。后两者的“一”意思就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孟子则更强调以仁来构筑权力的基础,而民众则会自然归附。
有一种观点认为,“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变革在方式上主要采用渐进和迂回的手段。尽管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但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变革总体而言仍然是渐进的。”(77)赵德昊、周光辉:《体制变革: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如果对“大一统”不加区分地做出这个判断是不妥的。前文述及,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大一统”是完全不同的,从前一种“大一统”到后一种“大一统”的转变,肯定不是渐进的,而是一种突变。而前后两种“大一统”作为政体而言,其自身内部实际上没有实质性变化。即便如公元前594年推行的“初税亩”,也只是治理政策上的变化,即制体改革,政体没有任何变化。至于统一后的“大一统”,虽然也历经众多改革,从王莽改制到王安石变法,以及明朝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等,这些也都是“大一统”政体下制体之术的变化,“大一统”政体之道并没有变化。因此,不能混淆了政体与治体的概念,自郡县制“大一统”政体确立以后两千多年来,国家层面的所有的改革只是治体改革,而不是政体改革。金观涛、刘青峰所说的中国“超稳定结构”,主要是指由郡县制政治结构和儒家学说意识形态结构构成的一体化结构,也就是“大一统”体制。(78)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1页。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直到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产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出的以“地方自治”为内容的“封建”主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受到自建立以来从未遭遇的冲击。这种主张相对于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不过昙花一现,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后来的民权革命价值的形成不可低估。
结论
从文献来看,以国家(或者是以古代部落国家)的名义探讨系统性的治国理政问题,古代中国可能的确是比较早的国家之一。上古时代的《洪范九畴》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完善的治国方略,在这个治国方略中,权力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而不是一种垂直的单向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治理”比“统治”诞生得更早。追溯“治理”这个概念的历史,目的是要回应当前一种观点,即“政治学要回到历史”,治理、统治都是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概念,所谓“回到历史”,就不能回到某一个时代的历史,而要追溯这些重要概念所体现的政治科学的本源意义的起点,尽可能地回到被今天所认知了的历史。
“善政”是人类作为理性的政治动物必然要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不同的民族在远古时代所追求“善政”的形式和内容是大相径庭的。远古时代的中国就已经明确权力的基础是民心,所以都主张以民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和政策取向来追求当时的“彝伦攸叙”理想秩序。尽管民本主义政治起源很早,但并非在政治发展史中一以贯之,不同政治体制之下,对权力的认知也不同。“大一统”始于远古而延续下来的政体,但“大一统”在先秦以前采取分封治理,而秦统一中国后采取中央集权治理。两种不同的“大一统”演绎了中国数千年的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和治理伦理。
治理伦理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趋向:秩序和正义。不过,从历史实践来看,在“大一统”的治理框架下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先秦与秦统一中国以后,合二为一的内容有根本性的区别。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是以正义为前提来追求秩序的,所以政治伦理则强调选贤任能,而在中央集权之下的“大一统”则是以绝对君权之下的秩序为前提来兼顾正义的。
最后,笔者要回到当前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的问题上。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一方面要从当前中国社会实践中进行理论概括,实践是理论之源,西方政治科学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实践。鉴于西方政治科学的“策源性”,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般性理论”,但不能将它用于阐释中国实践。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就成为必然,也就是从本土实践来创造出本土性的政治科学。这体现出中国政治科学的时代性。另一方面,任何知识又都是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积累所致,从这一点来看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必须有历史关怀,从历史中去梳理政治科学知识并将它系统化,这就构成中国特色政治科学的知识谱系。因此,“政治科学要回到历史”,不只是学者的研究兴趣所致,而是政治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