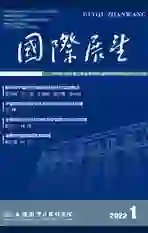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2022-01-13崔文星叶江
崔文星 叶江
【关键词】 国际发展合作 联合国2030年议程 全球发展倡议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2)01-0074-21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201005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争取盟友的重要手段。对于援助国来说,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通过援助使某个受援国成功留在己方阵营,而较少关注援助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不复存在,但援助国政府在制定援助预算时面临着新的合法性危机,议会和民众对本国进行的大量援助并未有效改善受援国状况提出更多批评。援助有效性(aid effectiveness)的讨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而对可衡量的结果的重视是讨论的主要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援助有效性辩论的重要参照,全球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亦开始了结果导向型援助新实践。中国高度重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了有机结合。目前,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各项落实工作已经在中国全面展开。 2021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强调中国不仅要通过自身发展,而且要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2021年8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以加强援外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10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的讲话中强调,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加快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落实,这标志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议程的对接进入新阶段。
援助有效性是发展援助在实现经济或人类发展方面的效力。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援助国的政府和援助机构开始意识到,它们在提供发展援助时所采取的不同援助方式和对受援国提出的不同要求给受援国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导致援助的效力降低。因此,它们开始寻求通过相互间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合作来提高援助的有效性。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困、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商定了一套有时限的目标,即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手段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这一目标体系为援助者之间的政策协调提供了重要参照,援助有效性评价的国际进程也由此开始。
2002年3月,联合国发展融资峰会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双边与多边援助机构同意扩大援助规模并提高援助有效性。 2003年2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援助协调高层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援助协调性的罗马宣言》(Rome Declaration on Harmonization),强调援助重点要与受援国发展的优先领域保持一致并加强援助国之间的协调。 2005年3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援助有效性高層论坛上签署的《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提出了国家自主决策(ownership)、一致性(alignment)、协调性(harmonization)、成效管理(management for results)和相互问责(mutual accountability)五项援助原则。 其中第四项原则强调需要加强对援助实效与成果的测量,使援助能够切实促进受援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2008年,第三届援助高层论坛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会议通过的《阿克拉行动议程》(Accra Agenda for Action)在认可南南发展合作价值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发展结果。 2011年11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上通过的《釜山宣言》(Busan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正式提出国际援助政策的关注点应从援助有效性转向发展有效性。结果导向型援助(results-based aid)模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多边援助机构中发展起来,并日益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
“聚焦于结果”(results-focus)曾是围绕援助所进行的辩论的重要维度。例如,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分析框架就将援助直接与绩效和结果相联系,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一书中就有相关分析。还有一些理论、概念和方法也与“结果”相关。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关于国家选择(country selectivity)的讨论也隐含着聚焦“结果”,其背后的理念是对那些表现良好的国家予以奖励,并激励它们表现得更好。 此外,为援助附加条件也直接涉及对政策实施与改革结果的激励。
对援助结果的重视虽然由来已久,但对结果导向型援助这一新援助方式的深入研究则主要是在2011年釜山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之后,在国际发展话语从援助有效性向发展有效性转变的背景下逐渐兴盛起来。在这次论坛之后,德国发展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ntwicklungspolitik, DIE)的一批研究人员开始对结果导向型援助进行专门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国际组织在非洲国家的相关项目,重点关注教育、卫生与治理。斯蒂芬·克林格贝尔(Stephan Klingebiel)对结果导向型援助方式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阿曼达·梅丽娜·格里特纳(Amanda Melina Grittner)对卫生部门结果导向型融资进行了研究。 莎拉·霍尔扎普菲(Sarah Holzapfel)与海纳·贾纳斯(Heiner Janus)对教育部门中结果导向方式的指标进行了归纳。 海纳·贾纳斯和莎拉·霍尔扎普菲对农业部门中结果导向方式所面临的挑战与教训进行了总结。 海纳·贾纳斯和尼尔斯·凯泽(Niels Keijzer)对坦桑尼亚结果导向型援助项目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分析。 除了德国发展研究所,英国、荷兰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研究人员也对结果导向型援助进行了研究。马克·皮尔森(Mark Pearson)对结果导向型援助概念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是否促进了结果的实现。 朱里安·图嫩(Jurrien Toonen)等以马里和加纳作为案例,对卫生领域中结果导向型融资进行了研究。 美洲开发银行则通过来自萨尔瓦多卫生部门的证据对结果导向型援助是否比传统援助更有效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世界银行对教育领域中结果导向型融资进行了研究,并对这种融资方式对加强世界银行系统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随着中国日益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国内学者在对援助有效性和发展有效性的讨论中也更聚焦结果。李小云对西方援助有效性战略为何走向无效进行了分析,认为援助主体、对象、机构和领域的碎片化是影响援助效果的重要原因。 张海冰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一种发展引导型援助,以发展的有效性作为衡量援助是否有效的关键标准,这一点不同于巴黎俱乐部所推崇的援助有效性概念。 黄梅波构建了援助有效性和发展有效性相结合的国际发展援助质量评价框架,利用该框架对中国对外援助效果进行评估。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在关于发展有效性的讨论中加强了对援助效果和结果的研究,西方学界和政策界则对结果导向型援助的概念、原因、效果等基本问题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并结合不同的国家案例进行了初步探讨。
与结果导向型援助相对应的是过程导向型援助。过程导向型援助是以投入(如提供了多少资金)和进展(如建成了多少所学校)为导向。与此相对应,对援助效果的衡量也通常是根据投入或进展指标来进行,例如,受援国是否增加了教育预算,是否出台了教育改革政策。这种援助评估方法主要关注的是受援国的活动,但并不确定预期结果是否能够实现。例如,预算增加和教育改革政策的出台是否实际促进了入学人数的上升和教育质量的提升。如果结果得以实现,其与援助活动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这些都是过程导向型援助难以回答的问题。结果导向型援助力图弥补传统援助方式的不足。
结果导向型援助致力于在援助活动开始之前确定可以衡量和量化的与发展援助活动直接相关的结果目标,援助国与受援国在合同中确定促使结果目标实现的激励措施,即援助的实施与结果目标的实现情况相挂钩。 援助国与受援国事先就结果的“单价”(Unit Price)达成一致,例如,受援国每有一名学生通过期末考试,援助方将会提供多少援助,但援助方并不参与援助项目的具体实施。结果导向型援助在援助支付和发展结果的实现之间建立了联系,旨在消除以投入为导向的援助方式的弊端,如没有明确的结果证据、援助交易成本高、大量使用援助方的执行能力而绕过受援国国家系统等。
结果导向型援助主要基于三个假设。第一,由于强有力的激励措施,结果导向型援助可以促进受援国在主要结果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第二,结果导向型援助降低了援助的交易成本,因为它需要的报告流程较少,而且受援国的国内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更好的利用。第三,受援国对结果导向型援助的计划制定和政策实施有很强的自主权,而且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责任分工也更加明确。
结果导向型援助在具體实施过程中主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援助国与受援国签订发展合作合同。第二步是开展实现结果目标所需的活动(受援国负责整个实施过程)。第三步是对结果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估(通常由第三方完成)。
“结果”通常被定义为“投入”(input)和“活动”(activity)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级。“产出”(output)通常是技术层面的结果,如新建的学校;“产出”可能会导致下一层级的结果是“成果”(outcome),如因有了新的学校设施而使儿童入学率提高;最具雄心的结果层级是“影响”(impact),如因教育成果改善而带来的减贫效应。
对目标结果的实现情况进行衡量需要使用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将指标定义为“定量或定性因素或变量,提供衡量成就的简单可靠手段,反映与干预有关的变化或帮助评估发展行动者的表现”。在所有类型的发展计划中都会使用指标对实施过程进行管理并对实施结果进行报告。
在结果导向型援助中,指标被专门用于决定所支付资金的数额。虽然所有发展干预都需要某种形式的证据,如资金支出的文件证据来确定援助的支付,但结果导向型援助通过与支付挂钩的指标(Disbursement-Linked Indicators, DLIs)将资金拨付与预先确定的目标或结果直接相联。与支付挂钩的指标有三种分类方法。
第一种分类是“进程指标”与“结果指标”。与支付挂钩的指标可以根据结果的不同层级来进行界定。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影响链条始于“投入”,然后是为实现预期目标所开展的“活动”,“投入”和“活动”有助于“结果”的实现。 “结果”又有三个层级:直接的“产出”、短期和中期的“成果”以及长期的“影响”。“投入”指标用来衡量所使用的财务、人力和物力资源,如分配给教育计划的预算。“活动”指标衡量所采取的行动或所开展的工作,如举办教师培训研讨会的数量。“产出”指标用来衡量发展干预所产生的产品、资本品和服务,如接受过培训的教师人数。“成果”指标用来衡量干预的短期和中期效果,如学生学习成绩的改善。“影响”指标用来衡量干预的长期效果,如青年就业率的增加。
第二种分类是“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直接指标”指发展的主体, 如接种疫苗的儿童人数是儿童疫苗接种计划“产出”层面的直接衡量指标。“间接指标”衡量与结果本身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很好地描述结果的实现程度, 如家庭资产和住房情况通常用作家庭生活水平的间接衡量标准。当收集“直接指标”的数据困难、成本高昂或不可行时,就会更多使用“间接指标”。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收入、支出和消费等生活水平的直接衡量标准难以收集或收集成本高昂,“间接指标”就特别有用。
第三种分类是“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定量指标”是通过客观或可独立验证的数值(如绝对值、百分比、比率等)对结果进行衡量,如接受培训的教师人数、受益于卫生条件改善的人数、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例、每一千名活产婴儿中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然而,并非所有现象和结果都可以量化,如促进民主、善治或机构能力建设的干预措施其结果往往是定性的,因此通常可以通过定性指标来衡量,如法律是否已获通过或是否已建立机构,受益人对服务的评价是优秀、满意还是不满意。
对与支付挂钩指标的适用性进行评估通常采用“聚焦于结果”“与受援方努力相关”“需财政激励”“可衡量验证”“考虑意想不到的后果”等有关标准。一是更加注重结果是结果导向型援助的主要目标之一,与支付挂钩的指标应聚焦于对三个层级上结果目标的衡量。二是当援助拨付与指标挂钩时,这些指标应衡量那些因受援方努力而产生的变化。三是在财政激励方面必须为在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定价,以及确定是否为额外的单位进展进行增量拨款。四是当支付与结果挂钩时,这些结果必须是可衡量和可独立验证的,这样才能确保其可信度。五是指标的设定要考虑意想不到的后果并注意避免激励扭曲。例如,当及格率指标被用于确定援助拨付时,受援方有强烈的动机把精力放在帮助那些最接近及格门槛的学生,而忽视那些距离及格线较远的学生。
世界银行资助的坦桑尼亚“教育中的重大成果计划”(Big Results Now in Education Program, BRNEd),是教育部门中第一个结果导向型援助的试点计划。该计划始于2014年,其目标是提高坦桑尼亚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其衡量指标包括:全国二年级学生的阅读平均成绩、全国二年级学生的平均算术成绩、中小学暗访期间在教室里发现的老师百分比等。 这一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坦桑尼亚国家改革议程中“立即实现重大成果”(Big Results Now, BRN)倡议紧密联系并保持一致。
该倡议聚焦于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六个优先领域,致力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可衡量的目标,表现出较强的结果导向特点。世界银行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在五年内(2014—2018年)出资1.22亿美元,共设立了16个与支付挂钩的指标对进展进行监测与评估(见表1)。

资料来源:Sarah Holzapfel and Heiner Janus, “Improving Education Outcomes by Linking Payments to Results: An Assessment of Disbursement-linked Indicators in five Results-based Approaches,”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2015。
從“聚焦于结果”标准看,与支付挂钩的指标分布在结果链条中的投入、活动、产出和成果四个层级。大多数指标对制定预算、生成报告等活动进行奖励,唯一的成果指标对阅读、写作和算术方面的改进进行奖励。从“与受援方努力相关”标准看,这些指标的改善与政府部门控制范围内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11个指标针对中央政府部门的行动进行奖励,5个指标针对向学校提供资金和教师的地方政府的行动进行奖励。从“财政激励”标准看,支付要么基于达到某些阈值,要么基于规模上的单位。在16个指标中,9个被确定为阈值,主要用于衡量是否已制定预算、计划或测量工具。这些指标的支付大多在第一年进行一次,指标是以二元术语表示的定性指标。因此资金要么全部发放,要么完全不发放。其余7个指标基于不同的尺度,对目标进展情况按比例进行奖励。从“可衡量验证”标准看,大多数指标都是直接和定性的,并评估政府实体的绩效。虽然这些指标在针对特定活动的意义上是直接的,但它们只是总体目标的间接衡量标准。从“意想不到的后果”标准看,许多潜在的意外后果和各自的缓解策略已经被提前考虑并包含在计划设计之中,主要风险包括2015年的国家选举结果、管理薄弱、执行部门的监督能力欠缺等。
结果导向型援助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促进受援国的发展。一是激励受援国,因为资金拨付与可量化的结果相联系,这可以激励受援国努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二是在受援国产生溢出效应,受援国在某一个部门所形成的发展成果会对其他部门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如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民众的卫生知识,从而进一步促进健康目标的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吸取了千年发展目标“筒仓”结构的教训, 致力于提高各目标之间的协同效应。三是加强受援国政府的自主权,2030年可持续发展子目标17.15强调要尊重每个国家制定和执行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政策空间和领导作用, 实现目标的任务在于受援国政府,这加强了受援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四是援助更具可见性,发展成果和援助激励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为明晰,这可以帮助援助国展示援助带来的具体成果。
然而,结果导向型援助也存在着劣势。一是造成援助“宠儿”与“孤儿”,即结果导向型援助仅适用于那些表现良好的国家,对于低收入和高度依赖援助的国家而言,这些激励条件不存在或效果不佳。二是对受援国执行能力要求高,该方法意味着受援国需要有能力取得成果。如果它们的能力不足、公共财务管理系统不完善,这种方法并不现实。三是容易导致整体政策缺乏系统性,对某些特定结果的关注往往会导致整体政策缺乏系统性,实现特定目标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对同一部门其他重要问题的忽视。四是部门限制,结果导向型援助无法在所有部门得到同等实施。教育、卫生等社会部门以及容易衡量的基础设施服务部门(交通、公共供水等)更适合此种方法。其他部门可能较难衡量这些结果或与受援国达成协议,例如,关于良好治理的复杂协议。五是预融资能力不足。在这种方法的设计中,受援国需要自己预先出资,然而一些低收入国家的预算非常紧张,这可能是一个主要障碍。六是时间范围。结果导向型援助往往具有短期视角倾向,因为它可能只考虑那些可以快速实现的目标,对于那些只能在中期或长期实现的目标可能会与短期政治目标(如赢得选举)发生冲突, 因此,结果导向型援助并非灵丹妙药,过于强调结果也会造成政策的短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国际社会为全球发展建立的一个结果框架。这一框架包含17个大目标、169个子目标以及230个指标,大部分目标的截止期限为2030年。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并不是为发展合作本身(包括官方发展援助)或单个发展合作提供方设置的框架,但它为结果导向型援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发展合作提供方(援助方)与合作伙伴(受援方)都可以通过将其结果框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系而获益。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發展议程于2015年通过后,西方国际发展学界及政策界就开始加大对结果导向型援助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指标的相关性进行研究。2017年9月,OECD-DAC发布了题为《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和指标加强援助方的结果框架》(Strengthening Providers’ Results Frameworks through Targets & Indicator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列举了由53个稳健指标(robust indicators)支持的42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成果”(outcome)子目标和涵盖实施手段(means of implementation)的18个可持续发展子目标及其指标,并建议发展合作提供方以此菜单作为制定自身发展合作结果框架的参照。
以教育目标为例,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目标4为“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与目标1—16中的其他大目标相同,该目标下设的子目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到2030年要实现的目标(主要聚焦于结果链条中的“成果”层面),第二部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主要聚焦于结果链条中的“活动”层面)。例如,子目标1为“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童完成免费、公平和优质的中小学教育,并取得相关和有效的学习成果”。衡量目标进展的指标则包括:在二年级或三年级、小学结束时、初中结束时获得基本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的儿童和青年的比例,按性别分列;初等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的完成率。实施手段则包括建立和改善教育设施与增加合格教师人数等。此外,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1—16的如期实现,目标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则专门强调了发展合作的作用,通过发达国家全面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以及加强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等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16方面取得进展。2030年议程中与结果导向型援助密切相关的子目标和指标为援助方与受援方在发展合作中确定责任归属、进行沟通交流、明确合作方向和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基础, 这是发展政策一致性努力的重要里程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2011、2014、2021年,中国发布了三份白皮书,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与成就、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国际发展合作趋势与特点等进行全面介绍。2011年白皮书将中国对外援助归纳为八种方式: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 总体来看,2011年白皮书对中国援助情况的总结主要是集中在结果链条中的“活动”与“产出”层面(如提供了多少价值的药品、援建了多少所学校和医院等),而对中国的援助在受援国产生的“成果”及“影响”基本上没有提及。2014年白皮书在2011年白皮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更加注重对援助所产生的结果的强调,这显然与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国际发展合作潮流是相契合的。2014年白皮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对中国援助在推动受援国民生改善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总结,但所提供的支撑材料的“成果性”并不突出,如中国在2010—2012年期间援建了156个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举办了1 579期官员研修班等。
2015年联合国2030年议程通过后,中国对外援助及国际发展合作开始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对接。2021年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将国际发展合作定义为“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的多双边国际合作”。这份白皮书除了将“援助”扩展为“发展合作”之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是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列为白皮书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这说明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向结果导向又迈进了一步,表明了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的意愿与决心。在此基础上,2021年9月1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新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的基本精神体现在具体的对外援助管理之中。总之,2021年中国发布的与国际发展合作及对外援助相关的文件都对结果导向型援助有所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社会对结果导向型援助的讨论是基本同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治理话语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更显示出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相通之处。
“对外援助”(foreign aid)、“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和“发展合作”(development cooperation)是相近的概念,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术语有着不同的使用偏好。美国多使用“对外援助”,且往往不对发展援助和军事援助进行区分。“发展援助”和“官方发展援助”在一些欧洲国家和国际组织使用较多,强调援助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而非出于军事或其他目的。 经合组织和欧盟的文献中则较多使用“发展合作”,以表明其致力于提高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平等性。长期以来,中国的官方文件中更多使用“对外援助”一词。例如,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又如,2011年4月和2014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第一份和第二份《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然而,2021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则将“对外援助”升级为“国际发展合作”,这一表述的变化是中国国际发展政策与时俱进的体现,且与结果导向型援助及联合国2030年议程相互关联。
二戰后的国际援助体制是以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启动为标志而展开, 在此后的4个财政年度,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促进了西欧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使西方国家认识到对外援助的积极作用,此后西方国家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援助逐渐展开。然而,在接受援助的几十年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成功走上发展之路,即使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然在为摆脱极端贫困而努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对援助效果不佳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首先,援助金额受到援助国经济发展情况及对外战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其直接表现是援助承诺出现无法完全兑现的问题。其次,大多数西方援助国都将提供援助与苛刻的条件挂钩,这降低了援助资金的有效额度、加剧了援助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再次,不同的援助方对受援国关于援助资源使用的报告和援助效果的评估有不同的要求,援助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给受援国带来了沉重的人力和物力压力。 2009年,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甚至提出了“援助死亡”(Dead Aid)的观点,认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对非洲援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已走入绝境,此种由外部力量主导的援助造成非洲对外部的严重依赖,埋葬了非洲自主、独立发展的机会与意愿。 而结果导向型援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与西方传统援助国的对外援助不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也注重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的提高, 将“输血”与“造血”相结合。 因此,将“对外援助”转化为“国际发展合作”更能体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平等互惠性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的发展援助理念与结果导向型援助理念相契合。
二战结束后,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国际发展合作实践至少存在着三条主线:第一条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第二条是苏联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第三条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始终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进行,强调合作的互利性。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对危机和疫情的不同应对导致国际权力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进一步加速,中国进一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此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许多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质疑的声音,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9年7月指责中国通过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在2021年4月也表示英国将会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对此,中国在2021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中重申南南合作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定位,强调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与南北合作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具有南南合作的特性,使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能够避免结果导向型援助的某些负面因素,比如能够避免援助中出现“宠儿”和“弃儿”的现象。随着中国更为强调国际发展合作,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关注援助结果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均衡地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以结果为导向的援助。
鉴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对殖民地的掠夺,它们在道义上有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而南南合作则没有这一历史包袱。另外,也同样由于殖民思想的影响,今天的南北合作依然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突出体现在发展道路的一元性与合作模式的垂直性。一元路径观的哲学基础是坚持西方社会的“先进性”和所有民族都要经历相同发展道路的社会进化论。 受此理论的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发展,只能沿着西方国家走过的路前行。这一思想在国际发展实践中的体现是垂直型的南北合作,即西方发达国家以“教师爷”自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种種发展“药方”,如结构调整、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人权、善治等。与南北合作不同,南南合作倡导发展道路的多元性与发展合作的水平性。中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时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尊重其他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这显然有助于在保持结果导向型援助优势的同时克服其劣势。
在2013年10月24—25日举行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4年7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时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援助话语中,援助方(donor)和受援方(recipient)的表述一方面具有居高临下和施舍的不平等意味,另外也体现出双方关系中资源单向流动的不均衡性。而“国际发展合作”显然更具平等性与均衡性,体现着资源双向流动与共同发展的内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更为契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以推动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落实为重要方向,毫无疑问这是对结果导向型援助的划时代超越。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对接所带来的机遇,同时有效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需要在借鉴的同时解构甚至超越西方的国际发展话语,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的全球发展理论。这样才能增强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话语权,并且更好地把握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
1949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宣布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计划”,他在为国际发展时代揭开序幕的同时,也在提倡一种构想国际关系的新方式。 这种“新方式”用全球经济中贸易伙伴之间的看似平等的关系取代了原来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制度。在新的国际关系中,一批“欠发达”国家落在后面,需要“发达”国家的慷慨援助才能赶上去。通过这种新话语,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新认知被创造出来,20亿人被贴上了“欠发达”的标签, 他们不再是原来具有丰富多样性的群体,而成为反映他人现实的镜子,这面镜子对他们进行贬低并将他们送至队列的末尾。人们在谈论他们时首先不再是其文化多样性,而是他们统统都是欠发达地区的人。 世界上存在着“发达”和“欠发达”的社会,前者在北方而后者在南方,后者问题的解决受益于前者的知识。这一思维方式类似于临床观察,其特征是将注意力放在他人的缺陷上,将有关治愈的知识归于自我,而忽略他人的知识。在这一视角下,北方没有成为发展干预的对象。因此,根据发展学派的观点,“发展”的不变特征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对“欠发达”社会进行干预的合法性,基于“发达的自我”(developed Self)的欧洲中心视角以及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知识的归因,基于可以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的普遍标准。 由此,结果导向型援助虽然克服了过程导向型援助的种种不足,但是却依然难以超越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中的以北方为中心的西方发展观。
从某种程度上看,联合国框架下的四个发展十年和千年发展目标体系都应该属于国际发展议程,议程中所设定的目标主要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则主要是援助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尽管结果导向型援助这一修正过去西方发展援助负面影响的理念对上述联合国的国际发展议程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但是却并没能改变国际发展中的这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单向流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和环境议题在发展议程中的进一步凸显,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环境等发展可持续性问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普遍适用性,适用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在促进目标实现的资源和知识方面,作为执行手段的千年发展目标8(建立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并未提到南南合作的作用。与此不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作为执行手段的目标17则明确将南南合作、三方合作与南北合作并列,强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也是发展资源与知识的来源。因此,从目标适用范围和发展知识来源的视角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属于真正的全球发展议程。更重要的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伙伴关系方面既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
通过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中国的发展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之路确立了信心,中国也开始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在全球发展话语建构方面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该倡议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影响下的全球发展指明了方向,对“要不要发展”“要何种发展”“如何发展”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回答。全球发展倡议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惠包容性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全球发展倡议是在充分借鉴全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蕴含了西方文明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的“公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等要素。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建构的重要基础,并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全球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明了方向。
多年来,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与民众的欢迎与好评,但也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学者与官员的质疑与诟病,“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缺乏透明度”等指责也一度甚嚣尘上。要增强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话语权,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效果需要更多可量化的结果证据来支撑。中国需要吸收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结果导向型援助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合作实践中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对国际发展合作的实践进行改进与完善。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既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是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的重要突破口。
在中国为全球发展提供的方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而生态文明则致力于解决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与自己的关系。生态文明不仅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传统的由西方主导的发展话语的超越,它既包含了替代性发展,也包含了发展的替代。这些理念为中国全球发展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发展理论,超越结果导向型援助,以增强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话语权,既与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责任编辑:石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