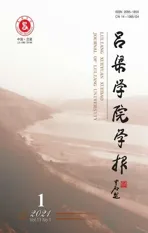《民权素》蒋箸超小说叙事分析
2021-12-29张海城段玉莹
张海城,段玉莹
(1.吕梁学院 中文系,山西 离石 033001;2.高唐第二中学,山东 聊城 252800)
《民权素》是民国初年创办于上海的一份综合性文学刊物,1914年4月25日发行第一集,至1916年4月被迫停刊,两年间共发行17集。刊物设名著、艺林、游记、诗话、说海、谈丛、谐薮、瀛闻、剧趣、碎玉等10个栏目。所刊作品体裁完备,新旧兼具。蒋箸超任该刊主编(1)《民权素》第一集由蒋箸超和刘铁泠同任主编,第二集开始到第十七集停刊由蒋箸超单独任编辑。。
一、《民权素》刊载蒋箸超小说概述
《民权素》刊载蒋箸超的小说作品共三篇,刊行情况如下:
1.《白骨散》第一集(1914年4月25日),署苦情小说。
2.《满腹干戈》第二集(1914年7月15日)、第三集(1914年9月10日)、第六集(1915年5月15日)连载,未完,署伦理小说。
3.《牛皮王》第五集(1915年3月12日),署滑稽小说。
蒋箸超的这三篇小说,兼用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既有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书写,也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一)文言苦情小说《白骨散》
《白骨散》(2)《民权素粹编》中更名“文字因缘”,各章名称略去。是一篇文言小说,1914年4月25日刊载于第一集,共六章,分别为:接信、访艳、惊婚、罹劫、完葬、和亲。小说以笈云和颉昭相识相恋的故事为中心,塑造出一种“历变不毁其盟”的真挚爱情状态。
江南书生笈云,因文采出众,为京城某公所赏识。颉昭是某公的女儿,亦富有才学,对笈云甚为仰慕,便私自写信寄予笈云。为躲避父母的逼婚,笈云应颉昭的邀请前往京城应礼部的考试,投奔某公,得与颉昭相识相恋,二人互为知己。笈云已与王氏之女有婚约在身,自觉对颉昭的倾慕之情不得言表,故而只得以兄妹相称,为此两人均大病一场。后逢“义和拳”大乱,颉昭父母死于非命,笈云与颉昭颠沛流离,相互扶持,感情日笃。最终义和拳祸乱平定,朝廷为某公之死正名,并追加抚恤。两人进京完葬某公后一同南下回到笈云故里。笈云母亲得知二人情意已笃,不忍拆散,于是向王氏提出双娶之议。王氏之女亦倾慕笈云才华,欣然应允。最终,王小姐与颉昭同嫁笈云,小说以大团圆结局。
中国古典小说中言情传统由来已久,及至民初,言情小说浩如烟海,且种类愈加丰富,仅《民权素》“说海”栏刊行的小说便有苦情、哀情、孽情、怨情、惨情、忍情、侠情、艳情等20余种,数量达73篇,占据《民权素》“说海”栏的半壁江山。
《白骨散》小序中写道:“比来言情之作,汗牛充栋。其最落窠臼者,大约开篇之始,以生花笔描写艳情,令读者爱慕不忍释手。既而一波再折,转入离恨之天,或忽聚而忽散,或乍合而乍离,抉其要旨,无非爲婚姻不自由,发挥一篇文章而已。”
据此可知,蒋箸超认为民初言情小说多为批判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婚姻不自由而作,因此创作《白骨散》时,他有意避开这一窠臼,“予尝疑之,以爲情之可哀者固多,然至毕生不渝其志,历变不毁其盟,仅仅爱情,似未可恃,则必有其曲折之苦难在也。爰本所见着是篇。”[1]25《白骨散》中,笈云与颉昭经历变故,颠沛流离中不离不弃,最后修成正果。在一见钟情的直觉之外,笈云与颉昭的感情经历了苦难的检验,是真正坚贞不渝之情爱。但是,“双娶”之计,又让蒋箸超处理爱情的方式显得过于简单。
(二)白话伦理小说《满腹干戈》
《满腹干戈》以白话写成,是“说海”中仅有的一篇白话长篇小说,连载于《民权素》第二集(1914年7月15日)、第三集(1914年9月10日)、第六集(1915年5月15日)。第六集文末标“未完”字样,表明该小说并未完结。但此后并未见续作。因此《满腹干戈》实为残稿。
现有的作品共三章(3)在第三章结尾处标注了“未完”字样,但在之后的刊物中未见续集,断更原因不详。,写杨氏夫妇教子无方,导致八个儿子兄弟阋墙,终致家门败落的故事。从已有内容看,《满腹干戈》讲会稽(今浙江绍兴)杨家,因前人在朝为官挣下一分家私,成为当地富户。然“门祚衰微”,数代单传。至杨家第六代,境况大转。杨氏育有八子,个个聪明伶俐,“有入学的、也有补廪的、也有中举的”[2]24,可谓人丁兴旺。父亲杨水心是会稽老名士,性好僻静,不喜与孩子亲近。育儿之事多由其妻杨氏操持。杨氏不曾读过书,教训儿女常偏爱偏憎,使得一伙兄弟竟生成一副独立性格,从小将兄弟当作仇敌一般看待,彼此间吵闹不断。杨氏为子说亲,不问女子德气,专在“富贵贫贱”四字上做工夫,“第一要妆奁丰厚,第二要门第阔绰,第三要面庞俊俏,这才是我的体面”。
杨氏八个儿子:炳熙、炳煦、炳炎、炳焘、炳熊、炳勋、炳烈、炳照,尤以三子炳炎最难缠,从小好赌好嫖,游手好闲,到处欠下债务让母亲杨氏去了结。杨氏对于炳炎的恶习不仅不加阻止,反而一次次帮他了结,终致惹下公案。为了帮炳炎了结债务,杨氏花费了大量钱财,使得分家时其他儿子不满意,认为杨氏夫妇偏袒炳炎。另杨氏替炳炎了结债务,并未告知杨水心,讨债人闹到杨水心的寿宴上,才不得已和盘托出,炳炎之债务越撒越大。
因小说为连载完结,故其后结果未可知。但在文章开篇可窥得几分端倪,即杨家衰落,宅邸易人。
蒋箸超藉此故事,指出为人父母的“通弊”:第一种是偏爱偏憎,第二种是不爱不憎,第三种是姑息养奸。杨夫人在此一项,“有大大的不是”。通过写杨氏夫妇教子无方,终致家门败落的故事,凸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以此警醒那些“为父母的”,即使孩子的残忍之性是胎里带来的,也可以从天性上下功夫。家庭教育不在于读书与否,请先生与否,而是“用其真正之爱情”,培养孩子的德性,将其野性渐渐改移。
(三)白话滑稽短篇《牛皮王》
《牛皮王》也由白话写成,篇幅短小,刊于第五集(1915年3月12日)。以“牛皮王”自述之语,借叙事者之耳,揭示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
《牛皮王》用通俗诙谐的笔触,塑造了滑稽、虚伪的“牛皮王”形象。作者通过牛皮王之口讲出“现在不要脸的后生,偷得几句唐诗,读过几篇聊斋,就混在书局里吃饭。还有那几个血腥气的书贩子,赚得几厘几分钱,便着实恭维他。诸君不看现在的报上,天天的名著出现吗”,反映出当时社会上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却自视甚高,讽刺世人唯利是图,趋炎附势的现象。
“牛皮王”形象是滑稽的,他“夸嘴”道“若倒退二三十年,不但这几位著作家,不在我眼里,便是那曲园樊山湘绮苏龛诸公,也都让我出风头呢,我还记得那一年同友人登高,有一脚踢翻宋,四拳打退唐之句”,“一拳打初唐,一拳打盛唐,一拳打中唐,一拳打晚唐”,刻画出一个妄自尊大,不知深浅的人物形象。
“牛皮王”也是虚伪的,他把五香鸽子吃个精光,又说“这个味儿实在不好”,只是因为自己肚子饿了,才吃个精光。他讲述自己制作鸽子的方法,极尽考究,在听者想去“登堂大嚼一回”时,他又含糊道“你来来……好……你来”,反映出了他的心虚。停一下又说“现在时候,做官也太容易,不管他识字不识字,懂理不懂理,只要有门路,有资本儿,不怕运动不到”,这也是中国吏治腐败时出现的“以钱买官”现象。说罢又“吹”自己与京城官员和大总统的关系,并将自己的辈分置于高处,最后又说到“……孙文是我老同行……黄兴是我旧门生……”,表现出其自欺欺人,自我陶醉的一面。
《牛皮王》通过记述在一枝香晚餐时听到的“牛皮王”的言语,塑造了一个虚伪、滑稽的“吹牛皮”的人物形象,借由“牛皮王”之口,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唯利是图、趋炎附势、官员腐败等不良现象。作者以滑稽的口吻,“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3],在闹剧式的场景中,把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加以集中,把各类不良现象揭露出来。
以上《民权素》刊载蒋箸超的三篇小说,兼用文言和白话两种写作语言,以文言写情,言辞绮丽,意境幽远,悱恻动人;以白话写家庭伦理和滑稽讽刺,通俗简朴,刻画细致,达意精准。
二、《民权素》所刊蒋箸超小说叙事分析
《民权素》“说海”栏刊载的蒋箸超的三篇小说,表现出新旧夹杂的特殊时代样态,最明显的体现在其文白兼用的叙事语言与新旧杂陈的叙事模式。
(一)文白兼用的叙事语言
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从文言到白话不是一条界限分明的道路,在由文言而白话的进程中,民初即是一个新旧杂陈的时代。经统计,《民权素》“说海”刊载小说共计134篇,其中,文言小说120篇,占小说总量的89.55%;白话小说14篇,占小说总量的10.45%。可见,《民权素》是以刊载文言小说为主的杂志。进一步阅读可见,《满腹干戈》为“说海”中仅有的一篇白话长篇小说,虽没有连载完,但就目前所发三章看已超越短篇小说范畴。所以,蒋箸超的小说创作,在《民权素》“说海”栏作家群中是独特的,同时,其文白兼用的小说创作,也是民初小说创作所特有的现象。
在《古今小说评林》中,蒋箸超写道“欧美各国文话一致,所以其优美小说,易于普及。中国文自文,话自话,所以有些没有价值的书,而能通行社会,妇人稚子亦津津乐道之”,而那些极有价值之书,文人“朝订夕考”,使小说晦涩难懂,难以普及,同时也贻害社会。“吾愿有改良之责者,于文话间加商酌也”[4],可见,蒋箸超意识到了中国古典小说中“言文分离”的弊端,并主张“言文合一”。可以说,蒋箸超对于使用白话写作的态度是积极接受的,甚至是主动选择使用白话进行小说写作。
虽然,蒋箸超主张用白话创作小说来影响世道人心,但其大部分的作品依旧使用文言,除小说《白骨散》外,《民权素》名著、诗话、谐薮、剧趣、碎玉等栏目所刊载的蒋箸超作品,亦为文言作品。整体而言,《民权素》多刊登文言作品,蒋箸超作为该杂志的主编,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他在吸收西方文学影响下,用旧有文学形式适应新时代的努力。
(二)新旧杂陈的叙事模式
蒋箸超主张“作小说之责任,不在存古而在辟新”。在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创新意识,但民初旧体文学创作勃兴的大潮中,以其为一代表的那批进行旧体文学创作的作家不可能割裂传统的给养,进而使其创作表现出新旧杂陈的特征。
“才子佳人”的言情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源远流长。“郎才女貌,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代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包办式婚姻,而这类作品惯用的“大团圆”式的结局也迎合了民众的追求圆满的心理。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才子与佳人的形象必得是“才貌双全”。
《白骨散》中的笈云符合“才子”的特征。他才华出众,“年弱冠,以诗文噪于郡,执行之有女者,争婿之”,而又多愁善感,“时而短叹,时而长吁,时而自言自语”,且“诗文多郁气”。笈云同传统的才子有相同的经历,即科场不顺,未得考取功名。颉昭亦是“佳人”,“举止倜傥潇洒,既不近浊,又不近拘”,不似传统小说中娇滴滴的大家闺秀形象,然“红粉队中,豪迈无匹”,且颉昭饱读诗书,“其书金石不啻”,亦可称得上“佳人”之名。相貌和诗文是才子佳人双方一见钟情的基础,笈云与颉昭两人前有书信相通,见面后“笈云此时,微颇有君子好逑之意”,相互之间的“怜才”之念,是才子佳人模式的典型故事情节。
纵观《白骨散》全篇,亦未脱才子佳人小说的“三段式”模式,即第一部分写两人一见钟情,吟咏唱和;第二部分写因缘阻隔,但二人矢志不移;第三部分写金榜题名,终得团圆。《白骨散》中笈云虽没有取得功名,但也是“抱得美人归”,故事大团圆结局。
本篇文章以骈散结合的文言写成,恋爱中,两人亦是以诗词传情。诗词的加入为小说增添风韵,有利于渲染氛围和刻画人物性格。在笈云与颉昭的相处中,二人始终恪守礼教,讲究名节,发乎情而止乎礼,有明显的纯情倾向。故事的最后,笈云与颉昭颠沛流离后回到江南老家,王氏之女遵照婚约与颉昭同嫁笈云。“大团圆”结局,体现了传统“才子佳人”言情模式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大都采用全知全能视角,以说书人的口吻掌控全篇,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但又与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叙事角度的优点是自由灵活,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故事,剖析众多人物的特征。但由于叙述者的过多介入,总是打断故事情节,现身说法评论故事中人物的行为,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作品的和谐统一。蒋箸超的作品《满腹干戈》就是采用这一叙述形式,作者以说书人的口吻讲述杨家的故事,并从自己的角度,对杨氏夫妇的做法给出评价,并给读者提出建议,破坏了故事叙述的完整性。
自晚清开始,小说家受西方小说影响,开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变化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变中起到先导与桥梁的作用。如吴趼人的小说《九命奇冤》就比较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胡适对此评价很高,称其为“在技术方面要算最完备的一部小说”[5]。《白骨散》即以限知叙事为主。小说以“予”的口吻叙述,讲述“予契友”(4)《民权素》第九集“名著”中有蒋箸超作品《与笈云书》,可见笈云确有其人,然《白骨散》中故事是否真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故事。吴趼人和鸯鸳蝴蝶派作家以第一人称创作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传统叙事形式形成冲击。《白骨散》中“予”仅出现在小序和第一章中,之后五章叙述者隐在故事中,在文章即将结尾处,又出现“以予所见”,作者又现身从自己的角度对事件展开评论,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叙述模式。小说《牛皮王》中开篇直接记叙“牛皮王”话语,以“我”为叙述的主体,通过自述的方式反映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话本式叙述。但中途又以说书人口吻出现,连贯全篇,保留了话本小说的叙述模式。
蒋箸超的三篇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全知全能叙事,已经产生了转变叙述视角的意识,但传统写作的根深蒂固也使他的超越带有不彻底性和妥协性,超越的同时还在固守传统,体现了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过程中的曲折。
三、《民权素》所刊蒋箸超小说叙事面向
“小说之关系于人心,关系于世道者,良非浅鲜[4]116”。晚清兴起的“小说界革命”,以小说改良社会为创作宗旨,其实揉合了中国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文学观念,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民初小说家虽然在实践中意识到“小说界革命”夸大了小说的作用,但是受其影响已形成思维定式,而且,以小说为职业,也使职业作家们舍不得丢掉“小说界革命”所确立的小说的价值。李涵秋对其弟李镜安说:“我辈手无斧柯,虽不能澄清国政,然有一枝笔在,亦可以改良社会,唤醒人民”[6]。由此,民初小说家的创作,都或多或少带有改良社会的责任意识。《民权素》所刊载的蒋箸超的三篇小说,体现了其“褒贬善恶,移风易俗”的小说创作观念。
(一)游戏消闲追求真情
辛亥革命后,人们还来不及兴奋,就已经进入一个更为令人沮丧的时期,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整个国家陷于混乱和动荡中。中国文人自古谙熟“以哀时嫉俗之志,托之香草美人”的隐喻手法。民初小说作家依然按照古代文人的既定思路,将自己生不逢时、郁不得志的哀怨,寄托于小说创作之中,一时间,哀情、苦情、孽情、怨情等小说汗牛充栋。
《白骨散》所写笈云与颉昭之爱情,乃经历一番坎坷才得以修成正果,书写出一种“毕生不渝其志,历变不毁其盟”的美好爱情状态。言情之作,关于青年男女,“下笔能慎,不着苟且,足以激发国人之情爱,保家保国”。作为小说家,不论采取自叙体或是他叙体,不论写何种爱情,“总以正式婚姻为合格,庶不致以偷香窃玉四字,令世上无赖少年,有所模样而扬扬得意也”,蒋箸超所写言情,旨在给青年男女塑造正确的爱情榜样,“如其不慎,则大者演为桑间濮上,小者养成痴女怨男,家国二字,将无所付托,流毒社会,甚于洪水猛兽”[4]131。可见,蒋箸超将言情小说当作激发国人情爱的手段,推崇“正式婚姻”,并认为以此可以“保家保国”。
《白骨散》中,笈云与颉昭因笈云的才华而互生情愫,笈云不愿服从家庭的包办婚姻,毅然前往京城投奔某公,与颉昭相恋,后义和拳作乱,颉昭失去父母,笈云不离不弃。笈云与颉昭的爱情,本是一曲自由婚姻的恋歌,然而,两人爱情的结局,是颉昭与王氏之女同嫁笈云。可见,蒋箸超所认为的“正式婚姻”,依旧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的“明媒正娶制度”,其婚姻思想虽有进步之处,仍未脱传统束缚。在《白骨散》中,笈云的父母是脱胎于传统家庭的形象,如笈云父母渐衰老,为子嗣着急,便“隐其子而为之论婚”,笈云以病拖婚期,“其父懊伤致疾,阅三月而长逝”。蒋箸超生长于传统家庭,虽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然其写作的内容与传达的思想,仍是传统观念。
《白骨散》是一篇蒋箸超用文言写成的言情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虽然笈云与颉昭爱情的开始,脱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制约,带有一定的婚姻自由意识,但其二人的结局又回到了传统的婚姻制度,满足民众对于“大团圆”婚姻结局的需求,也体现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蒋箸超的影响。
(二)亦庄亦谐维持风化
蒋箸超是1912年以后倡导文学“警世”作用较为用力的一位[7],在1919年出版的《古今小说评林》中,他依然申明“小说之主脑,在启发智识而维持风化。启发智识犹易事也,维持风化,则难乎其难,是非有确切之伦理小说,足以感动人心,而使愚夫愚妇,皆激发天良不可”。以“维持风化”为旨的伦理小说有“难乎其难”之处,即“措笔偏于庄重,则如城隍庙之皂隶,令见者望而却走,虽口口圣贤,句句经传,自以谓阐发无遗,于世道无小补也。偏于烘染,则失之油滑,必贻吃荤念佛之讥,而阅者亦无可注意。是标为伦理,而与不伦不理一类也”。[4]141-142.涉及“伦理”的“庄”的内容成为小说走向市场的障碍。因而,尽管当时的小说杂志大多创刊时就有“庄”的告白,但在具体实践中是很难走通的,不得已转而偏重于“谐”。
蒋箸超认为,“小说与教育,实有无形关系”,《满腹干戈》是“说海”栏中仅有的一篇白话长篇小说,作者用话本式语句,讲述会稽杨家由盛而衰的故事,“如今在下把一件故事,讲给列位听听,凡是为父母的,也该留点神,不要当作耳边风罢”。可见,其创作意图即为启发“愚夫愚妇”注重对子女的教育,突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发挥小说的教育功能。“盖作小说者,其心中固有一维持风化之成见在焉”。蒋箸超通过讲述杨家夫妇对子女的教育不当,造成家门衰落的结局,警示为父母的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三)滑稽讽刺批评时弊
清末民初,政局动荡,生活于商业都市的市民读者,厌倦了政治的多变与生活的严峻。滑稽小说中的轻松诙谐抚慰着那个喧嚣与动荡时代人们的心灵,麻醉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绝望与焦虑。作家借滑稽轻松的小说,寓讽于滑稽,将滑稽与讽刺融为一炉,暴露社会丑闻,将种种“怪现象”作为可笑的话柄,使滑稽不只是干瘪的调笑,而企图向人性的深处开掘。虽然此时间的滑稽短篇小说风格单一,形式单调,讽刺还没成为自觉意识,但是滑稽小说中蕴含讽刺意味已经初显锋芒。
滑稽短篇也是民初最具代表性的小说类型。《民权素》“说海”栏刊载的白话小说也以滑稽短篇为主,14篇白话小说中,13篇为“滑稽短篇”,体现了《民权素》滑稽、消闲的刊物定位。滑稽短篇小说多以浅显的语言、滑稽的风格、讽刺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也是《民权素》“说海”栏每集固定刊载的小说类型。
《牛皮王》中,作者借牛皮王之口,反映社会上存在的唯利是图、趋炎附势、买官腐败的现象,以滑稽的表现手法予以讽刺,这也是滑稽短篇小说普遍存在的价值。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密切,使得小说创作承担了更多个人思想与价值倾向。小说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力图通过小说影响社会,教育民众,而滑稽短篇的形式最易为民众所接受而为作家们喜爱。
《民权素》上承革命报刊《民权报》,虽言论较之更为平和,也以“文章的、美术的、滑稽的空前之杂志”作为刊物定位。可见,其追求纯文学的倾向,但是以蒋箸超为首的《民权素》作家群,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和影响,仍以小说为传声筒来关照社会。“说海”中蒋箸超的三篇小说,以游戏消闲的心态讲述世间真情,以亦庄亦谐的故事讲述希望维持社会风化,又以滑稽讽刺的笔调指擿时弊,体现出蒋氏以小说改良世道人心的创作主张;形式新旧杂陈,既有师法西方小说的叙事形式,又保留了传统小说的样态,兼用文言和白话两种写作语言,体现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中的曲折性,是中国文学转型中不可忽视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