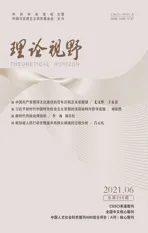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借鉴中共群众路线的过程分析
2021-12-28吕元礼
■吕元礼
【提 要】受到新中国成就的感召和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或潜或显的影响,1954年成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将“人民”一词融入党名,并将其名解读为“为人民而行动的政党”。建党之初,为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这一共同的敌人,党内“非共派”和“亲共派”走到一起,前者也向后者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执政之后的人民行动党将从中共借鉴而来的群众路线与国会制度相结合,并将群众路线制度化为国会议员挨家沿户走访选民和定期接见选民。议员走访和接见选民的做法在新加坡风雨无阻地坚持了数十年,是因为“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
引言
从历史渊源来考察,笔者认为:新加坡模式≈英国的制度+东方的传统+当年“共产党人”的作风。“改装”英国的制度,新加坡大体延续了英国的议会民主,表现出渐进发展的由民作主;继承东方的传统,新加坡政府抱持家长式情怀,表现出择善固执的为民作主;效仿当年“共产党人”的作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表现出着力坚持的认民作主。认民作主就是认人民为自己的主人。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即“百姓是天,人民最大”。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理念既可以在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根据,也可以从来源于本土的儒家孟子学说中找到源头。孟子引用并赞同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就是将民与天等同起来,即百姓是天;孟子提出并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就是把民的地位放在第一位,即人民最大。怀抱上述理念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并具体表现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无独有偶,人民行动党也在工作中强调“以民为中心”或“以人民为先”,并在将自己的党名解读为“为人民而行动的政党”的同时,倡导和践行“来自于群众,又回到群众”以及“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解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借鉴中共群众路线的过程,可以反过来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借鉴的背景:新中国成就的感召和共产党人民观的影响
人民行动党建党乃至执政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成就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海外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感召力。李光耀说:“除了40岁以上的人,所有华人都为毛泽东政府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一个政府能在五年内革除贪污腐败,使它顶得住美国人在朝鲜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称颂的。”[1]据人民行动党老党员马库斯回忆,留学过英国并受到其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李光耀等人,原本是想创建一个取名为新加坡民主阵线的政党。可是,马库斯从英国回到新加坡,发现先其一步回来的李光耀等人,已经将自己创建的政党取名为人民行动党。马库斯批评说,这个名字带有共产党的味道。身为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李光耀回应说,还是满足一下华文中学学生运动的口味好些。对于讲华语的社群来说,人民行动党的党名更有号召力。的确,“在那个革命的岁月,‘人民’这个词在华人群众当中确实容易产生共鸣。他们深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和人民解放军展示的力量所鼓舞,所以,‘人民行动党’能引起更深层的情感共鸣,意味着这是一个为人民而行动的政党”[2]。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和“人民解放军”的军名都包含“人民”二字。“人民”,这一被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的理念,就这样烙在了人民行动党的党名之中。
不过,人民行动党首任主席杜进才否认马库斯有关党名来源的上述说法。他说,党名中的“行动”一词,是从领导本地公务员争取自己权益的联合行动理事会的名称中获得灵感。党的行动要能取得成功,就必须发动群众,因此,就在行动之前增加了“人民”一词,并终于有了“人民行动党”这一名称。杜进才的说法看似与马库斯不同,其实并不相互矛盾,反而可以互相印证。人民行动党党报《行动周刊》刊登的《建立正确的人民观》一文指出,正确的人民观“就是把广大人民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他以最真诚的爱,来爱护人民,以实际的行动去解除人民的苦难,甚至于他认为,心身是属于人民的,为了人民,自愿牺牲个人的一切。总之,他不以自己的荣誉名利为出发点,他只以广大人民的苦难幸福为前提”[3]。
一位华文教育出身的人民行动党前议员告诉笔者,人民行动党曾认真向当年“共产党人”学习,并受到当年“共产党人”影响。重温该党上述言论,我们似乎听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语言,感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脉动。可以这样推论,就人民行动党的起名而言,共产党的影响也许没有进入起名者的显意识,但必定进入了他们的潜意识。换句话说,正是高举人民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上述议员所说的当年“共产党人”,让“人民”的理念广为普及,深入人心,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们才会这样自然而然地想到“人民”一词,进而毫无疑义地将它用在党名之中。
二、借鉴的途径:“非共派”与“亲共派”结合和前者向后者学习
人民行动党建党之初,党内乃至新加坡社会存在着倾向于运用激进方法和温和方法改变现状的两股力量。前者多为受华文教育者,代表人物有林清祥、方水双等人,并被李光耀称为“亲共派”;后者多为受英文教育者,代表人物有李光耀、杜进才等人,并被李光耀称为“非共派”。顾名思义,“亲共派”当然亲近共产党。他们阅读中国革命(乃至红色苏联)读物和毛泽东著作,并向李光耀热心推荐甚至具体指导他读这些书籍,其思想行为表现出与共产党人十分相似的一面。由于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将共产党定为非法组织,“亲共派”人士固然多半没有在组织上“入党”,却又往往已经在思想上“入党”。李光耀认为,这些“亲共派”人士与马来亚共产党具有很多联系,甚至在关键问题上听命于马来亚共产党。正因为如此,李光耀有时也将“亲共派”人士笼统地称作“共产党人”。
与“亲共派”相对而言的是“非共派”。李光耀曾将自己的建党目的表述为“建立一个民主、非共和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事业”。所谓“马来亚事业”,就是早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独立的马来亚。所谓“非共”,固然与“亲共”相对,也与“反共”不同;其意为“不是共产主义”,而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按照李光耀的说法,建党之初的“人民行动党基本上是革命者的运动,而不是改良主义者的运动”[4]。这个“革命”,就是逐出外国统治者,主要是欧洲统治者。正是为了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个近期目标,最终目标并不相同的“非共派”与“亲共派”走到了一起。
李光耀将当时两派的关系形容为“共生互利”的关系。首先,没有“亲共派”的支持,“非共派”就难能让党组织拥有群众基础并得到民众支持,该党要在一人一票的大选中获得胜利也就非常困难。“亲共派”加强了人民行动党的群众基础,可以从20世纪50年代亲共的华校生对该党的支持得到印证:在当年的政治竞选中,“华文中学的学生会在群众大会上手拉手唱着歌,为行动党候选人打气。热情高涨绑着两条辫子的女生,甚至在选民躲进厕所时,也敲门嚷嚷:‘请投行动党!’直到对方回应才肯罢休。她们也会蹲在洗衣服的妇女旁边,先问候再劝请他们支持行动党。”当党工沿户家访时,“她们会先和居民打交道,然后才让男生进行竞选宣传。在那段竞选期间,很多学生都旷课,他们就那样穿着校服上街游说居民投票给行动党。为什么他们都支持行动党?根据前学生领袖孙罗文的说法,马来亚共产党曾表示应该支持人民行动党,因为他们被视为最进步的参选政党”[5]。
其次,没有“非共派”的掩护,“亲共派”就容易让党组织凸显共产党色彩,党组织也难以获得当局批准而成立,更难能面对以英文作为官方语言的立法议院、政府部门和法庭,并进而施加影响和发挥作用。据说,当注册当局收到人民行动党的注册申请书后,就发信给以对付共产党为职责的政治部,询问该党是否有“不良记录”。在得到政治部“没有理由不批准”的回复后,注册当局才批准了人民行动党的注册申请。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党的领袖意识到政治部一定会派人来监视,便与暗探开起玩笑,故意在台上放了一张桌子,上写“刑事侦查政治部办事处”。会议开始前,李光耀用幽默的语气开口邀请政治部官员上台就坐。可惜,台下没人回应。[6]为了避免抵触法律,建党大会的组织者没有让那些有共产党嫌疑的人进场。同样的理由,已在政治部监视名单上的“亲共派”领袖林清祥,也没有登上讲台并发言,而是和其他听众一起坐在台下。
人民行动党建党之初的党内“亲共派”与“非共派”既相互联合,又相互斗争。李光耀说,自己在应对“共产党人”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共派”人士既防共,也仿共。据说,李光耀甚至说过大意如下的话:要战胜左派,必须比左派更左;要战胜共产党,必须比共产党更像共产党。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共产党人善于领导工人向资本家的剥削作斗争。据有关文献透露,曾经在某个时段(大约是行动党执政之初),为了赢得人心和下次大选,由“非共派”主导的人民行动党发动、支持的罢工次数,甚至比“亲共派”脱党后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发动、支持的罢工次数都要多些。
三、借鉴的内容:服务群众的观念和联系群众的方法
李光耀等“非共派”人士向“亲共派”学来的当年“共产党人”的作风,主要是根源于群众路线的精神观念和方式方法。首先,“非共派”对“亲共派”人士服务群众的精神观念深表敬意并加以学习。李光耀曾这样描述“亲共派”领导干部为民众献身的精神:林清祥和方水等人整天东奔西跑,发表演说,同刻薄的雇主进行谈判,晚上就在工会总部的桌子上睡觉。“他们穿着朴素,三餐在小贩摊位解决,所得的薪水很少,因为他们向资方争取到的一切都归工人了。我可不知道他们挪用多少钱来供养更多的革命分子,但我却没看过他们私下拿过一分一毫,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上可以肯定这一点。”“亲共派”所过的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对追随者产生莫大的影响。“大家竞相模仿,互相激励,以显示同样的自我克制精神。就连家境富有的年轻学生,虽然不是这个工会组织的核心分子,也愿意跟林清祥、方水双打成一片。有个巴士公司老板的儿子,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替他们当义务司机,用的是他家的汽车。这就是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他为能跟这些革命干部交往而自豪。”[7]相比之下,当年的“非共派”人士较为缺乏上述感染力,要寻找协助自己工作的人员也困难得多。当时,李光耀等人从工会和朋友当中吸收志愿人士。但是,他们都要准备回家用餐,要参加社交集会或赴私人约会,完全没有“亲共派”的追随者那种承担义务和献身事业的精神。“亲共派”的追随者们一个人就能承担“非共派”三、四个志愿人士的工作。
其次,“非共派”非常佩服“亲共派”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并加以学习。“亲共派”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主要表现为组织、发动群众等方面。李光耀曾用羡慕的口气描述过亲共的华校生们的组织纪律性:“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里,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男孩和女孩通过扬声器发出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8]“亲共派”领袖林清祥的华语演讲富有号召力:“听众有4万人,几乎人人都给林清祥的精彩万分的演说所迷住了。他打趣地说:‘英国人说,你们不能自力更生,你们要证明给他们看,你们是有能力靠自己站起来的!’就这样,4万人刷地站起来——全部闪烁着汗珠,无数个拳头在空中挥舞着,大家齐声高呼:‘默迪卡(意为‘独立’)!’”[9]
佩服的同时,当然是学习。“非共派”骨干吴庆瑞曾将“亲共派”称作组织和发动群众的魔术师。他说:“作为魔术师的学徒,我们站在有利的地点,从那里观察到大师精湛的表演,因而从广大的观众群众,引发出阵阵如雷震耳的喝彩和掌声。我们不止一次告诉自己:‘啊,原来这就是怎么做的!’”[10]以组织群众为例,李光耀总结说,自己从同“共产党人”的交手中认识到,选民的总体情绪固然重要,关键更在于争取民众支持的机制和组织网络。当年,他到“共产党人”的地盘访问时,往往遭到当地居民的冷落。选区的主要人物,包括工会领袖以及零售商或小贩工会、宗乡会馆、校友会等等的理事,全被共产党干部编织到同一个网络中,使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一支稳操胜券的队伍。碰上这样的对手,不管自己在竞选期间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终无法取得显著的进展。他们牢牢控制着基层。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年复一年地在大选与大选之间,坚持不懈地在同一基层下苦功。[11]
以发动群众为例,李光耀认为,“亲共派”善于“操纵”群众大会。每当演讲者在大会上讲到核心观点时,带头喝彩的人都会指挥群众长时间鼓掌。他说,自己起初不了解这点,以为鼓掌都是自发的。但是,当他不断出席群众大会之后,逐渐了解这些带头喝彩的人总是分散在群众当中。此外,他们还有个头头,其他人都得听他指挥。其他人自己也有三四十个下属,都跟着他鼓掌,从而引发四周群众鼓掌。李光耀指出,“亲共”的华校生们组织、发动群众能力的培养,甚至贯穿到游戏之中。“我看过他们在野餐会上‘抓领袖’的游戏:二三十个学生围成圆圈,人人都摸鼻子、拉耳朵或拉衣袖,目的是要抓领袖者认出带头改变信号,使其他学生也立即跟着改变信号的人,队员合作的话,领袖不是那么容易被抓到的。”[12]一位当年的华校生后来指出,这些游戏纯属娱乐性质,并没有政治目的。的确,就“抓领袖”游戏而言,做者可能无意,看者却是有心。正因为如此,李光耀这位“有心人”才能从当年“共产党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四、借鉴的创新:议员挨家沿户走访选民和定期接见选民
新加坡国会议员(包括朝野政党议员)必须在平日间以及竞选期间到所属选区挨街沿户地走访选民。一般来说,议员在两次大选之间的四、五年间,前两年必须挨家沿户地将本选区走一遍,后两年又要挨家沿户地将本选区走一遍,大选前夕的竞选期间又要突击性地挨家沿户地将本选区走一遍。竞选期间大约9天的突击性走访,议员每天大概要挨家沿户走访数百户乃至上千户人家;平日里的例行性走访,议员每周大概要挨家沿户走访数十户乃至上百户人家。竞选期间的突击性走访,主要是握手拉票,用人民行动党某议员的话说,叫“见面三分情”;平日里的例行性走访,如选民家里有人,议员就会进家问候并顺便解决问题;如家里没人,议员则会留下自我介绍的卡片。所有走访,都会有基层领袖和义工的陪伴和协助。
议员挨街沿户走访有助于与民众建立联系,也可以发现并解决问题。行动党议员任梓铭接到不少邻里投诉,往往涉事双方虽是邻居却互不认识。其实,只要他们肯踏出第一步和对方做朋友,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某次走访选民时,有居民申诉楼上邻居晾衣时滴水。任梓铭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发现,楼上住着一名老人家,由于没力气拧干衣服,所晾衣服才会滴水。于是,任梓铭又转过头来向楼下住户解释。听完解释,原本抱怨的楼下居民不但表示谅解,有时还上楼帮老人家拧干衣服。[13]为了鼓励居民多认识左邻右舍,主管坎贝拉分区的行动党议员林伟杰曾带头把居民委员会定期主办的聚餐活动从组屋楼下带到组屋的各个楼层。作为基层组织之一的公民咨询委员会除了承担聚餐费用,还会给参加聚餐的居民拍摄团体照、整理居民联络电话。每户居民只要缴交5元象征性报名费,就能带全家一起来与邻居聚餐,同时还可获赠镶好的照片和联络名单。坎贝拉分区内约有八十多座组屋。有兴趣参加这种“楼层派对”(floor party)的居民可以联络他们的居委会。只要他们那一层楼有八成居民愿意参加,基层就会着手为他们策划聚餐。林伟杰议员与基层组织计划在大约半年内主办100场这样的聚餐。该区公民咨询委员会将拨款大约3万元支持这项活动。[14]
新加坡国会议员(包括朝野政党议员)也必须每周一次在固定地点接见选民。新加坡居民住房按价格从高到低大体区分为私人别墅、公寓(商品房)和组屋(政府为民众所建公共住屋)。80%以上的居民都住在组屋。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也就毫无例外地设在最接地气也最有人气的组屋区。新加坡组屋底层一律空着,从而为居民提供了较为空阔的休闲、社交乃至婚丧嫁娶等活动的场所。组屋底层空地砌上几间房间,就成为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资助的人民行动党幼儿园所在地。白天,小朋友在人民行动党幼儿园上学;晚上,人民行动党议员就在幼儿园里接见选民。一位人民行动党议员说,其秉持的理念是“我们从人民中来,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续不断地为人民服务”。
选民有困难找议员,议员就会写信给相关部门,请求协助解决。普通议员需要处理鸡毛蒜皮的民众日常琐事,已经司空见惯;担任更高职务的部长、总理还要处理抓猫、救狗之类的事情,也在情理之中。在2011年国庆群众大会的讲话中,李显龙总理在重提“部长抓猫”的旧事之后,又亲口讲述了一则“总理救狗”的如下新闻:李显龙在自己服务的德义区接见选民时,曾为回应一位居民的要求而不得不亲自处理一件救狗的事。原来,这位居民偶然碰见一只野狗,非常喜欢,但又没办法领养。后来,这只狗被当局抓走了。按照有关规定,三天之内如果找不到狗主,这只狗将会被人道毁灭。于是,这位居民马上展开救狗行动,要求李显龙帮助她,希望当局多给这只狗几天时间,救救它的命。李显龙听说之后,也心生同情,便写信给相关部门请求救助。幸好,这只狗及时被人领养,“总理救狗”的行动也因此大告成功。[15]
人民行动党强调政策的制定既可以由上至下,也可以由下至上。议员接访选民就有利于开通由下至上的渠道。普通党员能够指清道明人民关心的课题和政策带来的冲击,而党中央则根据他们反映的意见思考分析,进行决策。例如,如果人力部长说失业率已经下降,但帮助议员接见选民的普通党员却提出在接见选民时还有人来要求帮忙找工作。这说明就业机会虽然增多,但人们对工作感到不满意。于是,政府就出台就业奖励花红,鼓励人们积极找工作,甚至接受较低的薪金。
结语
“改装”英国的议会民主、继承东方的家长式情怀和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新加坡模式就有了渐进发展的由民作主、择善固执的为民作主和着力坚持的认民作主。三者并不对立对抗,而是相辅相成。人民行动党在遵循议会民主和借鉴群众路线的同时,又强调政府必须做正确的事,即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的事情,即便有民众一时不理解、不喜欢,政府也要择善固执地坚决去做。换句话说,没有为民作主的精神作依靠,由民作主就容易滑落为民粹主义,认民作主也难免变质为做群众的尾巴。中国记者曾询问议员接访选民的做法为什么能够风雨无阻地坚持数十年?李显龙回答说:“选票掌握在选民手中,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16]这就是说,没有由民作主的制度作保障,为民作主就难免沦落为作民之主,认民作主也容易蜕变成认民作子。当然,由民作主的具体方式又必须与本国国情相适应。
注释
[1][7][12]《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第292页;第220页。
[2][5][6]叶添博、林耀辉、梁荣锦:《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秘辛》(中文版),新加坡报业控股2013年版,第40页;第65~66页;第51页。
[3]【新加坡】孙红鸥:《建立正确的人民观》,《行动周刊》1959年第7期。
[4]【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0页。
[8]《李光耀传记之二:骑在虎背上》,联邦出版社、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9]《林清祥与他的时代》,朝花企业、社会分析学会2002年版,第105~106页。
[10]陈淑珊:《吴庆瑞传略》,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版,第76页。
[11]《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13]沈斯涵:《任梓铭把投诉变体谅》,《联合晚报》2012年5月12日。
[14]《坎贝拉分区“楼层派对”帮助居民消除隔膜》,《联合早报》2007年9月17日。
[15]《部长捉猫 总理救狗……》,《联合早报》2011年8月15日。
[16]母发荣、郭芳:《李显龙: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选票》,《南方日报》2008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