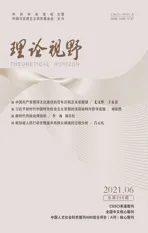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断”几个争议的辨析*
2021-12-28熊晓琳孙希芳
■熊晓琳 孙希芳
【提 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断”论述和预言了资本扩张后的发展结局,却未明确指出解决办法,因此,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争鸣不断。事实上,“机器论片断”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论述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我们必须结合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准确把握生产性劳动界定、总体工人概念以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理解;加速主义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上并未给出明确策略,自治主义对“机器论片断”的理解过分主观和政治化,寄希望于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本变革就自动生发出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人工智能等自动化的机器体系迅速发展给传统工人阶级带来极大冲击,但无法阻挡资产阶级消亡的最终命运。
1857年7月至1858年10月,马克思完成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1],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它一共包括4个手稿,分别写在8个笔记本上,其中第3个手稿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由于第一次以德文发表时被编者加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标题,从此它就以《大纲》闻名于世。其中第6本笔记本第43页到第7本笔记本第5页的内容,就是“机器论片断”[2]。它对应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8~110页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771~791页的《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章节内容。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机器论片断”争鸣不断。
一、“机器论片断”的出现违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吗?
随着资本在全球市场不断开拓,自动化机器、人工智能等科技因素和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非物质劳动等知识要素在生产中越来越发挥出无可比拟的效能,第三产业在社会中的发展越来越呈现相对上升势头,以及资本所有者依据分配制度取得的非劳动收入等经济现象,使得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看似发生了冲突。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要在马克思的语境下看待“机器论片断”,不能夸大其文本意义,更不能把它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理论支撑点。至于“非物质劳动”过程中资本吸纳数字技术、机器操作等方式的现象,可以沿袭马克思对经济学体系建构为主的理论叙述方法来面对。他提出:“重新去思考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活劳动,以及创造性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3]在未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非物质的创造性劳动如网络虚拟平台的源代码编程和创新设计等,也成为劳动的原创性起点。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可取的”[4],因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价值定义上背离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在价值产生的源泉上背离社会物质财富和生产力发展源泉的多因素互动论,在决定交换价值的环节上背离市场机制运行规律。该观点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只适应于简单商品经济和物物交换,已经不适应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不适用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认为,机器的对象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比如人工智能代替了部分体力劳动,甚至脑力劳动,人类的活劳动不再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还有学者认为“价值是劳动整体创造的”[5],现代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马克思重塑劳动价值论的时代,那时,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在全部社会劳动中比重极大。随着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服务在生产中发挥的增效作用,服务业的发展比例也日渐上升,非物质生产劳动作为整体劳动的一部分,也能创造价值。无论是学者们认为需要重新思考剩余价值的来源,还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抑或是认为整体劳动创造了价值,都说明以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是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辐射的时代;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确实存在有待厘清的细节。
科学的理论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表现,理应经由反映时代性的批判获得继承和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在继承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马克思论证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包括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其中,在特定形式下的劳动被称为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无差别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抽象化就是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断探索,他在揭示商品二因素创立劳动二重性理论后,又实现从劳动到劳动力商品的转变,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革命。他还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诠释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马克思重视生产力资源和技术变化在生产中的作用,他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6]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也强调机器在劳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7]对比机器,工人活劳动的地位和作用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8]。实际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小商品经济,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马克思终其一生为探索资本主义的本质及社会发展规律,他在“天才地”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为人类指明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方向。对于对象化劳动也能创造价值和价值是由自动化机器、原材料等物化劳动和工人的活劳动共同创造的结果的说法,固然有其现实意义,但不能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也能创造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只是把自身使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剩余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仍然是工人的活劳动。但财富的创造,确实需要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互相配合才能产生。马克思在《大纲》中富有预见地指出:“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所使用的劳动能力。”[9]可见,“机器论片断”中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论述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诚然,马克思在《大纲》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还不够彻底,尤其是对劳动二重性和相对剩余价值没能充分把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生产所涉及的技术问题有了更成熟的理解,尤其资本如何借助科学助力自身发展问题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而这些,都与他试图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辩证发展达到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目标的思考进路一脉相承。
总之,我们在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解时必须结合实践新情况,准确把握生产性劳动界定、总体工人概念以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理解。生产性劳动是作为劳动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体现,一方面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反映生产关系。判断劳动是否是生产性的,并非以劳动产品的物质或服务形式为判断依据,关键看能否使资本增殖。在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下,社会生产根本目标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确实需要对生产性劳动做出符合时代情景的界定。总体工人不仅包括生产工人、管理人员,还包括产品研发等科研技术人员。虽然他们的直接劳动产品不是物质形态,但他们提供的高新技术在生产体系中组合形成的生产自动化一旦融入总体工人的劳动就能够创造价值。科研技术人员提供的复杂劳动是总体工人劳动的一部分,同等时间下创造的价值比简单劳动多,在价值分配上毋庸置疑地要体现分配差异。科学技术本身如果不与科研技术人员的劳动结合就不能产生价值,它只是创造价值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但作为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的桥梁,科学技术可以扩大劳动对象,提升劳动者劳动效率,创造更多使用价值和价值。
二、“机器论片断”是“圣经式”文本吗?
近几年来,国外学者尤其当代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机器论片断”关注日益加深,其中,加速主义和自治主义甚至把“机器论片断”视为“圣经式”文本。他们都把“一般智力”和“非物质劳动”问题连接在一起关注和思考,其中“一般智力”就是指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人类的一般能力以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形式出现。“非物质劳动”就是对象化在机器中的智力劳动。
左翼加速主义者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提出,资本无法触及的技术领域本身就具有革命性的力量[10],主张摒弃资本主义各自为战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不影响目前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情况下,重建全球主义政治。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提出,阻拦机器时代的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罪恶之源是不断加速挤压生活时间的社会状态,现代人即使赔上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难以到达理想生活的深层次原因,应归咎于科技进步、生活变迁和生活步调的加速,应该让个体调整生存节奏,使之与社会发展节奏同频共振。罗萨对技术发展加速的观点与早期加速主义者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接近,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有革命性,可以凭借技术的发展使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走得更远。20世纪末,西方加速主义开始由社会思潮转变为政治理论。英国学者尼克·兰德主张不主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认为依靠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技术、现代性和异化的非人力量,就能使资本主义走上自取灭亡的崩溃道路。[11]但即使技术加速发展,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技术飞速发展的结果未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所以,无论面对左翼加速主义还是右翼加速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或现代性体制为加速主义殉葬时,另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制度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早已预言:“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2]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十分重视机器和“一般智力”的作用:“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3]他在《大纲》中判断,“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14]。西方加速主义将其解读为:随着资本扩张式发展,工人在劳动中将会被机器取代而越来越被边缘化。西方加速主义试图基于二战后资本主义的跨越式发展尤其从泰勒制、福特制转变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变化为现实依据,在“机器论片断”中找寻理论依据。但其实马克思这段话明显在论证上是不够充分的,因为代表“一般智力”的自动化机器对活劳动的影响只涉及代表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并不影响代表抽象劳动的价值体现,也就是说“一般智力”的发展并不一定引起交换价值体系的崩溃。加速主义对“机器论片断”的重视,反映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现时代发展变化现象的敏锐觉察,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并未远离我们的时代。但他们在理论上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上也未给出明确策略。加速主义的弊端在于忽视以下关键问题:技术并不能与生产力直接画等号。技术进步在为生产力进步增加可能性的同时,也把整个资本体系、社会发展速度和人类本身卷入其中,为生产关系增加了高度复杂性。加速主义只是基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现状,试图用“机器论片断”超越马克思主义自身,并未洞察资本主义本质矛盾及危机根源。
把“机器论片断”作为“圣经式”文本的还有意大利左翼自治主义,主张工人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脱离工会和政党,他们认为工人想要的是较少工作,而不是适应工作。意大利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奈格里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第2版导言中把《大纲》界定为:“一种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凡的理论预言……,一种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与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论战的人来说的重要阅读材料。”[15]他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在生产过程中物质性的劳动比例在不断减少,而非物质劳动即智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比例在增加。因此,新的斗争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以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统治下的民众。这与英国政治学家拉尔夫·密里本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现在的工人阶级不再只是提供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范畴,根据是否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处于雇佣地位、是否完成某种生产职能等判断标准,中间阶级的新兴“白领”工人及部分专业技术人员也应纳入工人阶级的范畴。奈格里指出,在网络信息高速发展趋势下,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也有了更细致的划分:剥削式资本和抽取式资本,即直接参与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减少,但另一部分资本通过整个社会分工合作和个体生命价值中仍然能够抽取剩余价值。尽管看起来工人由于减少个体劳动时间似乎受剥削程度在减轻,但他们受到的剥削反而紧紧嵌入生活,自治主义趁此机遇希冀工人能够拒绝工作奋起实行自治。技术的进步的确使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变长,但其实每个劳动者都被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裹挟,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和对立日益模糊,几乎个人所有的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一方面明确批判科学技术作为异己的力量对工人的压榨,强调“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16],使得人被物化和物被人格化,催生了异化性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又认同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表现形式,肯定机器和工艺技术的广泛发展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马克思预言过资本的发展前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17]意大利自治主义(也叫工团主义)认为“机器论片断”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基于上述论断提出“从生产关系内部反对”的口号。自治主义把对抗资本主义的着力点放在脑力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上,寄望通过工人阶级的自主反抗产生灭亡资本主义的力量,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不变资本不仅决定了生产力,也是变革一切社会的动力。他们的论据之一就是马克思曾说过:“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18]马克思明确表示:“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19]马克思认为变革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还是基本矛盾的发展过程:“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20]自治主义用理论重新突显了工人和资本的对立,并提出工人自治的方案,借助马克思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为分析非物质劳动、知识资本主义以及凭借知识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进行无孔不入的生命政治控制的抽象统治打下了理论基础,使政治经济学朝着生命政治学方向转变。但自治主义的理论是建构在对“机器论片断”主观主义和政治化的理解上,走向“充满伦理色彩的主体政治学”[21]。自治主义错误之一在于,对工人自治抱有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期待,只能诉诸充满伦理色彩的设想。错误之二在于,对马克思“活劳动”概念的误读,把活劳动直接与主体力量画等号,不考虑个体所处社会环境和周围的社会关系,把非物质劳动直接等同于生命政治劳动。错误之三在于,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和全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建立在“一般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之上,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扭曲为技术决定论,只能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阉割。
加速主义和自治主义都把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尚未深入时的“机器论片断”文本视为圭臬,一方面说明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敏锐的捕捉,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只看到表面现象并没有深入挖掘背后的主导逻辑,寄希望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进行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就能够自动生发出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这显然陷入对“机器论片断”的唯心主义解读,注定不能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找到真正出路,只能陷入更深的资本逻辑漩涡。
三、无产阶级会成为“无用阶级”吗?
由于机器自动化的迅速发展,意大利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简史三部曲”《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中直接明了地提出,人工智能将使无产阶级成为“无用阶级”。赫拉利从描述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入手,突出人类无论在身体机能还是认知能力上都逊于人工智能。在未来职业发展中,无论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还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群体,都可能被人工智能的算法取代。他阐述了AI人工智能由不公平算法导致的政治意义,最后得出颇为震撼人心的结论:被人工智能挤出就业市场的这批人,既“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22]。他们的结局要么是吸毒成瘾的药物依赖,要么就是游戏成瘾的网络依赖,最终成为“无用阶级”。赫拉利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人类必须开始思考自己究竟希望得到什么,即使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前进方向。赫拉利的“简史三部曲”形象地描绘了由技术进步引发的新一轮失业浪潮和社会阶层分化,其论述颇吸引眼球但又具有极强的误导性。传到国内以后,形成了一股新的历史虚无主义冲击,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民间甚至学术界的思想震撼,需要予以客观的评析。
从社会历史发展看,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400年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所引发的机器对工人阶级的排斥一直在资本主义社会广泛存在。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23]从18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开始,机器作为固定资产的重要部分,它的发明和由此建立的新产业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关键。19世纪60年代,电气时代来临,旧的蒸汽机被新的发电机取代。20世纪中叶,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这是一场涉及多领域的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而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量子通信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疾速而来。之所以目前看起来人工智能对无产阶级的排斥胜于以往任何时代,说到底还是源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汲取理论启发,无疑是获得思想启迪的好办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曾经极富预见性地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4],“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5]。其中,“两个必然”指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向和趋势,资产阶级必将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而消失,资本主义制度也必将终结。无论人工智能等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如何为资本主义赢得生存空间、缓解其灭亡速度,终究难以跨越无产阶级作为“掘墓人”将其葬送的历史命运。“两个决不会”则预示了这种斗争必然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不断更新换代,从本质上说,是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归根到底,还是迫于资本的增殖本能和资本逻辑的逐利性。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不过是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走出经济危机低谷的工具手段而已。人工智能在生产资料中既是固定资本也是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剩余价值,但却可以通过算法对工人阶级实施碾压甚至把他们完全排除在生产过程外,较之机器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工人与机器的错位的异化关系,人工智能时代则直接把工人抛弃。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无法彻底调和,机器给工人造成的生存困境和慢性贫困就不会停止。但凡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钻研过并赞同《共产党宣言》的人,绝不会赞同赫拉利对于无产阶级的虚无主义看法。在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自始至终都会面临无产阶级的反剥削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斗争,具体反映在社会主义50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学者兼政治家托马斯·莫尔创作了虚拟文学作品《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也就是被后人称为《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名著,展现出社会主义的雏形,但只停留在空想阶段。直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这之后,社会主义经历了从一国到多国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28年,1949年成立新中国,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挫折的严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使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为广大仍然在苦苦挣扎的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经验指导和中国智慧。
尽管人工智能等自动化的机器体系迅速发展给传统工人阶级带来极大冲击和挑战,甚至使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遭受前所未有的异化和折磨,但绝不能说工人阶级已沦为“无用阶级”。人工智能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活劳动参与的过程,也是在为以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全人类为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科学预示:“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6]未来将成为“无用阶级”的不会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再强大的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体系也无法阻挡资产阶级消亡的最终命运,那时将会是《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描述的未来社会开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2]虽然这样称呼这一节,破坏了机器体系在固定资本中的地位作用,但这是目前学界约定俗成的叫法,本文暂且沿用这一说法。
[3]【意】奈格里、【美】哈维、【美】普舒同、【法】斯蒂格勒、张一兵、许煜:《马克思的〈大纲〉与当代资本主义》,杨乔喻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4]晏智杰:《分配制度改革和价值理论重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2期。
[5]钱津:《论深化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学术月刊》2001年第12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页。
[7][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第91页。
[8][12][13][14][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4页;第3页;第785页;第783~784页;第3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10]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p.349.
[11]Nick Land,"Circuitries",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p.274.
[15]【意】马塞罗·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页。
[17][18][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第787页;第777页;第784页。
[21]孙乐强:《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2]【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24][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第406页。